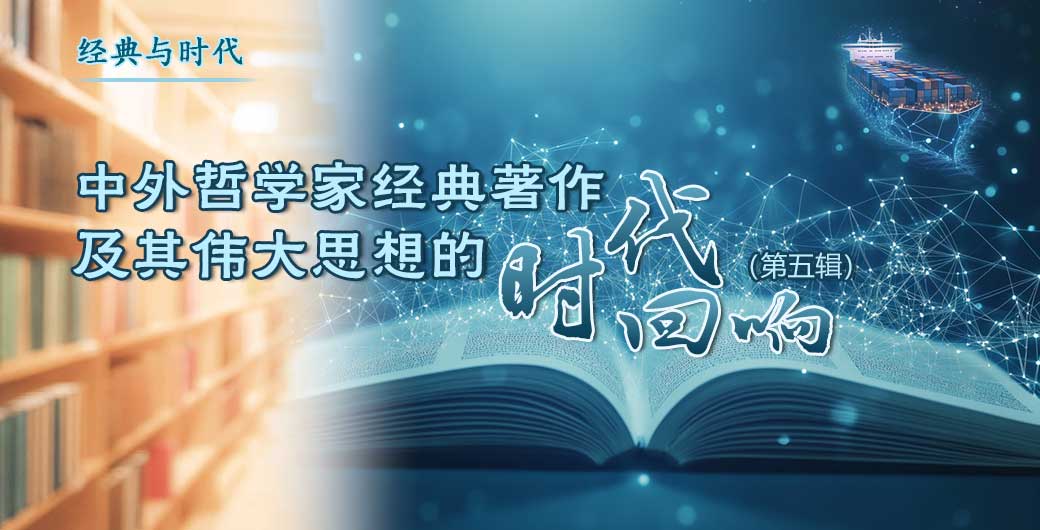导语
经典著作及其伟大思想是人类的文明符号。在现实与古典之间,经典著作的思想与时代的价值、文化不断碰撞,历史上伟大哲学家著述中的思想和智慧对人类和时代问题仍然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
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人类社会的困境与希望都需要在继承传统,吸纳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在传统和现代之中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系列专题《中外哲学家经典著作及其伟大思想的时代回响》,以飨读者。
在西方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无疑是一个必须浓墨重彩地叙述的对象。他是德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批判哲学的创立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对于中国读者们来说,也许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所提出的蓄水池之喻了,即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面两千年的水流入它里面,后面的水从它流出。
康德出生于当时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贝格一个清贫的皮匠家庭,从8岁起就读于弗里德里希公学的拉丁文班,接受了古代语言和古文献的严格教育。1740年,康德进入哥尼斯贝格大学学习。在大学教师克努真的影响下,康德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期间即撰成《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的思想》,想要对笛卡尔主义者和莱布尼茨主义者之间有关动能测算的争论做出裁决。
康德于1770年被聘为哥尼斯贝格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教授。大约在此前的1764年,康德萌生了“一种新形而上学的尝试”的想法。他的教授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的发表,标志着康德已经进入从前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的过渡。1781年,康德思考10余年之久、用4—5个月时间写出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康德哲学进入了批判时期。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相继问世,史称“三大批判”。除此之外,康德在这个时期还有《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等重要著作。康德把自己此期的哲学概括为“批判哲学”。
《纯粹理性批判》既回答了康德提出的“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同时也回答了“我不能够知道什么”这个问题,从而把信念、自由从知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埋下了伏笔。
…… 【原文阅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筹划中的“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或导论,而这个体系的第二部分应当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组成。如果说第二部分是科学体系的具体内容的展示,那么《精神现象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出什么是“科学”,即从概念上阐明“科学”的本质特征、基本方法以及内在结构等等。
绝大多数人一看到“科学”二字,马上就想到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成已有的学科,认为针对“什么是科学”之类问题,只需要以上述学科为例证就给出了答案。但德国古典哲学所说的“科学”(Wissenschaft),是一种整全性的、系统的、完满的“知识”(Wissen),而很显然,上述学科都是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领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黑格尔真正要挑战的常识观点——这个常识观点甚至被许多号称具有批判精神或怀疑精神的哲学家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是把科学或知识的对象理解为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仿佛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东西,仿佛认识者位于此一方,被认识者位于彼一方,而认识活动就是一方绞尽脑汁用各种手段把另一方抓住或攫取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出近代哲学的经典疑难,即这样抓住的认识对象究竟是不是它“自在的”“本来的”样子,甚至这种抓握活动究竟是否可能。于是各种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甚嚣尘上。但在黑格尔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托词,以此为借口,人们就可以大谈科学的无能,以便从科学的辛劳中脱身出来,同时又装模作样地仿佛正在为一些严肃而迫切的事情奔忙着。关键在于,假若认识者和被认识者原本就是彼此陌生的他者,那么上述情况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黑格尔恰恰要颠覆这个假定,正如他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旗帜鲜明地指出的:“在一个绝对的他者那里进行一种纯粹的自我认识活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以太是科学的基础和根基。”换言之,科学的本质就是在他者那里认识自身,或者说表明他者其实是自身的一个环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他者”,也没有单纯的“自身”,毋宁说“他者”和“自身”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环节,二者是如影随形的关系。因此,一切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自我认识。
…… 【原文阅读】

2025年是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诞辰250周年。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都会在今年开展相关的纪念性学术会议和活动。国内的首场纪念活动也于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召集人是汉译《谢林著作集》的主编先刚教授。在见证了《谢林著作集》以10年的时间完成所规划的全部22卷汉译工作之后,我不由也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谢林?
谢林是一个天才人物,他23岁当教授。他比作为同学的黑格尔成名早,但又被黑格尔盖过了风头。因此,他也有悲情人物一面,晚年想“东山再起”结果失败了。另外,他还是一个形象不定的人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普罗透斯”(变化莫测的海神)的外号。在20世纪哲学的叙事中,他的形象也变得更复杂起来。
我们说一个哲学家值得读,首先必定是在于他的思想重要。但首先需要厘清一个问题,什么叫“思想重要”?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为某个文明或者文化进行了原型性的解释或说明,或者为某一文明或者文化的基本气质进行了根本上的奠基,比如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其思想构成了现时代人类基本理解活动的观念来源,比如笛卡尔和康德。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其思想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具有历史节点的作用,比如阿奎那和黑格尔。尽管有瓦尔特•舒尔茨和埃里克•沃格林这样的知名学者为谢林“张目”,认为前述的第三种情况应该由谢林而非黑格尔代表,但笔者认为这种本身就具有学术争论性质的张目,自身也并不能证明谢林思想的重要。
哲学与其他科学“自证”其意义的方式并不相同。谢林曾经有一句名言,“哲学总是从头开始的科学”。哲学之所以需要不断从头开始是因为,人类对于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所需要的理解处境总是在发生变化,哲学必须保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概念工具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仍能展开和讨论涉及人类生存和意义的最根本问题。也可以说,哲学是最需要“与时俱进”的学问,哲学家总是在问相同的问题,但回答这些相同问题所需要的概念和处境总是在变化——开普勒和托勒密都要回答天球运行的问题,但他们各自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工具,甚至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谢林和柏拉图都要回答本原问题
…… 【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