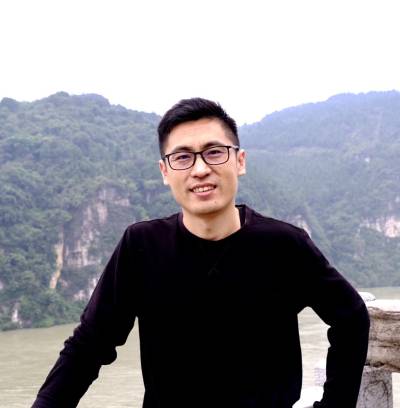
作者简介:代海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外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维特根斯坦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兴趣: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梦境哲学、原初规范性。
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正值科学与哲学快速发展,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争论异常激烈。他所面临的挑战性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哲学为科学奠基,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体现出哲学科学化的倾向;二是科学取代哲学,表现为科学主义思维,反映了科学哲学化的表现。纵观维特根斯坦一生,在他的前后期哲学中始终保持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呈现出一种连续性特征,他以一种元哲学式反思表明,哲学与科学具有不同属性,分属不同的视角,二者不应放在同一思维框架内比较,哲学的目的在于思想的澄清和概念混乱的清除,不应承担科学奠基的作用,也不是可被科学取代的附属品。
哲学优先论似乎自古有之,主张哲学应当是科学的基础,能为科学提供原则性和方法性指导。近代许多哲学家也多具有相近看法,哲学探讨形而上学,属于先验领域,而科学探索经验领域,哲学能为经验科学奠基。上述观点具有深远影响力,反映出哲学高于科学的倾向。不过,自上世纪初开始,随着语言哲学的兴起,这类观点遭到严重挑战。语言哲学家从语言的逻辑结构出发,考察各类哲学问题,重点区分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的界限。作为逻辑实证主义领军人物,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作出了批判,认为哲学是“科学哲学”任务,最终得到的不是陈述、理论或者系统,而只是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反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他指出“科学哲学”的意思是逻辑分析、探究逻辑基础的指定任务。祛除形而上学的观点带有科学主义倾向,反映了一类特殊的信念:“科学…和科学的方法…提供了获得关于任何真实事物的可能有用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自然手段”;“自然科学方法或自然科学中公认的范畴和事物构成了任何哲学或其他探究的唯一适当要素。”在当代哲学讨论中,科学主义依然具有影响力,例如,丘奇兰德主张,所有语言都要应当被科学语言所取代。上述两种立场体现了哲学与科学分离的思想,哲学要么在科学之上,要么被科学所取代。与此相比,一种中间立场尝试拉近二者的距离,建构科学和哲学的桥梁。奎因指出,哲学与科学应当是连续关系,而非分离关系。威廉姆斯提出,哲学与科学不存在分裂,哲学就是科学,“哲学在原则上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理论建构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寻求知识。”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无论是传统哲学还是科学主义,最大问题在于坚持一种固定的方式看待世界,这不仅会造成其自身内部的困难,而且会妨碍对世界的多样性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指出,传统哲学和科学主义同根同源,都是以科学思维方式为导向的一元视角主义。不过,他提醒人们,事实的发展并非总是以一成不变的样子出现:“‘当然,这必然会如此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想到:它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发生。”发生情况的不同能够帮助人们看到不同的世界样貌,所谓先验性的东西并不存在:“我所反对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确性概念,它好像给我们了一种先验性。在不同的时间,精确性理想是不同的;而且没有一个是超群的。”
在维特根斯坦的视野中,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对基本现象提供深层解释,建构理论。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基本上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前后期维特根斯坦都秉持一种元哲学的思考。哲学的目的不是通过提供正确答案解决哲学问题,而是通过指出哲学问题的症结消解哲学问题。《逻辑哲学论》将哲学的工作理解为语言的批判,通过澄清语言的本质,从而消解哲学问题。通过分析命题的逻辑结构,语言的本质被揭示出来,这是一项命题的澄清活动,也是思想的澄清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在后期思想中,维特根斯坦依然坚持一种澄清活动的哲学观念。与前期逻辑分析不同,后期转向了语法分析,主要处理语法混乱。语法误用来自表层语法的迷惑,在本不相似的地方制造相似,例如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第一人称语言表达和第三人称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处理。语法混乱导致进一步的问题,因此消除困惑就能起到消解哲学问题的目的——“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路。”比如,格洛克把这种哲学的成就看作是一种“如何之知”的类型,即知道如何消除哲学困惑,避免被语言舞蹈产生理智的迷惑。
在哲学与科学关系上,维特根斯坦的反思批判不是单向度的,他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从未停止过。“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经历了变化,但是他对科学主义的反对一直持续。”科学主义的根源在于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解决问题就在于发现新的事实。约翰森指出,维特根斯坦所针对的科学主义有两个特征:“首先,科学理解是唯一存在的理解。其次,为了知道一些现象,我们需要做出新的发现。”与哲学科学化相比,科学主义是科学哲学化的产物,体现出先验排他式的独断,在这种意义上,“这确实使他反科学,反对自鸣得意和未经审查的保证,即需要解释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工具是立即适用的……科学主义与传统的、更透明的先验主义方法一样,都是被误导的形而上学方法。”直接向科学寻求答案的倾向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哲学图景的表达。
在前期思想中,维特根斯坦对科学命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科学规律并非反映自然本身的规律,只是人们描述实在而采取的可能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面对经验世界时,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们是人们选择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命题、思想的逻辑分析是为了达到对思想的表达划定界限的目的,一旦界限被划定出来,在界限之内的事物就具有了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上。他指出,这里存在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科学地看待事实的方式和将事实看做奇迹的方式不同。”这种方式的本性可以用“看作”(seeing...as...)来刻画,“我现在将这样描述惊奇于(wondering at)世界存在的体验:这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奇迹的体验(seeing the world as a miracle)。”是对待事物的方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了对待事物的结果。方式本身不具有必然性,它们只是视角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学地对待世界仅仅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更不必说它不是必然方式了。在对视角的说明之中,可以发现,与看待世界方式相对应的是一种精神,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类似于艺术的风格,可以体现在一个时代的文化之中。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科学语言只是一类特殊语言游戏模式,无法适用所有类型的语言现象。比如,在对私人对象的批判之中,关于“疼痛”的私人语言是对象式语言的不适当扩展。语言在使用中其语法来源多种多样,对象式语言只是诸多语言当中的一种,这种语言模式遵循“名称-对象”的模式。但是,疼痛语言不属于对象式语言。如果用“名称-对象”模式对疼痛现象进行解释,就会认为在“疼痛”这个词背后隐藏着重要内容,也就是“疼这种东西”。但是,“我们恰恰就把自己固定在一种特定的考察方式之上了”。 当人们被一种方式固化之后,就被引诱着将其运用到其他领域,并且是一种排他式的运用,“一种方法将其他放方法都推到一边。与其相比,其他方法都是无用的,充其量算是原始的。”而接下来的任务似乎就只剩下找到更多的信息去回答它、解决它:“科学家的态度多么奇怪——‘我们对它仍然无知;但是我它是可知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这似乎不言而喻。”
结语
总体而言,在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中,始终保持着元哲学式的反思,用超出知识框架的思维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哲学并不是科学,它不解释现象的原因、提供知识,而是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提供对世界更多的理解。哲学的工作具有正反两个效果:清除由于语言误用导致的思想混乱,比如不合理的问题和错误的答案;澄清语言的逻辑和语法,获得正确看待事物的多维世界观。这种哲学观主要来自于他的视角思想,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多维的,每一个视角都有其独特的特性,没有哪个视角是唯一的。他前期提出了一种“看作奇迹”的视角,这与科学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后者会导致一种屏障,妨碍人们看到世界的奇迹:“为了惊奇,人类——或者人们——必须清醒过来。科学是使他们重新入睡的一种方式。”他后期在语法研究中提出了“综观”的视角,目的是看到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识别出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同,呈现出生活形式的本来面貌。
通过强调不同视角,超越固定的知识框架,维特根斯坦表明哲学与自然科学属于不同领域,二者的混淆会导致各种问题,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二者的性质,避免产生哲学困惑或者科学主义。因此,在他看来,哲学与科学不应当是奠基、取代或者连续的关系。但是,二者并非没有合作的空间。正像约翰森所说,哲学与科学应当也能够彼此合作。哈客认为,维特根斯坦给予“哲学批评科学家的许可”,因为他“说明了为什么哲学有权干涉经验科学——因为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概念批评者”。江怡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逻辑论证和概念支持,而是考察和清除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理论难题和思想障碍,作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和提醒者。”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反思,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二者特征,促进哲学与科学的合作,引发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