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科学史领域出现了一股较为明显的“全球转向”,倡导书写“全球科学史”,认为现代科学有着多元起源,并不是西方社会的独特产物,“全球科学史”借助众多的人和物组成的各种地方、跨国和全球的空间网络,不断地处于被制造、移动、流转、翻译和本土化的进程之中。
虽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科学史的早期奠基人已经有所倡导,但是科学史的“全球转向”主要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物质转向”(the material turn)和“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的基础之上。科学史的“物质转向”关注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实践者、物质材料、工具和机器等各种物品之间的复杂互动。科学史不再仅仅关心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还关注那些实际制作物品的工匠、科学仪器、动物、植物、矿物和博物馆等议题。“空间转向”则强调科学知识生产、传播和流转都是在不同的地点(包括实验室、博物馆、植物园、医院乃至病人身体等)、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不同认知体系进行交流的“交易地带”(trading zone)以及全球层面等空间中进行的。
2004年剑桥大学科学史教授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在国际科学史顶级期刊ISIS发表的重要论文《知识在流动》(Knowledge in Transit)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科学史“全球转向”的开端。他指出,要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沟通形式和流转的知识,因此考察知识是如何在全球等大的空间尺度里移动、翻译和传承,将会成为未来科学史研究的重点方向。2009年英国科学史学家丽萨·罗伯斯(Lisa Roberts)的《将科学置于全球史之中》(Situating Science in Global History)是第一篇明确提出书写全球科学史的论文。她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从西方单线传播到非西方世界,而是借助不同的人和物构成的网络,在全球空间中流传,因此需要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她还进一步强调,这类研究不能只关注全球空间,还要特别关注文化“接触地带”和在地层面上的知识交换和挪用过程。在此之后,很多科学史学者都认识到“全球转向”的重要意义,积极倡导全球科学史研究。
除了期刊论文之外,坊间也出版了一些全球科学史相关的论文集和专著。从研究主题来看,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多空间尺度下的科学流动。比如卡皮尔·拉杰(Kapil Raj)的经典著作《重新定位现代科学》(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关注17—19世纪的科学知识在南亚和欧洲之间的“接触地带”是如何被构建、流转的。其次是全球视野下科学知识的翻译和交流。科学知识要在不同文化和全球维度下流转、接受和再创造,就必须依靠翻译,因此当前全球科学史研究非常关注科学翻译的议题。斯科特·蒙哥马利(Scott Montgomery)的《翻译中的科学》(Science in Translation)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再次是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科学、商业与贸易。柯浩德(Harold J. Cook)的《交换之物》(Matters of Exchange)以17世纪贸易立国的荷兰及其全球贸易网络为中心,讨论了科学革命与商业交易的密切联系。将以上议题联系起来的则是对全球科学网络的研究,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主编的《知识的帝国:近代早期世界的科学网络》(Empires of Knowledge: Scientific Network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是其中的代表著作,探究了16—19世纪知识的中间人、科学网络的建构、知识的旅行和全球—地方的科学网络等重要主题。与近代早期相比,当前对20世纪全球科学史的关注较少,仍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约翰·克里格(John Krige)主编的两部论文集《知识如何移动》(How Knowledge Moves)和《全球时代下的知识流动》(Knowledge Flows in a Global Age)关注了20世纪科学知识和技术实践在跨国网络中的流转问题,是这方面的最新著作,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最后,研究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多物种(multispecies)全球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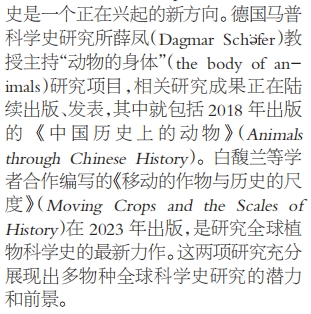
全球科学史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值得关注的新领域,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以往的科学史主流观点认为现代科学由西方单独开创,并随着西方的兴起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发展与进步,从而体现出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优越特质。虽然全球科学史认为这是一种必须要摒弃的西方中心论,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当前的研究仍然以现代科学的全球流转为主,很少有研究对现代科学的全球起源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一个例外就是英国学者詹姆斯·博斯科特(James Poskett)2022年出版的《地平线:全球科学史》(Horizons: A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而该书的另一版本《地平线:现代科学的全球起源》(Horizons: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则明确显示出作者正是要处理这一极为复杂、高度争议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科学并不是西方独特文化的产物,而是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在现代学科的起源和发展各个层面,都有着全球因素,其中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参与者甚至起了主导作用。例如,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他坚信哥白尼的成就是建立在14世纪帖木儿帝国伊斯兰天文学家的几何方法之上。牛顿的力学革命离不开黑奴贸易带来的财力支持和美洲土著在其理论实地证明中的苦力劳作;被殖民前的美洲和非洲土著文明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准,可以跟同时期的欧洲文明相媲美。进入20世纪,印度、日本和中国等非西方世界科学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正电子是中国科学家赵忠尧的发现,但是这些成绩被西方人刻意忽视和遗忘。博斯科特强调科学知识的全球起源、流转的重要性以及非西方科学家的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但是该书在很多层面刻意通过各种支线的关联,来否定西方在现代科学起源中的关键作用,漠视现代科学在西方社会内在的历史演进,并以文化相对主义来强调非西方社会科技更胜一筹,未免有点过于极端和偏颇。就如全球史一样,全球科学史的书写也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史议题都必须用“全球转向”的旗号进行强行阐释。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