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仲秋,入学不久,我和同门应邀到乐黛云先生位于北大中关园的寓所聚首。论及学业,乐先生笑说,希望我们尽快进入状态,撰写读书报告,为未来的硕士论文打底。
此后一段时间,我潜心琢磨乐先生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西潮涌动,“五四”前后掀起骇浪的尼采在文化界复活,与其他众多西哲一起,风靡校园。尼采提倡的“一切价值重估”,松绑着久受桎梏的人们,也激荡着年少稚拙的我。乐先生发表于1981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孤明先发,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对学界的影响既巨且深;她推崇鲁迅在尼采笼罩下标举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正与新时期的激昂慷慨同频共振。我捧读这篇经典之作,从字词句段到命意结构反复推敲。篇中所引证据,我也追溯出处,以还原乐先生的运思过程。我注意到,乐先生在诠释尼采与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关系时,论证周密而有力;在诠释尼采与国统区战国策派的关系时,则未免笔墨匆促。乐先生也说,20世纪40年代文学并非其着力所在,她鼓励我以“论尼采与战国策派”立题,对之做专门探究。
按照乐先生教诲,我开始研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选修陈鼓应先生开设的“尼采与庄子哲学比较研究”。陈先生是殷海光先生的弟子,崇尚民主与自由,辩才无碍;他有时着一袭草绿长衫,风度翩翩。他像乐先生一样,把自己倔强的个性、跌宕的人生和时代的潮汐融进了对尼采的解读。尼采提出的上帝已死和冲创意志、酒神精神与自我提升,以及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和洒脱深远,均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居住于北京友谊宾馆,一天,我贸然骑行到那座高华肃穆的园林向他请益,他的热情温蔼和诲人不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课下,我阅读周国平先生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因幻想有一日能读懂尼采等德国大哲的原著,我选修了难啃的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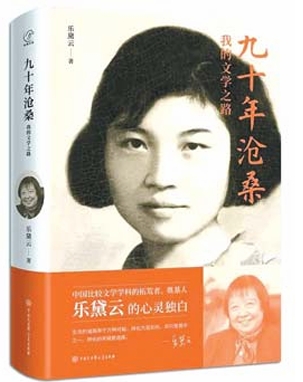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乐黛云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版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战国策派文献比北京大学图书馆要丰富得多。根据乐先生指引,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读陈铨、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学者的著作,阅读他们创办的《战国策》杂志。起初,由于茫无头绪,我不晓得哪些资料可用,只管埋头苦抄,抄个没完没了。收藏战国策派资料的清华学堂是一座德国古典风格的双层建筑,青砖红瓦,树木掩映。它矗立在大礼堂前草坪的东南侧,曾是誉满海内的清华国学院所在地。多少个上午,多少个下午,这座庄雅的名楼见证了我的迷惘、勤恳和振奋。
1987年夏,一篇长达17000字的习作《论尼采与战国策派》呈在乐先生案头。很快,乐先生约我到比较文学所所在的北大四教谈话。她先对此文的优长表示赞许,我以为修改后可以发表。接着她说,此文最大的问题是逻辑不清,表现在主题没有一笔到底、节与节之间联系松散、自然段与自然段之间总在跳跃,且口语和抒情笔调妨碍了表达的准确和清晰。她说,研究需要质疑,要在多层追问转进中把论述逼向深处;研究需要批判,不要老是追着研究对象跑动。她还问到我高考数学成绩如何,我接答后,也道及曾自学过微积分。她说用不着那么高深,我只需把初中解析几何的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就足够了。最后,她讲出一句让我此生铭心刻骨的话:如果过不了逻辑这一关,这一生就别干学问这一行了。说这话时,她背对着我,站在宽阔明亮的玻璃窗前,窗外就是我经常奔跑的五四运动场,午后的运动场上正传来声声年轻的呐喊。
说起来,乐先生对弟子的一篇习作,有鼓励,有批评,并有针对性地拈出逻辑一事加以发挥,何等自然正常,何等亲切有味,弟子亲炙先生的意义岂不正在于此?然而,那时的我,视域未开,胸次未广,敏感而自薄,闻听乐先生之语,心绪难免一波才动而千波随之涌起。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做学术研究,在此后不短的岁月里,一直盘桓在我的内心深处,啮噬着我,使我不能宁静,不能致远。至于那篇习作,我无心修改也无心投稿,甚至连再打开它的欲望也告消歇。后来,在一次搬家中,这篇留下我精神成长印痕的文稿浑然不知去向。当遍寻不得时,我虽有些不舍,却也没有生出敝帚自珍的情愫。只是近年,渐近落霞时分,每当忆起乐先生教养之恩,我才为未曾妥存那篇习作,真正感到惋惜,真正有些自悔起来。
乐先生重视逻辑的精警之言,召唤我回头是岸。此后数十年间,为锤炼逻辑能力,我用心阅读了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在撰写每一篇论文时、准备每一场学术演讲时,也总是临深履薄,从整体到部分、从起承到转合,在逻辑方面“斤斤计较”。即便如此,一些逻辑漏洞仍然难以避免,令我不能自安。同时,我也把重视逻辑这条“乐门家法”带进了教学之中。迄今说不出,我所伴读过的学生,有哪一位在逻辑方面没有受过我的苛责。这些年,如果说我和我的晚辈们一定程度上坚持了独立思考,坚持了质疑和批判精神,行文中减少了一些逻辑瑕疵,饮水思源,是不能不感激乐先生当年的苦心训诲的。
2022年春,我和妻子去拜见乐先生,相隔36年后,旧事重温。我请教乐先生:为何当年那么重视逻辑,批评起我那篇读书报告又是那么严厉。她朗声笑道:“汤老师研究哲学,常与我切磋,总嫌我在逻辑方面考究不够,所以我对逻辑问题就格外敏感。”
这使我想起,汤一介先生曾经提到,他大学期间最用功的科目就是“普通逻辑”“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1987年,我遵从乐先生之命,选修了汤先生开设的“中国佛教哲学”。他在课堂上讲述,中国数千年中没有形成深厚的逻辑传统,唐玄奘从印度输入的因明学,窥基之后便少有传人;中国缺失逻辑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者强制在下者服从,不希望人们独立思考,不允许人们对其所作所为发出质疑。
我有一个梦想:在未来某段时光,我要再入藤影荷声的清华园,再入新雅别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重新阅读战国策派的文献,重新结撰一篇读后感,题目现成,仍用乐先生起的旧名:“论尼采与战国策派”。这一次,我定全力以赴,力避逻辑谬误。
然而,北大朗润园那一栋我所熟悉的居处早已是人去屋闲,只有室外二老手植的苹果树依旧摇曳风前。那么,我的这一篇新作,又请谁来批阅?我的这一片沉沉思念,还有这一缕寸草微意,又向谁去漫诉?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