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作为体量最大、从业人员最多的学科之一,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自2017年起开始五条腿走路,即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外国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十年来,随着“四个自信”逐渐深入人心,“三大体系”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并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这其中自然牵涉到我国外国文学界的立场、方法与目的之变。

关于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经历了来者不拒的拿来后,于近十年转向较为理性的攫取。表面上看,外国文学曾经的显赫一时(譬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如今似乎风光不再。这固然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譬如中外交流的加强、资本和市场的因素、微博微信的普及、二次元审美的扩张,等等。曾经作为触角替中国革命和建设、替改革开放探路的外国文学,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黯淡,以至于有点蜕化为资本和市场的附庸,而大众文化便是后者的表征。
这就牵涉到立场问题,且不仅是立场问题,还有方法和目的。
先说立场。立场使然,奥尔特加曾经站在精英立场上反对大众文化,乃至现实主义文学和方法。用通俗简明的话说,奥尔特加出生在贵族家庭,毕生致力于“生命哲学”,一不小心成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自然没能预见萨特式存在主义对他的背叛。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终究或主要是为了强健中华文学母体的拿来。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高举的旗帜。遗憾的是,这面旗帜正在有意无意地被“世界主义”者们所抛弃。他们多少有些罔顾历史,罔顾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谈所谓的“世界文学”。真不知达姆罗什、卡萨诺瓦们眼中的“世界文学”是否包括《红楼梦》和“鲁郭茅”、“巴老曹”;是否包括“巴铁”文学和坚持文学介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这些问题不由得让人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古老的命题。人们大多将此命题归功于鲁迅,但鲁迅的原话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这的确是那个“五四”期间曾经矫枉过正的鲁迅。然而,立场使然,他弃医从文、口诛笔伐,为的终究是中华文化母体的康健。它与堂吉诃德(Quijote)精神可谓一脉相承。鲁迅倡导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难道不正是为了改变阻碍中华民族前进的文化糟粕吗?当然,凡人皆有矛盾之处。鲁迅也不例外,而我们不应以偏概全、以小节否定大节。所谓大节,恰是他的主要立场、主要方法、主要目的,以及他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树立的丰碑。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或者国际意识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认知。也正因为强调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批判资本主义。据此,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界的自觉。

关于方法
众所周知,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有关方法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令人目眩。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叙事学到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权主义到生态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存在主义到后人道主义,等等;或者流散、空间、身体、创伤、记忆、族裔、性别、身份和文化批评,等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可谓五花八门。
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曾经受到冷落。与此同时,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我国现代文学历经数十年建构的经典谱系,从而将张爱玲等“自我写作”者们奉为经典。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招摇过市。顺着这个思路推演,当代美国和西方主流学界冷落巴尔扎克们、托尔斯泰们当可理解,而我们紧随其后、欲罢不能地无视和轻慢这些经典作家就难以理解了。这中间除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逆反,恐怕还有更为深层的根由。顺便举个例子,曾几何时,当我们的一些同行忘却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的同时,另一些正兴高采烈地拿弗氏理论解构和恶搞屈原。
也正是在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驱使下,唯文本论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做法,与源远流长的形式主义不谋而合,或者变本加厉地沿承和发展了形式主义,作者被“死了”(见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形形色色的方法凌驾于文学本体之上。有心的同行、读者可以对近三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稍加检索,当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是自话自说和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或者罔顾中国文学这个母体的人云亦云。盛行一时的学术评价体系推波助澜,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纯粹”的工匠。量化和所谓的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模块化”劳作。我们是否进入了只问出处不讲内容的怪圈?是否让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为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的现象充斥学苑?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否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同行正致力于为了拿来的批评,我称之为新社会历史批评,当然还有方兴未艾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他们富有家国情怀、彰显国家意识的研究范式正在逐渐改变业已坚硬的唯文本论倾向,不仅着力开掘作家作品及其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且将本国读者及其接受和选择问题纳入文学视域。虽然历史不能还原,但历史的维度永远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方法。只消将“鲁郭茅”“巴老曹”和张爱玲们置于所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那么谁有资格成为国家脊梁、民族魂魄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也就不言而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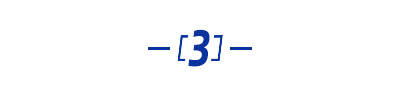
关于目的
有关问题或可牵出许多话题;但因篇幅所限,最后我想就与立场和方法关系密切的目的论稍加点厾。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中国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若非从纯粹的地理学概念看问题,“世界文学”确实不是各民族文学之和,经典更不必说。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所谓“世界文化”也主要是欧美文化。而且,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倾轧、颠覆和取代不仅其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回到“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这个话题,文学当最可说明问题,盖因它是世道人心的形象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道人心,却终究不能左右世道人心、改变社会发展。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繁世相和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且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能涵盖客体——这种精神劳动的复杂性、多面性;但文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目已经显现,唯文本论的泛滥也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尤其当中国作家不再迷信或饕餮般阅读外国文学时,我们更不能沉溺于自话自说、与他们渐行渐远。不消说,伟大的新文学传统需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不容被边缘化。是时候继续端正立场、改变方法了,否则所谓的“学问”必将被新时代所淘汰。
成绩讲够不易,且无法一一罗列;问题说透更难,因其原因复杂。以上是笔者有关近十年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一个向度的粗略总结,不当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