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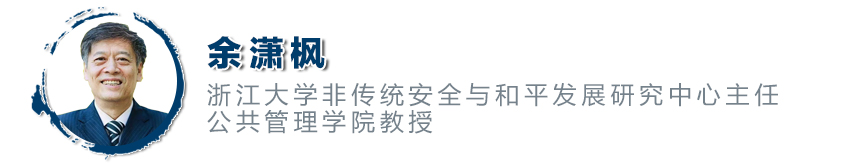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指求和谐,讲和睦,行和顺;“不同者”,指不违道而相谋,不无原则苟同,不委曲以求和。“和而不同”既是君子之道的隐喻,也是中华文明的要旨,更是中国式全球化探索与重建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点。
“和而不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样态,符合天之“道”。宇宙是一个和合相生的整体,在天地间的“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中,“量子求和”是万物演化的构成性本质。现代物理学证明,量子是万象宇宙的最小“构件”,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是量子的聚合体,而量子世界里每个粒子具有无数条路径穿越“设定”测试通道实现其“求和”式聚合的特性,量子纠缠的“远距相关、瞬间同步”正是其“求和”本质的昭示。
“和而不同”是社会融合发展的文化基因,符合人之“道”。世界是一个和合共生的家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类群求和”是呈现“战争—竞争—竞合—和合”演进轨迹的总体性规律。[1]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在共时态上是“共生”“共建”“共享”的,在历时态上是有着从暴力转向非暴力的“和合性”趋向的。数千年文明史,已使人类一步步从相互残杀与争斗中超拔出来,不断构建起“地球村”中和合共生、和衷共济的多种样式的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对“量子求和”规律的昭示与“类群求和”价值的彰显,既表达了中国人追求“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社会理想,也表达了中华文明对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包容性与互鉴性。中国人历来重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承认文明的共生多样;也历来重视“合羹之美,在于合异”,提倡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自古就形成有“协和万邦”“止戈为武”的王道传统,春秋时期有世界上最早的国家间会盟制度,秦汉之际有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唐朝以降有与周边国家间互惠自愿的朝贡关系。在与世界共处中,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内敛与防御,“重和”多于“尚争”,追求“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用“挑战—应战”模式解释了数十种文明兴衰之因,发现正是“和而不同”的生存方式促成了中华文明“有挑战又能应战”式的绵延与昌盛。
“和而不同”越来越被国际人士所认识、赞扬与推崇。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比较中西文明时,特地把中国的围棋棋谱画到书上,强调围棋的共存求胜的“战略灵活性”与国际象棋全胜全败的“目标专一性”不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国际象棋是通过不断地“吃子”,令对方走投无路,而绝对地“获全胜”;而中国围棋通过不断地“占空”,令双方都有活路,而相对的“积小胜”且以占有微弱优势者为胜者。[2]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岚安认为,“和谐”“大同”等词语正是区别于“国际”“安全”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而彰显出其“规范性软实力”,以“天下”视野来认识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世界未来存在着基于天下体系观的“中国式和平秩序”的可能性。[3]
“和而不同”其最大功效是能消解“异质性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难点,在于“如何对待现存的不同层次的‘异质性’因素:既包括文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等种种异质的历史性遗在,也包括因历史、地缘、利益、资源、制度、方式甚至误解引起的冲突与对抗而转化成的异质的现时性此在,也包括因对未来走向持有不同图景与追求的异质的可能性彼在。”[4]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常常以霸权立场,实施对异质世界的独断、强制、排斥与打压,惯用自身价值观与制度尺度去判定他者,其“霸权稳定论”的实质是“霸权自利论”。欧洲则在“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一体化历史进程中,面对异质性冲突,形成了“契约式”“法理性”“机制化”为特征的让渡主权策略,较之美国更为包容、共享与合理。
相比之下,中国解决异质性冲突的努力与贡献更具独特性。如: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岛屿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方针,处理香港、澳门回归的“一国两制”方略,处理大国关系的“不冲突、不对抗”“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原则,处理国际事务的“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观”的倡导等。柯岚安认为,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变化,均是用整体性思维解决异质性问题的典范,体现的是利用差异的模糊性而达到“和而不同”之“大同”境界的一种有内在逻辑的灵活方法论。[5]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落差。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人类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全球化浪潮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冲撞,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俄乌冲突持续不停,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人类再次徘徊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人类未来究竟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相互竞合?还是“中国式全球化”与“美国式冷和平”相互博弈?抑或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即小圈子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的竞合与替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扑朔迷离的乱象纷呈,消极人士认为,这是“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挫折”;积极人士认为这可能是“深度全球化”“再全球化”的开始,是一种“选择性全球化”的到来,是“替代型全球化”向“互补型全球化”的回归,或许这更可能是“中国式全球化”的开启。[6]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专门探究了“当今时代能否建立世界秩序”。他认为,“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与“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7]“和而不同”正是以其所特有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世界提供了普世性的“和文化”与理想性的“秩序观”。“和而不同”将改变信奉暴力的理念与以武力为基础的“均势”结构,转向信奉协商的理念与以和合为基础的“共赢”结构;将改变利益占有为前提的、以霸权式干预为特征的“权力算计”,代之以命运共同为前提的、以参与式治理为特征的“互惠和合”。事实上,中国正通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的努力构建,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和而不同”蓝图的实现,需要有世界各国的共识与践行,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建。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国策,与周边国家更加和睦,与地区性大国关系更趋和谐,与世界性大国保持“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为世界提供更多经济与文化上的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负起更多的责任。“和而不同”作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价值基点,终将成为支撑世界秩序的新核心理念,为世界持续性和平提供合法性基础,更为世界多样化发展提供凝聚力源泉。
注释:
[1]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55-56页。
[2]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6页。
[3]柯岚安、徐进:《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49-56页。
[4]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31页。
[5]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89页。
[6]余潇枫:《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非传统理念3.0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第203页。
[7]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XIX页、第489页。
(作者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声明:本网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相关领域学术理论研讨,为专家学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