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活跃着来自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诸多理论学说的交锋与争鸣固然有助于开辟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时常使许多待解的问题变得更加繁复,甚至使某些原本明朗的认识变得不再明朗。人们所拥有的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般丰富多样,但在解说诸多看似熟悉的概念和对象时,却从未有现在这么多犹疑和分歧。关于什么是“形式”,什么是“结构”,什么是“叙述”,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既然分歧越来越多,达成共识也就越来越难。毫不奇怪,伊格尔顿的名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以“文学是什么”作为导言,却始终没有为文学下定义;正如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开篇不久就专章讨论“文学是什么”,却以“文学的矛盾”草草收结。由此可见,如何认识文学的根本性质及存在方式,已经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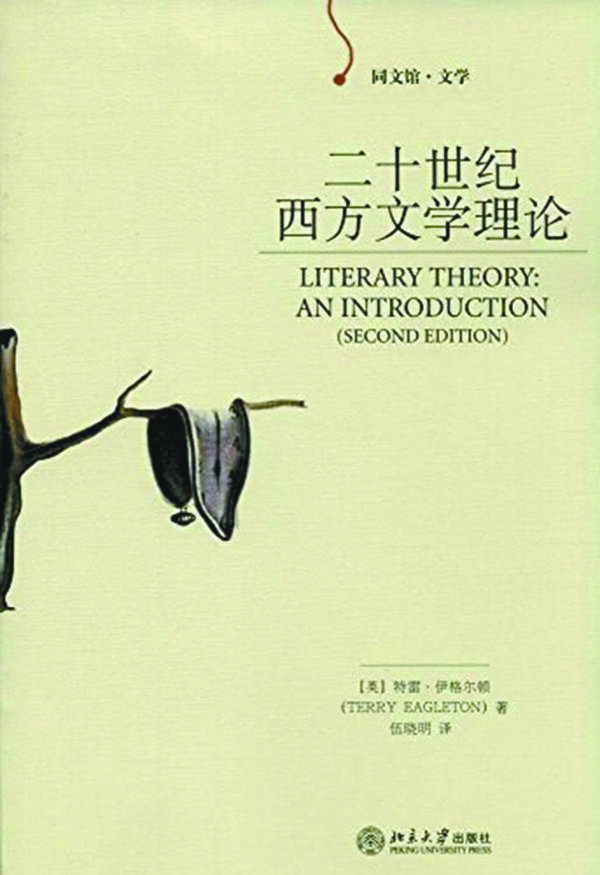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资料图片
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伊格尔顿固然无情地拆解了不少关于文学的定义,但也正是那些审慎的梳理与辨析,才为消除分歧、寻求共识提供了可能,使某种具有启发性的“文学观”得以凸显:“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与伊格尔顿小心翼翼地维护“价值”相似,卡勒在描述文学的功能时仍将“意义”设为落脚点,主张文学“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
文学始终与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密切相关,这也是我们当今所应坚守的观念底线。尤其在经历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终结论”的冲击以后,我们见证了文学至今仍在存续发展,应当更有理由确信:文学就是价值和意义的载体。那么,这价值和意义从何而来,又如何表现?以往的文学理论对此有不少解答。注目于作品,曾有论者主张“结构”与“张力”乃是价值和意义的不竭源泉;聚焦于读者,或有论者认为是“审美知觉”和“期待视野”等塑造了价值和意义;环顾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则有论者强调“生产机制”及“原型经验”等生产了价值和意义。
这些说法各有一定合理性。但笔者更想说的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只是从理论上得到支持或辩护,更有待作家付诸行动。作品总是先由作家创作出来,然后被读者阅读,最后才可能引发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与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这个时代的作家有无创造价值和意义的自觉追求。
作家的“叙事自觉”
当下文学应当是“用当下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当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为使表述更加简明,我们不妨将作家有意识地赋予作品以价值和意义的行为称为“叙事自觉”。需要注意的是,既往的优秀作品确实证明了文学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当下文学具有不言自明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近些年出现了不少深刻、感人的优秀作品,但少数空洞、庸俗之作也说明部分作家已在泛娱乐化的风气中丧失了叙事自觉。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的号召,正是希望新时代的作家要主动作为和自觉担当。
作家的叙事自觉越是强烈,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越是明晰。回顾文学史,前贤对此早已有过很多表述。一千多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对作家“神与物游”的描绘,至今读来仍富于诗意和美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这大概是作家得心应手的理想境界。但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作家意图与创作效果之间可能会有差距:“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或许“图谋”甚广,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效果往往不能如愿。陆机也说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我们看重作家的叙事自觉,并不是要求他们一蹴而就,而是期待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步臻于纯熟,最终达到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
一个半世纪之前,恩格斯在与拉萨尔讨论剧本创作时曾提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应成为剧作家的追求和戏剧未来发展的方向。此处所论虽着眼于戏剧,但这种提纲挈领的方法亦可延伸于描述其他文体创作。这既是关于叙事自觉的简明扼要而又高屋建瓴的认识,同时又将文学的特性和使命表述得如此鲜明。
当代学者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表露了对叙事自觉的高度重视。他们提出,“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不难看出,这个“表达”的主体就是中国现代作家。这个表述或许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气息,但仍指明了一条可靠的研究路径:若想真正把握现代文学的特质,可从认识现代作家的叙事自觉开始。与此相似,为了表明对当下文学的期待,我们也可以说:当下文学应当是“用当下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当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叙事自觉,并不否认抒情以及抒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只是为了在“情”与“事”相互依托的前提下,凸显叙事自觉的特殊意义。
文学的“当下感”与“形式感”
“当下感”彰显了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关怀,“形式感”则显示着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难度。作家的文思有快慢之分,如刘勰所云,“人之禀才,迟速异分”。但在成熟的作家身上,我们总能发现他们都拥有可贵的叙事自觉。叙事自觉涵盖面甚广,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两点:他们不仅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势有充分认识,还对自己所运用的文学形式有独到体会。前者若简称为“当下感”,后者则可称为“形式感”。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文学的面貌和质地,主要是由作家的“当下感”和“形式感”共同造就的。
“当下感”和“形式感”不是通常所谓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它们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作家应该充分“意识到的”内容。就两者的侧重点而言,“当下感”彰显了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关怀,“形式感”则显示着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难度。“当下感”和“形式感”均有着丰富的内涵。
“当下感”最基本的内涵,是体验和表现当下生活,是感受当下情势对文学的召唤。过去流行的“作家要深入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等提法,如今虽极少被年轻作家挂在嘴边,其实仍未过时。“当下感”的另一层内涵,是对当下的来路加以思考。这就要求作家对现实有总体性的思考,不仅要热切地表现当下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还要深情回溯人民业已创造的伟大历史。作家若能做到既执着表现当下,又自觉反观历史,必能超越特定生活背景的限制,从而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关怀。
“形式感”也包含不同层次的内涵。首先,它是指作家对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的明确认识。作家之所以区别于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正因为他始终意识到应以文学的方式反映当下现实、表达自我感受。优秀作品不仅能够有效反映鲜活生动的当下现实,还能有力地传达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独到思考。其次,作家的“形式感”还体现为创作过程中对文学体裁的传承与创造。优秀作家总是既尊重文学传统,又敢于打破成规惯例,从而彰显文学的守正创新之道。最后,在当前的媒介语境中,文学创作与发表的门槛似乎不断降低,文学的“祛魅”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恢复文学创作本来当有的尊严,可谓势在必行。最要紧的工作,乃是为文学“复魅”,使文学作品重新成为精心打造的语言艺术。在此情势下,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坚守,可以说是“形式感”的最低底线,也是最高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讲稿’的整合研究”(19BZW1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