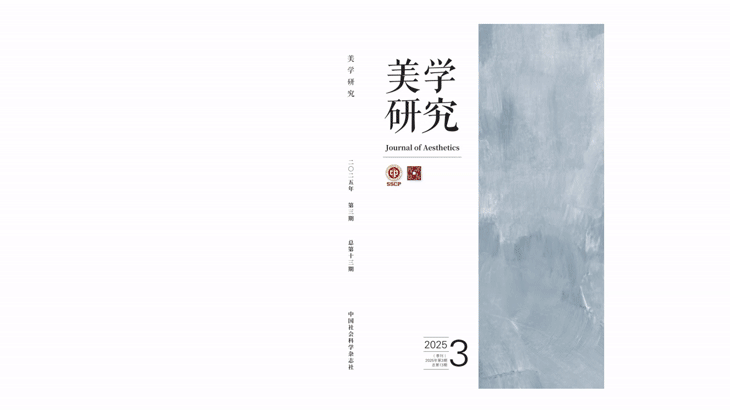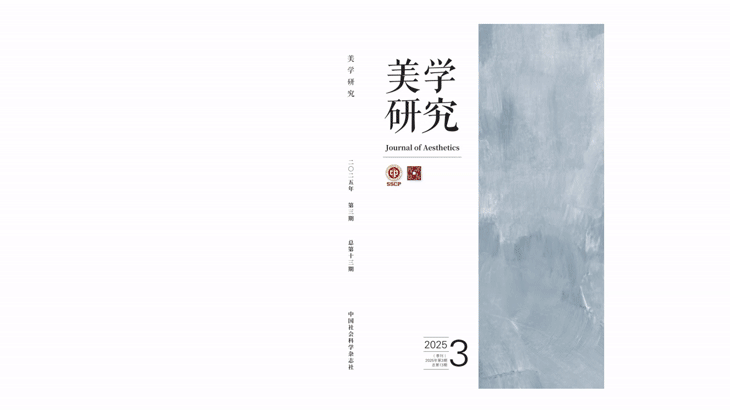
马远、夏圭是两位活跃于南宋宁宗朝(1194—1224)前后的杰出画家,在画史上往往被齐名并举。他们独特的取景角度在绘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画作尤其得到现代美术史家的赞许。譬如,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中就说:“马、夏之前的山水画,是很少有这种画法的。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可以说,马、夏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马、夏更能代表南宋山水画的新面貌。”虽然马、夏二人有杰出的创新,但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马远、夏圭之后,其二人影响的画家有很多,……但鲜有名家”。更需要指明的一点是,马、夏并不是默默无闻、直到现代才被重新发掘的画家。事实上,马、夏一度是最受古代士大夫群体重视的画家。祝枝山(1461—1527)在讽刺当时士人的学术视野狭窄时也专门提到马、夏:“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就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若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矣哉!可胜叹哉!”就是说,在弘治、正德年间普遍尊奉理学的士大夫中,马、夏二人是最为知名的画家,几乎无人不晓。从蔚为兴盛到乏人问津,这种巨大转变就发生在明代。这可以从王世贞(1526—1590)的观察中看到:“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
在现代的美术史家眼中,大多认为这种转变的发生与文人群体对“院体画”的排斥有关,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变与松江地区文人话语权的崛起和苏州地区的衰落有关,也有学者注意到明代理学内部的变化与这一转变的关系。但相关阐释大多只是从宏观角度提及心学的崛起对个性之真的推崇,而没有谈及思想史上的哪些观点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本文从明人所著画论入手,尝试对相关思想史背景可能如何影响这一转变的发生进行探究。
一、明代对马远、夏圭画作的贬斥
董其昌(1555—1636)的南北宗论可以视作明代画论对马、夏持贬斥态度的“定论”。一方面,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影响力极大,是后人理解美术史不能绕过的论点。另一方面,在南北宗论中,董其昌旗帜鲜明地将马、夏为代表的画法定义为文人画的反面,明确指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相关讨论中,对马、夏二人详细的批评并不多,但他明确分出了南北宗,则意味着对北宗诸画家整体的批评当然也适用于马、夏。董其昌说:“李昭道一派……五百年而有仇实父,……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这是用禅宗的南北宗来譬喻山水画史上的南北宗,董其昌在这里借助明代画家仇英的例子说明,北宗最大的问题是“其术近苦”,而且学习过程很漫长。禅宗南宗主张顿悟,是中国禅宗之正宗。董其昌所说的山水画南宗,当然也能像禅宗南宗那样“直入如来地”。但正如禅宗顿悟、渐悟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所需时间的不同,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真正指向的是对绘画这一事业的定位,他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虽品格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董其昌认为,值得倡导的绘画是一种寄乐的行为,是画家本人自身生机在画布上的体现。如果对于如实刻画外界过于看重,以至于人为外界之造物所奴役,则会成为外界形象的被动承受者,而非内在生机的主动表达者。正因为好的画是内在生机的主动表达,所以才可以顿悟而至,因为生机在自身之内完全充足。因此,可以说,以马、夏为代表的北宗画法,是对外界造物的刻画,自然需要一一去理解外界的造物,这不仅意味着需要耗时长久的苦功,而且未必能够表现宇宙内在生机。这一点,在董其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画的理解中体现得更为明确。董其昌说:“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失于自然,而后神也。此诚笃论。”最好的画是自然的,这里的自然不是指画要与外于人的自然界相符合,也不是指画有一种可被称为自然的固定状态,而是指在绘画中发挥了画家的自然。董其昌在另一处的表达更为明白:“气韵生动,必在生知,非学所及。然大要以淡为主,所谓淡者,天骨自然,况去尘俗,若有意为淡,去之转远。”董其昌所褒美的“淡”的审美取向,与“自然”相关,要求画家要表达出自己的自然,而不是有一种美被规定为“自然”。“天授”与“可学而致”相对,也就是说,董其昌强调画家的自然是有个人性的。因此,某个画家个人的自然,就不可能从任何一个画家或外物那里学到:“此者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顿悟这种个体性的体验被描述为唯一正确的法门。
与董其昌观点近似的明代画论还有一些,譬如陈继儒(1558—1639)的南北宗论。陈继儒与董其昌是莫逆之好,二人对绘画的认识也相近,他的南北宗论除人选上与董其昌稍有区别外,其他方面颇相似。关于马、夏代表的北宗,陈继儒说:“马远、夏圭皆李派。……李派板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尽管陈继儒没有完全展开他的观点,但他用禅宗南宗的慧能来比喻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画南宗,用禅宗北宗的神秀来比喻马、夏为代表的山水画北宗,这一观点与董其昌如出一辙。“板细无士气”,指的也是山水画北宗不像王维开创的文人之画能够表达创作者的精神,而重在反映外界造物的细节。
沈灏(1586—1661)亦有南北宗论,他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在马、夏问题上,他认为:“马远、夏圭……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从野狐禅的比喻来看,他对于马、夏等画家的评价并不高。但是,沈灏本人对“文人之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说:“今见画之简洁高逸,曰:士大夫画也,以为无实诣也,实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维、李成……辈,皆士大夫也,无实诣乎?行家乎?”可以说,沈灏本人认为,发挥画家之自然与对外物的刻画都是必要的,按他的说法就是“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块内,吾心中”。所以说,沈灏认为南北宗并不代表高下之别。他甚至进一步表示应该摆脱宗派:“董北苑之精神在云间,赵承旨之风韵在金阊,已而交相非,非非赵也、董也,非因袭之流弊。流弊既极,遂有矫枉,至习矫枉,转为因袭,共成流弊。其中机棙循环,去古愈远,自立愈羸。……孤踪独响,悠然自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对任一宗派的因袭或反对,都会导致流弊,最好的画是“自立”“悠然自得”的。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清对马、夏提出批评的理由,但显然不会出于“因袭”和“矫枉”二者之外。总而言之,沈灏显然反对当时士人对南北宗论的过度推崇,但他所说的“自立”和“悠然自得”,着实与董其昌对画家之自然的褒美有应和之处,都强调画家个性应在绘画中显现。对当时董、陈之南北宗论进行批评的还有陈洪绶(1598—1652),他说:“眉公有云:‘宋人不能单刀直入,不如元画之疏。’非定论也。……小大李将军、营邱、白驹诸公,虽千门万户、千山万水,都有韵致。”对李思训等画家的赞扬,并不影响陈洪绶非常严厉地批评马、夏,在夸奖完李思训等画家的下一句,他就立刻针对马、夏发动了攻击:“若宋之可恨,马远、夏圭真画家之败群也。”虽然陈洪绶并没有详细地解释马、夏“败群”体现在哪些地方,但从前一句他提到的韵致可以推测,他对马、夏的不满很可能是认为此二人的画作缺少韵致。
前述几位的画论,都受到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但在董其昌之前,也有画论对马、夏提出了批评。何良俊(1506—1573)的看法很可能是董其昌诸人的南北宗论的先声。何良俊说:“若南宋马远、夏圭亦是高手。……是画家特出者,然只是院体。”而所谓的南宋院体,代表的就是一种批评,认为作画者是画匠,即便绘制得很精细,但画中并不能体现出高深的境界,即“画之品格,亦只是以时而降,其所谓少韵者,盖指南宋院体诸人而言耳”。关于董其昌对气韵生动的说法,何良俊认为:“古人论画……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其论用笔得失曰:凡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意在笔先,笔周意内,笔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神不困也。”和董其昌一样,何良俊也认为气韵不可学而致,是“生知”的。当然,何良俊的表态并没有董其昌那样极端,在谈意时,也处处不离笔。何良俊虽然强调自足的绝对优先性,即画家表达的自然的绝对重要性,但具体的表述中用笔的重要性没有被摒弃,相反是通过对意的强调重新表述了用笔的内在意涵。但是,单就对马、夏的评论角度来看,何良俊完全预言了董其昌的说法,何良俊所说的“少韵”就是董其昌说的“无生机”,何良俊说的“院体”就是董其昌说的“习者”。
二、明代对马远、夏圭画作的褒扬
何良俊对马、夏的贬斥态度几乎是明代最早出现的。在他之前,大部分关于马、夏的看法要正面得多。不过当时对马、夏理解的着眼点大多仍聚焦于笔法。出生于洪武年间的史学家兼书画家杜琼(1396—1474),在《赠刘草窗画》中提及了从六朝的顾恺之、陆探微一直到明初的谢缙、金铉、苏复等数十位画家的特色,其中对于马、夏二人的评论是:“马夏铁硬自成体,不与此派相和比。”这是在强调马、夏绘画有着“铁硬”的独特风格,这显然说的就是马、夏画作中多用刚性十足的线条,而很少有淡墨渲染式的画法。尽管诗句中“自成体”三字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夏二人的独创性,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赞许,但这句诗本身主要还是对马、夏风格的描述而已。所以现代论者认为,杜琼的这首诗“不带偏见地论述绘画渊源,提出了二李和王维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绘画风格,从六朝直至元末,不论荆关董巨,还是二李马夏诸家,均述其风格特点,而无褒贬”。换言之,杜琼并不是作为一个严格的艺术史论家来进行艺术批评,而只是作为一个擅画的文人在谈及自己了解的画史,最终是为了自诩——“我师众长复师古,挥洒未敢相驱驰”。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的吴宽(1435—1504),对马、夏的赞许就不仅仅是从笔法上来评价了。吴宽说:“马远不以画水名,观此十二幅,曲尽水态,可谓多能者矣。全卿家江湖间,盖真知水者,宜其有取于此。”吴宽引用陆完(1458—1526)对马远《水图》的赞赏,其目的显然就是要以陆完的知水来说明马远的知水。但是,这里的“知水”是什么意思呢?吴宽没有做出足够的解释。不过,吴宽在赞赏王维画作时说:“右丞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渟,洞鉴肌理,细现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气,孰谓画诗非合辙也。”可见,吴宽认为,王维的画作之所以好,原因在于王维自己心中的洒脱境界,并认为这和诗的道理是相通的。吴宽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何王维心中的洒脱境界对绘画有帮助,他说:“若《行旅图》一树一叶,向背正反,浓淡浅深,穷神尽变,自非天真烂发,牢笼物态,安能匠心独妙哉?”吴宽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王维心中如冰壶澄澈、如水镜渊渟,所以他才能完全把握外在世界的种种细节变化,并将其如实地表现出来。所谓的天真,就是与“人为之伪”相对应的“天然之真”。可以想见,吴宽对马远之“知水”的理解可能与王维之“知物态”是相似的,即如实地表现了水的种种细节变化,是为“曲尽水态”。
与此类似的表述还有万历年间李日华(1565—1635)对马远《水图》的评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形者,方圆平扁之类,可以笔取者也。势者,转折趋向之态,可以笔取,不可以笔尽取,参以意象,必有笔所不到者焉。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而得也。性者,物自然之天,技艺之熟,照极而自呈,不容措意者也。马公十二水惟得其性,故瓢分蠡勺一掬,而湖海溪沼之天具在,不徒如孙知微崩滩碎石,鼓怒炫奇,以取势而已。此可与静者细观之。”李日华认为,马远的《水图》超越了得水之“形”“势”“韵”的境界,进一步抵达了“得水之性”的境界,而这是何种境界呢?是“物自然之天……照极而自呈,不容措意者”,即完美地捕捉到了事物自然的天性,没有在其中渗入一点自己的意见,“照”其实和吴宽所使用的“水镜”的比喻是一回事,就是为了说马远的《水图》是对水性的领会,而不是在表达自己之思的结果。
在这些人之前,生活于元末明初,但习惯于被认为是明初人物的王履(1332—?)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然揭示了吴宽、李日华的观点。王履非常直接地褒扬马、夏二人的成就:“夫画多种也,而山水之画为予珍;画家多人也,而马远、马奎、马麟及二夏圭(按夏圭之子名森亦工画,此处应言夏圭父子。)之作为予珍。”王履为何将马、夏诸人的画作视为所有绘画作品中最为出色的呢,他解释道:“以言五子之作欤,则粗也而不失于俗,细也而不流于媚,有清旷超凡之远韵,无猥暗蒙尘之鄙格,图不盈咫而穷幽极遐之胜,已充然矣。”在这段话中,虽然提到了粗、细,但并不主要在谈及绘画的笔法等,而是在谈画作体现的风格和气韵。王履认为马、夏辈的画不俗,也就是说有高雅的审美取向;不媚,就是说画家有自己想表达的意图。总而言之,王履不认为马、夏仅仅是为了表达外界的山水的样式而绘画,而是在通过画图表达“清旷超凡”的韵致。因此马、夏能做到仅仅绘制出景物的一小部分,就能展开极其悠远的映射空间。
另一个颇不相同的评价出自高濂(约1573—1620),他虽然没有直接对马、夏的画作进行评价,但他既在某种程度上赞扬马、夏,又认为马、夏算不上是最优秀的画家群体中的一员,这可以从高濂在赞赏赵孟頫的画作时所流露的态度看出。他说:“赵松雪……摘取马和之、李公麟之描法,而得刘松年、李营丘之结构,其设色则祖赵伯驹、李嵩之浓淡得宜,而生意则法夏圭、马远之高旷宏远。”在这段话中,高濂大大赞赏了马、夏二人画作中有高旷宏远的生意,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但是,必须了解高濂对“生意”的定位,才能完整理解高濂的评价。高濂说:“余所论画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夫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气之中。形不生动,其失则板;生外形似,其失则疏。故求神似于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这段话里,高濂事实上给出了三种不同境界的绘画:得神气的天趣之画、有生意的人趣之画、仅形似的物趣之画。从这个排序来看,马、夏诸人的画作仅能排在第二序列,并非最佳的一类。这也与高濂对历代画家的褒贬态度一致,他认为唐人之画高于宋人之画,而宋人之画又高于时人之画:“唐之天趣则远过于宋也。……然而宋人之画,亦非后人可造堂室”。
三、“气韵”“自然”等美学概念的变化
根据上文所述,明代的画论并不单纯对马、夏的评价不一致,对马、夏之认识也大相径庭,这才是这些评价大不相同的原因。譬如,何良俊、董其昌等人认为马、夏之画在气韵生动上有所欠缺,而这是画家没有表现其内在的自然导致的,而吴宽、李日华则认为马、夏之画不止有生动之韵,更超过了生动之韵达到了自然之天。同样谈“气韵”、谈“自然”,而他们的看法不同,这说明不同的画论家所使用的“气韵”和“自然”表达的不是同一个意思,这说明美学概念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王履论画时说:“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这段话非常精到地指明,无论绘画想要传递什么,都要通过其中的形象来传递,因此无论是“意”还是“形”,都必须还原到对形象的把握上来,所谓“仅得形似”恰恰不是在“形”这个维度做到了十足,而是做得不足。“形外有意”才是在“形”的层面做到了完美。在确定了“形”的根本性的基础上,王履指出,“若夫神秀之极,固非文房之具所能致也。然自是而后,步趋奔逸,渐觉己制,不屑屑瞠若乎后尘。每虚堂神定,默以对之,意之来也,自不可以言喻”。也就是说,在对“形”的完美把握之后,“意”会以一种“默对”的方式出现,“意”是一种可被作者表达和观者捕捉的东西,它本身与画作有区别,但在画上表现为对形象的安排和把握,作者和观者通过画上的形象进行交流。对于作者而言,“意”其实体现为安排形象的意图,所以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要表达华山的神秀之美,需要的是心中能有对神秀的理解,然后从容地运用形象去表达它,这个绘画形象的基础是心中的形象,而非某些对于华山的共见,这是与不能体会“意”的普通人“喜同不喜异”的偏见不同的地方。总而言之,王履所说的“意”是画家个人对绘画上形象的独特安排方法,而这种安排方法来自画家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是对自然界的形象和气韵有深入理解的表现。吴宽的理解与王履相对接近,吴宽将王维的画作赞赏为“天真烂发”“牢笼物态”,认为画家的“意”其实体现于画作上的形象,所以擅画者是“胸中自有九畹百亩,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间”,强调画家要具有对外在自然界进行捕捉的能力。
何良俊在一定程度上持近似于王履、吴宽等人的态度,即最好的画是对自然界的完美把握,他继承了把自然之逸品置于神品之上、将其视为最好之画的看法,所以他引用苏轼评论吴道子的话:“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盖古今一人而已。”所谓以灯取影,与吴宽、李日华的镜喻如出一辙,指的是对外在对象的完美表现。而且,就他对苏轼言论的引用来看,他认为她的画作尤其体现在对绘画对象的动态把握上。苏轼在评价历代水画时,赞美孙位的水画是“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盛赞孙知微的水画是“作输泄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又把蒲永升的水画置于二者之上,因为他的画能“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但可以看出,这种动态的评价其实体现在观者观看时的感受上,这就不仅仅是关于绘画的形象是否符合外在的对象了。因此,何良俊在另一方面又直截了当地表示,意或气韵完全与对外界形象的捕捉和安排无关。他就倪瓒画表示:“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尘之格,而意态毕备。……其庶几所谓自然者乎?”草草的画笔显然不能完美表现外界对象,而只能表达画家本人的意图。所以何良俊在另一处评价倪瓒的画论时说:“其即所谓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写胸中逸气耳。”自然的画是恰当传达了作者意图的画。这一点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既然画的动态的“目的”不过是让观者产生某种感受,那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绘画本身满足形似或别的对形象的固定要求。
到了董其昌,他虽然仍强调画家必须通过形象来传达意:“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但是他所说的神,已经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所谓“神犹火也,火无新故,神何去来?”神的传递有时需要依靠形象,但神本身完全不依赖于画中的形象。因此,董其昌甚至主张,为了表达画家自身的意图,可以违背外在自然界的规律,他说:“木不臃肿、经霜变红黄叶者谓之秀。”可见,董其昌虽然仍在画论中时时谈到笔法等,但对于“神”或者“意”的地位的推尊,已经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除了说“神”“意”是画家天授的自然之外,不能再说出更多,亦即前文所引“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之意。所以,对于沈灏、陈洪绶这类对董其昌南北宗论有所批评的人,就会重新强调法度和规矩,如陈洪绶说:“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即如倪老数笔,都有部署法律。”
总而言之,明代数辈文人之间,虽然使用了相似的“意”“气韵”“传神”等概念来形容画,但他们所用的词的含义并不相同。在对马远、夏圭评价发生变化的两端,分别矗立着两种观点。一者认为气韵(意)是画家对自然界的对象的某种独特而深刻的把握,并运用绘画的形传达出来。一者认为气韵是画家自身的某种心理状态在画作中的表现,它本身并不依赖于画。这两种观点不那么极端的变体及其混合,形成了明代画论多姿多彩的观点。按时间来看,大致是后者越来越获得各方认可,这种观点直到过于极端而被反对。嘉靖年间的何良俊可以作为一个转折的标志,毕竟他几乎同时持有两种观点。
四、理学发展与画论的转折
明代文人对这些美学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与明代的理学发展相呼应。明初,朝野上下流行的仍是南宋晚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程颐、朱熹的理学。而心学一脉在明代中期开始勃兴,至王守仁(1472—1529),心学逐渐成为文人间普遍流行的思想。这在时间上匹配前述的美学概念变化的曲线。理学发展中有两点可与前文述及的美学概念内涵的变化相联系。
其一,对“格物”的理解的变化。程朱学派非常重视《大学》这部经典,尤其是其中“物格而后知至”一章,被认为是修身的基石,而修身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石。朱子曾表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主张知识的获得需以对外在事物的探究为重要途径。通过对具体事物各个方面的理会,最终可实现内在认知与外在事理的贯通,所以朱子说:“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这种逻辑延伸至绘画领域,便是认为绘画的 “道理” 既需依托对自然物象的观察,也需结合内在的认知锤炼,对外在物象的专门钻研是达成绘画理解的重要基础。在这种理解下,很可能催生王履等人对绘画的理解。如同“理”往往需要通过外在事物才能得到理解,绘画也必须以了解所想绘制的事物为前提,所以王履说:“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
心学一派与程朱学派有所不同。王守仁曾在回应有关事父、治民等事的提问时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在这种理解中,别说绘画之事,便是儒家最重视的治民等事,似乎都没有一个预先存在的道理,道理是在实践的语境中形成的具体的应然性,获得这种应然性的前提是培养一颗纯然的心,这颗纯然之心在遭遇具体事情时能够自然发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学对事情本身的客观属性的全然否定,阳明学是在强调,内在天理之心的澄明这一“内事”在治民等“外事”上仍具有极强的重要性或者说优先性。那么,同理可得,并不能将绘画形式视作单纯需要去模仿的外在事物,在绘画过程中,最重要的仍是发现“此心”所独有的精神,所以学习绘画的过程本质上是画家在自己的心上用力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董其昌说:“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传神的画绝不可能依靠临摹前贤画中的形象来习得:“盖临摹最易,神会难傅故也。巨然学北苑,元章学北苑,黄子久学北苑,倪迂学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所谓的神会,就是对前代画家之精神、境界进行体会,其本质也是自身之独特精神、境界的确立,而绝不是对某个外在的具体主张的被动适应。
其二,尤需注意的是,“自然”等美学概念也是理学家们使用的哲学概念,而对“自然”的理解发生的转变也发生于明中期。在朱子那里,“自然”这一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天理,指的是天理本体完全实现自己或者被实现的状态。而对于阳明而言,自然往往用来描述“良知”自身的真和自发 。也就是说,对“自然”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从“理”到“心”的进一步“向内转”的趋势。这意味着,明代画论家对相关概念的运用,很可能是受到了理学发展的影响。从时间节点来看,在画论中首个严肃批评马、夏的何良俊(1506—1573)略晚于陈白沙(1428—1500),而最终通过南北宗论确立了马、夏“不可学”的董其昌(1555—1636)则略晚于王阳明(1472—1529),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明代画论家对美学概念理解的变化的重要动力很可能来自理学的发展。
结语
明代画论对马远、夏圭的评价发生了重要转变,马远、夏圭画作在明前期作为共识的标杆,而明中期以后却成为被贬斥的对象。但这一变化显然不仅仅因为当时对“院体画”的排斥这一简单因素,更重要的是明代文人对“自然”“气韵”等美学概念的理解发生了根本迁移。明初,王履、吴宽等将“自然”视作对客观物象的深刻把握,称赞马、夏画作“曲尽水态”“得物之性”。而后,何良俊兼具“重形似”与“崇逸气”的观点是对马、夏画作评论的转折。至董其昌则彻底将“自然”定义为内在心性的流露,认为马、夏“刻画造物”失却生机,认为“非吾曹当学”。
宋明以降,中国文化出现了逐渐“向内转”“向下移”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于阳明学中,即重视庶民教化。而明代中期以来画论中对于内在心性的流露的重视,与这一发展趋势有很强的一致性。本文认为,从哲学思想根源的角度入手,更能把握明代画论对马、夏评价发生变化的本质,艺术评价的深层逻辑,往往植根于文明史的演变脉络之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胡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