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底,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国际与欧洲研究系教授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Athanassios G. Platias)参加了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发布会和“浴火涅槃:文明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高度评价这一新的二战史力作,认为《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通过反驳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凸显了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性,为全球理解二战提供了更真实的视野。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普拉蒂亚斯教授。

■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 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一重要界定对整体理解二战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普拉蒂亚斯:将战争的起点前移到1931年,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它不再是一场最初爆发于欧洲、随后才向亚洲蔓延的地区性战争,而是自一开始就呈现出全球范围内多方力量此起彼伏、相互牵制的复杂格局。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帝国扩张、去殖民化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并非战争的附属现象,而是推动战争演变的核心动力。
例如,日本1931年开始逐步将侵略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战场,并投入了大量兵力。这一庞大的军事消耗,不仅无法与德国共同对苏联发动东西两线攻势,也大幅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国抗衡的能力。换句话说,东亚战场的僵持与消耗深刻影响了欧洲战场和全球战略的走向。
这一时间线的重构给战争史的教学带来了重要改变。传统叙事常常将去殖民化置于战争“结束之后”的章节,仿佛它只是战后格局的自然产物;而新视角则要求我们把去殖民化置于冲突的中心位置,认识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提出的政治诉求、爆发的抵抗运动以及具备的战略价值,直接影响宗主国在军事部署、外交策略和战后规划上的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同盟国整体的战争格局。
这种重新解读还鼓励学生跳出“战役—胜负”的叙事框架,不再仅仅把战争看作一连串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由长期消耗、帝国竞争、资源动员与战略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的全球体系。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正是这一体系不断演化、深刻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视角的转变为学者提供了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普拉蒂亚斯:时间线与重心的重新划定不仅改变了对战争本身的理解,也为跨学科和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首先,日本战略过度扩张的量化研究。学者可以通过系统分析日本在中国投入的兵力、资源和财政成本,探讨这种长期消耗如何限制其在其他战场上的行动空间和战略选择。其次,关于同盟体系协同效应的研究。美国的工业能力、苏联的人力资源、英国的海上力量以及中国对日军的长期消耗,看似各自独立,却在总体战略中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合力。这一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二战胜利的多元动力结构,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叙事。最后,战争期间的去殖民化进程。研究可以从殖民地士兵的参战、劳动力的调动、政治运动的兴起等角度,探讨亚洲与非洲殖民地不仅是战争的“背景”,还是积极塑造战争进程本身的力量。此外,还存在对后勤与地理因素的深入研究空间,如中国和苏联的战略如何决定战场态势的演变,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外交布局与战争总体走向。
总的来说,这种新视角不仅丰富了二战研究的维度,也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更具全球意识、跨地域、跨主题的研究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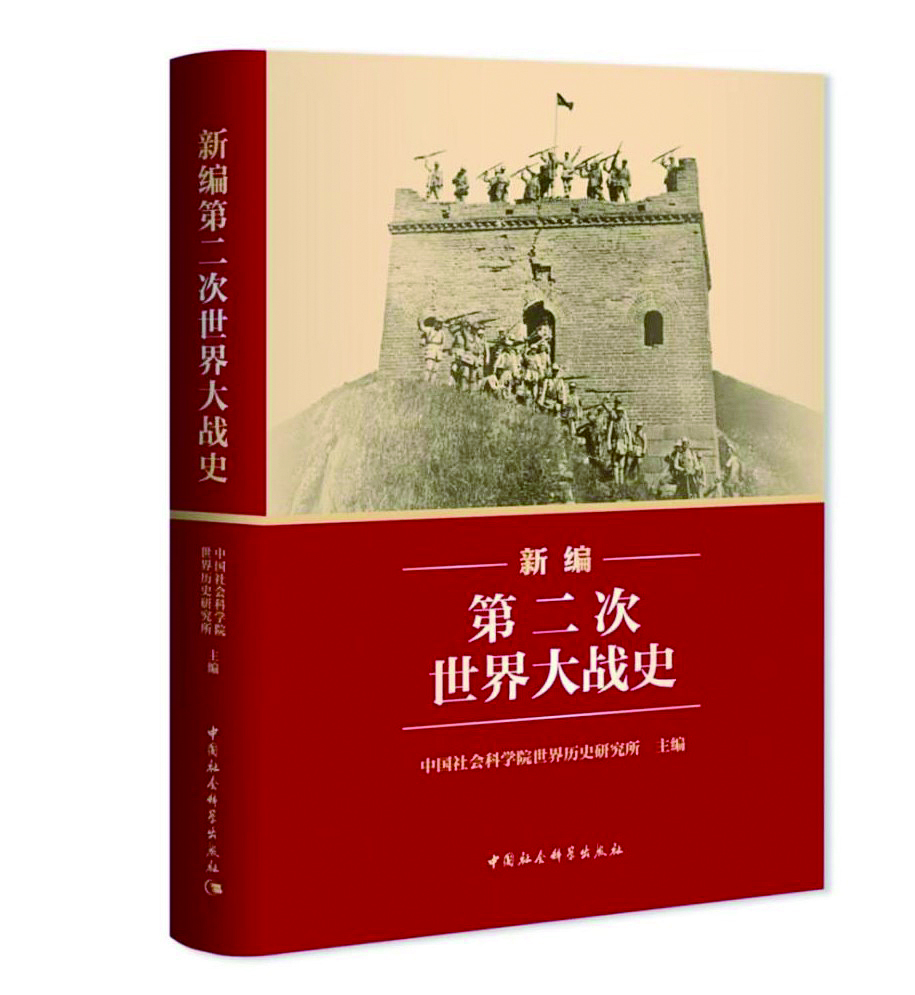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全球视角看,二战研究目前存在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学者的日益参与将如何推动这些问题的研究?
普拉蒂亚斯:仍有若干争论尚未解决。一是时间起点的问题。战争时间起点不仅是时期划分的问题,更涉及因果关系。这一选择会改变我们对联盟形成、包围态势和动员方式的理解。二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战争在单一决定性战场上已被决定,尤其是苏德战线;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系统性视角,认为日本的战略过度扩张、盟军的海上控制以及美国的工业实力同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是关于轴心国协调的问题。如果日本不得不将一半军队留在中国,那么德国与日本是否可能实现真正有效的战略协同?四是关于战争的结束问题。对日本、中国和苏联档案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深化我们的理解。五是暴行记忆的问题。如何保留对南京大屠杀的独特记忆,同时将对亚洲的大规模暴行纳入全球道德地图,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具备语言优势和档案获取能力,还能提出关于国家—社会动员与“人民战争”的新研究方向,并帮助纠正长期以来以欧美—大西洋视角为主的历史书写偏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您对二战作为全球事件的深入研究,您认为哪些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具有启示意义?
普拉蒂亚斯:首先,联盟的作用至关重要。二战中盟军之所以能够获胜,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力量,而是美国的工业能力、苏联的耐久力、英国的海上控制以及中国对日军的长期消耗,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力量体系。今天同样如此,在全球事务中,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往往比单一大国的实力更为关键。
其次,时间和持久力本身就是战略资产。在长期竞争中,国家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与战场胜利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具决定性。
再次,后勤与关键通道的控制对战略选择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后勤与关键通道决定了战争空间和行动范围;而今天类似的因素,如能源流动、海上咽喉要道、关键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依然在战略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
最后,叙事本身能赋予国家合法性。二战记忆自1945年以来一直支撑着各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理解国家如何构建和运用历史叙事,对于外交实践而言,也是重要的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