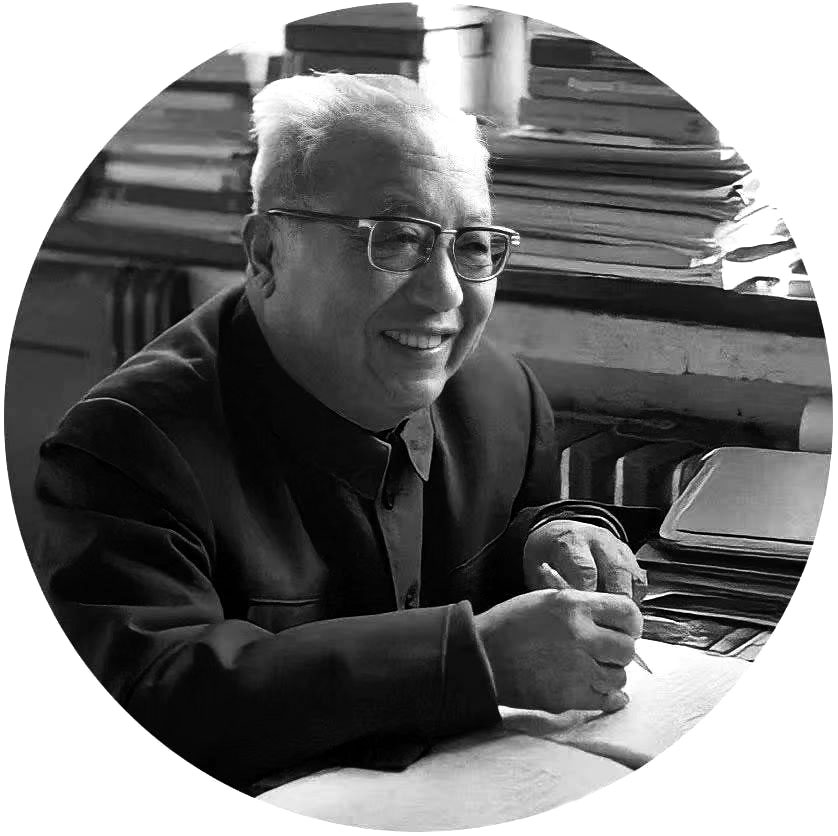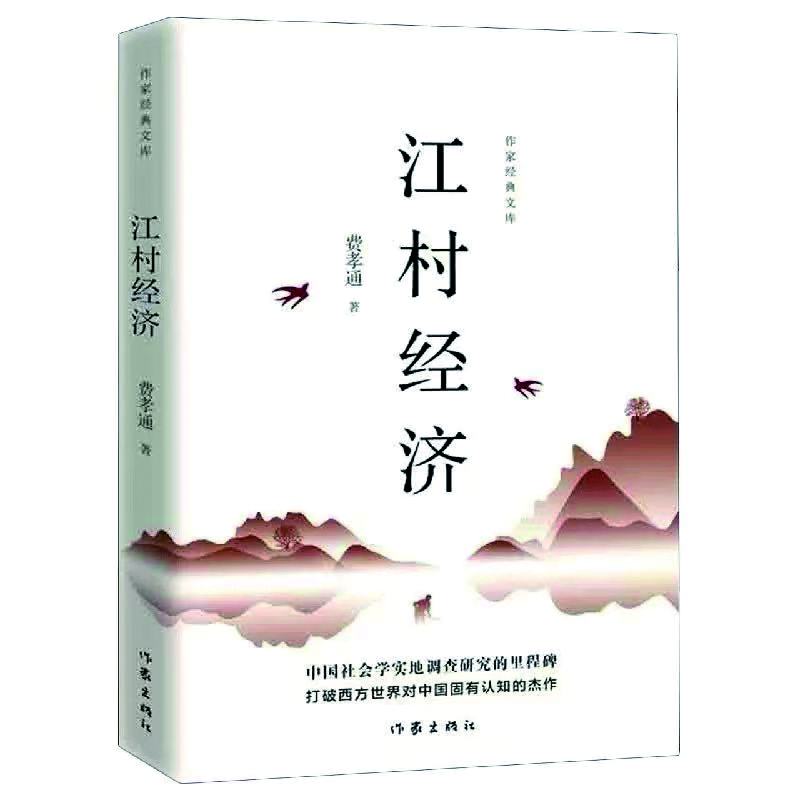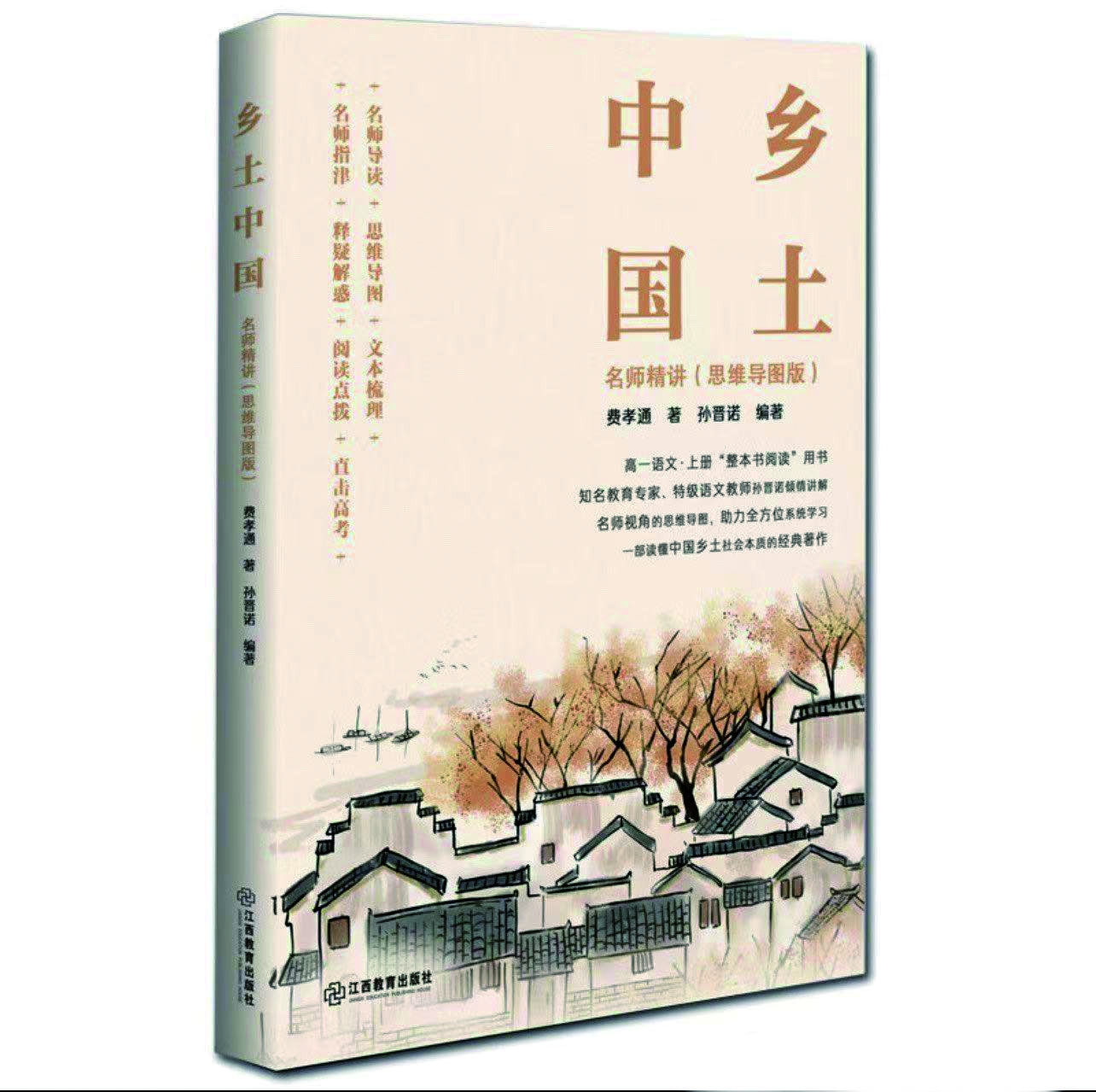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前辈学者中,费孝通先生是自主知识生产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是后学学习的榜样。那么,他治学的自主性是如何实现的?答案就在于费孝通对学术自主的自觉意识、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以及比较中作理论选择的判断能力。
学术自主的自觉意识
实现治学的自主性,首先要具有对学术的自觉意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了诸多的概念和理论,这些概念和理论都需要中国化,如同把喝了的牛奶转化为营养,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消化吸收得不好,就会出现“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问题。而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思想的消化与吸收却没有这样的自然机制,需要人借助自觉意识保持自主性才可以做到。这种自觉自主意识贯穿费孝通的一生。27岁时,他就在《关于实地研究》里写道:“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费孝通带领大家恢复重建社会学之时,他理想中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是要符合中国社会条件、服务于中国人民、本土化的社会学。1981年,费孝通参加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说:“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当这些概念传入中国,又有一个与中国特点相结合的复杂过程。”“一个概念要进入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正是它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起这样伟大的作用。”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促使费孝通的知识生产能够保持自主性。
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和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其一生学术自觉和自觉意识的反思性总结和提炼。他在1997年的一次对话中说:“我没有事先设定的想法,出来之后看到了事实。把我自己也放到实际里边去,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实际。我叫它‘文化自觉’。自觉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个不容易。我担心很多知识分子不自觉,跟着外国人走。他也想问题,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他不接触中国的实际。他不懂啊。他讲得很好听,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没有用啊!我是说,你写的东西要有用啊。”文化自觉里有着“自主”(调适)的意思,并主张“要从个体做起”,没有个体的自主性自觉意识,是很难实现治学中的自主性的;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必须要有这样的反思性自觉意识。
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始终坚持从实求知,重视社会调查的治学方法,这是他实现学术自主性的关键。要“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而不是书上说的就相信,就像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样,费孝通重视实地调查。他认为,自己比较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花篮瑶社会组织》,第二篇是《江村经济》,第三篇是《内地农村》,这些文章都是实地调查写成的作品。他晚年出版了一本学术反思文章的结集《从实求知录》,“为什么叫《从实求知录》呢?意思是书里边记录了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的经过”。在1997年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说:“我提出来的很多观点,都是从实际当中看出来的。每一个想法,都包括有一段真实的经历,一个故事。……不是空想,而是实际地看。看见具体事情,看出来意思,把意思说明白,再回到实际中去。”他的一生是这样认识学术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为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而“行行重行行”。
《乡土中国》资料图片
费孝通以从实求知的原则来做社会调查的治学方法,主要受到他的几位老师的影响。首先是他的学术启蒙老师吴文藻。吴文藻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虽然他本人博士论文是以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方式写就,但他当时在大洋彼岸留学时就已经强烈意识到一种剧烈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大转型,即“社会工程”的学术转向。原来的学者是图书馆式的,在图书馆里查文献、做研究、写论文,也就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新的“社会工程”项目即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把获得的知识用于对社会的改进的规划和指导。吴文藻回到国内就着手把芝加哥学派的社区实地研究与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相结合,以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启蒙了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开启了被国际学界称作中国社会学派的“燕京学派”。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伯特·帕克1933年来燕京大学讲学,对费孝通一生治学影响深远,后者的实地调查方法奠基于这位老师,晚年“补课”还回到帕克,完成《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费孝通把Park翻译为派克,我们一般译为帕克)。这种实地调查是社会学家从人类学家那里借鉴而来,所以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融合的结果,从影响费孝通的治学路径来说,就是社会学家帕克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共同影响的结晶,甚至还有人类学家史禄国的部分功劳。正是循着这些前辈学人的足迹,费孝通走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道路。
理论选择的判断能力
费孝通治学的这种从实求知、重视社会调查的方法,是社区实地调查和功能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质而言之,来自费孝通在比较中选择的自主判断力。费孝通选择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也是他自己比较人类学诸种理论流派之后的选择,这一比较和选择本身就是他治学自主性意识和能力的体现。费孝通23岁时批判地甄别了当时人类学的诸理论,尤其是进化论,之后理智地选择了功能论,并于1933年写就《人类学几大派别——功能学派之地位》一文。当时,他还没有见过马林诺夫斯基,而他师从马氏则是3年之后的事情了。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首先批评了进化学派:“进化学派的人类学是历史性质的。他们的贡献亦是在历史方面的……但是他们的见解和方法很有可议的地方。……此种遗俗方法,苟能严谨应用,自可有所发明,但其流弊所及,附会臆断,无可对质。……所以单就方法而论,很有危险的。……进化学派因概念上及方法的缺点所以产生很多错误的结论。”然后,在依次批评了“播化学派”(即传播学派)和“批评学派”之后,他开始称赞功能学派。
费孝通对功能派的赞赏与选择是与其他诸流派比较后的自觉行为。他认为,功能学派在人类学上贡献最大、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将人类学从历史性质转变为科学性质。功能学派所欲研究的对象是文化各部分之间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结构的功能关系。这种关系是抽象的、普遍性的、没有时间性的,因之是科学的性质而不是历史的性质,因此实地调查就非常重要。他接着说:“功能学派既以文化结构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注重文化的整体性,所以不能离开了研究对象的所在地而推考的。于是注重实地工作,进化学派所以会铸下许多错误,归根还是在当时实地观察的困难,即使实地观察时,亦是走马看花,选择对于自己先定的理论相配合的材料加以摘录罢了。所以他们的结论每与事实相悖。……功能学派实在人类学史上占一极重要的革命地位,因为它在根本的概念和方法上,下了一个极有系统的改造。”
除了采取功能主义理论,费孝通晚年在一篇访谈中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的一切。物质生产是人们的基本活动,它决定人们的观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费孝通“所有著作的基础”。正是这样的理论甄别和选择能力使费孝通一生为中国社会科学贡献了诸多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比如差序格局、双轨政治、多元一体、社会继替、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进一步说,费孝通是把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实现了很好的结合,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的。用他自己的说法,“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又要西方”是指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又要中国”是指在中国做了充分的本土实地调查,更有东方的底子,主要指观念、传统、学养等。高超的理论鉴别力与从实求知的“行行重行行”的社会调查有机结合,最终成就了费孝通的学术。
理论是从实求知的成果,用以指导实践,要对老百姓有用;从实求知也是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路径。米寿之年的费孝通曾这样说道:“我们要能讲出来,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是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中国化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提给大家,也提给自己。……我的主张是从实求知,从实际当中得到知识。理论从实际里边出来,经得起考验。”费孝通秉承中国士人经世致用的传统,从实求知,为了做有用的学问,一生“志在富民”,因此他说:“我们都在做学问,学问要做出点意思来。意思在什么地方?在于这学问的用处。用到什么地方?用到改善群众的生活上,用到提高生产力上。学以致用,这是中国文人的老传统,好传统。”故此,我们也可以说,费孝通治学的自主性来自他“从实求知”的方法,来自他“志在富民”的理想,更来自他“文化自觉”的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