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给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又增添了新的热度。谈及西夏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可不提。
西夏是辽宋夏金时期的重要王朝,主体民族是党项族,汉族也是其主要民族。元朝未修西夏史,导致西夏历史资料严重缺失。20世纪初,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掠走了大量西夏文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部分文献内容逐渐披露,国内外学者开启西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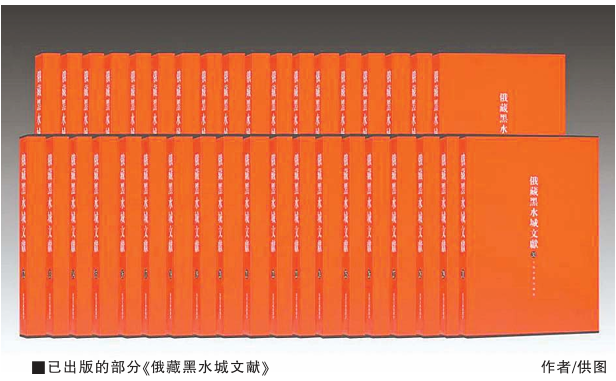
中国学者陈寅恪、王国维均撰写过研究西夏文献的论著。当时的年轻学者王静如师从陈寅恪从事西夏研究,创获良多,其中《西夏研究》(三辑)是他最有成就的代表作。1958年,王静如先生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研究所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他恢复西夏研究,配备了白滨等两名助手,并招收笔者为研究生,一方面组织搜集国外的研究进展和新资料,一方面放眼长远,传承学脉,培养年轻人才。
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物考古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与王静如先生组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进行系统考察,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做顾问,笔者和民族研究所白滨参加。经3个月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确定莫高窟、榆林窟有80多个西夏洞窟,改变了敦煌石窟的时代与分期面貌,开创了西夏艺术和历史结合研究的先河。
1976年,笔者和白滨用近4个月时间,到西夏故地西北五省区进行调研,了解山川形势,考察诸多重要西夏遗址、遗迹,搜集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资料。特别是在银川考察期间两次勘察西夏陵,并阅览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拓片,收获很多。此次调查为西夏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1981年,笔者和宁夏博物馆的吴峰云根据正史、文集和方志记载的线索,到安徽等地调查党项人余阙的后代。在合肥和安庆分别找到数以千计的西夏人后裔,同时发现两部余氏宗谱,对这支西夏后裔的渊源进行了研究,第一次找到有确切系统文字记载的西夏后裔。
1984年至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文宽作为领队,对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工作,出土西夏瓷器多达6400余件。1988年出版了《宁夏灵武窑》,首次对西夏瓷窑、瓷器和烧制做了深入研究。1995年,他又主编出版了《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更为系统、全面地阐述灵武窑考古发掘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权威资料。
2000—2001年期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陵区管理处联合对3号陵地面遗迹展开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堪称西夏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发掘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蒋忠义、徐殿魁、杨国忠3位专家受邀至现场进行指导,并参与发掘,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西夏陵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撰写多篇论文,并多次参加申遗文本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作出重要贡献。
译释价值高、难度大的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学者始终专注译释难度大、学术价值高的西夏文文献。《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对每一个西夏字形、音、义都有解释,学术价值极高,译释难度很大。史金波、白滨和古代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的黄振华经多年整理译释、研究,于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使6000多个西夏字中的5000多个可以释读,为西夏文译释提供了关键资料。
1993年,笔者和黄振华、聂鸿音出版《类林研究》,将西夏文《类林》译成汉文,恢复了失传已久的唐代《类林》,同时深化了对西夏语语法的认识。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长达20卷的西夏文法典,内容极为丰富,负载着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等重要资料,因无汉文本参考,翻译十分困难。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经过多年努力,将其译为汉文,1994年出版译著《西夏天盛律令》,2000年推出修订本,为西夏研究提供重要支撑,推动了西夏学的进展。
民族研究所专家在俄罗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契约、军籍、告牒、书信等。这些文书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西夏文草书残页难以辨认。经过多年探索,这些文书逐渐被破解。2007年、2017年、2021年,笔者先后出版《西夏社会》《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和《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皆利用了大量西夏文草书文献,揭示出鲜为人知的西夏社会、经济和军事情况。
编撰《俄藏黑水城文献》等文著
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苏联专家随研究进展陆续刊布其中一些文献外,绝大部分文献未能面世,制约了西夏学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指示和院外事局、科研局的直接组织下,笔者与俄方联系,达成了中俄合作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方人员自1993年至2000年间4次赴俄对文献进行整理、著录和拍摄工作,编纂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今已陆续出版8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31册(余2册待出)。这一大型文献丛书基本上涵盖了流失文献的全部内容,为西夏学和相关学科开辟了广阔前景。2005—2007年,笔者为主编之一的《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出版,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但未保存早期印刷实物。出土的西夏文献中陆续发现了活字印刷品,填补了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的空白。中国的专家们先后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笔者在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先后发现了多种西夏文和汉文活字印本,其中有木活字本,也有泥活字本。2000年笔者和雅森·吾守尔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出版,利用藏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多种西夏活字印刷品和藏于法国及中国的近千枚回鹘文木活字,结合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认识,对维护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起到重要作用。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民族研究所成立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的专家们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西夏的重点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于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笔者为首席专家。项目组组织全国近百位专家,设立30个子课题,经10多年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此项目内容主要有搜集、整理、出版西夏文献和文物;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推出一批创新研究成果。
系统出版《西夏文物》被列为该项目的重大课题。课题组对各地西夏文物进行普查,编纂出版大型文物资料丛书,共分为5编,即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石窟编、综合编,35册,现已全部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拓展了西夏研究领域,对西夏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笔者与宁夏大学的杜建录共同主编《西夏学文库》,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已出版国内外西夏学专家的论著、译著60种,多方面展示了西夏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了西夏学的发展。
除上述著述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研究专家还出版了不少著述,如笔者的《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教程》《西夏风俗》,白滨的《元昊传》《党项史研究》,聂鸿音的《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献论稿》《党项文献研究导论》,孙伯君的《西夏文献丛考》《元代白云宗西夏文资料汇释与研究》,和智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译补正》等。
此外,《西夏文教程》和《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已译成英文版在国外发行,欧美等多家著名图书馆入藏。这是中国西夏研究著作首次译为外文出版,对具有特色的西夏文化“走出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对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作出了新的贡献。
民族研究所陆续培养了20多名西夏研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宁夏大学授课,培养西夏文研究人才。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西夏研究方面传承学脉,将语言文字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将西夏纳入中华文明史研究,注重资料建设,不断推出创新成果,培养大量人才,引领学术潮流,为西夏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