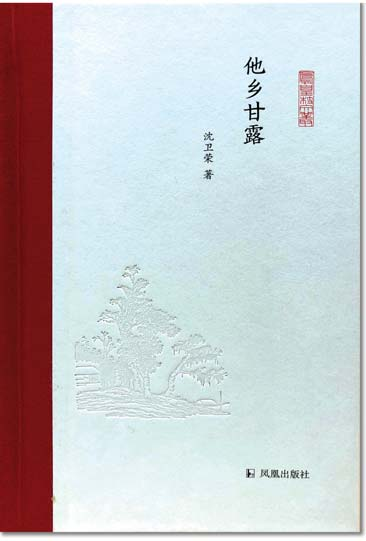
沈卫荣教授将自己最新的随笔集的题名定为《他乡甘露》,在我看来,似乎再没有比它更适合这本小书的名称了。只是这一书名中蕴含的密意恐怕的确让人乍一眼看去难以领悟。作者在前言中对书名有简短的解题,说明了“他乡”之称呼是缘于随笔创作于他乡,并且也为他乡而作;而“甘露”则正是作者自己的故乡。这一解释虽然直截了当,但显然只是书名的“世俗谛”,乃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只适用于还未读此书的“初业行人”。等到真的读罢此书,读者自然能领悟到“他乡甘露”最究竟的“胜义谛”——“他乡”乃是我们看待世界应有的一种批判性态度;“甘露”则是这种态度能为我们带来学术和人生圆满的内在功效。
对书名“胜义谛”的阐释毫无疑问潜藏在书中第一辑《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是完美的》这篇文章中。故乡必然是甜美的,因为它是形塑我们每个人习性的原初环境,我们的语言、饮食、习惯、思想都无形中受到故乡深刻的影响。也正因它塑造了我们,我们自然而然热爱的一定是故乡。但强大的人能够“把所有的土地当作故土”却是因为这样的人勇敢地走出了故乡的温柔,去欣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各式文化风貌,并且真正享受这种多元性带来的美感。最后,“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之所以完美,则是因为他们更进一步褪去了对世间任何一地的滤镜,能够做到真正批判性地、平等地看待自己的故乡与异乡,分辨出世上一切的美与丑、善与恶、纯净与污秽、高尚与拙劣。
将“他乡”之视角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语文学。这本书的第三辑集中讨论的就是语文学的历史、实践与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给语文学一个确切的定义。但笔者认为书中《再认识陈寅恪》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大略描绘出语文学的轮廓:“傅斯年先生等人留学海外的时候,语文学就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当时的人文科学研究提倡的就是用现代的、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正确地解读语言和文本,以重建历史文化思想。而语文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所以,它曾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总称。”
这里的关键词显然就是“现代”“理性”和“科学”。这就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走出我们所沉浸的传统,也就是我们精神上的故乡。经学家、佛学家都不再仅仅依靠师承中的口传来研究微言大义,而应尽可能多地关注不同的传统。但这还不够,我们对所有的传统都应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扎实地基于证据说话,而非不加分辨地采信,这就是从“把全世界当作故乡”走向“把全世界当作异乡”。但这种批判性的路径最终却会为我们带来爱,这是因为只有批判性的路径才会让我们寻找到真理,而真理必然值得热爱,一如作者在同一文章中说的,“语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态度,它是对学术、文本、语言的热爱,即对读书的热爱”。文中还创造性地指出陈寅恪先生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就是语文学的代名词。笔者对此完全赞同。“独立之精神”即语文学所采取的客观、公正的批判性态度,而“自由之思想”即是经由这一批判性路径之后所能探知的真理。
这本书的第二辑《藏传佛教》则是具体实践语文学的体现。《吐蕃僧诤背后的历史叙事》一文指出了“吐蕃僧诤”这一经典叙事事实上是较晚的历史建构。通过《禅定目炬》的研究,我们能发现禅宗即便在莲花生入藏之后依然在藏地多有流行。《从“大喜乐”和“演揲儿法”中还原历史》一文则是基于对藏传密教文献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庚申外史》等史料记载元代宫廷诸多荒淫之举一事其实都是对密教修法的误读。《“你看,我连这么恶心的东西都吃下去了,我成佛了!”》一文的题目虽然看上去荒诞无比,但内容却是对魏德迈《为密乘佛教正名》一书作出的扎实评论。这篇文章深入解释了魏德迈利用涵指符号学解释密乘佛教理论,说明了为何矛盾不堪的“恶心的东西”和“成佛”之间居然能够自洽。《玛吉阿米》一文则通过对仓央嘉措“情歌”的解读,指出“情歌”中出现的这位“情人玛吉阿米”就是被创造出来的传统,原语境中真正出现的那位“玛吉阿妈”不仅不是一位情人,而且还很可能指的是佛母,即所谓“情歌”其实很可能与法义相关,只是遭到了后人的误读。这一辑中的其他文章也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语文学作为一种“他乡”之态度,能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实实在在的启发。
《他乡甘露》的第四、第五辑虽然多是对学者及学术史的品评与追忆,但其中的心得也都紧扣着“他乡”的态度。如《大师的谬误与局限》一文指出了高罗佩先生《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的诸多错误。比如,高先生将“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一句翻译成The Emperor then summoned Indian monks to direct those ceremonies,明显是没有辨析出“司徒”为一官职名,而是将司徒这一官职的具体执掌写了出来。这必然也是一种语文学上的失误。
说来也巧,阅读这部分内容最让笔者有感触的实际是作者为“阿里王子”古格·次仁加布所作的悼文《阿里王子,你真的就走了吗?》。虽然在文章发表当时也读过这篇悼文,但只是惋惜一位学术巨擘过早的陨落。而现下在这本书里再读到时,更有感触的原因是笔者最近在撰写一篇与阿底峡传记相关的文章,而次仁加布先生曾有篇极重要的同一主题的文章《天喇嘛·意希沃非死于葛逻禄略考》(原文为藏文)。阿底峡在整个藏文化传统中被认为是肇始于后弘期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经典叙事中,古格的藏王意希沃不仅想方设法想请阿底峡这位高僧入藏弘法,还为此最终献出了生命。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的真实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遭到德国藏学家赫尔穆特·阿艾默(Helmut Eimer)的怀疑,次仁加布先生的文章则利用《娘氏教法史》与《弟吴教法史》等早期文献材料进一步证明了有关阿底峡的叙事大抵是一种后世的创造。笔者最近利用西夏文材料的研究则能够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在这段学术史中,最让笔者钦佩的是次仁加布先生作为阿里地区的藏族学者站出来挑战这一藏文化中最经典的叙事之一。假如没有“将故乡作为异乡”的觉悟,这一学术佳话就不可能发生。虽然作者并没提到这段学术史,但却写道,“阿里王子对本民族的学术传统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推崇理性、科学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这显然与我心中阿里王子的形象不谋而合。但我相信,次仁加布先生的批判精神绝非出于对故土的厌离,恰恰相反,这是出于对她真挚的热爱——热爱她,因此希望还原她的真相。
笔者的求学经历与沈教授类似,自十多年前走出国门以后,便游访美国、日本与欧洲,在全世界寻求自身学术的进步。刚刚踏上西洋之土地时,自然也是有种“将全世界作为故乡”的冲动。无论是西方学术的样貌,还是社会体系之情态,都让我钦慕兴奋不已。但走得久了,便也发现西方的种种不足——美国的学术天马行空,但时常缺乏扎实的文本根基;日本与欧洲的学术精雕细琢,但却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上略显不足。至于社会文化上的种种问题,则更是不必赘言。因此,当笔者真正将故乡当作异乡,将他乡也当作异乡看待时,反而能窥见真正具有意义的一些价值:我们需要人文精神,但这种人文精神必须是在坚实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的真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故乡走向他乡的第一步自然是痛苦的,但把全世界作为他乡则更具有挑战。笔者进入藏学之门径十几年,虽然学无所成,倒也确实尝到了“他乡甘露”带来的些许甘甜。如今《他乡甘露》的出版,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他“平生追求的是要做一个‘把整个世界都当作他乡的完人’”,相信能为更多人带来学术和人生上的养分。
(作者系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