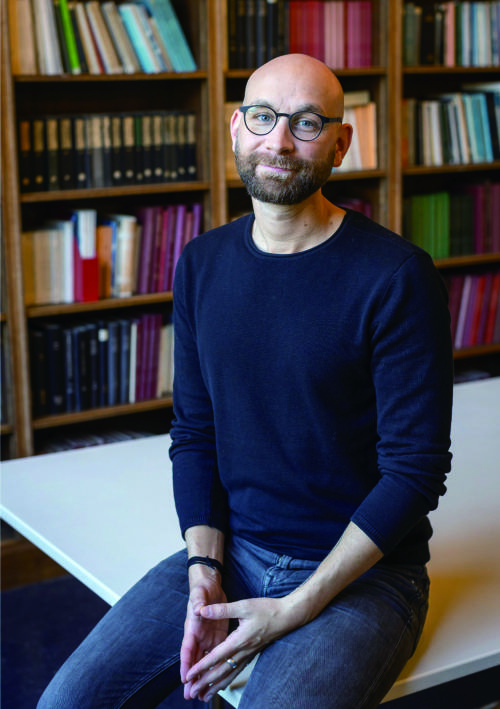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趋势似乎更倾向于验证性研究,而探索性研究则逐渐被边缘化。匈牙利罗兰大学元科学实验室教授巴拉兹·阿泽尔(Balazs Aczel)在一次心理学学术会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他发现提交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验证性工作,鲜少探索性研究。
■艾克·弗莱德(Eiko Fried)受访者\供图
在科学研究中,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是科研探索旅程中两个重要阶段。二者相辅相成,各自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定性的深度分析和定量的数据验证共同推进知识的边界不断扩展。围绕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的定义与区别、探索性研究被忽视的现状与原因、未来的应对方案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荷兰莱顿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艾克·弗莱德(Eiko Fried),他表示,该现象不仅影响了科研的全面性和创新性,还可能对科学发展的稳健性构成潜在威胁。
探索与验证相辅相成
“你可以这样想象探索性研究:研究人员进入尚未开发的荒野,他们四处走动,探索丛林、翻越高山、游过湖泊,其中一些人回来后报告:‘这个方向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弗莱德如此比喻探索性研究。
“科学研究的进程可简化为两个基本阶段:现象识别和理论建构。”弗莱德向记者介绍说,“首先是现象识别,即确定客观世界中稳定且反复出现的特征;其次是理论构建,通过理论框架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现象无需数据采集或统计分析即可直观感知,如人类具备语言能力;另一些现象则需通过数据挖掘才能揭示,例如吸烟与肺癌的关联,或女性抑郁症发病率较高。”
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分别对应两个科研阶段。探索性研究聚焦现象识别领域,要求研究者以系统化视角审视世界,敏锐捕捉潜在的研究线索。阿泽尔曾在文章中以探索儿童观看暴力影片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联为例,解释了何为探索性研究。他表示,研究人员会广泛收集信息,包括家庭背景、孩子的行为与性格、媒体内容等,结合理论知识多角度分析这些信息,挖掘潜在的规律。
验证性研究则侧重理论检验,通常基于现有理论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数据验证其有效性。弗莱德举例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即属经典验证性研究,该实验通过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预测并证实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最终助力研究者斩获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探索性研究可以提出假设,识别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型研究领域。验证性研究则具备假设检验优势,可对初步发现进行系统验证。沿用上述隐喻,“研究人员得出一个初步理论,整合资源、投入资金、周密规划,深入最初发现所在的那座山,开展系统性考察,最终确认那里确实有‘东西’,明确其真实性,精准描述特征,以及如何才能解释它。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这片学术‘无人区’将被纳入人类的知识版图”。弗莱德说。
总结来说,探索性研究始于具体的观察,深入剖析特定案例,提炼出可能的模式,其局限性为普遍性较弱。验证性研究则立足于既有的理论框架提出假设并验证。二者结合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偏差,有效提升理论的可信度、确保科学探索的严谨性。
探索性研究的价值被忽视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社会工作、教育和社区福利系教授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曾在其博文中论证了探索性研究的核心价值。他表示,研究不必受限于既定的理论框架,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都是在理论框架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开展的。“生物学在建立起正式的系统发育模型之前,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分类学和自然史研究;地质学在板块构造理论诞生前,岩石分布测绘早就开始了;在牛顿力学之前,人们就开始研究行星的运动等等。”探索性研究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和验证性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实证基础。这种论证方式既展现了探索性研究的历史传承性,也凸显了其在科学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然而可惜的是当前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性被忽视了。阿泽尔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大都将验证性研究作为主要工作,认为探索性研究“不值得发表”,当然这也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培训直接相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汉娜·柯林斯(Hanne Collins)研究发现,与验证性研究相比,研究人员认为探索性研究更有趣、更令人愉快,也更有动力进行,与更低的焦虑、沮丧和枯燥相一致的是,研究人员也会认为探索性研究科学性更低。因此随着验证性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人员可能会主观上避免开展探索性研究。
对于研究人员逐渐偏离探索性研究的趋势,弗莱德如此解读:他认为,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可重复性危机:诸多曾被视作稳定、可靠现象的研究发现最终无法复制,暴露其本质上的非稳健性。“这是因为本应从事探索性工作的研究者在完成‘荒野勘察’后,其研究报告偏离了客观描述。他们回来后没有说‘那里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而是说‘根据我的理论假设那里有东西,我找到了’。换句话说,研究人员明明在进行探索性工作,收集包含许多变量的数据集并将它们相关联,但在论文中将探索性发现包装成验证性成果,导致文献体系充斥大量假阳性结果,这些所谓‘现象’本质上缺乏稳定性,他们最初根本没有理论和假设支撑。”弗莱德说。
弗莱德也认同学界存在将“优秀科研等同于验证性研究”的认知偏差。他认为,期刊对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研究有明显的偏好,这促使研究人员将论文写成验证性研究(尽管其研究过程可能本质上属于探索性研究)。有学者呼吁期刊应该明确欢迎从事探索性研究的学者投稿,但弗莱德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强化学界对探索性研究价值的认知。
平衡创新与严谨
弗莱德认为,当前社会科学教育确实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假设检验训练体系,但探索性研究训练存在明显缺失,或也可理解为创新思维培养不足。弗莱德在采访中提到了生态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水生生态学和水质管理系教授马滕·谢弗(Marten Scheffer)的观点,谢弗将创新思维称为“科学思维中被遗忘的另一半”。他们都认同研究人员需要重新学习有助于激发联想思维的习惯,严谨的科学方法固然是去伪存真的基石,但当前教学体系过度侧重技术训练,忽视了最佳科研成果往往来自理性思维与创新联想的有机结合。弗莱德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考虑如何教导学生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他所属的莱顿青年学院近期联合谢弗教授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系统探讨创新思维培养路径,获得学者积极反馈。
探索性研究需要创新的同时,也要坚持科学的严谨性,但如预注册这样的传统标准可能会限制研究。柯林斯的研究也发现预注册会阻碍发现有趣但不符合假设的结果,因此在“维护探索自由”和“保护科学严谨”之间还需要更多平衡。对此,弗莱德与记者分享了近期与学生的一段对话,他说:“最近一名学生下课后跑来向我抱怨,为什么我布置了一篇这么‘烂’的论文给他们读。他解释说,这篇论文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没有进行预注册。我这里需要澄清一下,这篇论文其实是一篇十分优秀的探索性研究范例,不但分析了变量,还完整公开了原始数据。该学生认为预注册本身是一件好事因此要努力争取,甚至误认为预注册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反映了学界存在的认知偏差:将预注册等技术工具异化为目的本身,而非服务于捍卫开放科学价值(如透明性)的手段。”因此弗莱德认为,这些评判标准应具差异性,对于完整公开数据集,并如实报告变量关联的探索性研究,应持包容态度;反之,若研究者将本质为探索性的研究包装为验证性研究,且拒绝数据共享(当前心理学领域常见做法),则需引起学界高度警惕。
本报记者 练志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