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文文献浩如烟海,民族语文文献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珍贵资料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史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汉文文献是根基,民族语文文献是钥匙。运用民族史语文学方法把二者有机结合,则能实现新突破。在此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
“兜鍪”与“突厥”“突骑”
“兜鍪”即“胄”,指头盔。《说文解字》载:“兜,兜鍪,首铠也。”清段玉裁注:“古谓之胄,汉谓之兜鍪。”岑仲勉先生考证,兜鍪是指古代皮弁、高冠,哈萨克族旧式帽子之高冠,其方言称曰“土玛克”,“兜鍪”应为“土玛克”。对此说法,亦有史料可证。明代编修的《高昌馆杂字》中“罟

帽”一词的畏兀儿语为“土马哈卜儿克”。其中,“卜儿克”是冠、帽之义,而“土马哈”即土玛克。罟罟冠是古代北方民族贵族妇女头戴的高冠,尤其在金元时期盛行,其形状为以柳条或木条制成高约一二尺的高架,其上插羽毛,把高架固定在兜帽上。土马哈、土玛克即罟罟,表明古代兜鍪形状类似“罟罟冠”。
在汉文文献中,兜鍪亦作鞮瞀、鞮鍪、鞮鞪、兜牟等,这些不同的写法说明其为借词,而来自阿尔泰语中指高帽的“土马哈”说应属实。汉语翻译的“兜鍪”二字,不仅跟原词读音相同,也充分考虑了所选汉字的意思与原词词义的一致性。“兜”字之义为口袋、包裹,用于头部则指兜帽、兜巾等;“鍪”即古代炊器,与头盔形状相似。可见,“兜鍪”二字汉语本义也可指兜帽、头盔等,与古汉语“胄”“首铠”同义。
根据汉文文献记载,“突厥”号本义为“兜鍪”。《周书·突厥传》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突厥”是部落或政权之号,尤其在建立政权后,“突厥”二字在汉文文献中基本固定,未见其他写法。不过,此号用于本义“兜鍪”时,也应该用其他汉字记录。《南史·邓至国传》载:“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其俗呼帽曰突何。”“突何”词义为帽,这与“突厥”号本义为“兜鍪”说吻合。
国外学者从语言学视角把“突厥”号词义解释为力量、气力、出生、法律等。这些说法是由分析“突厥”号之原词türk或türük而得,属于语言学、词源学的解读。但这没有解释清楚汉文文献明确记载的“突厥”词义为“兜鍪”说,可能国外学者对汉文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有所怀疑。
其实,汉文文献的记载真实可靠,尤其在探索民族语言名号时,更是基础史料依据。《周书》是系统记载突厥的第一手史料。《周书》所记“突厥”号本义为“兜鍪”便是典型例子。中原更深入了解突厥是在唐初,唐朝平定突厥汗国,内迁突厥降民,又把部分突厥贵族迁至长安,充任官员和侍卫。因此,唐初大臣可以与突厥贵族当面交流,完全可以从突厥人那里核实之前史文所记“突厥”号的含义,也不排除唐初才得知此号本义的可能。总之,汉文文献保存的“突厥”号本义为“兜鍪”说,应源于突厥人的自解,其史料价值极高。
“突厥”号之原词为türük,词根tür-意为堆积、收集、包裹、聚合等。此意用于人的头部,指束发、盘发或保护头部的盔、帽等。这正与汉文文献所记兜鍪或帽说吻合。那么,词义为兜鍪的“突厥”号,为何成为部落之名呢?汉文文献的解答是源自山名即“金山形似兜鍪”。北方民族名源自山名是汉文文献常见的解释。如乌桓来自乌桓山、鲜卑来自鲜卑山、贺兰来自贺兰山等。中原史家这种惯用表述,应是结合民族词汇语义与部落肇兴之地,加工创作的起源。其中关于部称语义和起源地的信息自有所本。
兜鍪(突厥)为部落名,从字面意义解读,就是因其俗戴兜鍪。还有一种引申解读,就是“兜鍪”亦代指骑士、勇士。汉文文献有“突骑帽”之例可作旁证。《隋书·礼仪志》载:“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突骑帽“垂裙覆带”,类似风帽、长裙帽。唐颜师古《汉书》注把“突骑”解释为“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唐人据汉语词义,把“突骑”释作精锐骑兵。除此之外,“突骑”也有可能是借自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兼顾音义的汉字译写。历史上有“突骑施”部,其名音译于

一词。其中,“突骑”对应türgi,词根为tür-,这与“突厥”号词根同。所以,“突骑”也有可能与“突厥”一样,本义为“兜鍪”,而翻译记录时选用的汉字亦为音义兼顾。
无论如何,作为部名的“突厥”号本义为“兜鍪”,汉文文献记载确凿无误。
“驳”与“贺兰”“银川”
《说文解字》载:“驳,马色不纯。”“驳”字平常用于马的毛色,是指两种颜色掺杂,且一般是白色掺杂于其他颜色中,如青白马、红沙马等。但“驳”字在古汉语中亦指树皮,一般指梓榆树。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驳似马之驳者。”由此得知,汉语指称梓榆树皮的“驳”字也是由驳马毛色而来,属于比喻词。
汉语的“驳”,突厥语作“贺兰”,今“贺兰山”山名,还有历史上的“贺兰部”号,其本义源自“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兰山”条有“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的说法。这说明,唐人将突厥语的“贺兰”与汉语的“驳”对应翻译。杜佑《通典》说:“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同书记载突厥官号时又说“谓(驳)马为贺兰”。据此可知,“曷剌”“贺兰”都是突厥语,其汉字义为“驳”。
“贺兰”是突厥语ala(蒙古语alaγ)的音译。在文献中尚未发现贺兰山名的突厥语写法,但在蒙古语文献中把贺兰山称作“阿剌筛”“阿剌黑山”以及今天的“阿拉善”等。可知,其山名本义就是“驳”。突厥语ala,亦可读作hala,所以汉语译写时选用了“贺兰”二字。历史上的“贺兰”和“延陀”部,都是音译自突厥语hala-yundluγ之名(其中hala为“驳”、yund为“马”、词缀-luγ为“有”之义)。hala-yundluγ部,汉语意译为“有驳马之部”即汉文文献所记“驳马”部,而把此号之前半部hala音译为“贺兰”,后半部yund音译为“延陀”。汉文文献中的不同译写,实则为一部。
位于贺兰山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之名,也与驳马有关。唐代银州与今银川不同地,但需要由此梳理“银”字地名由来。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银州条”,银州、银川之名是因“旧有人牧骢马于此谷”,而“虏语骢马为乞银”,骢马即驳马。所谓的“虏语”当指羌语或鲜卑语。古银川地名之“银”,当源自胡语“乞银”,取义“骢马”。突厥语

词义为“斑白、银色”等,与“乞银”二字的古音相似,“虏语骢马为乞银”说确凿无误。汉语翻译时选用“银”字,与欲表达其原词本义斑白或银色不无关系。
又据文献记载,今银川市本名为“饮汗城”,古蒙古语则称作“额里合牙”“亦儿该”等,其亦为驳马之义。银川在唐代为灵州怀远县,《元和郡县图志》述其沿革:“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元朝秘史》中的地名“额里合牙”,汉语翻译为“宁夏”(今银川市)。《马可波罗行纪》也记载贺兰山下有Egrigaia(额里合牙)之地。实际上,“额里合牙”来自党项语

,义为驳马。蒙古语读作eriqaya,再按汉语读音翻译而成。文献中的汉字音写饮汗、亦儿该等也是额里合牙的变异体。
今天的银川,在元明时期被称作“宁夏”。从明末清初开始,在文人著作中使用“银川”之名,并以此比喻贺兰山下的黄河及灌溉区美景。可见,“银川”之名有民族语言交融文化底蕴,亦含赞美“塞上江南”美景诗意,是历史文化和抒情诗意完美结合的地名。
“桃花石”与“皇”
“桃花石”之名指中国,其音译于

一词。虽然学术界把“桃花石”与“拓跋”等同,但很多疑问仍然解释不清。根据汉文文献记载,“桃花石”号之真正内涵为“汉”“秦”。《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铁围山丛谈》《游宦纪闻》中保存的于阗国表,将宋朝称为“条贯主阿舅大官家”。黄时鉴先生指出,“条贯主”即《宋史·于阗传》文字“汉家阿舅大官家”中的“汉家”。在古代,国外称呼中国的名号有三,即秦、契丹和桃花石。中亚人马卫集在《动物与自然属性》一书中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即秦、契丹和回鹘,其中秦的地域最大。马卫集又听说,中国的京城叫扬州,流经该城的一条大河将它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国王被叫作桃花石汗,又号称为法格富尔。据此可知,“桃花石”应指当时的中国中原王朝。学术界指出,“法格富尔”词义为“天子”。与其对应的“桃花石汗”指“皇帝”,可能是宋朝皇帝。这是“桃花石”等同于“秦”的实证。
11世纪成书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里说得更具体:桃花石,“马秦”国之名。这个国家距秦有四个月的路程。秦原来分作三部:第一,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为桃花石;第二,中秦,被称为契丹;第三,下秦,被称为巴尔罕,这就在喀什噶尔。但是,现在认为桃花石就是马秦,契丹就是秦。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是指在东方的“马秦”,与契丹并存,是宋朝无疑。“马秦”之“马”义为“大”,而这里有原来、真正、旧有等意,指原来的、真正的“秦”。《突厥语大词典》又说,桃花石汗“有‘古老强大之国的可汗’之意”。马苏第的《黄金草原》也记载:“中国中原皇帝从其臣民那获得了‘贝格布尔’(Baghhur)的荣誉尊号,也就是‘天子’。然而,中国中原君主们的特殊尊号和在与他们讲话时对他们的称呼则是‘桃花石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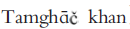
),而不是‘天子’。”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汗”与“天子”对应,确实是指“皇帝”。
更为准确理解的话,“桃花石”词义即“皇”。《说文解字》解释“皇”字:“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皇”字义为“大”,“桃花石”本义即此。突厥和中亚人以桃花石指代中国,是因中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其中皇帝即天子是最高权力的代表。粟特语中把中国称为“天子国”,与天子对称的皇帝代指中国也实属正常,即可作“桃花石国”。可见,“桃花石”之称蕴含着悠久且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
总之,汉文文献中保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名号、释义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汉文所记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有些是音义兼顾,其中蕴含着各民族语言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文化交流互鉴发展的结晶。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语言与古代民族语言具有传承关系,具有解读古代民族语文文献的优越条件,这是国外无法比拟的优势。把汉文和民族语文文献加以结合,更能深入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底色,全面、客观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历史。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突厥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研究员)
 帽”一词的畏兀儿语为“土马哈卜儿克”。其中,“卜儿克”是冠、帽之义,而“土马哈”即土玛克。罟罟冠是古代北方民族贵族妇女头戴的高冠,尤其在金元时期盛行,其形状为以柳条或木条制成高约一二尺的高架,其上插羽毛,把高架固定在兜帽上。土马哈、土玛克即罟罟,表明古代兜鍪形状类似“罟罟冠”。
帽”一词的畏兀儿语为“土马哈卜儿克”。其中,“卜儿克”是冠、帽之义,而“土马哈”即土玛克。罟罟冠是古代北方民族贵族妇女头戴的高冠,尤其在金元时期盛行,其形状为以柳条或木条制成高约一二尺的高架,其上插羽毛,把高架固定在兜帽上。土马哈、土玛克即罟罟,表明古代兜鍪形状类似“罟罟冠”。 一词。其中,“突骑”对应türgi,词根为tür-,这与“突厥”号词根同。所以,“突骑”也有可能与“突厥”一样,本义为“兜鍪”,而翻译记录时选用的汉字亦为音义兼顾。
一词。其中,“突骑”对应türgi,词根为tür-,这与“突厥”号词根同。所以,“突骑”也有可能与“突厥”一样,本义为“兜鍪”,而翻译记录时选用的汉字亦为音义兼顾。 词义为“斑白、银色”等,与“乞银”二字的古音相似,“虏语骢马为乞银”说确凿无误。汉语翻译时选用“银”字,与欲表达其原词本义斑白或银色不无关系。
词义为“斑白、银色”等,与“乞银”二字的古音相似,“虏语骢马为乞银”说确凿无误。汉语翻译时选用“银”字,与欲表达其原词本义斑白或银色不无关系。 ,义为驳马。蒙古语读作eriqaya,再按汉语读音翻译而成。文献中的汉字音写饮汗、亦儿该等也是额里合牙的变异体。
,义为驳马。蒙古语读作eriqaya,再按汉语读音翻译而成。文献中的汉字音写饮汗、亦儿该等也是额里合牙的变异体。 一词。虽然学术界把“桃花石”与“拓跋”等同,但很多疑问仍然解释不清。根据汉文文献记载,“桃花石”号之真正内涵为“汉”“秦”。《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铁围山丛谈》《游宦纪闻》中保存的于阗国表,将宋朝称为“条贯主阿舅大官家”。黄时鉴先生指出,“条贯主”即《宋史·于阗传》文字“汉家阿舅大官家”中的“汉家”。在古代,国外称呼中国的名号有三,即秦、契丹和桃花石。中亚人马卫集在《动物与自然属性》一书中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即秦、契丹和回鹘,其中秦的地域最大。马卫集又听说,中国的京城叫扬州,流经该城的一条大河将它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国王被叫作桃花石汗,又号称为法格富尔。据此可知,“桃花石”应指当时的中国中原王朝。学术界指出,“法格富尔”词义为“天子”。与其对应的“桃花石汗”指“皇帝”,可能是宋朝皇帝。这是“桃花石”等同于“秦”的实证。
一词。虽然学术界把“桃花石”与“拓跋”等同,但很多疑问仍然解释不清。根据汉文文献记载,“桃花石”号之真正内涵为“汉”“秦”。《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铁围山丛谈》《游宦纪闻》中保存的于阗国表,将宋朝称为“条贯主阿舅大官家”。黄时鉴先生指出,“条贯主”即《宋史·于阗传》文字“汉家阿舅大官家”中的“汉家”。在古代,国外称呼中国的名号有三,即秦、契丹和桃花石。中亚人马卫集在《动物与自然属性》一书中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即秦、契丹和回鹘,其中秦的地域最大。马卫集又听说,中国的京城叫扬州,流经该城的一条大河将它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国王被叫作桃花石汗,又号称为法格富尔。据此可知,“桃花石”应指当时的中国中原王朝。学术界指出,“法格富尔”词义为“天子”。与其对应的“桃花石汗”指“皇帝”,可能是宋朝皇帝。这是“桃花石”等同于“秦”的实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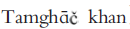 ),而不是‘天子’。”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汗”与“天子”对应,确实是指“皇帝”。
),而不是‘天子’。”这里明确说“桃花石汗”与“天子”对应,确实是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