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安乐哲(Roger T. Ames)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研究与传播,成果颇丰,在中西哲学界与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有助于将中西比较哲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让西方主流哲学界逐步走近中国古典哲学并感知其深刻意蕴,使中国哲学典籍充分产生世界性影响。因对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传播的卓越贡献,安乐哲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孔子文化奖”等诸多奖项。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安乐哲。访谈中,安乐哲与记者畅谈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西哲学对比、中国典籍翻译、儒家思想等主题的独到见解。安乐哲认为,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古典哲学存在诸多误解。令人颇感欣慰的是,这一学术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注意,并正在以一种良性的方式得到纠正。如今,中国古典文明的哲学层面受到广泛关注,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因子和丰厚思想价值引发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探究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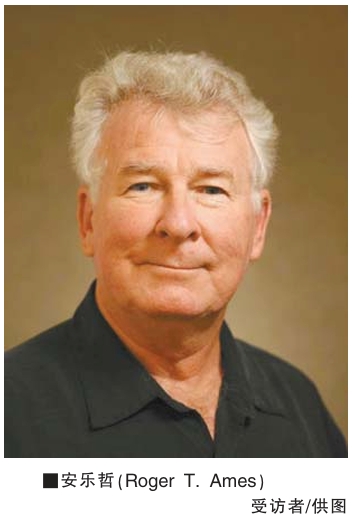
“偏差现象”造成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言,长期以来,中国的古典传统包括哲学传统曾经被置于不属于自身话语的历史背景之下。您曾对此表示过忧虑,并认为中国古典哲学应当用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呈现。请您谈谈这一点。
安乐哲:我的确曾经表达过这一观点。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书稿完成。在这一著作的影响下,耶稣会传教士和天主教徒陆续从欧洲来到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逐渐被翻译为拉丁文等西方语言,对欧洲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中国古典哲学被带入欧洲哲学界并传播至整个西方学界之初,所使用的术语表达,即在西方语言体系中对应的中国哲学词汇,未能充分体现中国古典哲学本身的含义与意蕴。
利玛窦、理雅各等传教士和教徒来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与中国典籍介绍和传播给西方学界的初始动机,是试图填平两个古典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缩小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距离。然而,他们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事实上是“强调西方文化重要性”的一种改写,而非呈现中国自身的文化特征。
遗憾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偏差现象”不仅至今仍然存在,有时还在近些年的典籍传播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强化。当我们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拉丁文版和英文版时,会发现西方语言的框架、概念和术语“重新定义”了一些古典文本。这种语言的应用被视为对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明的某种理论化或概念化,但仍未准确而恰当地映射出中国古典哲学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西方理解中国典籍的语义框架根植于一套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学术体系之中,从而造成了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扭曲。
19世纪下半叶起,在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性议题被进一步植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亦即西方现代化的所谓“科学理性”通过语言传播,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被“空运”过来并潜入亚洲学术体系之中。今天我想表达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未来也希望利用更多机会对此作进一步分析。我认为,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古典哲学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我在多个国际场合说过,中国古典哲学需要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以自己的方式发声。我也试图对西方所诠释的中国古典哲学包括伦理学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希望中国古典哲学能够用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呈现。我听闻目前中国正在建构自主的古典哲学知识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事项。
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对甲骨文等中国早期文字的深刻认知。借助甲骨文,我们可以抚今追昔。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国古人和祖先对话的方式,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传承早期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国古典哲学知识也出现在甲骨文记载中,例如,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甲骨藏品涉及不少中国古典哲学知识。20世纪,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荆门郭店村等地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知历史遗迹。郭店楚简提到了《易》,并将《易》与儒家其他五经并列。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授课的时候,我与硕博研究生们一起讨论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他们在自己撰写的论文中,也多次提及中国考古发现所涉及的古典哲学知识。
以“阐释域境”视角还原中国古典哲学真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典籍翻译需要运用“阐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的视角。可否进一步诠释您的这一观点?
安乐哲:“阐释域境”需要把文本放置到它原有的时间和域境中。要理解这些文本,就要尽最大努力将自己的想象力与文本本身相关联,将文本置于其所处的上下文语境之中。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实际上,西方的中国学学者理雅各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并未把中国古典哲学文本放置在它本来应有的文化土壤中。这造成的结果是,《道德经》在西方语言体系中被与柏拉图以后的西方文化传统相关联。举个具体的例子,阿瑟·韦利将《道德经》翻译为《道及其力量》(The Way and Its Power),并在文本中将其与“上帝的模式”联系起来。“道”被理解为上帝的“道”,力量被理解为上帝的创造力。当许多西方学者提及力量的时候,他们将所有创造力来源的可能性都与上帝相关联。上帝被视为真理和美的唯一来源。
直到20世纪,西方古典哲学都带有浓厚的神学性和宗教性。上帝、理性、绝对精神、基督教精神等,成为西方古典哲学体系中的关键词。而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的说法,人类并非上帝的产物,而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并参与到生生不息的宇宙运行过程中。正如《易经》所阐述的那样,人类与生存的外部空间达成了富有成效的协作共生关系。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与地分不开,天与地相感应。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曾言,中国智慧无需上帝的观念。对于中国宇宙论而言,万物互为依存、相互转化,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本源之点。
然而,由于未能从“阐释域境”的视角去还原和审视中国古典哲学的真面貌,中国古典哲学被打上了与西方古典哲学相近的神学性和宗教性烙印。如果去一些西方国家图书馆寻找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书籍,我们会看到,这些书不是被放置在哲学区域,不是与黑格尔、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书籍摆放在一起,而是在东方宗教学区域。
这种文化差异也导致了翻译偏差。在现今西方学界流传的中国典籍译文中,普遍将“天”翻译为“heaven”、“义”翻译为“righteousness”、“礼”翻译为“rites”、“仁”翻译为“benevolence”。这些中国古典哲学术语的翻译不是完全准确,也并非十分达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讨论的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有所不同。国际儒学研究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信广来(Kwong-loi Shun)近期在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许多不对称之处,这种不对称很多时候是由翻译偏差造成的。
当然,无论何时,在两种语言之间穿梭,很难做到游刃有余、绝对精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在谈到“完美词典的谬误”时表示,两种语言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等。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言,“我的语言之局限就是我的世界之局限”。我们会发现,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翻译中国典籍的。比如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英国伦理学家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方法论。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有关人的本性方面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与巴特勒的主张相近。
儒家“角色伦理”注重人的多重特殊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撰写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一书是一部中西比较哲学力作,著作出版后颇受国际中国学学者欢迎。可否介绍一下您著述该书的初衷,并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谈谈您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与认识?
安乐哲:几年前,我写了《儒家角色伦理学》这本书,写作该书的初衷是阐述儒家“角色伦理”中的“关系”这一关键词。我一直认为,人活于世,并不只是肉体意义上的一个生命。人类的一切行为,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毋庸置疑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关系”。儒家“角色伦理”尤为注重人的多重特殊角色;多重特殊角色成为约定俗成的各种关系样态,呈现为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多向互动。
在儒家思想中,这些特殊角色具有很强的“指征性”,象征着多种规范意义。家、国之繁荣兴旺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特殊角色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人皆为社会性产物,深受与我们互动的他人的影响。这也是中西方绝大多数派别的哲学家广泛认同的观点。不过,在西方古代文明与现代话语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人“自我意志”才是一切事务的决定因素。“自我意志”即人具有的采取目的性行为的能力以及自我作为的能力,决定人类的意义、尊严、人格与价值。这种观点将人的社会性边缘化,并认为,就本体论层面而言,社会自身不可能存在有很大意义的价值,因为我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在严格意义上讲是偶然性的,而我们束手无策。
然而,这种“自由意志”观点在西方的盛行,可以说对现代道德和政治哲学造成了恶劣影响,使得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极端自由主义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为了实现个人自由,对任何对个人自由有阻碍的正义观念,都以“不道德”的名义加以拒斥。这种倾向为某种放任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幌子,正在迅速催生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贫富不均、环境恶化等问题。应当说,“自由意志”的概念是有害的,本质上是一种对西方知识分子意识的垄断与控制。如今,西方社会存在的保守派、自由派、社群主义者等,都深受这一概念的影响。
与“自由意志”形成对比的是,儒家思想并非一套外在的、以个人利益为终极意义的原则,而是提倡一种有赖于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互动等多重关系的价值观,这是成就“仁”的关系的核心。儒家思想中包含一种敬畏自然且志存高远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与人类的平凡经验、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儒家思想中一些有关“共享”“和谐”的概念,可谓对角色和关系的最好阐释。根植在这种“关系”之中的原则,要求个人持续培养一种富有道德感的意识,使人致力于追求既利己又利他的人生境界,从而处理好自己所扮演的多重身份角色与各种关系,在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同时达到济世、济国的最高目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论语》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里的“道”指“道义”。孔子一向认为,道义是可以传承的。“人能弘道”即人可以提升自身修养,传播道义,将“道”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同时,通过弘扬“道”的这种行为,人们自身也能达到一种与世和谐的状态,使自己的心灵完满且宁静,当然也能使自己达成人生的成功。然而,“非道弘人”,道义不能让人的品质直接拔高。如果一个人想通过“道”来彰显自己、名扬万里,那就是在利用“道”装点自己,并非真的在“修道”。那么,最终的“弘道”目的也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