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迈进,除了生产力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外,国际交往的作用也同样重要。总结国家间交往互动的有益经验,提取历史上那些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效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最近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一书,以本土资源从东方视角对“西方中心论”加以解构,提出许多新思考,通过构建东方外交史研究体系的理论框架,体现出作者在东方国家崛起的背景下对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的基本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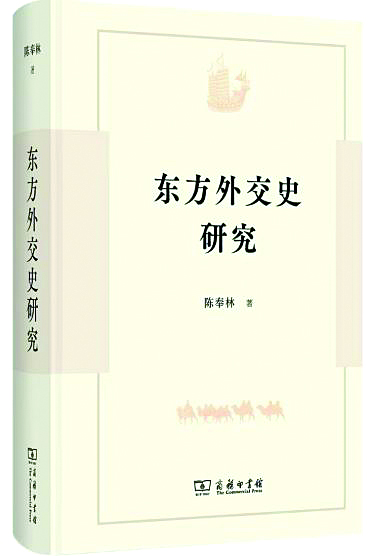
■《东方外交史研究》,陈奉林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东方”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中被广泛使用。一般认为,它是指地中海以东的亚洲地区(习惯上也包括埃及,把北非埃及纳入东方研究的视野是东方学的历史传统)。西方对东方的真正了解是在东西方交流扩大之后。长期以来,“东方”作为一个地理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被研究者广泛使用。我国学者鄂裕绵编著的《近代远东外交史》、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撰写的《古代东方史》、日本学者定金右源二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的再建》都有所涉及,但他们构建的体系研究范围狭小,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近代以前东方存在完整、独立的经济—文化圈和交往圈,说到底就是没有解决好体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建立东方学术研究的话语权问题,并付出了巨大努力,改变了中国在国际学术上无话语权的被动局面。
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不仅有新材料、新理论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打破了外交史研究的许多禁区,在国别外交史、双边外交史、专题外交史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必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将国别外交史、双边外交史、专门外交史和外交史材料汇编整合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外交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符合历史实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因此,完整地反映东方外交史的关键是东方学者要置身其中,发挥主体作用,根据历史实际与社会需要撰写历史。只有深入到东方历史中才能发现其联系的纽带和动力源泉,只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东方外交史。
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反思,如何发挥东方学者的长处和东方古籍材料的优势,重视使用考古发掘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摆脱世界史编写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都是作者在此书中考虑的重点。为此,《东方外交史研究》一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这里略举数端,予以评介。
第一,关于东方外交史的上限问题。该书提出了以东方国家进入封建时代作为外交史的上限,看到封建时代较以前时代创造了国家关系新形态,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关系体系的核心力量,不同于以前时代以掠夺奴隶、土地、水源和人口为目标的军事争霸活动。在东方近代外交史开端上,作者提出以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作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第二,关于应用理论。该书强调要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与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果有选择地吸收利用,经过抛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我国的治史实践。第三,关于东方古代社会是否停滞与内部封闭循环问题。该书倡导以发展的观点观察东方社会及其变迁。可以说,这些都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在理论上的新考虑,也是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可贵努力。
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基本构建素材的崭新趋势。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和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方法。为此,作者回顾以往的编纂实践,对东方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外交史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与思考,使用本土材料,既注意到各国交往的纵向发展,也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发展和联系,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新体系。作者强调对于不可忽视的西方研究成果要有选择地借鉴与吸收,但不能作为评判和裁剪东方历史的标准,在借鉴与反思中做到中国视角与世界视角的统一。作者认为,应该根据东方人的史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作者能够正确看待历史上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东方社会,不同意西方一些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把古代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看作停滞的和不发展的谬误,摒弃陈旧的王朝循环史观和落后的亚洲观,提出了编写东方外交史的五个原则,即地域原则、整体原则、发展原则、联系原则和综合原则。旧的外交史在取材范围、应用理论、材料的收集与使用以及史观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许多方面显得陈旧过时,不能为今天的社会提供具有新鲜活力的理论支持。长期以来,西方人撰写的外交史居多,在使用的材料与关注的重点上都以欧洲事务为中心,很少关注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或者将东方外交作为西方外交依附性的点缀,忽视了东方各国的首创精神。作者认为,西方学者探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大多数人是以欧美发展理论作为参照系,以进化论的线性发展模式作为分析框架的,对于东方社会内部发展机制、动力源泉、联系纽带、崛起的历史文化根源等方面的探讨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撰写一部中国的东方外交史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欧美国家学者习惯上把东方外交史看作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在取材范围、使用的材料、关注的重点以及史观上都存在重大缺陷,不能真正地反映东方国家的历史实际。在中国,以往的外交史基本属于“无所不包”的中外交通史或东西交通史范畴,把外交史从中外交通史中独立出来,从复杂众多的历史材料当中理出头绪,进行艰辛的修史工作,需要十分的耐心与百倍的努力。东方外交史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编纂体系与史学理论,不仅要把东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史以及发生在亚洲历史上那些重大而有意义的外交事件梳理出来,而且还要在理论的高度上把亚洲国家外交思想与理念总结出来,加以系统阐释,构建起东方国家自身的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这更是一件艰辛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东方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疏于对这些外交思想作系统的总结与理论升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外交史话语体系,就必须努力构建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与分析模式,作出顶层设计。有学者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思路缜密开阔,观点敏锐独特,将东方外交史与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整合成一体进行综合研究,开辟出一个崭新的领域。”(序二)但是,这部著作也存在自己的不足以至缺陷,如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外交史关注较多,对西亚地区国家外交史关注较少,出现畸重畸轻的情况,也说明在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诚恳地希望作者将来再版时能补上这一不足,把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做得更好。任何一部著作都是在探索中向前迈进的,留下探索者的劳绩与时代痕迹。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