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甘露,1959年出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史馆馆员。著有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呼吸》,中短篇小说集《时间玩偶》,随笔集《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时光硬币的两面》,访谈录《被折叠的时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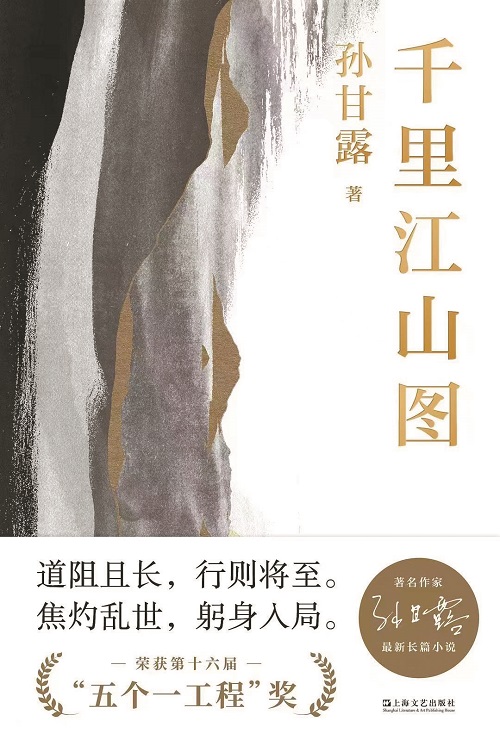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大约二十年前,也就是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有次董乐山先生路过上海,由陆灏先生引荐,我们去和董先生见面,因此机缘得识《鬼作家》的译者。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菲利普罗斯的《垂死的肉身》中文版时,约我写篇序言,便斗胆应承了下来,在短文的篇首还记述了此事。今天看来,这篇题为《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的短文,未尝不可再读,但是,以我这样一个晚熟之人,当年强解老年罗斯的情感羁绊之作,不说完全不得要领,今日重温,令我颇为错愕:
“对男人来说老年是一场意外。”
“胆小的人无法面对老年。”
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人们当然知道这些话出自哪里,而我仿佛直到今天第一次读到这些话的那一刻,才忽然意识到,我曾经评论过的“年龄的伤痕”究竟是什么。
是当你自己,一个写作者,也迈入了老年?来到了我在《〈小团圆〉中的“小物件”》里谈论过的所谓“晚期风格”?还是如同所有小说一样,天然地隐含着一个回望的视角,在所有的叙事中不停地被提示?也因此不断地被强化?如同老年人伴随着衰退的感觉不断地陷入模糊不清的往事,因此使人更强烈地试图复原旧貌?或者相反,不断地对自己说,放手吧。或者,米沃什后期的一个重要主题“衰老”,是人生“更远的地方”?
总之,不像年轻的叙述者那么摇曳多姿,它甚至是沉郁的,也许是凝神静气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写作的意义上展开的。包含了身体的认识,而不仅限于此。
或者,像卡尔维诺所说,你需要把一个地方变成你的“内部风景”,你的想象居住于此,把它变成你的剧场?
它不仅仅是指你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看待外部世界,而是如何不断地把你曾经忽略的部分纳入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察中去。不是在画布上不断涂抹,增加新的笔触,覆盖调整本来的面貌,而是像修枝嫁接那样,使用现实世界的材料而加入你的想象,使既有的世界,因为讲述获得新的可能性。
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正是这样一段不断被讲述、不断被发掘、不断被研究所形塑的历史,那些杰出人物的思想、风华绝代的形象、错综回旋的思潮、隐秘复杂的世事,如同漫长的中国历史一样,还将被继续讲述、塑造。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塑造着你的经验,它被不同的人不断地讲述,一点一滴地影响着你。但是,就像我曾经在一次采访时说到的,它如同我们的爱人,她有一个名字,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是她也有一个只有你才会那么称呼她的名字。她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她因为你的讲述才得以存在的一面。
所有那些个别的、独一的、隐秘的,讲述和召唤,最终能否会汇聚在一起,即使彼此冲突,也趋向于那个复杂多面的上海?
就像人们常说的,事物只有被恰当地讲述出来,它才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