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志军,1955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海底隧道》《潮退无声》《无岸的海》《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雪山大地》。作品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当代》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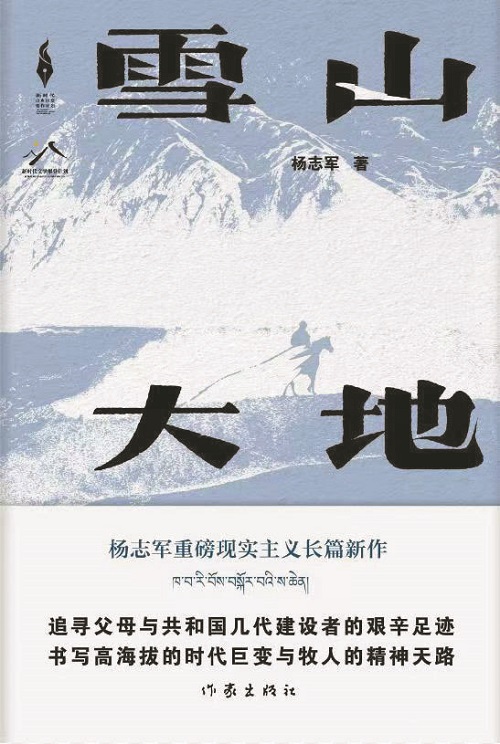
《雪山大地》,杨志军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我出生在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西宁市,我的父亲在少年时离开河南老家外出求学,从西北大学毕业后一路西进定居青海,生命奉献于这片高原,终身未再回到老家。我的母亲是1949年后国家培养的第一代青海本地医生,70多岁仍然服务于患者,90岁还在关心民族的医疗发展。他们终其一生知行合一的生命存在,是我为人为文的生命准则,而我诞生的这片雪域高原,在生命之初就给了我雪山大地的深恩厚养。从肉体到情感及精神,青藏高原都是我的血亲。
古称西平郡、青唐城的青海省西宁市,古为羌地,坐落在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湟水流域的河湟谷地,古“丝绸之路”青海道亦沿湟水上溯,经西宁而至河西走廊。老西宁四周有因历代战乱围城而筑的老城墙,那些老城墙,历史短的有300多年,长的有1000多年,我家就在城墙边上。20世纪60年代,我和一帮孩子在古城墙上玩石头仗的游戏,守城与攻城双方你追我撵,仿佛奔跑在吹拂了1000多年的连天烽火中。夕阳下,西宁城安详寂寥,淡金色的余晖照着城市平房的屋顶、街道小巷,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驶过,城市更加静谧,那时的西宁城市不大,城墙外围是连绵的山峦,山上终年不长树和草,裸露的山体上是粗粝的沙石,风一吹,满目苍黄。多年后我回望历史,看到我们小时候爬过的城墙都没有了,在南面偏远的地方,还保留了一点点城墙,现在被围起来变成了一个公园,留下的那一截其实就是个比较长的小土堆而已。如今,在西宁北大街的最北端修复保存了一座城墙的城门遗迹北门城楼,古称“拱辰门”,在历年的损毁与复原之后,诉说着昔日晚照的记忆,这座城楼与我和父母早年居住的青海省委大院仅一条马路之隔,是我孩提时奔跑的第一座城墙。我那时并不知晓历史的风在耳边呼啸,我正穿过烽烟四野、旌旗猎猎的古战场,但命运已在我和一群孩子手握取自城墙的石头抛掷时,触摸到了石头的温度与呼吸,在自己的身体里种下了苍阔与强健的种子。
小时候我的很多快乐来自于父母因工作接触的草原牧人,他们来西宁看病,住在我家,带来牧区特有的奶皮子、酥油等,这是那个困难时期难得的吃食。我喜欢这些醇厚朴实的人,也喜欢跟随他们去草原骑马、与牧狗赛跑、跟孩子学藏式摔跤、找羊羔、牵牦牛……我梦里的故乡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站在一顶黑色牛毛褐子缝制的帐房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我原该是一个在草原星空下穿着光板羊皮袍的马背上的骑手,带着藏獒追撵失群的牛羊,抱着羊羔睡觉,嚼着风干肉呼啸草原的牧人啊!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我,我们是游牧民的后代,祖先曾是驰马如风的蒙古人,我们都是流落在外的游子,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一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多年后才知道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我们终归是回到故乡了吗?草原唤醒了我血液中蒙古后裔的野性与自由的天性,大自然令我震惊不已,苍茫雄阔、辽远无边的荒原,在我还无意识像成人一样思考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了我的身体。从草原回来后,我常常会陷落在动物与植物的迷思里,城市的空旷加剧了我的热望,我用各种办法弄来草原鼢鼠、斑头雁的雏鸟、红嘴鸦、松鼠、兔子、鸽子、百灵鸟、鱼蚕、狗、藏獒养育,这也为我最早意识到生态问题埋下了伏笔,日后我作品中数十种动物以及植物的描写,都可以溯源到此时的草原记忆。我热爱草原,那雪山大地的全部生活都在告诉我,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我的一触及藏地就永不会枯竭的写作,源于单纯而辛劳的游牧,源于我天性里的藏式人格,青藏高原是我生命写作和精神流浪的根柢。
青藏高原有最蓝的天,那种一碧如洗的明亮与蔚蓝,而且各处的蓝也不尽相同:青南高原晶亮华丽的蓝,柴达木荒原遥远永久的蓝,藏北草原祥和亲切的蓝,雅鲁藏布江河谷平原茫无际涯的蓝……天上的蓝与青海湖、纳木湖、奇林湖等高原大湖的蓝交相辉映、水天一色。在青藏高原有高极之山、大极之川,祁连山、布尔汗布达山、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阿尔金山……每一座山脉都是人类没有穷尽的未知区域。格拉丹东冰川、阿尼玛卿冰川、年宝玉则冰川等多条冰川构成青藏高原的盛极之水,水从山峰极顶流淌出来,是三江源的源头,也是其他河流的发源:长江发源于格拉丹东冰川,黄河与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雪山,澜沧江与怒江发源于唐古拉山,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冈底斯山。这些水源之山都是在人文经典和社会意识中取得了崇高地位的山,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青藏高原有阔极之原,山和原不分,行走在茫无际涯的原野上,即是行走在高入云天的山顶上,大山大到极限就是原,高原高到绝处就是山。在这样高寒的雪山大地上,野生动植物的生命力却异常顽强,有很多珍稀物种或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例如藏羚羊、黑颈鹤、普氏原羚、藏原羚、藏野驴、岩羊、野牦牛、野驴、盘羊、雪豹、喜马拉雅旱獭、白唇鹿、荒漠猫、胡兀鹫、高山兀鹫、鹅喉羚、野骆驼、狼、藏狐、赤狐、兔狲、猞猁、狗獾、鼠兔、高原兔、金雕、草原雕、白腰雪雀、猎隼、地山雀、渡鸦、大石鸡等野生动物;绿绒蒿、狼毒花、乳白香青、马先蒿、水母雪兔子、金露梅、白蓝翠雀花、冰雪鸭肢花、格桑花、唐古特乌头、蕨麻、冬虫夏草、伏毛铁棒锤、黑蕊虎耳草、藏波罗花塔黄、龙胆草、梭梭、雪莲花、垫状点地梅等野生植物,都是其他地域的人极少与闻的。生命是如此凛冽,生命又是如此辉煌,满怀信仰生活和行走在世界最高陆地青藏高原,便能够感悟自然无限、奥秘无穷的真理,获得水澄明、山虚静、地方圆、天亿重的智慧,体验孤独、寂寞、壮美、辽阔、生与死的界限、神与人的连接、人与自然的一体等独特的生命境界。
“从青藏高原播种,在黄海滩头开花;从世界屋脊起源,在大洋此岸成海。我有一个妈妈,她代表孕成和哺育,代表缘起和萌发,她是永远的高海拔。”2016年秋冬,我在散文《十万嘛呢》的结尾写下这段话。彼时的我从青藏高原的青海西宁移居黄海之滨的山东青岛已有21年。“十万嘛呢”是对我具有个人精神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77年夏天,22岁的我作为《青海日报》社的记者,搭乘一辆从玉树拉羊毛到西宁羊毛加工厂后返回玉树的卡车,去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采访当地的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车外的景色,远远近近是圣洁的雪山和苍绿的草滩,清透遥远的川谷不时有河流出现,激越而孤独。车到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我要求下到更远的杂多县,被县委机关藏族司机送到孤零零伫立在当曲草原的一顶黑色牛毛帐房前。站在辽远的苍穹下,我的心里滚过无边的寂寥:天色一半明一半暗,帐房的背景上,血红的晚霞里,云雾就像流淌的河。黑魆魆的远山以粗犷的线条描画着自己,那种从未见过的放肆的跌宕让我有些胆怯:这个地方太远太远了,远得山脉可以如此的放浪,太阳可以如此的孤冷和凄凉。一切都是原始而随性的,这片走向无极的原,那些走向苍茫的草,还有鹰的盘旋,几只牛犊定定地站在草地上,一律朝西望着远方,帐房边大黑狗的吠鸣是这片极原唯一的声响。帐房、晚霞、远山、鹰、牛犊和黑狗,像极了一幅美丽的绘画,却是草原深处最寂寞也最荒凉的风景。
在我最初关于雪山大地的意象里,就是草原上这顶普通的帐房,一位普通的藏族老阿妈在等待着我这个远方的汉人游子向着精神母亲漂流而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与陌生、沉静的藏族阿妈同处一顶帐房,善良、宽厚的阿妈就像草原的太阳和风,自然地接纳了一个来自远方的青年。阿妈把我当作和儿子巴桑一样的家人,教我学藏语、打酥油、骑马、拾牛粪、甩乌朵(一种放牧的工具)、在河边洗脸时怎样保护河水的圣洁;当我打了一只哈拉(旱獭)时,惊慌失措的阿妈会颤抖着跪在佛堂前念诵嘛呢超度草原的生灵;她给我吃的酸奶上撒稀有的白糖、喝的奶茶里放很多的酥油,寒冷的晚上把自己仅有的皮袍盖在我身上;天气转冷牧民们要迁徙去冬窝子时,县上的藏族司机忘记了来接我,偌大荒寂的草原上,不能及时转场的阿妈守着我等待不知何时来临的汽车……这是一位总是面带微笑、沉默寡言的草原母亲,她的坚忍与慈悲、善良与温暖是雪山大地最深厚、最清澈、最仁爱的母性,护佑了我年轻的生命。更让我心灵震撼并从此走上精神路途的是这位藏族阿妈最后的情义:1977年的高考讯息来了,父亲通过层层电话,从西宁到玉树再到杂多,藏族司机旦周终于想起还有一个记者在当曲草原,于是驱车来接。临别,阿妈把她毕生的积累——“十万嘛呢”送给了我。念一个嘛呢就是念一句“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十万嘛呢,阿妈会念多么漫长的时间!它代表所有,代表阿妈毕生的积累——她从小到大六十年或者七十年念诵过的所有的嘛呢。念嘛呢就是积累功德,积累功德就能带来幸福——今生今世的安康与富足、往生来世的美好与吉祥。十万嘛呢,阿妈把今生的功德和来世的福运都送给了我,这样的礼物,代表世代相传的信仰,是超越一切物质、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馈赠,是阿妈生命的全部。“十万嘛呢”是我的精神滥觞,那一刻石破天惊,如醍醐灌顶,我踏上一个精神朝圣者的长旅。
珍藏着藏族阿妈的十万嘛呢,深怀着对雪山大地的爱与敬畏,我最早的写作《环湖崩溃》,1988年发表的《海昨天退去》和散文《青海湖——断裂和崩溃之湖》,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写作,也开始了对人类道德精神的探索。此后四十年的写作,我没有离开雪山大地的馈赠,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氤氲着雪山大地的气息与魂魄,都可以找到雪山大地的泉源。比如《大悲原》是荒原英雄的悲歌,《藏獒》是道德危机与精神建树的呐喊,《伏藏》是拯救灵魂信仰的掘藏,《西藏的战争》是爱与人性及信仰的归一与大同,《藏獒不是狗》呼唤悲悯与良知,《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海底隧道》都是人性、良知、爱与担当的书写,《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是草原、动物、人的生命光亮,《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雪山大地》是理想主义三部曲,等等。它们构成了我的作品的荒原系列、藏地系列、海洋系列,其实就是更为宽广、辽阔意义上的雪山大地。
雪山大地从生命之初的血脉相连,成为我的心灵之根、精神之源、文学原乡。父辈们在雪山大地的理想与信念、情感与热诚、勇气与坚韧、奋斗与希望,是与雪山大地同在的光明,也是不该远去和消逝的地平线。虽然说父亲终身未能返回老家,但其实他已经魂归故土,埋骨于祖先曾经扬鞭催马奋力生存的大地,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回到了真正的故乡。我的出生是为了与父辈一同寻找,寻找活着的意义以及使命担当,寻找在这片大地上安身立命的珍贵启示。雪山大地确立了我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依托青藏高原和我所生活的青岛以及我的祖国,塑造中国人的现代形象和理想人格,肩负着良知建树人类的精神家园以及关于“人”的全部内涵。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回报,用我的心、我的血、我的爱,回报我的故乡青藏高原,回报我的文学原乡雪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