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中,量的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单纯谈论量的问题是庸俗经济学物化思维的表现,而《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主旨恰恰是要破除这种物化思维。但是,这并不表示哲学研究就应当放弃关于量的讨论。恰恰相反,仔细阅读《资本论》开篇“商品章”就会发现,量的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涉及诸多哲学史背景。
“量”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马克思使用了四个与“量”相关的语词,即Quantum、 、 Quan
、 Quan 、 quantitative
、 quantitative  ,且明显带有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痕迹。
,且明显带有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痕迹。
对于“1夸特”小麦、“a英担”铁等带有特定度量单位与数值的量,马克思称之为Quantum(定量)。这是《逻辑学》“存在论”第二部分“量”中的第二个环节,其基本界定是“具有规定性或一般界限的量”,与第一个环节中尚未有界限规定的量即“纯量”相对。
谈论几个定量相互之间构成的比例关系(1夸特小麦=a英担铁)时,马克思用的是quantitative  (量的关系)。这是“定量”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高的环节。这种“某一定量与另一定量的联系”自身也可以是“直接的定量”(例如1/a),黑格尔称之为“指数”(Exponent)。作为关系项的两个定量会随着指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定量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指数的变化:“我们可以用3∶6代替2∶4,而不改变两者的关系,因为在两个例子中,指数2仍然是一样的。”在指数固定的情况下,作为关系项的两个定量就只能在指数制定的规则下变化,例如当小麦从2夸特变为3夸特时,铁就必须从4英担变为6英担。正是因为这种制定规则的特点,康德在阐述纯粹知性原理时也将它们称为“指数”。而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价值量”称为交换关系的“指数”,即交换比例的规则。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三章中也有出现。
(量的关系)。这是“定量”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高的环节。这种“某一定量与另一定量的联系”自身也可以是“直接的定量”(例如1/a),黑格尔称之为“指数”(Exponent)。作为关系项的两个定量会随着指数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定量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指数的变化:“我们可以用3∶6代替2∶4,而不改变两者的关系,因为在两个例子中,指数2仍然是一样的。”在指数固定的情况下,作为关系项的两个定量就只能在指数制定的规则下变化,例如当小麦从2夸特变为3夸特时,铁就必须从4英担变为6英担。正是因为这种制定规则的特点,康德在阐述纯粹知性原理时也将它们称为“指数”。而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将“价值量”称为交换关系的“指数”,即交换比例的规则。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三章中也有出现。
谈论这些量的关系背后的共同东西的量时,马克思用的是 。在强调与“质”(
。在强调与“质”( )相对的量的规定时,马克思用的是
)相对的量的规定时,马克思用的是 。
。 和
和 在《逻辑学》中基本同义,可以互换,它们既是“存在论”第二部分“大小(量)”的统称,也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纯量”的称呼。马克思这里也基本如此,它们要么是对量的泛泛统称,要么是强调其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不确定具体大小,或者不知道其度量单位或尺度是什么,甚至这种量的实体或质是什么都不清楚。即便确定了实体即抽象劳动,但在未谈及价值量的大小及度量规定的时候,马克思使用的依然是
在《逻辑学》中基本同义,可以互换,它们既是“存在论”第二部分“大小(量)”的统称,也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纯量”的称呼。马克思这里也基本如此,它们要么是对量的泛泛统称,要么是强调其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不确定具体大小,或者不知道其度量单位或尺度是什么,甚至这种量的实体或质是什么都不清楚。即便确定了实体即抽象劳动,但在未谈及价值量的大小及度量规定的时候,马克思使用的依然是 ,所以《资本论》在谈及“价值量”时基本上都是使用
,所以《资本论》在谈及“价值量”时基本上都是使用 。而一旦涉及对价值量的度量时,就会用到“定量”。
。而一旦涉及对价值量的度量时,就会用到“定量”。
同质性作为度量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曾多次强调,“同质性”的价值实体是商品交换中量的比例的前提。这一观点时常被简化为:同质性是交换的必要条件。但是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交换的必要条件并非同质性,而是异质性。恰恰是使用价值不同的东西,才有必要进行商品交换:“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但是,如果交换中涉及量的比较或度量,那么就需要同质性,它是度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泛而言之的交换的必要条件。
这也意味着,交换是一个复合现象,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其中所包含的不同要素与层面。除了主体、行为和对象这三个要素,尤其需要区分的是商品所有权的变换与价值大小的度量。如果对应到货币职能之上,就是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区别,而马克思对于这两种职能的定位是:价值尺度要优先于流通手段。
通常对于交换的抽象作用是从流通手段出发来解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借此进入交换关系当中,而这一点就表明,交换的实质与使用价值的具体内容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可以从“交换”一词(Ex-change/Aus-taush)的前缀“Ex-”或“Aus-”中发现,这是一种“外在于”商品体的运动或变化,是商品的所有权以及背后的劳动支配权的变更。
但是,从度量出发也可以得出同质性的抽象,并且要更符合“商品章”的语境,因为所有权的变换还没有涉及量的问题,而马克思强调的则是:在“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中,必然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小麦、铁等使用价值得先化为这种共同的东西,然后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因此,“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定的可交换性……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性”。马克思在此秉承的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度量观。库萨的尼古拉在《论有学识的无知》开篇考察人类知识的条件时就指出,“一切知识都预设了一种比较,而更确切地理解的话,比较又无非是一种度量(Messen)。任何内容相互间若要加以度量,这一程序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同质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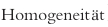 )这个条件。它们必须被还原为同一种度量统一体(
)这个条件。它们必须被还原为同一种度量统一体( ),必须能够被设想为从属于同一种量的秩序(
),必须能够被设想为从属于同一种量的秩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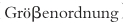 )”。而这种度量观也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应用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当中。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十章中,李嘉图就是从度量的角度来反驳萨伊的,并指出度量的真正对象是劳动,尺度是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而这种度量观也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应用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当中。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十章中,李嘉图就是从度量的角度来反驳萨伊的,并指出度量的真正对象是劳动,尺度是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作为度量方式的“价值形式”
所谓“价值形式”(Wertform)就是指价值的表达方式或表现形式,价值形式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实体的“价值”如何得到“表达”(Ausdruck)或“表现”(Erscheinung)。从度量的角度看,其实质就是作为纯量的价值量以何种方式进行度量从而转变为定量。这正是价值形式的必要性之所在。价值形式之于价值量,正如太阳的周期式运动、沙漏的运动、机械钟或电子钟之于时间或先后关系,米尺之于空间关系,温度计之于温度,杆秤、天平之于重量一样。
从度量的视角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充实关于价值形式发展的四阶段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理解。价值形式发展的四阶段阐述的并不是流通手段的发展(不管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而是对度量方式发展阶段的一种重构:“扩大的价值形式”意味着一种分散、多元的度量状态,而“一般价值形式”中等价形式的“简单性”和“统一性”,则意味着在各个度量领域中都至关重要的统一度量衡的问题。此外,商品拜物教的痛点也在于其度量之后的量的规定,而不是单纯无量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撇开这层量的规定,商品拜物教也就失去了客观规律般发生作用的特点。
黑格尔在评价开普勒的功绩时指出,他将第谷的数据提升到了“量的规定的普遍形式”,从而成为“一个规律或一个尺度的环节”。但是我们还需由此出发继续抬升,“从相关的质或确定的概念(如时间与空间)去认识它们的量的规定”,这是哲学的任务。马克思的任务或许也在于此。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