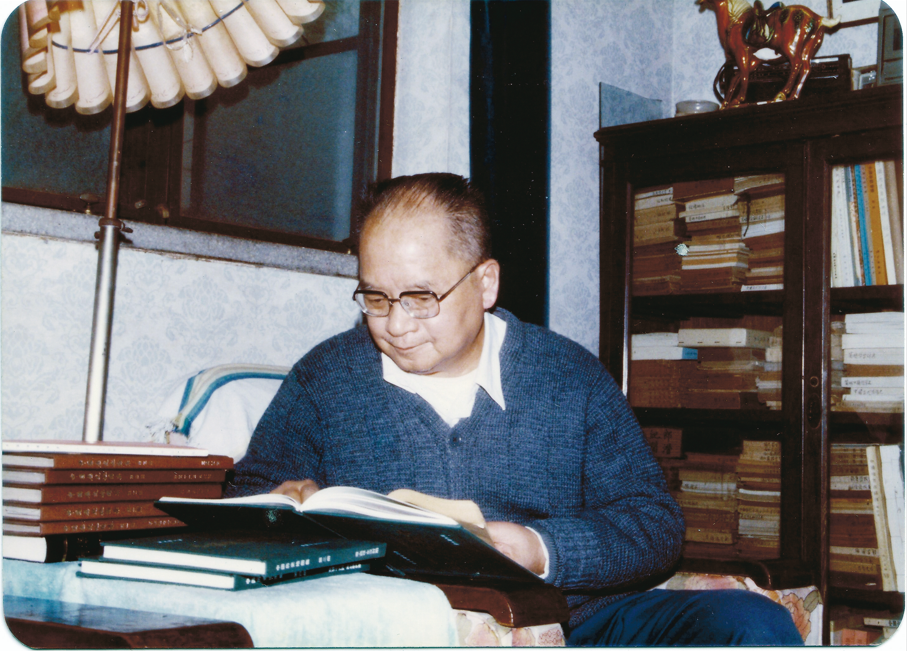■谭其骧先生在查阅资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供图
对黄河历史地理研究,谭其骧先生发表过三篇重要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以下简称《安流》)、《〈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以下简称《山经河》)、《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第1期,以下简称《西汉黄河》)。对这三篇论文,谭先生自己也有较高的评价:“我自以为这(《安流》)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他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故道来,怎不令人得意!”
的确,到目前为止,黄河历史地理研究这三个高峰尚未被超越。
黄河在东汉以后存在长期安流的局面
《安流》首先需要确认的,是黄河在东汉以后是否存在过长期安流的局面,因为此前从无人正式提出。谭先生是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中发现这个事实的。早在1955年5月为中国地理学会作的学术报告《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中,他就肯定在东汉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还从史学史专业角度提出一条强有力的理由:“从《后汉书》到两《唐书》所有各种正史都没有河渠书或沟洫志,这当然是由于自东汉至唐黄河基本上安流无事,无需专辟一篇之故。”“成书于东汉三国时的《水经》和北魏的《水经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所载的黄河经流,几乎可以说完全相同,并无差别,更可以证实在这一时期内的黄河确乎是长期安流的。”
至于“长期安流”的原因,有关历史学家和水利学家,如魏源、刘鹗、李仪祉、岑仲勉等,都归功于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但谭先生认为,“黄河的水灾虽然集中于下游,要彻底解除下游的灾害,却非在整个流域范围内采取全面措施不可,并且重点应中上游而不在下游;单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王景治河的施工范围只限于“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全部措施集中于下游,都不出工程治理即治标的范围。此外,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技术,东汉初王景能调动和运用的总是有限度的,难道能比以后从明清一直到近代的更大更高明?
谭先生根据公认的地理学常识指出,“降水量集中在夏秋之交特别是夏季,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是黄河善淤善决的两个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的水文实测资料又证明,决溢改道虽然主要发生在下游,其洪水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以往数十年的实测数据证明,下游洪水的流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来自中游,来自上游的不超过百分之十。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晋东南沁丹河流域的暴雨经常能使本区黄河河床产生一万秒立方米以上的洪水,如果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陕甘二省的渭水、泾水、北洛水流域和河南弘农河流域一角产生的洪峰同时进入下游,就会出现险情。在流经陕县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口镇以上的只占11%。而自河口至山西禹门口的输沙量即占陕县总量的49%,自禹门口至河南峡县占陕县总量的40%。
那就证明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就输沙量的变化,根本在于这两区流域间水土流失程度的不同,即水土流失由严重变得轻微。在战国时期,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原始植被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和西汉时期,大量移民迁入,从事农业生产,原来的牧地都被开发为农田。到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已有240万人,大规模的乱垦滥垦破坏原有植被,造成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两汉之际的战乱使边郡人口锐减,东汉初匈奴南单于率数万部众入居塞内,以后又有大批匈奴内迁,分处北边诸郡。大批羌人被安置在渭水上游的陇西、天水和关中盆地的三辅,泾河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亦所在有之。迁入的边疆部族人口总数在百万左右,都以畜牧为主,而留在那里的汉族人口大大减少,成了少数。耕地的缩减和牧地的扩展,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唐代安史之乱前,这一带农垦区区域有所扩大,但公私牧场占用了大量土地,农民的耕地最多时也比隋代少。这段时间的水土流失对下游河道已有一定影响,先后出现9次决溢,但未改道,严重性远不如西汉。安史之乱后,郡县建置有所缩减,编户锐减,但实际人口并未减少,牧场废弃,农业规模扩大,乱垦增加,故下游河患仍有9次,且出现了改道。五代以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近代。
对谭先生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特别是在水利学界。但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治理的成功,已经完全证实此结论的正确性。对黄河中游小流域的治理就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荒,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减少水土流失,黄河下游的年平均输沙量已经从16亿吨降至几亿吨。
“山经河”的复原
从司马迁到清代研究黄河变迁的名著胡渭《禹贡锥指》、现代研究黄河的巨著岑仲勉《黄河变迁史》,讲黄河变迁都从《禹贡》所记载的“大河”讲起,从未有人再追溯此前。之所以如此,一是囿于《禹贡》中大禹治水导水后方有“大河”下游河道的成说,二是在《禹贡》以前、以外找不到任何此前黄河下游河道经流的记载。
通过对《山海经》的研读,谭先生发现它的地理学价值,特别是其中《山经》的主要内容就是一部地理书。他发现,《北山经》记载了三十多条“入河”“入于河”的河流,而这些“入河”的地点大多是可以考证的。根据水文地理的基本原理——所有支流与主流的交接点都在主流上,将这些交接点连接起来就是主流河道。
但要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真正在地图上复原出这条水道,还需要对历史地理文献深刻的理解和对古地名的辨析考证能力。因为《山经》并非同一作者同一年代的系统性著作,其中记录的水道也不一定同时存在。有的水道已经消失湮没,有的已经改道,有的早已改名,甚至改过多次。由于“入河”“入于河”的地点是这些水道的终点,已在低海拔地方或平原,变化更大,有的已无踪影可寻。只有将某条水道的走向复原,才能确定这个交汇点。对涉及自然地理的地名,还要看与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如果发现不符合,就要分析是地点定错了,还是自然地理景观本身发生了变化。就这样,谭先生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说文》《淮南子·地形训》《初学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隋书·地理志》《大清一统志》《元和郡县志》《通典》《读史方舆纪要》《史记》《山海经笺疏》《汉书》《尔雅》等典籍中的记录或线索,最终考定这三十多条支流与河水的汇合点,复原出这条从未被前人发现的“山经河”。
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西汉黄河》的研究也是从质疑前人的结论出发的。黄河以“善决善徙”著称,西汉以后改了很多次道,但西汉以前居然没有改道的记载。《史记·河渠书》从大禹导河叙起,但只有“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才开始有改道。对此,前人形成两种说法。
一是根据《汉书·沟洫志》所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所引《周谱》中“定王五年河徙”这句话,认为这是汉以前唯一的一次改道。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南宋程大昌,清代阎若璩、胡渭均持此说。“定王五年”即春秋时周定王五年(前602)。二是清焦循所著《禹贡郑注释》认为《周谱》之说不可信,西汉前黄河未发生过改道。
谭先生认为,既然黄河下游容易改道的基本条件早已存在,怎么可能到周定王五年才出现第一次改道,甚至到汉武帝元光三年才出现第一次改道?他对“山经河”的发现已经推翻了这一错误论断。但传世史书中有关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即使是片言只语,也早已被乾嘉以来诸多学者挖尽收全,再也找不到新的线索。在历史地图和考古遗址地图上,谭先生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华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和聚落。总的来说,这片空白地区是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且有规律可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到战国时期,平原中部的空白才归于消灭,出现了十多个城邑。
这说明在没有堤防约束的情况下,“黄河下游每遇汛期,当然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河床日益淤高,每隔一个时期,当然免不了要改道,情况大致和近代不筑堤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差不多”。到战国中叶、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河北平原上的黄河下游已筑起堤防。由于黄河经常性的泛滥控制住了,土地迅速得到垦辟,大大小小的居民点和城邑也就逐步布满了原来的空白地区。据此,他的结论是:在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的改道决不是一次二次,更不会是亘古不变,而应该是改过很多次。但因为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至少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灾难,所以尽管多次改道,却基本上一次都没有被史家记载下来。发生于周定王五年的那次改道可能影响较大,因而为《周谱》作者所记录。但也说不上很严重,所以仍然不见于别的记载。
近年来,有人注意到,自谭先生进行这项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一条开阔的空白带内发现了好几处文化遗址,那么谭先生当年的结论是否还正确呢?我认为,谭先生根据科学原理得出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但具体范围应该根据新的发现作相应调整,如这片空白地带不一定都有那么宽,可以根据那些新发现遗址的年代推测收窄的时间和过程。但在渐次入海的低平土地上,河道尾闾的摆动并不需要太宽的距离,除非被堤坝严格约束,所以西汉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曾经在此范围内漫流并多次改道的推论依然成立。
在此基础上,谭先生全面复原了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厘清了“《禹贡》河”“《山经》河”“《汉志》河”的关系。此文的结论有十二点,可谓黄河历史地理研究集大成者。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