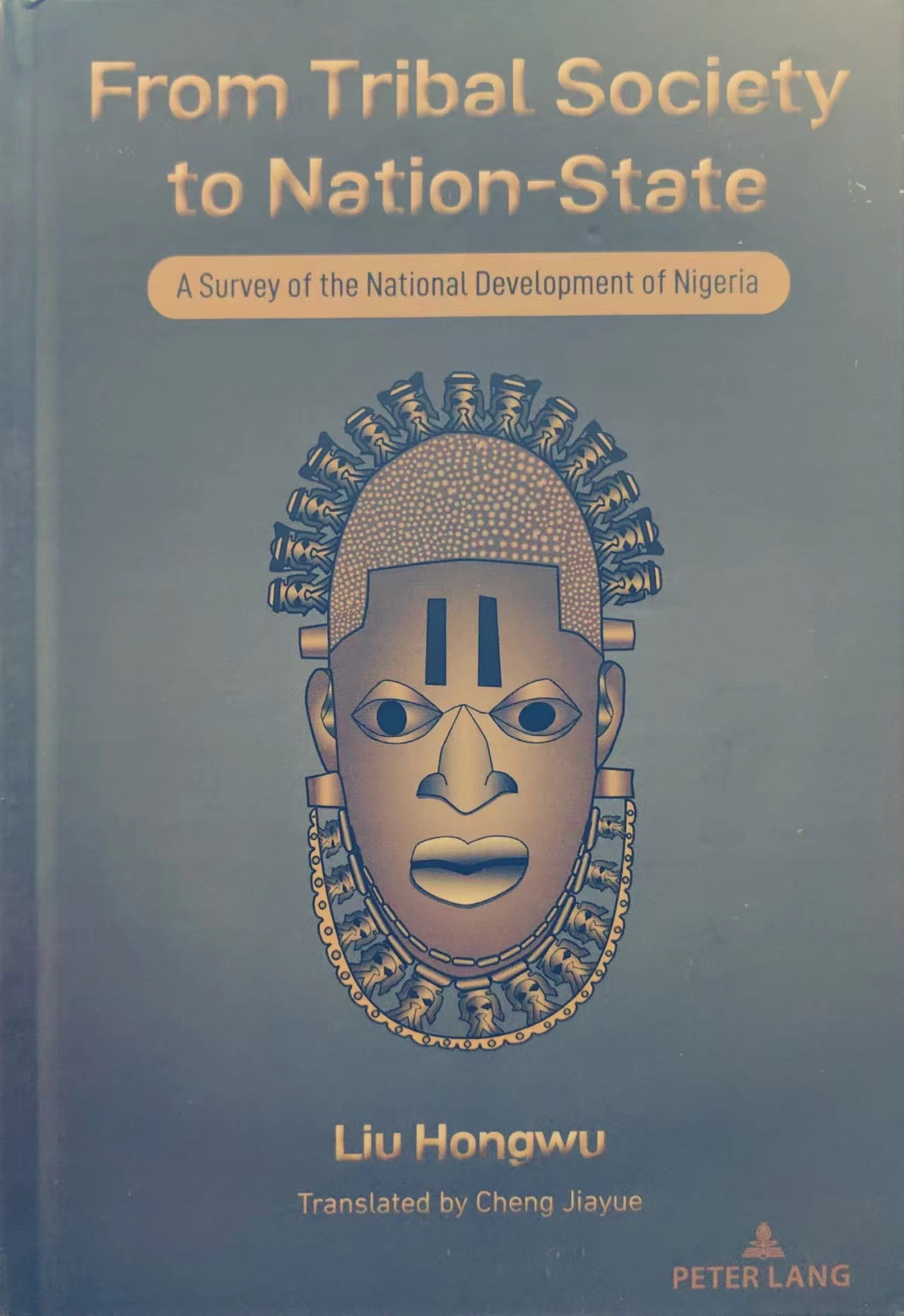
书影
在非洲大陆的后殖民国家建构历程中,尼日利亚始终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个拥有250多个族群、三大主体族群(豪萨-富拉尼人、约鲁巴人、伊博人)以及多元宗教文化的国家,其民族国家构建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堪称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实验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于2000年出版的《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以历史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的多维视角,系统梳理了尼日利亚从传统部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百年历程。时隔25年,该书的英文版问世,不仅为国际非洲研究提供了中国学者的独特观察,更引发了尼日利亚本土学界对自身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本文将从“多元一体”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对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行评析。
一、理论框架:民族国家建构的“非洲命题”与中国回应
本书的核心关切是当代非洲国家如何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作者认为,非洲国家的特殊性在于“国家先于民族而存在”——殖民者人为划定的疆域与本土多元部落社会的割裂,使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不得不以政府权力为工具,强行推进民族一体化进程。这一“逆向建构”的困境,与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积淀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强调“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了“自在”的文化认同,而现代国家则通过制度设计(如民族区域自治)将这种认同转化为“自觉”的政治实体。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部落社会缺乏长期共处的历史经验,英国殖民者“间接统治”“分而治之”的策略更强化了部落、王国间的隔阂。本书指出,非洲国家的“泛政治化”倾向(如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军人政权频繁更迭)本质上是民族整合乏力的一种代偿机制。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经验对非洲的启示在于:民族国家建构不能仅依赖政治权力的强制整合,更需要文化认同的柔性塑造。例如,中国通过推广普通话、普及国民教育、挖掘共享的历史记忆,成功将不同地域、语言、宗教、文化的族群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框架。而尼日利亚虽在独立后推行“统一国民教育”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但殖民造成的南北文化分野(北方“伊斯兰教化”与南方“基督教化”)仍深刻制约着国家认同的生成。本书对尼日利亚“国民文化共识体系”构建困境的分析,恰与中国“文化润疆”“文化兴边”等政策的实践逻辑形成呼应。
二、历史叙事:从古代王国到现代国家的断裂与延续
本书的另一贡献在于,将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置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考察。作者详细梳理了豪萨城邦、约鲁巴王国、贝宁艺术等本土文明的历史遗产,揭示了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复杂性与能动性。例如,豪萨诸城邦通过跨撒哈拉贸易形成的商业网络,以及伊费—贝宁文化中体现的自然主义艺术传统,均表明非洲并非“无历史的他者”。然而,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打断了本土文明的自主演进,使得独立后的尼日利亚不得不面对“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嫁接”双重任务。
这一历史断裂性在非洲具有普遍意义,而中国则呈现出更强的文明连续性。尽管近代中国同样遭遇殖民冲击,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例如,清朝通过“改土归流”将边疆民族纳入中央集权体系,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理念则延续了多民族共治的传统。相比之下,尼日利亚的博尔努、贝宁等古代王国多为松散的城邦联盟,缺乏制度化的中央权威;殖民统治的“间接治理”策略(保留豪萨-富拉尼贵族特权)进一步固化了部落政治的路径依赖。因此,独立后的尼日利亚虽试图通过“建州计划”“非洲社会主义”实验等方式削弱部落主义,却因缺乏社会经济基础而流于形式,始终难以摆脱“三族鼎立”的政治格局。这种差异凸显了制度移植的本土适应性问题。
三、现实挑战: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重构
英文版序言中提到,本书在尼日利亚学界引发了关于“21世纪非洲国家向何处去”的讨论。当前,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未竟之业在全球化时代显得愈发紧迫。作者在书中强调,经济现代化与民族一体化必须同步推进——若无法解决南北发展差距、资源分配不公等结构性问题,族群冲突的幽灵将始终在人间徘徊。
在这一领域,中国的模式或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反观尼日利亚,尽管其石油经济曾带来短暂繁荣,但“资源诅咒”导致的腐败与分配失衡,加剧了族群间的地缘竞争。
四、学术价值:中国非洲研究的范式突破
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首部系统性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专著,本书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拒绝将非洲视为“失败国家”的典型,而是以“同情的理解”揭示其转型的内在逻辑。例如,作者对“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并非简单否定,而是将其置于殖民经济依附性的背景下,指出其作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历史合理性。这种立场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学者立足第三世界发展经验,深入尼日利亚田野实地、与尼日利亚人民休戚与共的共情且独立的视角。
本书英文版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中非学术对话。尼日利亚《非洲中国经济》杂志主编、非中媒体中心主任伊肯纳·埃梅乌(Ikenna Emewu)直接以“中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向尼日利亚人讲授尼日利亚历史”为标题表示,“本书为尼日利亚当前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也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写作尼日利亚历史的头部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刘鸿武教授对尼日利亚和非洲的兴趣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根深蒂固、坦率真诚且富有思想性的。”
当然,本书亦存在若干局限。首先,对女性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角色关注不足(如豪萨女性的宗教与政治参与、伊博人母系遗产的现代转化);其次,跨国族群(如豪萨人在尼日尔、乍得的分布)对主权国家认同的冲击尚未充分讨论。再者,尼日利亚的诺莱坞(Nollywood)电影产业通过本土叙事塑造国民认同,约鲁巴传统戏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嬗变,均可为“国民文化”塑造研究提供鲜活案例。这些议题或可成为未来中非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
总之,《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英文版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非洲研究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向“全球理论对话”的跨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不仅关乎非洲大陆的未来,也为所有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刻启示——如何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历史断裂处重建连续,将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共同课题。中国的“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智慧与非洲的“乌班图”(Ubuntu,意为“我在因我们同在”)精神,或可在这一探索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