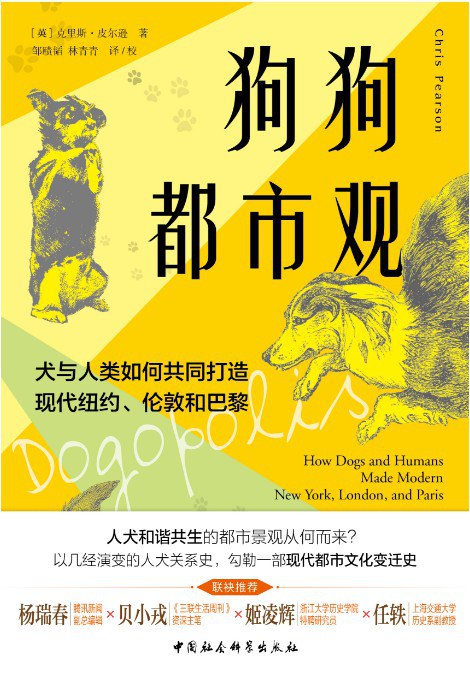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人发生深刻联系的动物不在少数。但其中被驯化程度最高,且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具有“食物来源”之外重大意义的动物,其实相对有限。其中突出者,当属马、猫和狗。而三种动物里,又以狗在人类情感体验中的定位最为繁复——有的人喜欢狗,有的人厌恶狗,还有的人对狗是“又爱又怕”。与此同时,狗在近现代人类社会运作中充当的角色,也远比马、猫等其他动物丰富——雪橇犬、缉毒犬、搜爆犬、抚慰犬、导盲犬……可以说,狗方方面面的优长都得到了人类的重视,早已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可靠伙伴。
由此,当我们审视历史上人犬关系变迁之时,我们所能看到的,不独是简单划一的“管理史”,还有人与狗之间持续交互渐进构成的,基于跨物种情感与价值观念的“情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以下简称《狗狗都市观》),就系统讨论了“情感史”视阈中的都市人犬关系,绘写了一幅流淌着多元情感的“大城小狗”历史长卷。
《狗狗都市观》的叙事视野,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宏观地看,这是世界城市史上剧变频出的转型期。缩小至都市中人犬关系的范畴,该时段也是人犬关系从农业社会模式过渡到工业(城市)社会模式的关键转型期。不同于今日都市人犬关系建设更多关注“宠物友好”总纲下的陪伴心理与消费文化,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人犬关系,首先要历史地解决一道难题:怎样让初入城市环境的狗改换“现代”面目、融入“城市”语境,使之不会与霓虹灯下的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甚或有碍于城市平稳运转。围绕这一目标,两方面“情感”建设,被推到了现代城市中人犬关系重构的舞台中央。
首先是弭平恐惧。有一种千百年来令人闻风丧胆的传染病——狂犬病,被19世纪的欧洲人称作“死亡之吻”。19世纪至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不少都市,都尝试通过检验登记、项圈嘴套、扑杀野犬等“管控措施”来减少狂犬伤人风险。虽然相关尝试良莠不齐,但客观地看,这些措施对当时市民降低对城市中“健康狗”的恐惧,起到了一定的抚慰作用。当然,上述“管控措施”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唯有觅得高效阻遏狂犬病的良方,才能真正帮助更多都市居民走出“恐犬”阴霾。1885年,路易斯•巴斯德研发的狂犬疫苗宣告成功,防治狂犬病的天际晨曦微露。一如作者论断,巴斯德狂犬疫苗作为一种“遏制狂犬病潜在致命威胁”的可行方案,能“消弭(恐惧狂犬病造成的)情感影响”,而“这点对狗狗都会的出现至关重要”。
其次是重建价值。在历史步伐迈入近代门槛之前,狗之于人类的农耕与狩猎,有着直接而深长的价值。然而,这层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农业合作”关系,在近代城市化浪潮中瞬间“失音”。由此,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文明,亟需从狗身上开掘出适宜现代城市的“胜任点”,进而使脱离农事生产的狗,在现代城市中获得更广泛而稳固的定位。《狗狗都市观》追溯了警犬“在充满不安情绪的现代都会中,站出来保护、帮助”市民的历史。通过磨合试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支持城市配备警犬,希望借助这些“新型护卫犬”的“思维能力、勇气、忠诚以及强健力量”,有力地震慑犯罪分子,巩固市民的安居之心。警犬案例也表明,狗本身具有的潜在“暴力”并不只导向撕咬路人、诱发狂犬病等负面结果,也完全可能化为人类社会认可的“忠勇”气概,守护一方平安。而左右潜在“暴力”是“伤人”还是“护人”的,并非狗本身,乃是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表明,“狗不教”,归根结底还是“人之过”,正如《狗狗都市观》作者引用的19世纪宠物狗养育指南所言,“狗主人应认真训练他们的狗狗,以此拉近人与狗的联系”。
站在近代城市史的延长线上,《狗狗都市观》也叮咛今人:我们身处的现代城市不单是“人的城市”,现代城市的情感与精神,亦不可拘囿于人的“一己之情”。纵然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空间,但人类漫长农业社会中反复磨砺的“自然情感”,特别是人与身边其他动物的互相信赖、亲近、交融,不应消泯于城市之中。现代都市文明愈是昌明进步,她的“自然情感”也愈当不断抬升。从都市中的人犬“情感史”出发,我们或可畅想一种更有益于市民精神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城市文明。
(作者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