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诗虽然在当代新诗坛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接受范围日趋狭窄、接受程度日益降低等问题,而新诗重新回归格律的看法和实践也一直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新诗的格律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以更好地思考新诗的发展路径。新格律体诗既可以从中国五、七言诗与西方格律诗那里借鉴顿数与押韵的规律,也可以从词体中借鉴节奏模式。相对于旧格律体的“严格的重复”,新格律体是宽松的,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现代感性”;相对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它又是规整的,较容易在作诗者与读诗者之间形成某种“视野融合”。注重形式的规范与要求形式的解放同样重要,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对于发挥汉语优势、丰富意蕴表达以及促进诗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自由诗;旧格律体;新格律体;进化
作者潘建伟,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杭州31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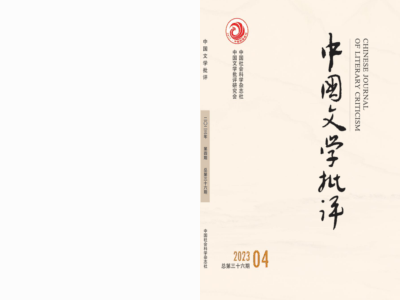
引言
废名有一个说法广为人知:“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他断言:“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废名说新诗要用“散文的文字”,即指明了新诗的文字应该是一种语言的自然节奏,颇具灼见,但他将“诗的文字”与“诗的内容”二元对立化,并以此作为区别新诗与旧诗的标准,反而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他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撇开了新体格律诗,更是一种“偏见”,即便这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偏见”,也仍然是一种“偏见”。简单否定废名的“偏见”,自然失之肤浅,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新诗发展至今,为何走上了他所谓的“自由诗”的路子?
这里面原因很多,在思想观念上,对诗体进化论的信奉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进化论”萌芽于黑格尔,由达尔文在生物学上正式确立,此后斯宾塞将之运用于社会学,赫胥黎在伦理学上提出修正,又有托马斯·门罗(Thomas Munro)发展于艺术学,是主导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波及文学、艺术、教育、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在中国,严复节译《天演论》,改造赫胥黎的思想,宣扬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法则,影响了清末至“五四”一代的文人。就文学而言,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提出的诗体“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的诗史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代变论,都很难撇开进化论的因素而得到完满的诠释。五四时期文学界在清末民初文人思想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当时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诗史是一个从文言到白话、从格律到自由、从束缚到解放的进化过程,似乎中国诗从过去到现在,迈向未来,最终必然汇入一个白话自由诗的大合唱。诗体进化论之流风所及,也使得当代诗坛产生一个普遍的观念,即认为自由诗就代表着中国诗未来发展的唯一方向。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翻译的影响、视觉文化的浸染、诗人个性的张扬等,都使得格律诗不再为当代诗人们所尊崇。比如翻译的问题,卞之琳原本设想通过“以顿代步”的方式引进西方格律诗,以此来推动中国新格律体的发展,但他的主张除了在余光中、黄国彬、黄杲炘、江弱水等少数人那里得到贯彻之外,在诗坛响应者似乎不多。人们常常把西方的格律诗译成自由诗,既不考虑韵脚,也不考虑顿数。译诗与作诗往往同步而行,译诗是一种典范,可以为作诗提供依据,既然译诗并无格律可言,作诗自然也就不会去遵循形式规范;不用“以顿代步”的形式来处理诗行,便无从借鉴西方格律诗,也就无助于新诗格律的建设,只是打开了自由诗的方便法门。又如视觉文化的问题,对于当代人来说,“眼睛成为最忙碌的感官”,新诗写作也受此影响。很多新诗人勤于意象的经营而忽视声韵的建设,甚至将表现意象看作写诗的唯一目的。再如诗人个性的张扬,每位诗人都希望自己所写的诗具有独一无二的形式。个性解放,诗体自然也须解放,诗人们都不愿意遵循外在于自我的规范,导致自由诗几乎成了新诗的代名词。于是,格律也就被认为是阻碍抒发诗情诗思的绊脚石。但伴随着自由诗的流行,一直存在着对这类诗体的质疑,不少人希望重新回归格律。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矫正新诗运动以来提倡形式解放而导致的诗律散乱、诗风散漫等问题,提倡新格律体,它注重诗的音乐美与建筑美,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并有规律的押韵。新格律体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为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等现代派诗人所继承,并为朱光潜、罗念生、何其芳等批评家阐释发扬,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晚近的余光中、黄维樑、江弱水、许霆等诗人、学者在此前的基础上对新格律体的建设也多有探索。新诗格律化是中国诗的“逆流”、传统的“复辟”,还是为中国诗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衢,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做深入的考察。本文认为,新格律体是居于旧格律体的“严格的重复”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之间的一种新诗类型,它不像前者那样严格均齐,也不像自由诗那样过度随意,而是一种适度的重复,既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又有某种可以寻找的规律,是在借鉴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格律诗的形式特征基础上力图创造的新的格律体诗歌。
格律的价值
诗体越解放、越自由,就越能“言之有物”,大概是自由诗提倡者最大的理由,而格律往往被认为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这种论点完全将诗的思想感情与诗的格律形式割裂开来,格律是内化于诗本身、与思想情感密不可分的“有意味的形式”。但如果非要将两者区分开来理解,也可以这么回答:正是因为有了“声调格律”,不好的思想才更加易于传播;反过来说,好的思想如果有了好的“声调格律”,才更易深入人心,陶冶性灵,从而达到变化气质的效果。格律本身并无善恶,它并非必然就能造就好诗,它只是利器,关键在于诗人如何去运用它。奥登(W. H. Auden)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韵脚、格律、诗歌形式等,犹如仆人。如果主人足够公正而赢得他们的爱戴,足够富于主见而获得他们的尊敬,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井然有序的幸福家庭。如果他过于专横,他们会辞职离去;如果他缺少威信,他们就会变得懒散、无礼、嗜酒成性且谎话连篇。”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说,格律能让诗讽诵于口吻,有助于记忆。虽然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下社会,可资记忆的载体极为丰富,诗早已不再充当单纯的“记忆术”之用,然而如果只留意于“目的诗”,不同时注重“耳的诗”,只追求画面感,不同时注重音乐性,诗终究无法打动人心。佛家早言,五根之中,耳根最利。诗要让人兴发感动,须以口引心,以声摄耳。一首诗让人记住,首先是借助声音,不是依靠意象。格律诗在这个方面就远比自由诗更为便利,故而很多格言、警句,甚至广告、医方也都用定型化的诗体来表现,如奥登所言,“诗歌在便于记忆方面拥有奇异的能力,于是,在用作说教手段时,它超越了散文。那些谴责说教的人必定‘更加’厌恶说教性的散文;生物碱—塞尔策片的广告可以证明,如果用诗歌来写,说教性广告词的粗鲁腔调会减少一半”。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声色浮动、光影变幻,才需要有格律诗这样的容器将某种瞬息、短暂、流动的情感与思想加以承载、藏存。冯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最后一节正是表达了这种观念:“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江弱水也有类似的看法:“格律诗绝不等于在大致齐整的诗行中顺手押几个韵脚那么简单,它不仅可以借助其外在的统一,而且可以建构其内在的统一,以双重的有机统一来抵御时间的侵蚀,让一篇音义俱佳的作品,在现代世界浮动的声色与光影之间,轻轻地,但是却牢牢地,抓住些什么。”而在奥登那里,格律则又是“某种防御”,现代社会浮动的声色与变幻的光影也让人内心意识到“混乱及恐惧”,有序的形式就能让混乱的心神趋于稳定,从而掌控“那些他无法直接掌控的情绪”。
流动的情感、变幻的思想与声色浮动的世界,都是所谓的“物”;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容器将这些“物”加以承载,它们就流离失所。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诗派的观点就认为写诗无法“言之有物”,是由于格律的束缚,因而要解放小脚,倡导自由。戴望舒翻译瓦雷里《艺文语录》时借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言之有物”:
“而我的诗,不论好‘坏’,永远言之有物。”
这就是无限不堪入目的东西的原则和萌芽。
“不论好坏”,——多么地洒脱!
“有物”,——多么地自负。
如果我们隐去原作者的名姓,这段戏剧性的对话简直就是针对胡适观点的绝妙讽刺。“言之有物”,散文足矣,何必写诗?将重心放在所言之“物”上,大量的坏诗正在这样的名义下生产了出来,其流弊直至今日仍没有消除。
新格律体的建设
卢前任主编的《民族诗坛》第4辑刊登过一个“征集当代诗人‘对于创造新体诗歌之意见’”的公告,其中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新体诗之试验已十余年,何以不能普遍流传?是否本身有其缺点?请申论之。
(二)今日我国所需要者,为何种新体诗歌?请各就理想中之“形式”言之。
(三)创造新体,以我国固有乐府体,古近体诗,词或曲为依据乎?抑一概摒弃?请裁夺之。
(四)创造新体,以异域之各种体制为依据乎?抑一概摒弃?请裁夺之。
这四个问题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讲现状:新诗为何不能普遍流传。其次谈理想:既然新诗有缺点,那么理想的新诗体应当是怎样的形式。接下来的两个问题谈两种途径:创造理想的形式,该以中国固有诗体为依据,还是以外国诗体为依据。卢前提这些问题时新诗诞生才20年左右,现在100多年过去了,这仍是今日新诗坛及新诗研究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明显,卢前所提出的问题中,如何创造“新体”(新格律体)是最根本的内容,归结起来也就是两条路径,即从纵向继承中国古典诗与从横向移植西方诗。
中国与西方都有大量各式的格律诗,可称之为古典诗体(classical verse)或传统诗体(traditional verse),也有人称之为“预设诗体”(predefined verse),即在创作之前已经预先存在的诗体形式,比如中国的律诗、绝句,以及词、曲中的各类样式;又如西方的英雄双韵体、十四行诗、三行联韵体、维拉内拉体等。格律运用既久,遂成固定样式,既须符合这些诗体的形式规范,亦须留意其特殊的表现功能,或适合此类诗体的特殊风格与思情。比如“英雄双韵体”宜刚不宜柔。刚柔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范围很宽,一般来说,雄浑、沉着、高古、劲健、豪放、悲慨、旷达都属于阳刚的范畴,蒲柏用这类诗体来翻译荷马史诗,就较易传达原诗雄壮奔放的风格。冲淡、飘逸、绮丽、含蓄、疏野、纤秾、缠绵、凄悲、谐谑则属于阴柔的范畴,“英雄双韵体”不适宜表现阴柔的情思,尤其不适于传达谐谑的风格。根据奥登的考察,这一诗体并不具备“喜剧性”的特征,虽然也可以写出“意趣横生”的内容,但如果去写某些滑稽、诙谐的内容或某些被嘲讽的对象,往往会归于失败。而中国的绝句就与“英雄双韵体”相反,根据沈曾植的说法,“绝句以风神为主,宜柔不宜刚,柔者宜情不宜理。韩、杜多涉理,故以拗句出之,此不得不然者”。绝句也很适合传达“英雄双韵体”不适于传达的谐谑与讽刺的风格,尤其是七绝。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嬉笑讥讽,所写208首诗全是七绝,正是这个道理。另外,随着社会之发展、名物之演进、词汇之更新,诗体也常需斟酌新声而随时代变。在新格律体中,创作者不再遵守传统的格律,而是根据新的现实、新的感性的要求创造出新的形式,虽然每行仍有一定的顿数、押大致相近的韵脚,但正如闻一多所说,这是“相体裁衣”,故而“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在中国,新格律体由闻一多、徐志摩发轫,为卞之琳、冯至、梁宗岱、朱光潜、罗念生、何其芳等继承,包括朱湘、林庚、唐湜等诗人,都有过不少作品或做过相应的理论探索。很显然,新格律体是中国格律传统最晚近的发展,那它能够从旧格律中继承哪些内容呢?闻一多、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主张,一方面借鉴英语格律诗“音步”的划分方式,另一方面从五、七言诗中借鉴“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化”这个坚实的“旧基础”出发,来创造新格律体。规律化的押韵比较容易理解,问题比较大的是规律化的顿数。朱光潜在《诗论》中对此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尖锐的疑问:
旧诗的“顿”是一个固定的空架子,可以套到任何诗上,音的顿不必是义的顿。白话诗如果仍分“顿”,它应该怎样读法呢?如果用语言的自然的节奏,使音的“顿”就是义的“顿”,结果便没有一个固定的音乐节奏,这就是说,便无音“律”可言,而诗的节奏根本无异于散文的节奏。那么,它为什么不是散文,又成问题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因此立论,质疑新格律体以音义相符来划分节奏的有效性。在旧格律诗体中,“义的顿”如果与“音的顿”相矛盾,那么前者必然需要迁就后者,这在英文格律诗中尤其明显。比如刘易斯(Charlton M. Lewis)举过拜伦的一行诗:
Then tore| with bloo|dy ta|lon the| rent plain.
这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第三章第十八节第六行。整首诗的格律是所谓的“斯宾塞体”(Spenserian stanza),每节共九行,前八行抑扬格五音步,第九行为抑扬格六音步。故而这一行中的“bloody”与“talon”两个词被强行拆散归入不同的音步中,意义必须迁就音律,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每首英文格律诗都会出现,无须多举。
在中国旧诗中,也会出现“义的顿”与“音的顿”不相符合的例子,比如“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风”,按照“义的顿”,需划分为“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风”;而根据“音的顿”,则必须读成“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风”,前者需要迁就后者。再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按照“义的顿”,需划分为“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而根据“音的顿”,则必须读成“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前者需迁就后者。但是与英文格律诗普遍存在这种音义矛盾不同的是,中国旧诗中的这种情况并非普遍现象。旧诗中的顿绝大多数情况仍然是音义相符,或者说,出现音义矛盾的诗行远远少于音义相符的诗行,比如杜甫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基本没有出现音义矛盾的诗行。在旧诗中尚且如此,在新诗中,这种音义的矛盾更可以忽略不计。新诗的语言是近似说话的调子,也就是口头语言的节奏,而口语的节奏一定是音义相合,形式化的节奏需要符合语言的自然节奏,如果严守“音的顿”而不顾“义的顿”,听起来会相当不顺。事实上,朱光潜在1959年发表的《谈新诗格律》一文中对《诗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有所解释,他认为旧诗中“音的顿”与“义的顿”并不能完全符合,这是允许的;而新诗的诵读方式是根据“语言的自然节奏”,就不能再用旧诗的诵读方式来处理顿,因此,“那种可不依意义而分顿的办法就不适用”。需要补充的是,新格律体诗以顿作为划分诗行的单位,并使“音的顿”与“义的顿”相符,也仍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格律诗节奏划分的主流。只不过在五、七言律诗中,每行的顿数与字数均相等,且每行最后一顿往往是三字顿;而在新格律体诗中,每行的顿数虽然常常相等,但每个顿包含的字数却常常不相等(因此每行包含的字数也就经常不相等),且每行最后一顿往往是二字顿。这是新格律体与五、七言体在诗行特征上所体现的最大差异,也可以看成新格律体对旧格律诗的一种发展。
中国古典格律诗每行顿数相同,字数也相等,而新格律体诗行常常只有顿数相同,字数却不相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往往有大量的虚字。比如冯至《十四行集》第一首第一节: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各行凡是有虚字的顿,大多是三字顿:“准备着”“深深地”“不到的”“岁月里”“彗星的”;甚至是四字顿:“在漫长的”。而没有虚字的顿则大多是二字顿,个别是一字顿。这就造成了在每个顿上时间分布的不均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罗念生认为,可参照英语诗的轻重音,将中文诗中的虚字处理成轻音,实字处理成重音。但这种做法很难行得通。第一,在中文里实字要远多于虚字,如果实字一律重读,虚字一律轻读,势必产生大量的重音,整首诗都显得声调沉闷。第二,虚字轻音,实字重音,于是同一行诗就变成了既有“重重”的顿,也有“轻重重”或“重重轻”的顿,显得极为凌乱。比如上面所举冯至的这四行诗,如果按照罗念生的观点来排列轻重音就是如下的图式: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即便是英语诗中,虚词也不必然就是轻读,实词也不必然就是重读,而是要根据格律规范来确定重读还是轻读。比如《失乐园》第一卷第163行与第164行:
Our la|bor must| be to |pervert| that end,
And out| of good |still to |find means |of evil;
第163行虚词“to”必须重读,第164行中的虚词“out”“to”也必须重读,而第164行中的实词“find”却必须轻读。
笔者以为,仍然可以借鉴英语格律诗的顿数划分,但不是像罗念生那样胶柱鼓瑟,将虚字轻读、实字重读,而是学习英语格律诗对于顿数的灵活处理方法。中国的五、七言律诗,不但每首句数固定,每行字数相等、顿数相同,并且平仄押韵也有严格的规定,如此高度形式化的诗体,即便置于世界诗史中也颇为少见。形式固定,法则也就方便把握,一旦把握了法则,就很容易分析它的体式特征。但英语诗的音步划分远不像中国古典诗那样简单。王力就感叹过:“分析音步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为什么“不很容易”?因为英语诗的音步划分很灵活,不像中国诗那么固定,一望即知。在英语诗中,划分音步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重音,而一个英文词是否需要重读是不确定的,有些时候,日常语言中不需要重读的词,在诗行中却需要重读;反过来说,在日常语言中需要重读的词,在诗行中却反而不需要重读。这仍然需要根据整首诗的格律来确定。比如前文所举拜伦的这行诗:
Then tore| with bloo|dy ta|lon the| rent plain.
如果根据单词的日常读音,第四音步“-lon the”是抑抑,第五音步“rent plain”是扬扬,但是整首诗的格律要求这两个音步均须读成抑扬。所以如果我们仅读英语诗的某一行,往往就分析不出它究竟是属于什么格律,必须将之纳入整体诗章中才能加以确定。
英语格律诗对顿数的灵活处理还体现在它常常会增删音节。一般来说,英语格律诗行以抑扬格五音步最为常见,但是在这类诗体中常常会出现缺失的音节或多余的音节。布鲁克斯、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举过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的《再会了,谷仓、烟囱与丛树》(Farewell to Barn and Stack and Tree)中的四行诗:
Long| for me| the rick| will wait
And long| will wait| the fold,
And long| will stand| the emp|ty plate
And din|ner will| be cold.
这节诗奇数行抑扬格四音步,偶数行抑扬格三音步。第一行中的第一个音步“Long”就是“不完全音步”(defective foot),或者称为“缺失了音节”(missing syllable)的音步,故可在朗诵时适当延长。多余的音节可以举《失乐园》第6卷第167行为例:
Mini|st’ring Spi|rits, train’d |up in feast| and song:
梁实秋说《失乐园》每行10个音节,不够准确。这行诗同样是五音步,却有11个音节,第四个音步是抑抑扬格,但是由于“up”“in”拼写都很短,可以略读“up”,或者略读“in”,两者相加的时长与一个音节相似。缺失音节与多余音节在英语格律诗中均很常见,在朗诵过程中这种细微的差异对节奏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故而新格律体既然在学习五、七言诗对顿数的处理之同时,也借鉴了英语格律诗对音步的划分,就必然不可能再像中国旧诗那样有着绝对固定的节奏,它需要根据诵读的需要进行调整。新格律体诗行的顿数是一种适度的重复,相对于旧诗的“严格的重复”,它是宽松的,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现代感性”;相对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它又是规整的,较容易在作诗者与读诗者之间形成某种“视野融合”。新格律体既不像吴兴华、林庚等人追求与五、七言诗类似的均齐整饬,也不似自由诗那般完全凭空而设、另起炉灶。新格律诗是相体裁衣,是一种开放的形式,但又不是没有规律可循。
新格律体诗不但可以从西方格律诗与五、七言诗那里寻找依托,还可以从词体中借鉴节奏模式。卞之琳《谈诗歌的格律问题》一文并未提到词对于建立新格律体的意义,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虽然提到词的意义,但却认为词对于“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参考价值,是不如五七言诗的”。在笔者看来,词体对于建设新格律体同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很多新格律体诗表面上看去是移植了西方诗体,但实质上与固有的词体有着隐秘的契合。比如一首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的结构,如果不考虑押韵与对仗,就可看成一首《玉楼春》加上一首《浣溪沙》,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出过精要的分析。再如英国“利默里克体”(Limerick),每首共两节,每节五行,三长两短(第一、二、五行9个音节3个音步,第三、四行6个音节2个音步,一般为抑抑扬格),押韵格式是aabba。这种结构与词体的《少年游》也较为相似,比如柳永写过: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词共两阕,每阕各五行,一、二、五行稍长,三、四行稍短;上阕押韵格式aaxxa(x代表不押韵),下阕押韵基本相同(一般首句不入韵,但柳永常以平仄声韵互押)。徐志摩著名的《偶然》一诗既可看成对利默里克体诗的模仿,也可看成对《少年游》的借鉴: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 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中国古典诗一个题目下有几首诗,成为所谓组诗,这首《偶然》正可看作两首利默里克诗的组合。而如果从词体的角度来看,《偶然》一诗的结构像是一首《少年游》的上下两阕,可看成对这首词的格律的创造性转化。也正是由于在词体中早有这样相似的“隐性文本”(invisible text),这首诗才让人感觉流畅自然而不觉生硬。
新格律体借鉴五、七言诗相对简单,只要各行顿数一致,并有规律的押韵就可以了;而借鉴词体就复杂得多。如果单从上节看,词体会显得不那么有规律,但两节合而观之,则仍然有规律可循。新格律体从西方格律诗与五、七言诗那里主要借鉴的是诗行顿数的重复,而从词体那里则借鉴的是诗节的重复。词体远比五、七言诗丰富,倘从中找出一些适合新诗的体式,应该可以为新格律体的建设提供不少启发。
未来的诗体
20世纪50年代,朱光潜、王力、冯至、何其芳等人关于新诗格律问题有过广泛的讨论,他们都相信“新诗是一定会走向格律化”,并且除了格律的新诗外,“自由体的新诗也还会长期存在”。但遗憾的是,新格律体的探索和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早期20年代豆腐干式的新格律诗已经让当时的诗人对格律产生了质疑,50—70年代“新民歌体”的大量涌现更加深了当下新诗作者对格律的偏见。到了80年代,当中国诗面临着一个开放的创作环境时,自由诗迅速占据了主流。格律诗所走过的各种弯路使得新诗人愈加相信只有自由诗才是新诗的正途,代表着中国诗的进化方向。但当代新诗的自由化也产生不少问题,如使新诗接受范围日趋狭窄、接受程度日益降低等。张枣在90年代中期接受黄灿然的书面采访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读现代诗的修养。”这不一定只是激愤之语。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研究者都缺乏读现代诗的能力与修养,恐怕不仅是读者的问题,它同时也道出了现代诗在接受层面的困境。孙郁《新诗之路》一文的开篇就说:“缪钺论宋代诗歌时,引英国安诺德的话说:‘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证之于中国文学史,古代可以,现代则不太适用,原因是我们的现代诗还在幼稚的层面,不能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精神。”郜元宝《离开诗》一文也认为:“在杀死了真正的古典主义之后,中国诗人的情致一脚滑入了闻一多所谓的‘伪浪漫派’、‘伪浪漫主义’。他们没有传统,只有所谓的‘灵感’与‘个性’……中国当代诗歌的可悲正在于有诗人而无诗篇,诗人自恃的灵感与个性被无情地堵在语言之外。”他们的观点让人感慨不已,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代表了除当代诗研究者之外的文学研究者的一般看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新诗的自由化应该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自由诗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主导权完全归于作者,不考虑读者能不能接受或愿不愿意接受,夸大了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对立,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统一。克莱夫·斯各特(Clive Scott)对这个问题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评论:“在自由诗中,读者容易成为诗人的玩物,因为诗人的责任就是确定诗行;写出的是一个混种却迫使读者——如果他愿意读的话——接受这是一个纯种,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趣却又更容易破坏诗的好名声的行为呢?”每一位诗人都力图证明自己所构造的形式是独一无二、标新立异的,要求读者接受他所创作的既有别于传统格律诗与新格律诗、也有别于其他自由诗的独特节奏。比如有人分析,陆忆敏气质纤细文弱,于是她的诗也就形成“相当短促的句式,轻盈而能上升”;而翟永明的诗正好与之相对,是某类“深沉、忧伤和粗质的嗓音”。这些节奏都非常个体化,只能说是一种“情绪的节奏”,能为某个圈子内的特定群体欣赏,却不能在作诗者与一般读诗者之间形成“视野融合”。“情绪的节奏”,或作者自己的独特节奏,或只能为个别诗评家辨识的节奏,基本上等于没有节奏。卞之琳说过:“所谓‘思想的节奏’,‘感情的节奏’,要形成诗,并不能代替语言的节奏、广义的节奏以至狭义的节奏。”这句话大概就是专门针对这类情况而发。因为虽然心灵犹如一面镜子追求意义的丰富,希望照出宇宙万象的新奇与多姿,但是如奥登所言,耳朵却“较少渴望新奇,更欣赏节奏的重复”。为了要让节奏能够为耳朵接受,一般来说,格律诗总比自由诗更为便捷,它比较容易能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如卡勒说的,“形式格局意义的本身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阅读期待”。
更进一步说,自由诗如果要在听觉上获胜,仍然需要借鉴格律诗所遵循的重复这一法则。有识之士大多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即自由诗写作的难度要远大于格律诗。宾雍(Laurence Binyon)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自由诗)要想在没有格律的情况下成功写作,就需要比用格律写作具有更强大的灵感、更熟练的节奏和更严格的形式感,纪律规范不是更少,而是更为严格了。”除了运用各种叠词、叠句外,自由诗往往仍需要押韵,包括行内韵、行间韵、首韵、尾韵、叠韵(类似英语中的谐元音,assonance)。押韵本质上也是一种重复,如什克洛夫斯基说的,“不是因为韵是谐音,而是因为韵是重复——是回到前面已说过的词。韵脚似乎在诧异,为什么如此相似的词意义却不相同。在诗歌里,这种多种意义的联想的发挥与冲撞,是靠韵脚和诗节结构来实现的”。优秀自由诗的用韵往往更加丰富,更为多姿,可以根据诗情的节奏来调整用韵的变化。比如艾略特(T.S. Eliot)的《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常常是行内韵与行间韵并用,首韵与尾韵齐发,还屡用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押韵却常被当成是韵脚的“头韵”(alliteration,又译“协字”)。比如《四首四重奏·东科克尔村》第一部分第二节最后十行,用韵非常密集,又极为多样,仿佛让人听到了村庄中男女围着篝火舞蹈的节奏,也仿佛让人感受到日月推移、四季变更,人们劳作、交媾、欢娱、死亡的短暂的一生。从《烧毁了的诺顿》到《东科克尔村》,“时间”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选择了自由诗的确是选择了一种最为复杂的诗体,其创作难度远比格律诗困难,绝非像常人想象得那样率尔成章。自由诗一统天下的状况可能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逆转,但必须指出的是,自由诗终究不是诗体进化的终点,它只是一场运动。隆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说:
罗威尔常说自由诗的运动是“回归生命的突破”(breakthrough back into life),仿佛自由诗不是某一种诗的形式,而是超越了单纯文学意义上的一场运动。
自由诗是一场运动,不是进化的目的,更不是发展的方向。只要是运动,就会有终结的时候。戴望舒曾译过瓦雷里《艺文语录》,其中文末是这样一句话:“在一个一向作‘自由体’诗的文学世界中,一个倡制亚历山大体的人,一定会被当做狂人,而因此会做革新者的先导。”在当代中国,写作格律诗一定也会被认为是保守、传统,甚至顽固,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百年新诗史中,我们确实已经拥有了不少格律诗的佳品,从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到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再到食指的《相信未来》、江弱水的《原道行》,从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到冯至的《十四行集》再到张枣的《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都属此列,还有如戴望舒的《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余光中的《白玉苦瓜》等半格律体的杰作。我们不能明确说这些作品一定会是下一个时代“革新者的先导”,但是在诗史上,要求形式的解放与要求形式的规范,原本就是两种此起彼伏的思潮,当某一类型的诗体流弊丛生,往往会产生其对立面的反拨,两种相对力量不断的制衡方能构成中国诗发展的良好生态。
中国诗体的发展路径不能没有自由诗,它突破了格律诗所设立的规范,拉近了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当前时代所出现的新名物与新词汇。但诗体建设同样需要格律诗,它使浮于事物表面的语言渐渐沉淀、凝聚,使词汇与句子通过形式的淬炼不再如光影般转瞬即逝而逐步融入我们的汉语,丰富我们的表达。“自由”与“格律”也像是两种个性或两种才智在诗中的体现,一种趋向博放,一种趋向收聚。现代人面对世界时所产生的彷徨、孤独、焦灼,不仅仅是恣肆与张扬所能完全解决的,它也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与尺度性作为约束。如果说精纯的旧格律对某些人来说已然是一种严酷的外在标准,那么融会中西诗体的新格律则更像是诗人为自己创造的法则,它既有迷人的秩序,又有多彩的变化;它既独特别样,又似曾相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