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千里江山图》可以视为一部带有“先锋性”叙事姿态的谍战小说。孙甘露以类型文学的形式讲述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高层从上海撤离至瑞金的历史性事件。在小说中,孙甘露征用了多种文学资源,辩证处理了历史与虚构、青年与革命、信仰与背叛等多种话题。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千里江山图》兼顾了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与类型文学的可读性,也可看作孙甘露创作的一次成功转型。
关键词:先锋;谍战;历史;青年
作者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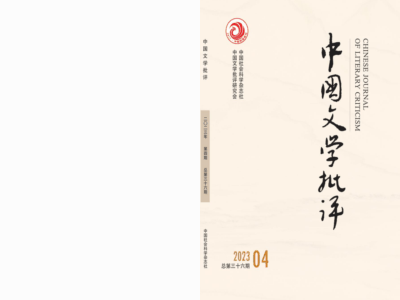
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大家总还是习惯性地把孙甘露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联系起来。在那个追求“形式探索”、语言变革的潮流中,孙甘露或许不是影响最大的,但其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能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从《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到《信使之函》,孙甘露在语言、叙述等方面不断寻求新变,尤其是《信使之函》把“那种‘感悟’连同它发生的感觉一并交付给语言,叙述的感觉已经为语言内在的诗性碰撞和外在的语言感觉所替代,语言的诗性碰撞激发了语言自由播散的连锁反应。”然而这种形式与语言的“极致”追求,也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戛然而止”。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场域中,先锋文学的主将们也纷纷“转型”。时至今日,先锋文学浪潮过去已经近40年了。在一次纪念先锋文学30年的会议上,那些先锋文学的主将们回首往昔,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度反思。苏童说先锋文学就是“裸奔”,而在格非看来,“支持你写作的那个氛围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写作,当年有支持先锋小说的东西都不在了。我指的先锋小说是要打引号。我们这代人,在从事文学实验的时候,背后支持它的力量突然消失了”。其实,所有先锋文学作家在作为潮流的先锋文学结束之后,都要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自己的创作“怎么写”。在先锋文学潮流中,经历过从“写什么”到“怎么写”洗礼的先锋作家,再一次遭遇“怎么写”的挑战。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也可看作他对先锋文学之后“怎么写”的一次文本回应。与先锋文学“晦涩”“难懂”的阅读体验相比,《千里江山图》可以算得上是“好读”的。

《千里江山图》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要将领导同志顺利安全地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历史事件。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故这项绝密行动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计划”,“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从小说的题材和内容上看,无疑是属于“革命历史题材”。但是,与大多数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讲述的并不是革命的“起源”问题,而是讲述革命“过程”中的敌我斗争,而且是在“隐秘战线”上的斗争。
如何在诸多既存“革命历史小说”中实现叙述的突围,是孙甘露在创作《千里江山图》前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题材的写作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前辈作家们写了很多,比如我们知道的《红岩》是一个示范性的作品。……也有不少作品虽然主题非常好、非常突出,但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些吃力。我觉得要突破一种比较概念化的写作,在形式上找到一种比较特殊的、跟这个小说的故事内容比较吻合的方式。我在想,中央特科和国民党党务调查科这么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以我们通俗讲的‘谍战’这样一种类型小说的方式来写作,应该是非常契合的。”
在写作《千里江山图》时,孙甘露依然在思考讲述革命历史的“形式”问题,这也可看作他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在写作“革命历史题材”或者“现实主义题材”时的“先锋姿态”。“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小说承载着文学的教化功能。但也正如孙甘露所言,一些题材很好的作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好的阅读感受。没有好的阅读感受,自然也难以承载文学的教化功能。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理,不同代际的人切入历史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以何种“形式”讲述“革命历史”,能让当下的读者走进那段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是作家写作“红色主题”时要考虑的前提。“谍战”作为一种类型文学题材,受众广泛,同时也与青年文化中流行的推理游戏密切关联。
小说的开篇没有过多的铺垫,直接进到紧张的“斗争”场景之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11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员秘密集会准备执行一项绝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但因内部出现了叛徒,走漏了会议消息,开会的现场已经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布控。一位地下党同志用自己的生命,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警报,一部分同志趁乱躲过一劫,但仍有6名同志被捕。这6名同志被押至龙华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千里江山图》并没有像同类题材小说那样,过多讲述国民党对革命者的严刑拷问,而是讲述敌人将6位同志以“囚徒困境”的形式分别审问,试图让他们在“隔绝”与“猜忌”中,相互“怀疑”,进而露出破绽,以便找到“千里江山图计划”的蛛丝马迹。但是,这种“囚徒困境”式的审讯收效不大,敌人很快就把6位同志释放了,让他们继续执行“千里江山图计划”,以期“放长线钓大鱼”。由此,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陈千里、叶启年等陆续登场,一场围绕个人“爱恨情仇”与民族大义的历史抉择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小说的叙事空间也从公寓扩展至上海,再扩展至南京、广州,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进行一场成功的转移与伟大的斗争。“从上海到瑞金,三千多公里,少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
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孙甘露一方面遵照类型文学写作的基本套路,用各种悬念和破局推动小说叙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以一种“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技艺,将类型文学的要素与细节尽可能复杂化。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渗透了“西施”作为卧底,这可算是叶启年的得意之笔。“真正”的“西施”卢忠德是叶启年的得意门生,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举办的职工运动讲习所,加入工人纠察队,后又在叶启年的安排下进入了公安局。在工会讲习班中,他利用工作的便利,将一些所谓的情报混杂着小道消息,说给讲习班的人。在经受了两年的考察后,他见到了中共广州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龙冬。卢忠德最后杀害了龙冬,挖出了龙冬的情报网,立下大功,成为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王牌,有了“西施”这个代号。“西施”如此重要,按照正常的情节设置来推演,这个“西施”一旦“暴露”,小说也就即将落幕了。但是,孙甘露在小说中对“西施”的情况做了一个交代——
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扬扬,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作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近投敌的叛徒。
从上面引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施”是潜伏在我们党内部的特务,这个情报已经被我们党掌握。从一般的阅读经验来说,“西施”作为潜伏特务的一个代号对应的大概就是一个人。但是在中共情报部门对“西施”的“复杂性”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个“西施”既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又像一个“新近投敌的叛徒”。这个“西施”可能有着“双面”的性格,也可能对应的是两个人。
引述的文字来自小说的第6部分,算是刚开篇不久。刚阅读至此,也很容易忽略掉这段文字里的“暗藏玄机”。国民党特工总部的副主任叶启年也意识到陈千里已经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内部被渗透了,便将计就计,让“西施”(崔文泰)去执行危险性极高的任务,以此来钓出中共的“大鱼”。但是,崔文泰很快就被党内的同志怀疑,林石“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林石的怀疑很快就得到了印证,“西施”崔文泰“暴露”了。“西施”崔文泰的暴露,是为了掩护“真正”的“西施”易君年更好地“工作”,让他在中共地下党内部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撬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直到最后凌汶付出自己的生命,揭露了卢忠德的“真面目”,“真正”的“西施”才浮出水面。在《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对“西施”的复杂化处理,让他成为陈千里、叶启年之外的又一条人物线索。“西施”一方面关联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的历史侧影,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现实”,“深度”介入了“千里江山图计划”。通过追索勾勒“西施”的前世今生,既可以见到“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与波澜壮阔;同时,也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隐秘战线”上与国民党的智勇较量,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在革命舞台“幕后”的奉献与牺牲,处处体现了革命与信仰的力量。
在《千里江山图》中,类似于“西施”的复杂化处理,还见于小说中的一些其他情节。有研究者认为,《千里江山图》的这种叙述,摆脱了此前一些谍战小说模仿“狼人杀”等游戏的基本结构方式,“利用类型文学的某些固定套路,为读者设置了明确的阅读预期,接下来却又出人意料地将这种预期打破,似乎与读者开了个善意的玩笑”,是“反套路和反类型文学”的。革命、历史、谍战、先锋,在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用类型文学的讲述方式汇聚在一起。孙甘露启用一种新的“形式”召唤起精神与信仰的力量。

孙甘露在接受访谈时说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个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让人想起来就很激动。在《千里江山图》中,那些青年革命者塑造得尤为成功,读起来也让人心潮澎湃。青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所着力塑造的一类形象。只是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青年形象不同。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与人生选择,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点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千里江山图》就讲述了革命年代里青年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分化。
国民党特工总部的副主任叶启年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世界语教授,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一些热爱知识、满腔热忱的青年,其中就有陈千里。这些青年开始是崇拜叶启年的博学——
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语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那里。
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但他们没有看到叶启年的心里还“装着历史”,陈千里也逐渐发现叶启年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发生转变,他们的叶老师开始看戴季陶的书了,参加戴季陶组织的秘密聚会。悄然的转变,自然会带来诸多的分歧——
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阅读”对陈千里的影响。阅读书籍的变化带来思想立场的改变,在此前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曾出现过这类情节与内容。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在一起的时候,余永泽和林道静谈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涅、拜伦的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冯沅君的《隔绝》,等等。余永泽与林道静讨论的这些书籍都是张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女性解放和浪漫爱情的。而当林道静结识了卢嘉川之后,她读的书就成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阅读的变化,让林道静从一个“五四”青年逐渐成为一个“革命”青年。这种知识青年在思想立场上的“变化”与“转折”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是一个常见的情节。这似乎已经成为此类写作的一个“传统”,《千里江山图》在写陈千里这位知识青年的“转变”时,显然也继承、遵循了这一传统。
但也正如艾略特所说:“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曾经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出场的孙甘露,显然不会止步于简单地追随此前的写作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中,知识青年的转变往往离不开一个革命者的指导和引领。在这样一个革命启蒙的结构中,引领者往往都是男性,而被引领、被改变者常是知识女性。但在《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改变了这样一种革命启蒙的结构。叶启年的女儿叶桃到北平读书时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成为一个革命者。是她启蒙了陈千里的革命意识,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了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她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
女性革命者引领了男性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孙甘露在此“改写”了此前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的革命启蒙的结构。艾略特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不能单独地呈现出他的意义。他的意义与价值,是在与以往的艺术家的关系中实现的。《千里江山图》既承继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小传统”,同时也在对这种“小传统”中的一个典型结构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实现了此类写作的一个“新变”。
在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往往都会写到一些女性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兼具“性别”和“知识分子”双重属性,参与了中共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但是,她们往往在“身体”和“思想”上呈现出“软弱”的一面,身体上的弱不禁风,是思想立场上软弱、动摇的“客观对应物”。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豆》中的江玫、《在医院中》的陆萍等人物角色。当然,这类女性知识分子不仅存在于讲述革命“起源”与“进程”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同时,也存在于讲述革命胜利之后,即革命“第二天”的一些小说中,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赵慧文等。这些知识女性在“身份”和“思想”上的“状况”与“转变”也构成了女性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之间的互文与张力。
在《千里江山图》中,除了叶桃之外,还有一位知识女性应该受到关注,就是凌汶。凌汶的丈夫龙冬既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广州的负责人。凌汶与龙冬在五卅运动中相识。后来,凌汶知道了龙冬牺牲的消息。但是,凌汶总是忘不掉龙冬身上的点点滴滴,而与她配合工作的易君年(卢忠德,就是杀害龙冬的特务),在工作时和龙冬简直一模一样。但是后来,敏感的凌汶又隐约察觉到两人“越比较越不像”,“她知道易君年对她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她,如果它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地摆在自己面前,她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此时,凌汶并不知道是易君年杀害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凌汶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力和智慧,发现了易君年的过去,这让易君年始料未及,“他确实没料到凌汶会想起那照片。给凌汶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她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她看,还告诉她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凌汶用她的生命,进一步将“西施”易君年暴露出来,这也更坚定了陈千里对易君年的怀疑。
我们从凌汶身上,并没有看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那些女性知识分子的摇摆以及后期在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上的“转折”,也没有看到“大革命”时代知识女性的软弱、动摇与幻灭。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知识分子与女性革命者的完美融合。这两种身份的融合碰撞出了巨大的精神动能与思想智慧,让凌汶在革命的征途上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与冷静。孙甘露对凌汶这个形象的塑造,显然也是对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之后“怎么办”的小说,在女性知识分子人物塑造上的一种调整与超越。这种性别、知识与革命历史从起点上就凝结在一起的女性知识分子丰富了这类题材写作中的人物群像。
《千里江山图》中关于青年的书写,对当下的写作也具有一种借鉴与启示意义。在当下的写作中,青年形象往往都是“失败青年”,缺少青春的力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青年主人公的消极认同日趋严重(比如‘失败青年’大规模出现);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渐淡漠,在丧失介入性的同时退居‘宅男’‘宅女’状态;青年的文学形象逐渐告别以‘新青年’‘新人’为代表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主流面貌”。为何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是“消极”的,缺少“力量感”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些青年与时代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连接,对生活缺少“介入性”。而《千里江山图》中的青年,则是与“大时代”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关联,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正如小桃源中的孟老在打断叶启年说话时所言:“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这些青年将青春的力量投射到伟大的信仰之上,激发出了巨大的历史动能。《千里江山图》借助这些青年呈现出的“历史意识”与“当下性”,重新唤醒了青年的“力量感”与“时代性”。

《千里江山图》在地理空间上涉及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但其主要的地理空间还是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千里江山图》也是关于上海的一部作品。近年来关于上海的书写还是以“摩登上海”为主。这类书写侧重于上海这座城市的“都市”属性和“国际化”属性,外滩、舞厅、咖啡馆、公园、电影院等建筑、公共空间是其外在标识。孙甘露坦言并没有见过“摩登上海”,不知道“摩登上海”是什么,也想象不出来。与这种“摩登上海”书写不同,还有一种左翼视野下的上海书写,此类书写通过对底层苦难生活的叙述,重在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的罪恶。《千里江山图》中关于上海的书写,则在这两种典型的上海书写之外另辟蹊径,孙甘露写的是一种“日常上海”,正是在这种“日常上海”里,孕育着青春的激情和革命的力量。
作家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与《千里江山图》中上海书写的关系:“我出生在上海,一直就在这里生活。……书中写到的很多地点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比如书中主角陈千里的弟弟陈千元的住址,实际上就来自我读书的路线。从澄衷中学也就是我的母校开始,四年时间里我沿着现在的唐山路,在公平路/唐山路那个路口上,一直经过下海庙,然后是提篮桥监狱的那个围墙,再一直经过书中描写的陈千元租住的地方,穿过霍山公园,一直到临潼路、到榆林路回到自己家。那个时候没有分初中、高中,就是中学,中学四年我每天来回一遍。虽然都是很简要地写,但我对这个环境是非常熟悉。”在“摩登上海”和“左翼上海”之外,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写的是“日常上海”中的“革命性”。在小说中,有一段写女地下党员董慧文的父亲,让女儿请陈千元来家里吃饭。董慧文的父亲是沪上大厨,政商两届的一些人都喜欢她父亲做的菜,时间久了自然也会有些交往。小说中关于这部分的描写,精妙简练,陈千元到了董慧文家里,直接看到的就是客厅——
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中间放了圆台面,客人加主人只有三个,放了三把椅子。圆桌上几只小碟,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 醉鱼,加上一碟什锦菜。拌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 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烫好的绍酒,董师傅却仍在后面厨房。
精致的菜肴彰显了董慧文家境的优渥。直到董慧文被抓进了龙华看守所,董师傅才意识到家里出现了共产党。孙甘露在这种“日常性”的书写中,埋下了“革命性”的伏笔。这种叙事方式,也正是孙甘露在“摩登上海”和“左翼上海”之外,探索一种书写与上海有关的革命历史的新形式。“《千里江山图》凸显空间因素化解旧模式,却并不沿袭新套路。小说并不将时间与空间截然分立,而是调和历史世界和‘生活世界’、历史时间与日常时间,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却将其聚焦在为数不多的各有其职业、公开身份、经历和性格、心理的人物身上”。
在《千里江山图》之前,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潮流出现以来,大都是以民间的、个人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革命与历史。而在此之前的“革命历史小说”,则是从一个与历史潮流相一致的方向上,对革命历史的起源与过程进行书写与阐发。这种创作的模式与类型,是对历史进行了一个本质化的、逻辑必然性的理解与阐释。在这一类型的小说中,一些与历史潮流和逻辑必然性无关的内容,是无法进入到这个“宏大叙事”之中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小说,往往会不大生动,阅读感受不佳,人物塑造存在概念化等问题。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与“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相反,它以个人化、民间化的立场,采取不一样的叙述姿态,呈现出“宏大叙事”之下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细节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修正”与“补充”。《千里江山图》“既不遵从既定的革命历史叙事规范,也不戏仿它们”。孙甘露重新回到以“庄重”的姿态书写革命历史,但其叙述历史的形式却与“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同。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在寻常百姓中召唤革命的力量。

《千里江山图》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原型”的,这种历史感极强的写作,自然要注重叙述的“真实性”问题。孙甘露为了写这部小说,不仅专门到龙华纪念馆参观、查阅资料,还翻阅了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量历史文献和报纸杂志,“把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按时间表全部都排出来了,阴历的、阳历的,以及在这前一两年上海是不是发过大水,包括当时的报纸广告,这些东西的时间全部都是排出来的。陈千里到上海,船在吴淞口停着,那个水文资料我都查过”。当然文学写作与历史写作不同,这么多的资料如何处理,如何进入到文学叙述中,变成小说的一部分,是作家要考虑的问题。孙甘露用大量的历史细节或构筑或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世俗生活”和“物质世界”。这种“历史性”的构建,营造了小说叙述的“真实性”基础。但是,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的本质还是“虚构”。在“虚构”中的“真实性”不仅要与历史趋势和历史细节“相符合”,同时也要“符合”小说情节和人物的需要。为了后一种“真实性”,小说在“虚构”中可以对一些历史细节进行“改动”。《千里江山图》中写到易君年和陈千里接头时的场景,孙甘露在这里对历史细节做了一个小的“改动”——
比如我说个细节,里面讲到易君年跟陈千里接头的时候,在卡尔登戏院门口。当时国际饭店还没造完,还有脚手架。跑马总会原来也有,也是后来翻造过,那个年代是差不多都能翻造完。虽然小说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但是作者要了解、掌握这个情况。然后是卡尔登戏院正在上映什么电影,这个我查过报纸,也就是当时《申报》的广告,说意大利的一个歌剧团在这里上演歌剧。但是剧目被我换掉了,换成了《图兰朵》。《图兰朵》开场时,合唱队唱道:在图兰朵的故乡,刽子手永远忙碌。
此处的“改动”,显然是为了更贴合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关系。易君年是革命的叛徒,他先是杀害了龙冬,化名易君年来到上海,成为打入组织内部的“西施”。后在被凌汶发现了真实身份后,他杀害了她。对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小说在讲述陈千里与他接头时,用上了《图兰朵》的开场,“在图兰朵的故乡,刽子手永远忙碌”,与情境和人物身份再贴合不过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虚构”的“真实”,比历史更“真实”。像这样一种将历史事件、社会事件作为“原料”的写作方式,如何“把所有这些素材,所有这些配料转化成文学……如何借助语言把它们变成想象的现实”?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以“虚构”的“真实”将历史文献、社会资料借助有先锋姿态的语言风格和叙述形式呈现出来,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想象与历史之间构筑了一种“历史性”和“认同性”的“真实”。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杨琼 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