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今天的艺术形式与现象面前,艺术生成的表述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创作者所接受和使用,并提供了新的艺术哲学语境。生成的哲学语义涵盖事物的创辟发生,也具有对事物变化转易过程的解释力。中西艺术精神和美学智慧都强调艺术生成过程的生命意涵。在新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艺术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系统,艺术生成依赖实践活动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无限生成过程即艺术品本身,也是作品的生命系统本身。以生成言说今天的艺术实践,并未削弱人的主体性,反而正彰示了实践过程中人的自由活动与自觉意识。
关键词:艺术生成;生命育成;生命系统
作者朱俐俐,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430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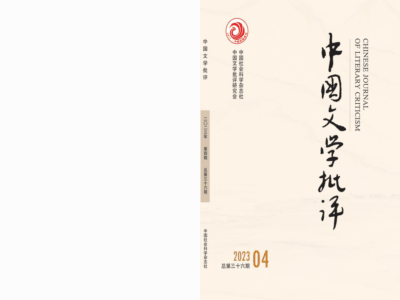
艺术生成是一个近来得到较多关注和使用的流行词,在某些语境中被用以替代艺术创造。现代艺术的出现与发展挑战了传统艺术创作与批评思想中的创造观念。在面对当代包含现成品艺术、交互艺术等在内的具体的新艺术形式、运动、现象时,创造一词常常会因艺术活动缺乏对材料的赋形,或倚重不同要素间的对话与影响而缺乏解释力。这促使我们反思保持使用创造一词之惯性的必要性。那么,为什么是生成?生成一词已以多义的外观在中西哲学的领土频繁出现,在美学与艺术领域,也不乏对艺术生成一词的应用。但前人对它的接受往往缺少对为何要使用它和为何可以使用它的论证。基于此,本文将考察生成概念的哲学语义与语境,以及在艺术问题上的解释能力,并结合一些新艺术现象的发展背景,展呈在艺术活动中使用该术语的合理性和在某些语境中的必要性。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反思艺术活动中生成的主体边界、实践机制、艺术之物性等问题,还可以启发我们重思术语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转义与流变。
一、造物推移:艺术“生成”的哲学基础
在中文中,“生成”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产生与发生,即某物原不存在,经过制作塑造活动获得了实在性。在这层含义上,“生成”一词的语用范围与创造一致,即造物。二是已存在的某物因为某些动因得以进化转易,在变动不居中获得新的身份,拥有新的意味,即推移变化。中西方对事物生成的哲学思考都涉及这两层含义。这些思考最早从宇宙论出发,历经追补充裕,为人们讨论艺术的生成提供了哲学基础。
古希腊的生成论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当时人们对事物生成的根源的构想,既有神创世界的想象,又有抽象转化的构思。对不可见、不可知的神灵创造了世界的想象与寄托,塑造了原始人对世界的认识。早期希腊罗马思想家们围绕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一问题,曾给出过一些朴素的答案:是水,是气,是火,是“数”,是“一”,是“道”,等等。这些答案反思了早先的神创万物说。例如,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BC544-BC483)相信神是存在的,且比人更美更智慧,但世间万物不是由任何神创造的,万物的生灭出于火的“转化”,认为构成宇宙生命的正是变化转化。同时,这些回答也倾向于去把握神话与物质本原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像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认同水是本原的人会认为,在将海神夫妇视作创世父母的神话里,其实就有了将水视作世界本原的意思。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更早的思想家在言说事物的生成(出现、发生)时,使用的词是 (genéseos),
(genéseos), (génesis)。柏拉图认同赫拉克利特关于现象世界处于变化中的观点。在《蒂迈欧篇》和《斐利布斯篇》中,柏拉图讨论土、气、火、水等不同元素间的转化影响,变易的过程与目的,等等,他所说的事物生成,既有事物发生、出现的意思,又有事物变化、变动、运动之义。世界灵魂能够自己运动,也促使其他事物运动。柏拉图还认为,无数理念构成了有理性的宇宙,理想的秩序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他的宇宙生成思想中的宇宙理性观念和理念观念,令柏拉图主义自然哲学强调在“在”(being)和“成”(becoming)之间进行二元划分。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但其“形式”是稳定的。事物的生成和衰亡是一种实质性的运动,此外还有数量上的、空间位移上的运动变化,以及物物转化。他还在《论生成和消灭》中评说过早期自然哲学家们对生成的理解,这些思想家们在生成是否是质变的问题上观点不一,有的人认为生成即质变,而且认为被生成的东西就是被质变,而如恩培多克勒(Empedocies, BC493BC435)等人则认定生成与质变不同,因为他们假定事物的质料多于一种。在这种对生成与质变关系的思考中,可以看到早期哲学家关于对象变化与产生另一实在间的区分。
(génesis)。柏拉图认同赫拉克利特关于现象世界处于变化中的观点。在《蒂迈欧篇》和《斐利布斯篇》中,柏拉图讨论土、气、火、水等不同元素间的转化影响,变易的过程与目的,等等,他所说的事物生成,既有事物发生、出现的意思,又有事物变化、变动、运动之义。世界灵魂能够自己运动,也促使其他事物运动。柏拉图还认为,无数理念构成了有理性的宇宙,理想的秩序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他的宇宙生成思想中的宇宙理性观念和理念观念,令柏拉图主义自然哲学强调在“在”(being)和“成”(becoming)之间进行二元划分。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但其“形式”是稳定的。事物的生成和衰亡是一种实质性的运动,此外还有数量上的、空间位移上的运动变化,以及物物转化。他还在《论生成和消灭》中评说过早期自然哲学家们对生成的理解,这些思想家们在生成是否是质变的问题上观点不一,有的人认为生成即质变,而且认为被生成的东西就是被质变,而如恩培多克勒(Empedocies, BC493BC435)等人则认定生成与质变不同,因为他们假定事物的质料多于一种。在这种对生成与质变关系的思考中,可以看到早期哲学家关于对象变化与产生另一实在间的区分。
在西方现当代哲学中,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等人都围绕生命及其他事物的生成进行了集中思考,他们的论说凸显了变化之义。在《创造进化论》一书中,柏格森受叔本华的影响,将现实的本质视作一个绵延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处于变动不居和连续不断的生成状态中,世界真正的存在方式即个体的绵延与生命之流,生物是在不断变化的生命状态中得以演化的。与此同时,他认为这种绵延意味着创新和“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柏格森提出美和艺术也是在无尽的时间绵延中生成的,它们身上具有某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可见,在柏格森看来,事物的变化和产生是密不可分且相互蕴含的,变化是生成过程的根本特质和永恒状态,新形式的产生则是该过程的伴随态和阶段性特征,创造蕴含于生成中。在关于主体、实践、媒介等问题的思考中,德勒兹则直接以生成为名进行了概念上的突破。德勒兹强调差异与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这种生成是区别于存在(being)的变化,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它们最为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也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进行生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如生成生命(becoming-life)、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生成女性(becoming-woman)等。另外,生成也是胡塞尔、德里达等人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德里达在其著作《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中对胡塞尔的生成思想进行了重新阐发。
在中国哲学思想中,物的生成也是一个重要话题。同样的,古人对万物生成的认识既包含神创论,也包括其他抽象的宇宙论思想。在中国早期神话宇宙论里,盘古的开辟使天地摆脱了“混沌如鸡子”的状态,由此万物生。这种神话宇宙论融进艺术思想中,便有了清代石涛“出笔混沌开”(《为友人写春江图》)的绘画思想,后者正是在征引早期宇宙观的基础上,将艺术活动的主体思考赋予人的。与这种凸显创造主体的神话创造论不同,许多以“生”为核心的哲学思考着意于展示事物自身的变化规律与生长能量。
中国哲学重视变化。在众多宇宙论哲学言说中,对关于艺术生成的思考影响最大的是《周易》展现的“生生”哲学。“《易》者,易也”,《易传》概括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对“生生”的理解有生而又生、不断变易之义,也有创生生命之义,这样的义理构成了《周易》生命哲学的基础。“生生”哲学探讨人与天/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强调生生不息的生命义涵。另外,《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里相生、相成的思想,不仅体现相反者相成的辩证哲学,更体现出对对象之间的连贯性与转化关系的思考,该思考也体现在《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表说里。此外还有“阴阳和而万物生”、万物来自五行元素、万物生于虚空等生成观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宇宙观,是后来的美学与艺术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今天许多哲学学者在生成思想上有进一步尝试,比如,金吾伦以生成论的宇宙观批驳了预成论的不足,指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和种种定律都经过了生成的过程;段德智以“主体生成”探讨了主体性哲学;鲁品越从物的相互作用入手,在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深层生成论”的世界观;隽鸿飞展示了生成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在文化哲学范围内的应用。这些尝试在延展生成论思想的同时,展示了生成一词在哲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哲学各领域对生成的言说之丰富和对它的使用之频繁,甚至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生成论的过度使用。可见,生成一词已然经历过了广泛思考与接纳。
总的来说,这些对事物生成的论说,既关注事物的产生也关注它们的变化。人们对生成一词的使用,在凸显事物自身的演变移易的同时,并未湮没其创生之义。这些哲学思考,为今天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哲学进一步接受和反思艺术生成的表述和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二、生命育成:“艺术生成”的内涵与动向
生成宇宙观迁移到艺术与美学中,便有了艺术作品和艺术哲学思想中的生长、变化、生动、节奏、绵延等时空观念与生命意识。艺术的生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有机生命体之孕育成长的比拟同化。中西某些艺术哲学思想在艺术具有生命性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同时,新的艺术现象的出现也使得中西艺术思想不得不面对一些共同的挑战。
西方对艺术及其生成过程的生命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艺术生命的生成问题上留下的关键遗产在于,他们将文学作品比作活的有机物。这一思想随后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 204270)那里得到发扬。普罗提诺指出,艺术是美的承担者,并对自然所缺乏的东西作补充。他的意思是,艺术活动能够像自然创造那般进行孕育。新柏拉图主义在艺术上的自然观念,影响了后世宇宙论视域中的许多艺术创作与批评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世纪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艺术宇宙观。爱默生认为艺术作品类似自然,是有机的,是“自然的一个新作,犹如一个人似的”。
这种艺术生命观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达到了高峰。自18世纪开始,艺术创作与想象、天才和虚构紧密相关,人的艺术行为不是在了解和遵循规则以及练习技艺,而是在自由创造,艺术创作被视作创生出了新的宇宙。这些艺术宇宙生成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对作为有机体的艺术作品之生成的构想。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 1683-1765)在随笔集《试论独创性作品》中将艺术创作比作有机体的孕生:“独创性作品可以说具有植物的属性:它从天才的命根子自然地生长出来,它是长成的,不是做成的。”杰拉德(Alexander Gerard, 1728-1795)在《论天才》中也将天才的创作比作植物的生长。艺术作品在他们看来是具有生命力的、能够自我生成的东西。康德以降,对独创性而非模仿,对天才、灵感而非技艺的重视频繁进入思想家和创作者的观点中,许多人将创作艺术作品与孕育有机生命做了深层次的类比。在强调天才、独创与想象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创作被视作像育成有机生命那样的活动过程。例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认为艺术规律是有机的规律,艺术家创造第二自然,好的艺术作品“是一件精神创作,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同一个精神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他和同时期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都持有一种有机论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从人与自然的整一中生长出来的。又如,奥·威·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区分出有机形式与机械形式,指出艺术形式是“从内部展开自身”的有机的形式,机械形式不具有这种有机性,“当形式仅仅作为一个脱离其本质的偶然的附加物,通过外在影响而被注入一种材料时,这种形式便是机械的”。此外,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还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一种自身从内部生长发展的生命力,在他的有些剧本中,“一切都是生长(growth)、演化(evolution)、生成 ”。20世纪符号论美学中也有将艺术生命与人的生命进行同构的思考。所有这些观点都在比拟艺术活动和生命育成的基础上,重视艺术实践和作品内在生命的生长、演绎、运动等。
”。20世纪符号论美学中也有将艺术生命与人的生命进行同构的思考。所有这些观点都在比拟艺术活动和生命育成的基础上,重视艺术实践和作品内在生命的生长、演绎、运动等。
中国学者对艺术之生成的思考,根植于早期哲学思想,尤其是“生生”的生命哲学。在艺术创作和批评领域中有对“生气”“生意”“生机”“生趣”“生动”等的审美追求。作画上要求外师造化,“格法本乎自然,气韵必全其生意”,这就体现出“生”这种观念在中国艺术精神与美学精神中的关键地位。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是“天地蕴,万物化醇”这种“生生的节奏”,中国画的对象是“生生之气”,艺术中有“纵身大化,与物推移”的生命观,这便受到了“生生之谓易”的影响。宗白华还总结道:中国绘画拒斥“板、刻、结”,书画既是空间单位,也是生命之流,艺术应当“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可以看出这一思考也受到柏格森生命之流观念的影响。方东美从中国哲学精神出发,博采怀特海过程哲学等西学思想,以“生生”解释宇宙生命的创进完成过程,概括人类的生命情调和艺术理想。他提出,先秦至汉的思想家采信“万物有生”的哲学见解,“道生一”之“道”即最先的“能生”(begetter),能生产生“所生”(begotten),所生又生能生,因此道中有生生不已的创进生命。他将中国宇宙论中的“生”的要义概括为“育种成性”“开物成务”“创进不息”“变化通几”“绵延不朽”等,认为生命的运能、创进、机趣和创造力都是无穷的,在连续的时间之流中,创造性的生机能够透过绵延为生命赋形。方东美将这种不断带来创造的“生生”对译为“creative creativity”,即强调新的形式与结构秩序的创生会孕生更多生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能够与宇宙物质融会浑成,“一切至善至美的价值理想,皆可以随生命的流行而充分实现”。方东美对“生生”的重视和运用,影响了曾繁仁等人对“生生美学”的提出和思考,后者用该术语去概括天人相和的中国传统美学智慧,将其应用于对艺术的品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机生成”思想去构想城市美学以及美学与生活的融合。
在今天的国内艺术理论领域,已有不少学者使用生成一词去思考艺术创作与批评问题。总体来看,这些思考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尝试总括式地探索艺术生成过程的机制、特征、要求等。例如姜耕玉认为,来自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潜能”是艺术生成的根据,艺术生成过程的实现体现在反馈和对话上;张法关联不同文化语境,将形式美的根本归于人与宇宙的同一性,以此分析艺术生成的原型;卢文超提出艺术在差异的逻辑下进行了自我生成,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论说了艺术在与其他事物的差异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的体现等。另一类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大多通过艺术实践考察人的美感生成问题。例如任海探讨了在对社会参与式艺术的鉴赏中形成的生成式审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讨论,也常常会在行文中采纳生成的表述,并至少涉及造物或推移其中一层含义。总的来说,“生成”一词在艺术理论中的语用基于其哲学基础,并且已被用于和适用于普遍地讨论作品的产生与变化。
现代以来,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的出现,启发我们回望生成的内涵,思考艺术生成的新特征。传统的艺术创造/生成论为讨论艺术形象与意义的二元生成提供了钥匙,而现当代艺术现象的发展要求人们持续反思艺术品的性质。对艺术生成的考察除了要求人们关注作品的形式和意义外,还常常要求人们从艺术品之外的因素出发,关注作品对自身艺术身份的获取。这呈现了今天的艺术生成在层次上的错综性。当然,无论作品的生成有多少层次,最核心的仍是作品的意义。
不同艺术形式与现象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有其自己的生成轨迹,具体作品的生成机制要求更具区别性的分析。随着新的语境的出现,艺术的生成还有更多形态,人们对艺术生成的文学与哲学探察还有更大空间。
三、“生命系统”:艺术生成的当代演绎
艺术生成过程和艺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流动而复杂的。在艺术自律的转变和要求下,以及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文学与艺术文本的意义之生成是相对独立的。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者只解读分析文本的内部意义,解构主义的兴起使得文本的意义更加开放,接受理论则强调“读者的崛起”,主张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主观性的交融——作品的生成逐渐被锚定为交流互动的结果,艺术家无法挣脱文本意义在交流中被阐释、补充和误读的命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交流形成了共同的“意义生成体”。作品的生成不是艺术家凭借天才、灵感与想象的个人创造,而是演变为多要素干预与集体思考的结果。随着近年来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艺术欣赏者与作品和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在方式和程度上又有了变化,人们在考察作品生命的生成性时,需要考量更多要素。一些研究者尝试为新语境下的文学艺术活动归纳出新的范式结构,并为其绘制知识图谱。这些尝试准确地把握到,新的艺术活动不是只突出艺术家或欣赏者或文本内部意义,而是更一般性地展示出各要素之间互动的随机、自发、多维并行的网络化过程特点。如果说,接受理论中的交流较为迟搁、曲折和单向,指向欣赏者与已生成的文本的对话,以及欣赏者与艺术家的跨时空交流,那么,今天新媒介技术艺术活动中的交互则更为即时、直接和多维,艺术家之外的其他要素主动、直接参与作品外在形式的生成。代表性艺术现象是交互艺术,也涉及狭义的生成艺术等。这些作品呈现为新的“生命系统”,它们的生成具有浪漫主义者眼中创作活动的非理性特质,同时由于媒介技术和欣赏者的即时介入而显得更为随机混杂,展示出了与单向孕生的艺术形式不同的特征,启发人们重思艺术生成的机制和艺术概念的边界问题。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艺术实践者尝试用计算机装置进行影像创作。其中有不少人机互动作品。许多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生命育成的观念。代表性作品是克里斯塔·佐梅雷尔(Christa Sommerer) 和劳伦特·米尼奥诺(Laurent Mignonneau)的《交互式植物生长》,这一作品结合了生物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知识,具有隐喻意味。作品使用了几株真实的活体植物,邀请参与者与活体植物互动,互动过程会通过电子信号在电脑显示屏上转化为虚拟植物的实时生长,这种虚拟生长的情况完全取决于参与者与植物的互动。两位作者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装置所生成出来的艺术图像是变化着的,是不可预测的“生命系统”(Living System),参与者“可以停止、开始、继续、变形和控制虚拟植物的生长,并以意想不到的组合培育出新形式的植物”。在文章中,生命系统的概念被用来指涉生成出来的装置图像,这些图像是动态的、无法预测的,反映出观众与装置互动过程中的动作及其速度、方向等变化。使用这一思路的互动艺术装置并不少见,同时期法国艺术家米歇尔·布雷(Michel Bret)和爱德蒙·库绍(Edmond Couchot)的作品《蒲公英》也具有代表性。在传感器、摄像头等外接设备的辅助下,作品会根据欣赏者的动作、力量以及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等因素生成形象,屏幕中蒲公英的飘散形态会随欣赏者对传感器吹气的力量和方向随机转变生成。这两件作品都可以被看作互动艺术的生命性的直观外化体现,都将艺术作品的生命与有机生命进行了隐喻式的同构。
事实上,佐梅雷尔和米尼奥诺所说的“生命系统”这一概念,并不仅限于解释他们的那件作品及其后续进展,还更广泛地适用于分析、阐释当代的交互性的艺术。生命系统不仅是生成出来的变化着的图像,还更可以被看作整个行动整体。在这个行动整体中,参与交互的每个要素都能够影响阶段性生成的图像(在文学性作品中,则是情节)。图像是不断生成的,行动也是不断生成的。根据欣赏者对作品生成的参与程度与互动强度,当前的交互艺术可被大致分为两类,弱交互类和强交互类。这些艺术作品的生成过程,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也是不同的。在技术介入较浅的作品中,比如国内正兴的实景体验情景剧这类实景互动型艺术形式中,人际互动远多于人机互动。如果我们将作品看作植物,那么这类作品既定的叙事框架与情节设计是其根茎,使作品生命形态相对固定,不论观众如何改变观看顺序或与演员互动,故事的基本走向和总体结构都有迹可循,整个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是较为稳定的。而在技术介入较深的作品中,生命系统的生成情况要复杂一些。比如,由故宫博物院策划的《清明上河图》3.0版,在多种数字技术的辅助下,画中人与物得以“复活”,观看者也可以“步入画中”,感受古画中鲜活的生命和生动的生活。在这样的作品中,设计作品的艺术家、技术与设备、观看者等,都是艺术作品生命系统中的关键要素。
这些要素在生命系统的产生和变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原初的那个作者,尤其是技术深度介入的作品之作者,只播下了种子。技术扮演着灌养植物的水的角色,决定作品的生灭,同时,它进入作品的肌体,化为整个艺术有机体的一部分。不论是哪一类、哪一型作品,交互艺术的生成都需要通过欣赏者成为艺术装置的一部分来实现。欣赏者是作品这株植物生长的养分元素,影响植株的长势形态,欣赏者不在场,则作品生长受阻。正如洛佩斯(Dominic M. McIver Lopes)所指出的那样,欣赏者的交互行为塑造了“交互实例本身的特性”。作品的无限生成过程就是艺术品本身,既是它的身体又是它的生命意义,“互动本身成为审美对象”。艺术这种生命系统是在变化着的时空中生成的,而不是在确定的时间节点或空间方位被制作出来的,只要生长要素齐备,它们就具有生命力,可以在变动不居中自我生成。
新的技术还孕生了生成艺术(generative art),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关于艺术的生命性的讨论。如今人们讨论的生成艺术往往有特定指涉,泛指数字时代基于计算机图形学发展出的作品及其创作方式,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近来发展到常常特指由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生成或参与生成的数字作品。AIGC在应用层面已经是高效的生产工具,其生产机制在于计算摹仿。工具自身不具有生命,借助它完成的图像与文字作品,或许能够短暂显示出现象上的新异性,看起来具备生命性外观,但其实并无生命整体的有机本质。
总的来说,在术语表述上,艺术生成凭借其生成论哲学基础,和在文艺思想中的生命意涵,适用于对新艺术现象进行文学描述和哲学阐释。在新语境下,“生成”一词不仅有益于人们反思智慧的能力边界,应对不断迭变的工具,对艺术实践过程的可能性保持开放,还关注艺术本体,重申何为艺术的论题,提醒人们艺术仍是一个语义流动的概念,帮助完成对今天的艺术概念的必要扩容。
结语
艺术生成,既含蕴了艺术世界在宇宙论意义上的发生,又呈现了艺术生命的形式与意义在有机论层面上的流动转变,还令艺术活动能够融会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命境遇。中西方对艺术生成的使用,各有哲学基础,也能够在各自的艺术精神和美学智慧中找到深厚的思想积淀。面对由新媒介技术深度介入所促生的新艺术现象,艺术生成所蕴含的生命意涵,能够保护和彰显人的自由的能动作用,固定媒介技术的工具性。在今天,艺术生成的表述不仅并未削弱创造观中的人的主体性或主动性,还恰恰尤其能够突出艺术实践过程中人的自由活动。在面对新艺术现象时,很多人保持使用创造一词的惯性,有时是出于对该词最初的神圣色彩的有意移用,即愿意相信和希望凸显人的力量、想象与自由意志。这其实与生成的含义并不矛盾,且“生成”一词的包容性更强。艺术不是对更高级的东西的模仿,也不是为了捍卫教义或强化皇权,它有自己的价值和不息的生命力,其自身便具有成为尺度的可能。此外,在艺术生成的过程中,人也在深刻变化,人生成艺术,艺术也生成人。在艺术生成过程中,通过对艺术的理性判断和审美判断,人可再生为一个具有审美智慧的新人。当然,未来艺术世界的新现象或许还将给生成的语义与语用带去新的挑战,那便需要交由将来的思想者去面对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 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