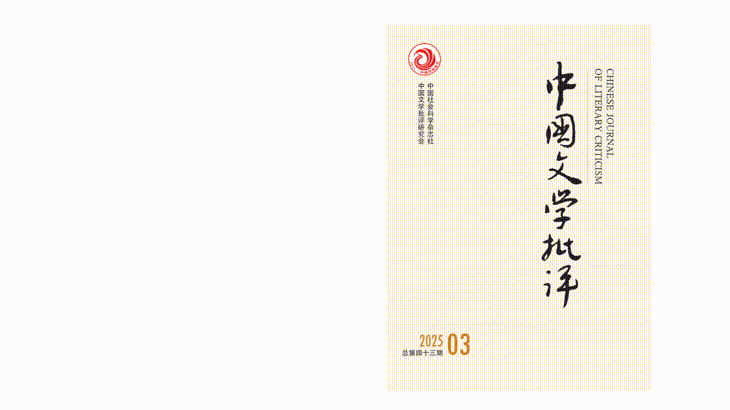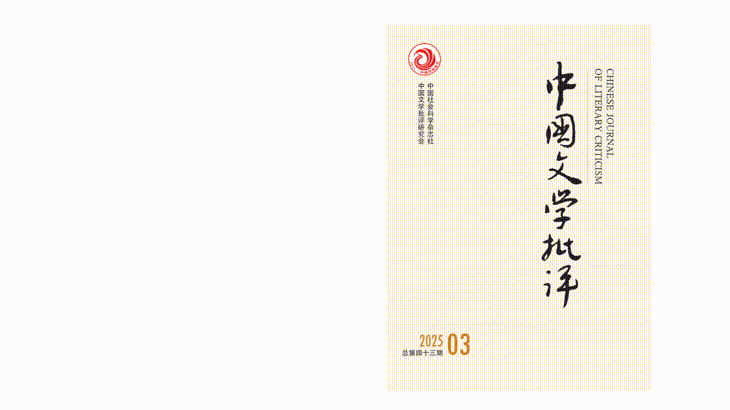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日趋频繁、深入。“经过百多年演变,中西学术碰撞形成了一个高度压缩型的古今中外资源和理论谱系高度混杂的状态”。为了更好地理解、吸收西方文论,以重构自己的文艺理论,中国学术界引入、总结或提出了诸多概念、术语。一种研究方式总是产生于特定的需求和环境,它在此时此刻的优点,在彼时可能被暴露为某种缺陷,也就需要不停修正甚至迭代以解决问题。同时,总在迭代的概念、研究方式等都在遵循着某个象征秩序的指引,它们因而递归于这个象征秩序,递归于“我们的”文艺理论。
一、 文论演变与迭代
晚近以来,对文艺理论发展的“分期”进入了诸多学者的视野。钱中文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在不同阶段不断提出新问题,讨论新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建设,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识别这些阶段的基础上,能更好地理解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高建平、王一川、刘锋杰等人的分期和解读虽然略有不同,总体上延续了钱中文的思路。刘方喜的解读虽然颇不同于这三位,但仍在阐发钱氏关于中外文论对话中存在两次“错位”的见解。总体而言,分期能够提供全局性的视野,因而能更好地探寻特定时期发生的问题、方法和规律,臧否其得失。
另一种类型的整体反思侧重于讨论方法和质性,王一川、曾军等人着眼于中外文论交流中的不平等,并尝试加以克服。王一川辨析了叠加式、疏离式、追补式和平行式等中外文论的相遇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文论交流逐渐实现了“平行”。不过,“平行式相遇毕竟不等于、更不能被误认为是平等式相遇”。相遇方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这种相遇在总体上当属于一种由‘一’向‘多’、由‘同’到‘异’的破裂式转向。 ……中国文论以‘破裂’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展开了”。但破裂之后呢?破裂只是发展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递归”,只是在彼时,后者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曾军则阐释了“化”,并总结了以中化西的“体用”范式、以西化中的“西化”范式和以马为主、以马适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然而,曾氏对“化”的使用并不一贯,“化”既是他构想的中外文论交流的理想状态和方法,也是对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文论交流的总结和描述。
赖大仁的讨论则更具体,他提出以蔡仪、以群主编的教科书以及它所表征的“认识论文论”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在三个方向寻求创新发展:(1)对原有体系中过于简单片面以及被庸俗化了的一些基本理论命题进行纠偏与拓展;(2)另辟蹊径,探索构建新的文论系统;(3)突破和超越原来认识论文论的框架,多元综合或宏观整合。第一种路径的例子是审美反映论对反映论的纠偏。审美反映论“着力深入探讨文学审美反映的特殊规律,其中尤其注重文学主体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在审美反映中的作用”。从审美反映论到审美意识形态,文艺理论开始探索其自身的独特规律。不过,审美论、自律论“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而将文学反映现实、介入现实、影响现实变革的观念完全当做过时‘他律论’观念予以否定解构,其结果只能是促使文学和文论本身远离现实”。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文学艺术和发展文艺理论,就有必要限制审美论、自律论的范围,使之只能在原有的认识论文论体系的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样的观点并非赖氏独有,直至今日,自律论始终没有在国内文艺理论界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但这不是自律论本身的问题,按伯林所说,艺术自律和艺术责任并不矛盾,艺术自律意味着要以艺术来构造现实,这是艺术对现实最深刻的介入,这和艺术反映/模仿现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关于第三种路径,赖氏指出,国内诸多学者尝试过以更宏观、综合的视角,突破和超越原有认识论文论的框架。晚近以来,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究其根本,过细的分工日益成为学术研究推陈出新最大的掣肘之一。
现在,有必要讨论这些研究体现出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关系问题。大部分学者或隐或显地都呈现了不同时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迭代。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前一代理论以及它尝试去解决的问题和方法,会成为下一代研究的起始,下一代理论因而在前一代的变异中生成。在赖大仁的论述中,蔡仪、以群等人编著的文学理论教材确立的文学理论体系成为上一代,其核心在于照搬了哲学反映论。审美反映论是下一代,其要点在于以审美反映区别哲学反映,并以之来探究文学审美反映的特殊规律。汪正龙进而设想了两种新一代研究取向:其一,把生产论与反映论相关联;其二,深化与拓展反映论的机理研究,把反映论与创造论或者生成论相结合。
迭代源于理论研究的语境化。从哲学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不仅是知识型的变化,更是知识所处语境的变迁。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语境化特点的是王一川描述的“追补式”:“‘新时期’国门重开、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就变得十分迫切, 80年代的人们恨不得立时追补完过去三十年光阴所耽误的整个中西相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曹顺庆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按照曹氏的解释,大概可以提炼出相关语境的两个要点: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第二,“在整个20世纪,学界大多数人担心的不是失语,而是担心传统文化死灰复燃,……不惜完全抛弃传统话语”。此外,还应考虑到第三点: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极大鼓舞了学术界的文化自信。1994年,张法、王一川等人就在呼吁一种名为“中华性”的新知识型;同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提出了“文化自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并非文论界的独特发明,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转换在文学理论上的体现。
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也就是赖大仁总结的第二种路径,其意在反对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式。这种路径最广为人知的是建构主义的文学研究范式,来源于当时勃兴的文化研究。受其鼓舞,周宪指出经典的塑造中隐含了复杂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还原这些看上去“‘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的本来面目,揭橥隐藏其后的话语霸权或权力关系,“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使经典‘去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值得思考的‘文学问题’”。出于同样的考虑,陶东风认为,既有的文艺学知识是本质主义的,它先验地预设了“普遍规律”和“固有本质”,陶氏继而阐释了建构主义文学观:“文学的‘本质’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文化与语言建构,我们不能在这些制约语境之外,也不能在语言建构行为之外谈论文学的本质”。
但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一种观念或方法的超语境能力。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在“文学”被建构出来之前,《诗经》这样的文献不能成为“文学”。然而,正是这个例子暴露了这种理论的重大缺陷:何以是《诗经》(以及《楚辞》,诸如此类)被追溯为“文学”?如果一切都来自眼下的语境,是短暂的、偶然的,那对文学的理解到底源自何处?进一步讲,难道不是“诗”“骚”奠定、构造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赋予了文学特定的“本质”?这关系到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的“集体意识”:“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它与个人所处的特殊状况是不发生关系的,所以其人已去,其实焉在。”集体意识至少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是我们当前所处的语境中蕴含的超个体的意识,第二是某种能够超越当下语境而跨时空的意识。这也提示我们,我们在特定语境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或观念、方法,总在向我们揭示传统的存在,尽管我们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周宪同样揭示了这一点,文化研究的勃兴是全球化和去传统的产物,但正是全球化引发了文化自觉。从文化研究于21世纪初引发广泛影响至今,大众文化的变迁不知几许,变迁背后的那些东西却岿然不动。这指向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象:语境变更导致的迭代只是表面的,它解决的只是特定语境中产生的偶发问题。既然如此,就有一个不变的事物给予迭代方向,也驱使文艺理论递归。
二、文学理论的递归
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在迭代的同时走上递归之路?正如赵汀阳所言,“所有思想问题都有着历史性的来路,而原初问题肯定是首要问题,并且成为所有后继问题的前提条件,所以原初问题就是思想的本源。”某些事物或固然是“建构”的,但一经确立就会产生超时空的影响。开端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总会被不停地重返与修正。由此也提示人们在多变的现实世界里“勿忘初心”。不难发现,始终有一条线索贯穿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中,这条线索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其目的是构建一种自觉/自信的文学理论话语——与其说是线索,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秩序,它向后来者揭示了开端所奠定的精神取向。
以形象思维的讨论为例,当前的回顾往往集中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的祝词。一般认为,这次讲话帮助学术界确认了形象思维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文艺回归文艺本身。形象思维讨论试图激活对传统文论的再阐释,高建平即认为,从蔡仪以赋、比、兴发挥形象思维说,到后来诸多学者阐发“意象”论,都可以视为形象思维讨论的发展。也是在这个时期,“传统”焕发了新活力。譬如,叶朗于1988年提出了现代美学体系的四大原则,其中两项是传统和当代的贯通、中国与西方的融合。在朱光潜、宗白华诞辰10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叶朗发表了以“接着讲”为主旨的纪念讲话,即为何、如何接续朱光潜的美学,并阐发了意象理论。
无论是文学主体性,或者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的演变,其主旨都在于对文学价值的确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迎来了他们在中国的高光,但也很快就被指控为科学主义,它完全忽视文学的内涵,从而败坏了文学。有趣的是鲁枢元的选择,他认为不能以文学的社会功用看待文学,否则会致使文学迷失其本质,解决的方式是把文学还原为作者的心理事实。作为国内较早的形式主义的批评者,鲁氏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选择和他着力批评的形式主义其实别无二致,都是把对象个体化、孤立化。这在欧洲启蒙运动时已经发生过,其结果是个体无法承受绝对的孤立,而不得不被以维柯、赫尔德为代表的另一种启蒙纳入历史/传统中。形式主义正是这一历程的产物。作为显明的表征,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都阐释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乃至构造了一套文学史理论。按照这套理论,一件人造物只有符合这种文学史所蕴含的观念,才能获得艺术作品这个身份。这种观念不是凭空建构得来,而是由最初的民族诗人的作品奠定的,这些作品会产生一种倾向,使文学艺术依据这种倾向演变。文学不是心理事实,而是历史事实。
20世纪80年代末,乐黛云重新觉察到《学衡》派的价值,“《学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相号召的新人文主义”。按乐黛云所言,《学衡》派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他们深知必然要创造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文化,但此新文化仍然要以原来的文化为基础。随之而来的90年代没有给这样的运思留下充分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文论失语症”“重述中国”“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等话语。这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时激荡神州的“后学”的产物。某种意义上,“后学”既是控诉中西间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利器,也启发中国学者发掘出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些学者或明或隐地认为,或者要以中华性取现代性而代之,或者“在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同时,将中国这一特定区域与文明体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对那种普世化的西方文化体制的质询”。后一种观点来自致力于“重述中国”的学者,其未曾明言的意图是,以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的现代重述,既批判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为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弊病,也为现代世界提供更多选择。但在秉持中国立场之际,该如何接续传统?又该去接续何种传统?这或许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文化建构仍然任重道远。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稍异于以上话语,其要旨在于,承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经验和问题时的限度,进而要求建构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文论话语或中国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曾军提出的需要警惕和克服的“来源谬误”“主体谬误”。前者要求克服对传统中国的美化,避免把中国经验纯粹化,也避免一定要从中国本土和传统中建立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后者则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诸种理论创造,而不局限于某个个人或民族。但如何“以‘有效阐释’为目标,展开对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理解、增强中国文论话语阐释的有效性,从而影响中国之外的,尤其是西方主流的文论话语,才能获得中国文论的话语权”?为此,吴娱玉指责“从事文艺理论的当代学者甚少系统严谨地反思孔孟,接续古代文脉,更别说熟识之后的批判生成……我们大多只是古今中外杂取种种、浮皮潦草烩成一锅”。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亨利·米勒关于中国文明的引用给了她充分启发。但米勒的论述是否就是对孔孟“系统严谨”的反思?吴氏避而不谈。正是跨界和“解域”这样的后现代方法和精神,成为其建构中国文论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后现代精神几乎弥漫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全部言辞中。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倡议者和践行者,刘康提议,“认真思考西方‘后学’对普遍与特殊的历史化和元批评的路径”,这将让中国学者的思考走向更广阔的思想空间,也能更便利地创新。刘氏的后现代典范是福柯,但福柯式的理论及其所表征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值得现代中国人追求吗?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理论、品格和生活是值得追求的?
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晚近以来,张江从整体上将当代西方文论的弊病归结为“强制阐释”,并审视被其裹挟的当代中国文论。张氏有强烈的问题和主体意识:“在被西方文艺理论裹挟时,我自己是什么姿态?我对这种裹挟有没有警惕?如果有,警惕在什么地方?”因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理论本身,而是我们因何使用一种理论?进而,张氏从两个方面建构其阐释学,一为公共阐释,一是“让阐释学说汉语”。它们互为表里。
三、文学理论的超个体性
文学理论的迭代或递归,总是与时代环境休戚相关,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直至衰亡,都是在应和时代之问。因而,文学理论是超个体的,绝不是个体或私人的言说。
言说具有超个体性,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布拉格学派,并在扬·穆卡洛夫斯基(J. Mukarovsky)的(艺术)符号学中得到了深远的阐释。穆卡洛夫斯基较早意识到了“审美对象”(亦即分析美学所称的“艺术品资格”)不是自然获得的。艺术作品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人造物,其次才是“审美对象”,后者是栖身于集体意识中并由集体意识赋予的文化身份。因而,艺术作品必须脱离它的创作者,亦即必须卸去人造物这个身份,使它那超个体的(supra-individual)精神内容得到呈现,才能成为审美对象,穆卡洛夫斯基又称其为符号,以此来强调它具有的整体性,并区别于日常表达。符号的超个体性的重要一面在于,它在作者和集体间充当中介,其意义由在一个特定集体中的成员唤起的集体意识组成。参与交流的个体想要使用这个符号,就必须拥有与之相符的超个体属性。穆卡洛夫斯基的论述基于艺术,其原理则具有一般性:一种表达之所以能被视为符号,要归功于它具有超个体性。作为一种表达,文学理论总是以各种方式回应时代的呼唤。无疑,文学理论具有显著的超个体性。
那么,文学理论何为?韦勒克认为,“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后来者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删,譬如佛克马所说“不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理论,要使文学研究达到科学化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但总体上没有超出韦勒克的界定。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古希腊人以诗和诗教作为文明和生活方式传承的根本渠道,这样的渠道自启蒙运动以后拓展为包含诗、小说等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在内的诸多艺术,尤其是“美的艺术”。另一方面,理论(沉思)在古希腊有崇高的地位,是最高的知识和生活。由此可知,作为诗学和美学在20世纪以降的现代替代物,文学理论除了承担着前引的作用,还有一项更为值得关注的功用:教导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读者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首先,文学理论是语境化的,它受当前时代环境的影响。从形象思维讨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对文学和审美自律的追求显然与改革开放休戚相关。一种文学理论的诞生和阐发,总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但更需要警醒的是,这不是要回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流行观念。正如上文所论,文学理论的首要目的不(仅)是对文学经验的阐释和批评,而是对理论和理论生活的追求。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研究者们在“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之际,能否真正“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同时,一种文学理论一旦产生,就具备了超越其诞生的语境的能力,从而拥有更广泛的解释力,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对形象思维的讨论,这次讨论的方法和精神取向,时至今日仍影响着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超语境的情况需要做一些甄别。比如人和文的“觉醒”。自20世纪初提出并在80年代复活之后,“觉醒”就迅速超出了它诞生的语境和目的,被用来解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它也被用于解释一切异于社会主流或传统的思想、行为,甚或被不合宜的拓展,比如把文学觉醒回溯到先秦,把人的觉醒降格为欲望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嬗变成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超级概念”,它们几乎完全抽象化,被任意挪用,乃至彻底沦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其次,文学理论具有潜能(potentiality)。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修斯以“潜能”来描述语言的一种自我拓展的特质:“静态摇摆(static oscillation),也就是在一段给定时间内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不久后他将之改为“弹性稳定性”(elastic stability)。这是对语言与其目的间张力的描述。就其稳定一面,语言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实现它的目的,也就是可以正确表达。但在面对新情况时,“稳定”就成了它的缺陷。好在语言具有先于言语行为的能力,它在被使用时,能创造出新的语言现象,引发其自身的变动,从而满足新的要求。这也是文学理论的特性。文学理论总是循旧迹而来、矫往事而偏至。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一种理论总是从前一个理论中诞生、变形和发展。
最后,仍需提及个体在文学理论迭代中的作用。在讨论符号理论时,穆卡洛夫斯基提示他的读者,一方面,不能忽略(艺术)交流总会带入个体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个体总是同时处于不同的集体中,也必然会带入异于这次交流所属集体的因素。因而,对符号的使用和交流总是异质的、复杂的。得益于此,交流必然会产生意外和创新。这重新回到了上文提到的对研究者的要求:什么样的个体才是能真正创新的个体?
结语
本文尝试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的迭代与递归。迭代旨在回应某些具有即时性的问题,递归具有双重作用:对传统的自觉,并以之指引当下的迭代。叶维廉认为,一切心智活动都以某种“模子”为起点。就文化交流而言,不同文化的模子只有某些相似/交叠之处,“而往往,不交叠的地方——即是歧异之处的探讨和对比更能使我们透视二者的固有面貌,必须先明瞭二者操作上的基础差异性,我们才可以进入‘基本相似性’的建立。”需要警惕的是,并不存在一旦成型就不变的模子,模子会不断演变,激发后人的创新,乃至走向模子的方面。因而,对模子的寻根以及其演变历程的认识就尤为重要,否则就会产生众多不幸的歪曲。递归于传统,对传统的自觉,不是因为传统具有不变的本质,而是不停的复归和审视传统及其变迁有助于我们辨析世界的善与恶,也随时警示我们“勿忘初心”。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