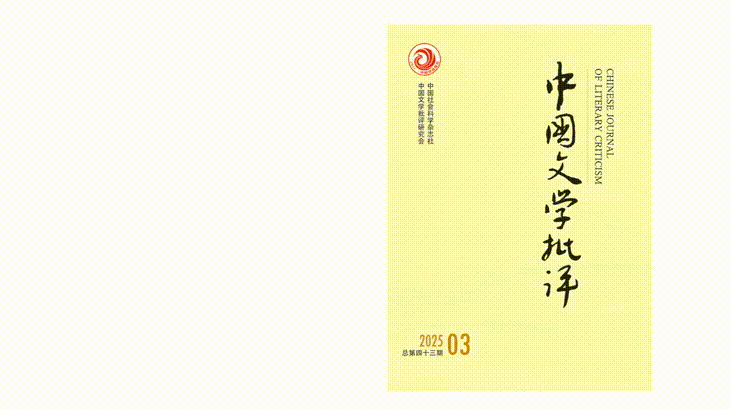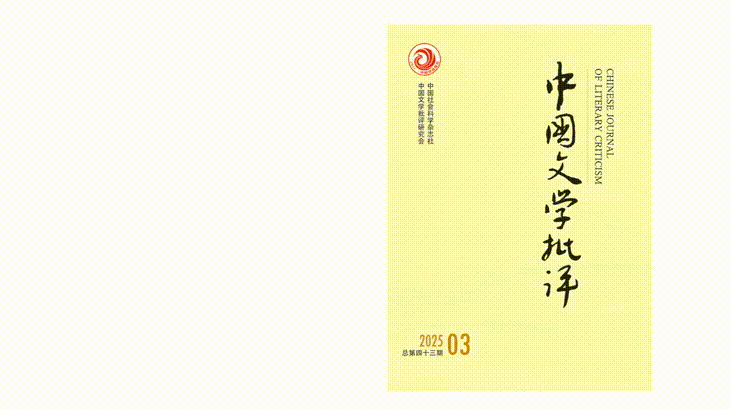
“奇”是中国美学独有的一个范畴,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老子》《庄子》,独立于魏晋时期士人的“尚奇”追求,在明末清初成为社会普遍的审美风尚。在西方,“奇”虽然没有一个严格对应的范畴,但是有很多表达类似意义的美学观点。我们可以从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维度,来探讨中西方的“奇”的最初语义内涵。“奇”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关键节点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从历史变迁的视野中,分析“奇”的不同价值表现,评价“奇”对于社会文化所起到的效用,意义重要。价值是相对的,一定要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联。“奇”作为艺术创新与审美体验的重要内容,是构成人类艺术发展史的不竭动力,更需要在一个价值论的立场上进行评判和衡量。因为艺术本身就存在个人性与历史性互相观照的视角,无论是何等新奇的艺术,只有在历史价值的前提下将其圣化,“也许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艺术的概念开始超越单纯技艺的概念”,才能使具有个人化创新性的技艺走进艺术史的叙事链条。因此,以“奇”在中西方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价值转向为节点,建立起一个有关“奇”的中西方美学比较研究框架,为今天我们评价一种新奇的艺术现象提供可借鉴的参考,正是当代继续探讨这一美学范畴的意义所在。
一、“奇正之辨”为何具有鲜明的伦理价值
“奇”作为一个范畴,主要出现在中国文论与美学研究之中,与“正”相对,但二者最基本的字源含义却同出一源,都是指“一只脚”。但为什么都是表示数量的“奇”与“正”,却产生出以“正”为根本而以“奇”为少数的价值意涵呢?答案是,“奇正”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伦理价值,根源上离不开“奇”与“正”在中国历法中的不同地位。说到底,奇正之辨与“中国之为中国”具有深层的逻辑联系,这一对范畴的确立与讨论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国家正当性认知的建构,进而引申出审美的内涵。也就是说,对“奇正”而言,表示数量关系的含义先于审美含义。要理解“奇”的价值影响,离不开对“正”的字源意义观照。
“正”来源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与“统”相关。根据饶宗颐的解释,“正统说”的起源有两个:一个是邹衍的五德运转说,用来确定年的正、闰;一个是《公羊传》的“大一统”说。“统”的古义是时间,表示“一纪”,意为“开始”。所以,在“正”和“统”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转换关系,这就为哲学问题伦理化的价值转向提供了阐释的平台。“正”的古义虽然也是“一足”,但它表示“足亦止也”。因为“足”停止在了恰当的位置,所以,作为方位的“正”暗含了褒义的色彩;而与“正”相对的“奇”在表示时间时,就被用来指并不常见的“闰月”或“闰年”了。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正”发挥了重要政治任务与教化使命。正的最初起源是定型于商周之际的文教传统以及《公羊传》中的“正统”观念。首先,“周人通过‘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来解释‘天命’之所归(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确立了古代中国文教传统中意义最大、影响最广的正当性观念”。其次,《公羊传》的“大一统”虽然是指从时间上的开始,但是,“中国”的命名则在于主体性高扬的空间化定位,意为“中央之国”,“居正”不仅是一种地理方位上的确定,其深层的文教根基在于由华夏族所创立的文化教育传统。因此,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以大一统的文教传统为文化遵循。中华礼乐文化的外在体现就是各种符号性的建构,如第一次记载“中华”的《唐律释文》的释义为:“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由各种文化符号所体现出的文化秩序与品行修养。
综上所述,既然“正”拥有如此重要的文化建构意义,那么与之相对的“奇”自然成为被贬斥的对象。“奇”的本意是“异也,一曰不耦,从大从可”,“奇”是《周易》中出现的一个最基本的数量关系,与“偶”相对应,如“归奇于扐以象闰”,意思是在筮法操作中,通过取出一根蓍草后,剩下的奇数部分象征着时间上的间隔,即闰月。“奇”因此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老子》从根本上肯定了“奇”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是用兵的根本之法。奇与正之间也会相互转化:“正复为奇”。“一阴一阳谓之道”,结合《周易》的卦象构成来看,阴阳、奇偶是世间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们是构成宇宙根本规律——“道”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中国古代,“奇”“正”成为时间开始的标记,是中国历法运算的结果。“正”是主流,是平常;“奇”是闰月或者闰年,是零余之后的汇总。“正统”“正常”成为农业文明最为期待的时间状态,这样意味着天时地利人和。而“奇异”“畸形”则成为身体的缺憾和时间的调整,它就变得“不正常”了。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奇”“正”虽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两只脚”,但它们的地位自然不能完全匹配,以“正统”为纲,“奇”则成为不按套路出牌的计谋,因为中华文化提倡“止戈为武”,用兵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常态。
其实,“奇正之辨”在中国美学史上替代“美丑”之辨,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恰恰由于这种贬斥,使得“奇”拥有与“正”相对的边缘性地位,从而成为突破“正”的各种约束,体现出审美和个性解放的含义,“奇”也使得有限人生和无限天道之间取得了通达的途径,因为“奇”开辟了一条绕开孔孟之“正”的通途:“嵇康与向秀的奇正相补的批评,触及到人生与天道的最深玄的地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在讨论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时,遇有孔孟的问题时,碍于圣人的面子,再伟大的思想家也往往要回避,而唯有在魏晋那个特定的年代,遇到像嵇康这样的人物,才能如此无所顾忌地批评孔子,对于人生的根本价值观念加以议论,谈论得如此深刻与透彻。”除了魏晋时期,中国历史第二次将“奇”作为审美的高峰,出现在明末清初时期,“奇”的美学内涵更加丰富和立体。这两个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高峰期,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时期。可以说,奇正互补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审美体验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形成共同体的过程。因此,魏晋和明清时期为“奇”的伦理价值转向从贬斥到弘扬提供了变革的文化动力。
二、“奇”在魏晋时期审美内涵的变化与明清时期的重心下移
国家大一统的追求在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念中得到了政治层面的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在国家政权与文化传统中不断得到强化。而“奇”的美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但是,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以“正”为纲的中国美学,不断体现出对“奇”的发现、对“奇”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对“奇”的崇尚。这是中国美学范畴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国美学命题不断对话的过程,也是中华美学精神价值体系不断多样发展的过程。
“奇”作为一种审美风尚,《庄子》的《人间世》和《德充符》“在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和孔子‘文质彬彬’的主张很不相同的审美观”。我们细读《庄子》可以发现,“奇”出现的位置是《人间世》,而且也是仅此两处:“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至,则多奇乐。”庄子在书中描绘的支离疏、兀者王骀等各种奇怪的人被赋予审美的含义,导致了现代学者将汉语“奇”和“怪”连用,同时也是将二者等同于“丑”并实现了现代美学转换。在《庄子》中,“怪”出现的次数要远多于“奇”。如第一篇《逍遥游》记述了鲲与鹏的奇特外形,庄子将其归结为“志怪”。对于“怪”的评价,庄子认为,无论正邪,其实都是道的表现形式。所谓“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所以,将《庄子》中所描绘的外形怪异的人作为通向内在道德崇高的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外形之“怪”而非“奇”。对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庄子用反讽口吻调侃了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 彼且蕲以诡、幻怪之名闻,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庄子》展现了与儒家完全不同的出世价值,为“奇”作为新的审美范畴及其延伸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审美范畴的重要阶段,魏晋时期是“奇”走出伦理价值判断而走向真正审美的阶段。魏晋时期,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制度衰落,其间,中原大部分时间政治权力在不同民族之间更迭,处于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状态,西晋结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东晋建立之后,匈奴、鲜卑、羯、氐、羌在北方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既是各少数民族“中华化”的历史主流时期,也是中原汉族文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时期。从政权命名来看,“‘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式国号,并不突出‘族性’,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性政权’为目标,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汉族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如鲜卑族的高足家具逐渐成为主流,汉族服饰的袖子变窄,合餐制代替原来的分餐制,胡乐、胡舞成为丰富汉族娱乐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等等。在社会阶层方面,政权的频繁变化必然带来士人阶层的动荡,再加上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治的把持,大量出身寒门的人无缘“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这是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化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社会思潮发生重要转向:“及至汉末魏晋南北朝,……儒家秩序衰微,玄学思潮大兴,情与礼之间出现了严重冲突。在情与礼之间,与先秦士人对其时溺情毁礼的现状所持反对态度迥乎不同,魏晋南北朝士人几乎全面地倒向了情的一方。”此外,玄学作为影响社会思潮的又一大因素,与佛教、道教共同对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故魏晋玄学之影响于文学者自可在于其文之内容充满老庄之辞意,而实则行文即不用老庄,然其所据之原理固亦可出于玄谈”。
魏晋美学在精神内核方面取法老庄,而这正是“奇”作为审美范畴的滥觞。在魏晋时期出现以奇为美的社会思潮,也就“不足为奇”了。首先,从整体审美风尚而言,“奇”渗透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服饰追求、诗文辞章、形神画论、书法品鉴、山水风景等名士生活所及的各种情形。《世说新语》一书大量用“奇”品评人物,或者用奇来赞美清谈中的辞藻。诚如郭象所注《庄子》中提倡的观点,“各以所美为神奇,所恶为臭腐耳。”只要是风流名士喜爱的事物,都可以冠以“神奇”之名,足见“奇”在魏晋时期得到士人的普遍认同。其次,“奇”作为审美范畴,刘勰功不可没。“刘勰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把兵家的‘奇正’观念转化为文学理论的观念。”同时,刘勰所论述的作为文艺理论范畴的“奇”还是离不开与“正”相对的伦理价值观。刘勰倡导写作过程中要“宗经”“征圣”,“经”是儒家经典,而“圣”则是孔孟开创和发展的圣人之道。在此前提下,与“正”相对的“奇”自然不能离开“正”的统御。对于《离骚》中体现出来的辞采华美,刘勰认为它“酌奇而不失其贞”(正)。最后,在魏晋历史上,钟嵘的《诗品》是使“奇”与“正”脱离对立的重要著作,将“奇”彻底审美化。“《文心雕龙》也常用‘奇’字来品评作家作品,但其涵义与《诗品》并不相同。《文心雕龙》书中所谓奇,有褒义、贬义之分。”“奇”在钟嵘这里全部是褒义的。王运煕总结钟嵘《诗品》之奇包含三个层次,分别是通篇风貌之奇、章句词语之奇以及比兴寄托之奇。笔者认为,在这三奇之中,通篇风貌之奇是最为关键之所在。因为诗歌章句与比兴寄托都体现在辞藻用典等技法层面,还没有走出文学形式的园囿,而通篇风貌成为一种“势”,奇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审美高度。钟嵘将奇提升为文章总体风貌的评价,是赋予文学超越性的具体途径。总之,魏晋时期是中国审美自觉的时期,“奇”作为超越平淡的审美范畴得到正式确立。
晚明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尚奇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首先,从文体上说,明代尚奇之风从诗歌走向了传统文人并不看重的小说、戏剧等新型文体之中。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的正统受到了严重动摇,与正相对的奇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生发基点。这一点与魏晋时期颇为类似,也体现了明代尚奇之风的历史传承。与魏晋时期的尚奇略有不同在于,明代尚奇之风进入文学,是从诗歌走向了小说和戏剧。这既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结果,也是“奇”从士大夫走向民间的一个开始。因此,明代尚奇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出现了“奇常对举”的状况:“最早明确提出‘常中出奇’这一观念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晚明思想家李贽。”将这种观念付诸文学实践的是凌濛初,他的《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共包含80篇短篇小说,记录了当时市民生活的多个方面,这些故事往往具有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结局。明代四大奇书也都以小说为主要文体。在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可以为情死而复生,也是“奇”在戏曲中的鲜明体现。其次,从成因上说,晚明尚奇不仅是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还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影响。魏晋尚奇之风受到佛教影响,佛教从文化背景上来看,还属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有诸多相通的理念,而明代则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魏晋时期所不能及的。明朝在解除“海禁”之后,面对东西方的贸易带来的大量货物,开阔了世人眼界。《东西洋考》中记载:“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从思想来源来看,对提倡“奇常对举”的李贽而言,传统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受利玛窦影响,李贽提倡“道外无人”,要求把天道的根本放置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上。最后,晚明还是“奇”作为审美范畴重心下移的时期。魏晋时期尚奇主要体现在士人阶层,无论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放浪形骸,还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求新求变,基本掌握在士人文人阶层。明代求新求异之风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笔记、小品记载了晚明民间风俗之盛况,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岱《陶庵梦忆》、谢肇淛 《五杂俎》、顾起元《客座赘语》、张瀚《松窗梦语》等著作,为后人展示了风情万种的民俗画卷。”由于晚明之奇根植于与日常生活之“常”的对立,“奇”的意趣在于对庸常生活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使“奇”获得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审美内涵,也为文人士大夫引导社会审美风尚提供了空间。李渔的《闲情偶寄》不仅是一本士人鉴赏雅俗的笔记,同时也对引车卖浆者的审美能力提供了蕴含“雅”的精神指导。因此,由“奇”作为审美风尚的重心下移,沟通了士人与民间的审美对话。从社会伦理价值来讲,尚奇之风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批判,转而追求个性解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促进人们从封建礼教之中解放出来,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三、西方美学视野中“奇”的价值转向
在西文中,有很多词可以表示“奇异的”“奇特的”“不同寻常的”,如“strange”“peculiar”“weird”“bizarre”“curious”“marvelous”“wonderful”“mysterious”等。但是,同时具备“奇数”的数量含义,“odd”与中文的“奇”最为接近。西方的“奇”最初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具备典型的伦理价值,所以,我们并不限定中文“奇”的对应西文,而是遵循“奇”在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节点进行比较。如此一来,中文的“奇”在西方文艺理论历史上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事件与主张。古希腊相关文献在涉及“奇”的时候,更多是与“常”对举。因此,“奇”最初在西方文化中体现为认知价值,而非伦理价值。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把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特智慧称之为“奇特的”,因为这种智慧并不指某种具体工艺的知识,而是用来考虑国家长治久安的护国者所掌握的知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奇异词”的内涵与作用。奇异词包括外来词、隐喻词、延伸词以及任何不同于普通用语的词,并认为奇异词可使言语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但是,亚氏也并不主张奇异词的过分使用,因为这样会把句子变成谜语。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还将“平淡无奇”作为批评的重要标准,认为克勒俄丰对作品的处理并不精彩,显得“平淡无奇”。在贺拉斯的《诗艺》中,同样论述到了创新。与“奇”相关的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字的创新,一个是篇章结构安排的创新。对于新字而言,贺拉斯认为,如果表达的内容很深奥,必须用新字,则可以创造一些“围着腰巾的克特古斯这类人所没有听见过的字”;贺拉斯强调,这类字必须渊源于古希腊,在篇章结构安排方面须遵循原有的程式。在组织材料方面可以出奇制胜,这样来体现独创性。从贺拉斯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中国古代“奇正之辨”的情形。
随着千年中世纪的到来,西方文化塑造了除希腊经典之外的第二个正统,即基督教的传统。文学艺术的创新也因此而体现出种种反抗与叛逆。就“奇”而言,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点,第一是中世纪的传奇文学。13世纪时,法国作家纪尧姆·德·洛里斯创作的《玫瑰传奇》在14世纪由乔叟译成了英语,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叙事诗体。这种文学通过做梦和幻觉形式塑造了一个充满反讽和象征的世界。《玫瑰传奇》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高尔的《情人的忏悔》、“高文”诗人的《珍珠》、乔叟的《公爵夫人之书》等都可以看到《玫瑰传奇》的影子。到了14、15世纪,英国本土民间的冒险传奇得到极大发展,浪漫传奇文学在此时成为英语文学的典型代表,“浪漫传奇,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是中世纪方言文学中的最突出成果。”传奇文学突破了神学所确立的理性与克制的原则,表达了真实的人性欲望。它打破了拉丁语在文学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各国方言的发展。传奇文学的民间性动员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力量,对于中世纪后期民族主义的兴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魏晋时期尚奇处于中国文学自觉的时期,而中世纪的西方还没有明确的“文学”定义,当时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传奇的发展更加彰显了语言文字的虚构功能,拓展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文学的认识。在浪漫主义思潮来临之前,后期新古典主义为文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无论是题材还是表达方式,都有严格的限制。文艺规则在启蒙运动者看来,都是对于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波兰学者亚当·密茨凯维支在《论浪漫主义诗歌》中谈道:“在那里是不能找到任何大胆的、超过现实界限的虚构,任何与神话相结合的传说。……情感也受到同样的约束。”
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具备了明确的宣言,成为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具体实践和立场主张,“奇特的”审美风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著名的《〈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回顾了有关滑稽丑怪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位。对于奇特的、丑怪的人物形象和审美范畴,雨果给予崇高的评价,认为丑怪和奇特其实蕴含着一种不同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现代精神。“这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原则,是进入到诗中来的新类型;既然增加了一种条件会改变整体,于是在艺术中也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类型,就是滑稽丑怪。”它将追求合适原则的古典主义与代表现代精神的浪漫主义区别了开来。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巴黎圣母院》中奇美与奇丑的对照,在《悲惨世界》中也有冉·阿让在负伤严重的情况下救助他人等诸多离奇的情节,这些都是雨果浪漫主义宣言中的具体实践。此时,“奇”更多地与“怪”甚至是“丑”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取得独立的美学地位。“在18世纪的英国,不寻常性(uncommonness)有时也被称作新奇性,而伟大有时也被称作崇高,但是名单基本上仍保持不变。它至少是在英国,构成了启蒙时期美学之不变的常项”。西方文艺理论史真正把“奇特的”赋予独立的美学范畴是在19世纪。冯德里希·西奥多·菲舍尔在1846年列出10种范畴,其中包括“奇异的”(marvellous)这一种。菲舍尔所处的时代是心理学、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段,此时他对于“奇异的”美学范畴的分类,建立在对审美心理认识的基础上,在他同时列出的10个范畴之中,将“奇异的”与“怪诞的”(grotesque)区分开来,与雨果浪漫主义时代将“奇异的”与“丑怪的”联系起来一并论述是不同的。在雨果的时代,“奇”包含“丑”的涵义,主要目的在于反抗古典主义的理性、合适原则。因此,菲舍尔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这里开始,“奇”正式独立为一个审美范畴。“美学”本意是“感性学”,“奇”是最主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它引起不同寻常的心理感受,而在菲舍尔所处的心理学开始兴盛的19世纪,“奇异的”被作为单独的审美范畴而彻底取得独立的地位,主要着眼于事物本身所引起的审美心理感受,使“奇”回归美学研究的无功利属性,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到了19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奇”,才真正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而被确定了下来。
结语:“奇”的价值选择
纵览中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西“奇”具有许多类似之处,诸如,“正”与“奇”之间的关系及其阐释,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断反思与价值选择。所不同的是,“奇”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范畴,经历与“正”的相对到与“常”的并举,是“奇”不断摆脱社会伦理价值而走向审美独立的过程。“奇”在中国作为风尚,是先从魏晋时期掌握封建时代话语权与文字书写能力的士人阶层开始,直到明清时期成为社会市井百姓追逐的对象。在西方,“奇”起初与“常”对立,随着希腊正统和基督教正统而走向与“正”的对立。然后,“奇”在浪漫主义时代一度与“丑”相联系,直到19世纪才真正取得独立地位。从传播路径来看,“奇”的传奇文学在中世纪则是从民间开始,直到启蒙运动时代成为知识分子的明确追求与艺术实践。这是与我国不同的地方。
寻找和发现“奇”的过程,就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建立新的对照关系的过程。相比于其他的美学范畴,“奇”的相对性更加鲜明,它的发现与外延对象的确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更加具备文明互鉴的意义。“奇”本来并不是一个确定项,它是文人生活和市井烟火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文化传统形成某种确定的程式、标准或者经常性、习惯性状态的时候,“正”和“常”得以确立,“奇”的偶尔出现或者被掌握符号生产权力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使用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化表达过程中较少出现的那一项,于是成为一种奇特的标识。正是因为有被标出项的存在,才进一步推动了对文化价值多样性的认识,造就更多的文化表述方式,从而促进文化表征的繁荣。范畴价值层面的意义,往往是多样的和因人而异的,对“奇”的发现就是不同语境中对各不相同的价值强调的结果。如同一面镜子可以激发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奇”存在的价值论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价值选择,这就回答了中西方文艺理论历史上,“奇”为什么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这正是“奇”的镜像效果。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迭代,“奇”与“正”“常”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地变化,类似于一个系统中的“熵”,虽然它的出现造成了系统的不稳定,但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熵也造成了系统的不断更新。当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熵又被重新定义,这就是价值的不断选择与重塑。从绝对意义来看,价值一定是多样的,相对的;然而,在相对的和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价值的选择又具有一定的确定性,那就是应该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这样的“奇”才可以在艺术史与文化史中留下相应的痕迹,而不是单纯在技术、辞藻方面的“为奇而奇”,或者行为的刻意“惊世骇俗”。比较研究为中西方文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奇”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新的参照,亦为当代的文化批评提供了具有审思力的价值评价标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