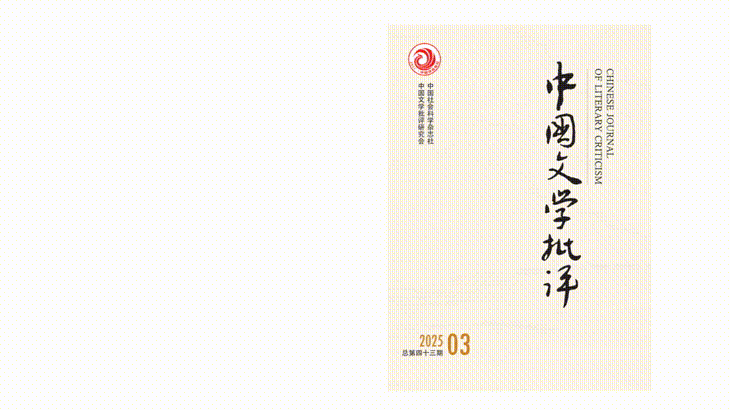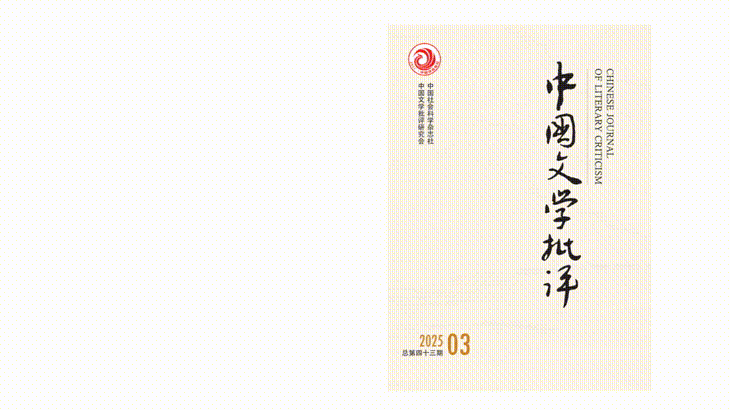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术语中,“奇”历来受到关注。早在《孙子兵法》中,“奇”就被作为军事术语加以使用,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六朝时期,刘勰将之运用到文艺批评领域,用以讨论文学风格和作家创作的构思等问题。这是“奇”正式进入文艺批评领域的开始。自古至今,人们关于“奇”的讨论和界定大体从两方面入手:从主体角度看,“奇”指的是作家与艺术家独特的思想、情感和趣味;从作品角度看,“奇”指的则是对日常规则的超越,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偏离正统风格之外的新的艺术风格——“奇”由此被界定为艺术家反抗传统、表现自我的标志之一。这样一来,“奇”在内涵上便成为西方天才论艺术观和美学观的概念,也成为现代学者反对模仿论、倡导独创论的手段和工具。实际上,在神话思维弥漫的时代,人们并不用“奇”指称、讨论宗教问题和神怪意象。人们用“奇”讨论各种问题,说明人类此时已进入较为理性、实用的日常化阶段,“奇”的事物和观念由于稀见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特点。换言之,“奇”并不是“奇”本身造成的,而是人自身识见狭隘,同时被各种常规性、日常化、重复性的现象、观念和标准障蔽的结果,“奇”的事物和观念本身客观存在。在此意义上,“奇”正是主体认识、呈现、把握真理的“另一种”方式。
一、“奇”:一个主观化的术语
一般认为,在文艺审美领域,“奇”是对作品内容、风格或艺术家构思的指称。根据这一思路,“奇”指称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创作完成后与作品相关的各个要素、构成,其指称对象是客观的。事实恰恰相反:“奇”实际上是文艺欣赏者或批评者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评价,是专属于欣赏或批评的术语。人们认为,作品之“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艺术家独特的人格品性和精神世界,而形成自我独特新奇的艺术风格也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追求。根据这一标准,“奇”就成为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独特性的评价标准——“奇”被个体化了。事实也是如此:某事物是否“奇”,不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观者的情趣、识见决定的。对艺术家来说,随着年岁、阅历、学识的增长和改变,艺术内容和风格的“奇”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一般来看,艺术家年少时期,多会追求恣肆放逸的风格,表现对象也以奇物异事为多;进入中老年后,作品风格则偏向恬淡自然,表现对象则以日常风物为多,枯淡风格也会体现出某种“奇”的特质。
实际上,如果艺术家对世界没有深刻的领悟,呈现的对象即使是奇物异事,艺术表现也会落入俗套;反之,呈现对象即使是日常所见,其作品也会形成某种奇境。例如,在邓椿的记述中,赵大年的皇室身份,使其天然具有神童或天才的特质,虽然这些特质可能更多来自其优渥的出身及其接受的教育,但人们仍愿相信这是其先天具备的。赵大年以王维、苏东坡为师,能写自然山水,思致殊佳,乃是其好奇的少年心性导致的(“实年少好奇耳”)。这就指出了艺术家尚奇心理形成的生理学基础。论者也发现,赵大年单纯以尚奇心理、师法古人进行创作,虽构思奇佳但缺乏余味,根本原因在于他作为皇族宗室不能远离京城、遨游世界所导致的视野狭窄。这进一步说明,艺术家如果缺乏跃身大化、体验日常百态的生命经验,只以单纯的尚奇心理、新颖构思进行创作,其作品终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尚奇”,最终导致创作灵感的衰竭和作品意境的偏狭。
对于观者和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艺术作品呈现的世界和风格是否“奇”,取决于其自身阅历识见的多寡和思想情感的厚薄。在以内省著称的宋代,形成一股将艺术的品格高度与艺术家人品高度相等同的批评风气。人们无视艺术创作的技法问题,直接将艺术家的身份、品行、学识、人格等因素置换为艺术作品的优异品质,形成了较为主观化的批评潮流,艺术作品中荒寒、奇诡、瘦硬、恬淡、深远、险僻诸风格都被称为艺术中的奇境。这是因为文人士夫在人生中难免出现各种波折,人们常把人生低谷时期的心灵和情趣视为艺术风格的根本。例如,文与可和苏轼所作墨竹枯树图,奇诡怪异,颇有奇趣,米芾评价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人们认为苏轼所画枯木怪石“怪怪奇奇”的形象,是其胸中郁结情感的形象化:艺术意象直接成为情感的表征,艺术风格与艺术家本人的情感世界被等同了。作为艺术风格和内容表现的“奇”,是作者内心奇诡的精神世界的直接呈现。这是北宋时期批评家将艺术家本人的思想品格与作品意象和境界关联起来论述的趋势的反映。
这一批评方式影响深远。在中国,性灵派是将文艺创作和批评主观化的代表。在他们心中,文艺创作和欣赏完全是主观精神世界的产物。为立意新奇以彰显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不仅否定客观世界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否定前人作品对文艺创作的基础性作用,认为艺术家宁可使用俗字今文,也不能蹈袭前人。薛雪《一瓢诗话》云:“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语陈而意新,语同而意异,则前人之字句,即吾之字句也。”对于艺术作品的形式技法来说,更是如此。袁宏道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这样一来,包括“奇”在内的所有艺术内容与风格,都成为艺术家“胸中之竹”的替代品。在这一语境中形成的对“奇”的追求及其实现,使“奇”成为艺术家心灵和情感的产物,“奇”被个体化和私有化了。不独作品内容成为主观的产物,作者所使用的技法与形式也变成艺术家情感的产物。人们讨论的问题已不是艺术问题,而是艺术家的人格品质问题。邓椿在说明自己编撰《画继》的目的和标准时说:“若虚虽不加品第,而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这种思路奠定在这样一个决定论的基础上:人品高下决定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下。邓椿因循了郭若虚将气韵生动作为评价作品的第一标准并发展了一步:作品是否达到气韵生动决定于艺术家本身的身份、地位、才情;反之,作品再好,也只能是“众工之事”,他的作品就不成其为作品。像康德对于天才“不可传授”特征的界定一样,这种“高雅之情”既不可传授也无法学习,只能为轩冕才贤、岩穴上士所特有。他们对这种人品特质享有专属特权,从而也占有了品评艺术的专属特权。这种“人品即画品”的观念看似荒诞无稽但影响深远,以至于古原宏伸不得不这样评价:“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美术史都未见到的,是中国独特的美学。”在中外艺术史上,这种个体化、私人性的“奇”观念确实存在,由此形成康德所谓的“审美自我主义者”:“审美的自我主义者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他自己的鉴赏就够了;哪怕别的人会认为他的诗、画、音乐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很糟糕,予以指责甚或是嘲笑。”在西方,浪漫主义艺术观与此较为相似。
实际上,苏轼、米芾等人的观点,与真实的艺术创作之间差距甚远,他们对艺术之“奇”的主观化评价,只是他们个人艺术观的反映。对于苏轼来说,其观点存在随意点染的成分,有些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实际。对于米芾来说,情况同样如此。邓椿说米芾“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是因为米芾在画艺掌握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靠书法闻名于世。他少有的画作将梅松兰菊置于一纸以此标榜自我情怀,人们认为此作“太高太奇,实旷代之奇作也”。这些都是虚夸的评价,无法证实。邓椿对米芾这种以奇特画作自我标榜的做法甚为理解,认为此乃“好名”的产物:“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苏轼的情况也是这样。但艺术的任务在于呈现真实,让真理从不可见状态转变为可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化、精神化的“奇”须与客观真理的呈现保持一致。
因此,万物本身无所谓“奇”与“不奇”,这种看法是主体自我识见的反映,万物与艺术都是道的运行和真理显现的载体,否则艺术便失去其规定性。正因如此,艺术作品过于求“奇”,则会险怪诡谲而气象逼仄,终落第二义之作。黄庭坚在《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中对米芾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苏轼创作意象奇诡的枯木图,并非如米芾所说的那样以此比喻其心如槁木、盘郁不得抒怀,只能借枯木以托终古;苏轼所作枯木呈现的是亘古不变的自然之美,就像“虎豹之有美,不雕而常自然”一样:虎豹的五彩斑斓之美不仅属于虎豹自身,它同时还是自然之美的体现,无需雕琢而存在。黄庭坚此论将艺术意象纳入永恒的宇宙造化之中,使人摆脱对奇诡滑稽之形象的执迷而上升到对宇宙朝彻的体悟:“奇”的表现和形式是表面的,对宇宙自然之道的体悟和呈现才是艺术家最根本的任务。艺术家寂然凝虑的思想状态,是实现以天合天的手段而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在风格方面,人们则强调蕴藉平淡是尚奇风格形成的基础,单纯求奇而缺乏蕴藉平淡,只能是哗众取宠之作。贺贻孙指出:“诗以蕴藉为主,不得已溢为光怪尔。蕴藉极而光生,光极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诸大家,各有一种光怪,不独长吉称怪也。怪至长吉极矣,然何尝不从蕴藉中来。”“光”是蕴藉至极的产物,二者之间类似于“绚烂”与“平淡”相互转化之关系,蕴藉之美转化为光彩四溢的状态,其极致就形成光怪的风格,所以清人卢震云:“以奇而归于平,平中之奇,乃所谓真奇也。”因此,不存在单纯的奇异诡谲之风格,这一风格须与意趣之深远蕴藉相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奇”的过度追求。艺术作品所呈现的“奇”应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万物之理的体悟、理解和呈现,“奇”只有体现“理”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奇由耳闻目见得之”:“奇”的来源问题
在神话思维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人们不会使用“奇”讨论艺术问题。对宗教信仰世界或异域世界的描绘,虽满足了人们尚奇的心理需求,但与艺术领域对“奇”的追求有本质区别。“奇”作为一种观念或标准,是人类生活发展到理性、实用阶段的产物。“奇”似乎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观念的对立面。人们不会将自己日常生活中常使用或见到的东西称之为“奇”。同样,一部分人称为“奇”的对象,在他人的生活和认知中也不会被以“奇”称之——“奇”或“不奇”极具变动性。例如,苏轼读到《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的记述,将之与当时济安江上常见之美石相比,感叹道:“岂古所谓怪石者耶?”随之苏轼发表了一番关于“怪”的议论:“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苏轼此番关于“怪”的讨论,用之于“奇”同样适用。这说明事物或存在的“奇”与“不奇”完全是不同主体的主观所见,由主体日常生活的内容和范围所决定。人们大多喜爱追求日常生活中罕见的奇人轶事、奇珍异宝。这反映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否定性态度。
在文艺创作领域,“尚奇”似是艺术家基本的创作方式和追求,其表现之一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超越,这也是对日常生活重复性的否定和超越,但这不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审美追求的主流。西方现代以来的美学主要由浪漫主义美学观构成。这种观念要求主体对重复性、机械化的日常生活进行否定,他们认为审美的生活和艺术创造是新奇而唯一的,不能重复,故而日常生活与独一无二的艺术追求根本对立。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日常生活之所以需要被“审美化”,原因在于其本身不是“审美化”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这一观念并不适用。魏晋时期,佛教经卷故事传入,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故事与之合流,产生了大量志怪作品,似乎兴起了一种“尚奇”的创作倾向。这些故事以鬼神信仰为主要内容,看起来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但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佛教进入中国,因果轮回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对这些故事的坚信,目的在于希望来生能有更好的生活。大量以道教信仰为基础的神仙传说,其思想根底和诉求则是在神仙幻境中永享世俗生活的乐趣:“奇”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而是肯定。
廓清这一问题的本质,关键在于理解神话思维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先秦两汉神话思维弥漫的时代,人们对世界充满奇异的幻想,通过各种神异非凡的神怪意象将之呈现。这时,支撑“奇”的是神话思维,它是先民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人们把这些内容作为真实的对象加以看待并顶礼膜拜。神怪意象虽超越日常生活的常规性而以怪诞奇崛的面貌呈现,但它带给人们的感觉是真实而神圣的。换言之,“尚奇”是神话思维在人类文化创制活动方面的体现,以神话思维为基础所创造出的神话意象体系,是先民呈现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规则的基本方式,神怪形象和事件之“奇”体现的是神性,它也是神话呈现真理的基本方式之一。例如,善画神佛形象的吴道子的作品影响极大,汤垕《画鉴》云:“尝见吴道子图‘荧惑像’,烈焰中神像威猛,笔意超动,使人骇然。”荧惑星君乃是马首、人身、六臂、食火的神怪形象,吴道子的传神笔法将其神性呈现淋漓,故能使作为艺术家的汤垕也产生“骇然”的感觉。这是在观览神怪意象中获得的超越世俗生活的心灵震动。我们不能把宗教作品对神灵的表现作为艺术尚奇追求的反映。人们对神灵神物的奇异表现,是由神灵形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神灵所生活的神山雾海、险山绝境属于神圣空间,与人们生存的世俗空间绝然不同。
随之,神话思维转化为艺术审美思维后,这种对奇异形象和事件的追求仍在文艺领域继续盛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延续神话意象或根据神话思维,对自然和社会中出现的超越常规的人、事、物进行记录、描述乃至创作,各种文人笔记、“剪灯”系列小说、谈狐说鬼的故事等,都是这种思维和趣尚的延续;在书法和绘画领域,人们往往呈现出对奇崛意象和风格的偏爱,以此呈现自我不同于流俗的高尚人格和思想,“奇”成为人们抵抗世俗规则和思想观念的一种方式。人们把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图绘为图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表现神仙幻境、神魔鬼怪的作品。与神魔小说成为文学作品类型的情况一样,这些作品也成为画科的一种,以牧溪、罗聘等人为代表创作的魍魉画,甚至成为文人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形貌怪异的魑魅精怪、枯木怪石、狂风骤雨,与文人们充满不确定性的宦海生涯以及纠结不清的心理世界正相吻合。数量庞大的宗教故事作品,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尚奇的心理需求,后世艺术家从中借鉴诸多元素,使自己的创作与正统风格保持了距离。另一种情况则是将“奇”转化为文艺创作的技法问题,认为只要超越前人的表现方式,使常规技法显出新意,便是对“奇”的实现,从而超越前人。这时“奇”就成为一个技法和修辞问题:修辞在语言艺术领域的变化和总结,皴法在绘画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域外技法的吸收与使用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自宋元以降,人们对“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奇”并不是偏离自然和日常生活而产生的新奇感,而是对自然和生活的重新发现。在重复性的日常经验中,我们一方面受到各种前见或标准的影响,不能形成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全面把握,从而对其客观存在之现象、性质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识见、经验、趣好往往限制我们对客观对象的全面认识。我们对客观真理和永恒法则的认识,通常是局部性和渐进式的,这为“奇”的存在留下了空间。对于艺术家来说,他正是要从眼前寻常之生活内容呈现出他人易于忽略或未发现的客观真实,人们一般把此类作品称为“奇作”,其语言被称为“奇语”。所谓“奇”者,正是对自然和生活真实的新发现。清人贺贻孙《诗筏》:
吾尝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如飞星过水,人人曾见,多是错过,不能形容,亏他收拾点缀,遂成奇语。骇其奇者,以为百炼方就,而不知彼实得之无意耳。
贺贻孙指出,“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只要“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也就是说,那些看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句”,正来自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细微而常见的景象和情境。正因为它们来自日常生活,如飞星过水,极易被忽视,那些对此类生活细节有所观察、体验、感动并以浅易晓畅之笔写出者,便可成就佳作、奇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之句就是如此:此景何人不见、何人不晓,却唯有杜甫能写出这样“状溢目前”的诗句。这种对日常生活本身之美的体悟,为诗为文为画作,实现了对平澹宁静之美的追求。晚唐艺术追求险怪、繁缛、华丽之风格,宋人矫正之,形成了对平淡之美的追求。在绘画领域,这种转变是通过舍弃险怪山石、悬崖绝壁等意象而追慕平凡风景的方式实现的。人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奇异之物,终究会乏味而难以为继,最终会导向内心的虚无,因为世间并无如此多追求不尽的美玩奇珍,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其本身蕴含的无限美感,才是品味生活乐趣、生命真谛的最终归宿。
明代中后期,人们对日常生活细致而全面的玩味、体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们非常重视从日常生活本身获得审美的愉悦、心灵的安静,从而为自我生存寻找更可靠的根基,日常生活、百姓俗事,成为“传奇”的对象,“奇”的观念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奇”不是对奇闻、异事、异物的记述,而是对寻常所见所历之日常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思索,从中悟解出常人不能见之意趣、思想。在艺术领域也有以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大量反映日常市井生活题材的画作。这些画作规模巨大,几乎将日常生活中所有正常、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面呈现。在文学领域,规模同样巨大的长篇小说形成,对市井生活进行细致描绘的《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是昆曲剧本规模的逐渐扩大,人们似乎沉浸在对世俗生活的体验之中而不可自拔。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市井俗事,人们却以“传奇”称之。文学艺术作品不再追求对荒远异事的记录,而转向对当下日常生活的关注,它们才是真正“甚奇特”的存在。这种对日常生活完整而细致地沉浸、玩味、观赏的审美追求,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形成并成为潮流。人们认为,“奇”并非来自异域灵府,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由于我们自己对日常生活缺乏耐心,故而不能发现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新奇之处。这对主体的识见经验、审美能力、立意情趣,提出了更高要求。李渔曾谈到填词文字对新奇的要求:大家创作都力求新奇,而新奇可分为“意新”“语新”“字句新”,但用语造句之新奇,比不上立意之新奇,而立意之新奇并非指专门摹写超越我们寻常见闻之外的事物,《齐谐志》《南华经》记述的妖魔鬼怪、荒远异事,都是新奇的皮相而非真正之新奇;作者描写的内容来自“别有所闻所见”,这种新奇是表面上的。也就是说,不常见的“奇”不一定就是“新”,在神话思维消隐的时代,奇异怪诞并不具有更多美感,有时还是美的对立面。而“新意”必给人“奇”的审美感受。立意是否新奇,关键在于艺术家本人能否从“饮食居处之内”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之意,这种新奇才是真正的新奇。与此相关,立意新奇之作,看其所用字句造语均极为平常,但透过字词修辞而领略其中所蕴藏的深意却是发人所未发,这是“词内之新”。在李渔看来,新奇的立意本就蕴含在“眼前事、口头语”中,并非能被人看完说尽;而能发现“眼前事、口头语”中新意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这种创作也才是真正的“点铁成金”。
可见,艺术作品的“奇”,应是诗人、艺术家以其独到的观察、灵动的体验、真切的情感,让原本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新鲜意趣和生命真实完整呈现,日常生活才是艺术作品“奇特之意”的最终来源。李渔等人的观点,不仅有效矫正了苏轼等人将“奇”等同于艺术家内心世界、将文艺创作和批评“尚奇”特征主观化的倾向,而且也向世人说明艺术作品描写神灵精怪、荒远异事、奇谈怪闻,都是浅层的“奇”。正因“奇”来源于日常生活,艺术作品对“奇”的表现也须符合自然和生活本身的原则,归根结底是对“理”的呈现。
三、“奇而入理”:“奇”作为呈现“理”的方式
当使用“奇”对某事物(包括思想、命意)进行评价时,我们就已预设了其与其他事物的差异——尚奇艺术观本质上是差异论艺术观。如果将之推向极致,则会导致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忽视普遍性的问题。孟子提出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也是强调万物之间的差异性乃其本身的存在特点。孟子指出,万物之间存在差异是万物本身存在的客观情势,不能强行将万物同一化,否则将引发天下大乱。对艺术作品来说也是如此:万物参差不齐,各有情态,无法以同样的形象呈现之。这种强调差异性的哲学观奠定了尚奇艺术观的思想基础。就像莱布尼茨所描述的那样,一位聪明睿智的伟大王后,在她的花园中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并不存在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这种强调差异性的思想,被认为是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或契机。但天下万物又共享一个“理”,万川之月实乃一月,“月印万川”和“理一分殊”的情况是并存的。这决定了艺术家对“奇”(万物的差异性)的表现须以“理”为最终根据,达到“奇而入理”的境界。
宋代学者董逌对此有过精深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形象虽有万千差异(“奇”),但这是由万物本身情态、形势的差异造成的,形象差异的背后共享了更为根本的“性”或“理”。如果人们只醉心于各具差异的“形”,而忽视背后同一的“理”,则无法领略艺术作品背后的真意。他在《书〈百牛图〉后》一文中以画中百牛为例说:“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异,所以使形者异也。画者为此,殆劳于知矣。岂不知以人相见者,知牛为一形,若以牛相观者,其形状差别,更为异相。亦如人面,岂止百邪?且谓观者,亦尝求其所谓天者乎?本其所出,则百牛盖一性耳。”董逌观看《百牛图》后发出了上述感慨:牛的形象虽各不相同,但“牛性”是同一的,“百牛盖一性耳”;观者如果只看到画中百牛的不同形象而为之感叹,则不能从中领略画家的本意。实际上,画面上牛的形态虽多,但仍未能穷尽牛的形态,如果要真正了解牛,则应在动静之际观牛之种种相,随见得形,才得“真牛”。
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奇而入理”的评价标准,“理”是“奇”的依据、标准和最终归宿,“奇”只是“理”得以显现的方式之一,“奇”与“理”须实现有机而辩证的统一和共生关系。人们认为,艺术家创作时虽强调奇异的构思和不同寻常的修辞,但这些须以“真”为第一标准,要遵循真实原则,否则便是胡编乱造。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诗奇而入理,乃谓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大抵读古人之诗,又必身亲其地,身历其险,而后知心惊魄动者,实由于耳闻目见得之,非妄语也。”洪亮吉指出,诗是否达到“奇”的标准和境界,须“入理”方可,否则便不是“奇”;诗作的“奇”不是胡编乱造、向壁虚构,而是诗人亲身经历过的各种险境、产生过各种“心惊魄动”的情感体验的结果,“耳闻目见”乃诗作能否“奇而入理”的关键。这是强调主体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诗人的情感、思想、眼界均是其不断拓展日常生活的边界而形成的,没有生活事实作为基础的胡编乱造只能是“妄语”,而不是诗。苏轼评柳宗元《渔翁》一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又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这说明,诗人创作虽然“以奇趣为宗”,要超越他人和日常,但须“反常合道”,不“合道”乃至与“道”背离,也就失去了诗的趣味。“反常”是手段,“合道”才是目的。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学创作中的“奇意”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时代、习俗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奇意”不会凭空产生,不能脱离人伦物理而存在。他指出,春秋战国之时,北方战乱频仍,六经之作、百家之书均在战乱中流散,故而使北方文学不彰,但“齐楚两国”却“颇有文学”。这是因为孟轲、邹衍、荀子等人创立了学风自由的稷下学派,而地处南方的楚国以屈原和宋玉的诗赋创作为代表,他们的作品辞藻丽比日月、彩逾风云,似乎已超过《雅》《颂》中的作品:“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所谓“纵横之诡俗”,是指楚国地处南方,宗教信仰发达,神话与民间传说盛行,风俗仪式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故而形成了楚国文章奇诡炫目的特点。这实际是说明楚国的文艺创作之所以形成“艳说”“奇意”,达到很高的成就,与艺术家所处时代和地区纵横驰骋的民俗风气有关。在绘画领域,《西域图》《职贡图》《王会图》《外国风俗图》等,本是实用图像,但因它们呈现了域外国家或民族的人像、习俗、器物乃至动物神灵,与中原差异极大,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从而在后世被不断临摹和仿制,以满足人们追慕异邦奇物的心理。这说明,事物奇异与否并非由事物本身决定,而是由观者识见所决定。艺术家应首先根据日常事物本身的性质特点进行客观描述和呈现,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新意。
所有诗作和艺术均须“入理”“合道”,而“理”或“道”只有一个,故而存在前人作品与后人作品的相似问题。今人作品与古人作品的不同,只是在“入理”“合道”的方式方面存在差异,本质上所有优秀作品均应达此境界。这样一来,今人作品与古人作品之间便存在似与不似两种形态共存的情况。同时,由于诗作需要“入理”“合道”,古人作品与今人作品实无古今之区别,亦无技法、情趣之区别,在这一标准的要求下,艺术的求新、尚奇不再具有优先性,这也是今人作品与古人作品“不能不合”的原因所在。今人作为今人,毕竟有自己“耳闻目见”的经验和体验,化而为诗,自然存在与古人“不能不异”的局面。因此,相比于古人作品,今人作品本身不求异而异自在,不求奇而奇已然。因此,后人学习前人作品,如仅重视技法、意象、构图,而不能对自然万物有自己的体悟,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与古为徒”的境界:作品中的“古意”历久弥新,表达的是永恒无声的自然之境,这才是后人学习前人作品的根本所在。沈周跋《沧洲趣图卷》云:“以水墨求山水形似,董巨尚矣。董巨于山水,若仓扁之用药,盖得其性而后求其形,则无不易矣。今之人皆号曰‘我学董巨’,是求董巨而遗山水。”董源、巨然的山水之作之所以能尽山水之形,乃在董巨能得山水之性。后人如果眼中只见董巨山水而不能得山水之性,他们学习的只是董巨的技法,却把真山水遗失了。反之,如果后人在得山水之性的基础上创作,即使不学甚至不知董巨山水,那他的作品仍可不异于董巨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万物的“理”(“道”或“性”)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化的存在,自然本身的奥秘,主体之情思,在艺术作品中往往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以真实性为核心的复杂的情境关系。这种综合性的情境既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也与一切事物相联。作品的“奇而入理”就是要呈现这种真实性和复杂性,让观者与之融为一体,领悟“道”的存在,沐浴在“道”的真理性光辉中,“道”也通过作品被复现。因此,人们并不会因为作家和艺术家创作了与自然、现实外在形象完全一致的作品而将之称为杰作,而是需要艺术家将各方面因素融合为一个完美整体。所以,“奇”是对客观真理、事物本身呈现的另一种方式,而与作品呈现的对象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本土的还是异域的,关系不大。这需要艺术家对客观世界本身抱有浓厚的兴趣,细致观察、认真思考,以高超的技法、无比的耐心,独有慧心地选择对象的某一特质而加以呈现。
由此可见,艺术作品是否呈现出独特的美感,其形式、造型是否新奇,关键在于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把握和呈现。这样,作品才能真正达到“奇而入理”的境界。
余论:“奇”与艺术独创性问题
上述论述意在表明,艺术作品的“奇”并不仅仅是独异性(Singularity,也有人译为“奇异性”)或独一无二性(Uniqueness),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独创性(Originality,又译为“原创性”),或者艺术家基于独特的想象力和修辞习惯所形成的艺术个性与风格。这些特征也包含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奇”范畴的内涵之内,对此,学术界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总结。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常将“奇”界定为艺术的独特性或原创性,这与康德美学的影响直接相关。在西方,人们在反思康德美学强调独创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将独一无二性、独创性融合而成的独异性概念及其美学形态。人们认为这种审美观是一种“基于自由感的精神愉悦,它肯定着独创性、独特性与个体自由,肯定着个体事实的独立存在,它正在影响着美学与艺术领域的评价尺度,正在生成为一套独异性美学”。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当代中国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古人的诸多论述表明,“奇”所指称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等,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变动性或不稳定性。在表层内涵上,艺术作品的“奇”考验的是艺术家和欣赏者本身独特的情趣、识见和能力。在这一层次上,以“奇”为标准的艺术观,类似于独创论或天才论美学观。在深层内涵上,艺术作品的“奇”须以“理”的准确呈现为根本旨归,基于此,可将“奇”界定为艺术家发现、呈现真理的另一种方式。艺术家对自然万物隐微秘境的领略、对深刻人性的洞察,都属于此。在这一层次上,以“奇”为标准的艺术观则是一种真理论或摹仿论美学观。
显然,这一界定与我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奇”的内涵有很大不同。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的标准,“奇异性”(defamiliarization,又译为“陌生化”)是文学作品的本质规定性,文学语言应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通过各种修辞,拉远语言所传递的经验与欣赏者日常经验之间的距离,而且文艺作品本身的审美属性只存在于这种独特的语言修辞和结构之内,带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学艺术(诗意)与日常生活是根本对立的。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将奇异性作为文学艺术得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也是其审美意蕴形成的最终根源。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语言模型的帮助下,无法计数的偏离正常语法规则的句子或语言表述被持续生成,但我们并不将之称为文学作品,原因在于这些语言模型的产物无法与人们的生命经验发生互动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秉持陌生化观点的理论家,不得不反思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修辞或语言表达所形成的“奇”的风格或内容,并不是文学性产生的必备因素。
关于艺术作品独创性的现代论述,是由康德开启的,康德之前,人们基本不讨论这一问题。比康德稍早的英国墓园派诗人爱德华·扬格,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讨论了艺术独创性问题。他们的讨论启发了康德,但两人的观点截然不同。扬格指出,无论是模仿性作品还是独创性作品,都是摹仿的产物:前者模仿他人的作品,后者则是摹仿自然,而摹仿自然的作品被称为独创性作品。康德将不可重复性、不可传授性、独一无二性等特质赋予天才以反对模仿。正是这些特性形成了艺术作品的独创性,而拥有独创性的作品须与其他作品区别开来。这与中国古人关于“奇”的论述有部分重合。
但是,对艺术作品独创性或独异性的理解,先天带有比较色彩。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独创。这一特点决定了关于独创性的判断必然带有某种滞后性。这是因为主体只有在体验对象之后,才能判断这一体验本身是否具有与其他事物相比而特有的差异性。因此,当我们使用独创性评价某一作品时,就已暗含了与其他作品的比较,而比较是在两次甚至多次类似的体验之后完成的。这样一来,我们关于独创性的判断便显得相当滞后。一旦这一比较和判断完成,艺术作品的独创性也会同时消失,因为这一特性被赋予艺术作品后,它的独特性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它已被多次欣赏、体验和比较。这一过程既是独创性产生的过程也是其消失的过程。
实际上,艺术作品在形式、主题、命意等方面重复或摹仿前人,并不影响其本身成为杰作,而那种将奇特性、独一无二性视为杰作特质的观点,反而使作品本身失去了存在根基:如果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与作品之间便失去了可比性,从而也使艺术史失去存在基础。对作品来说,形式与内容的新奇独特与否,并不是它能否成为杰作的必备特质,更重要的是它要与时代和过去密切相关,这样,艺术作品才能成为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艺术作品意蕴的厚重不在于艺术家本人,而取决于它与历史的关联度;奠基于此,它才能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呈现出来。这也正是前文所述艺术作品应该“奇而入理”的意义所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