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西美学和诗论中,与“奇”相关的如惊奇、新奇、险奇、清奇、奇辟、奇趣、奇崛、陌生化、非人化、间离化等概念,满足了相似性属性,形成了一组独特的家族相似概念,构成中西美学与诗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主题。这些概念提倡突破“文字之本”,创造与前在符号不同的“奇”符号,更新主体的感知体验,可以说都体现了“逐奇”的审美倾向,有着共通性的审美内涵。借鉴钱锺书对中西观念的比较思路,突破中西语境的限制,从“逐奇”这一审美范式维度对中西“奇”进行通约对读,不仅可能,也是当下文艺美学研究应有的理论姿态。
关键词:奇;中国美学;西方美学;逐奇;比较
作者杨向荣,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杭州 31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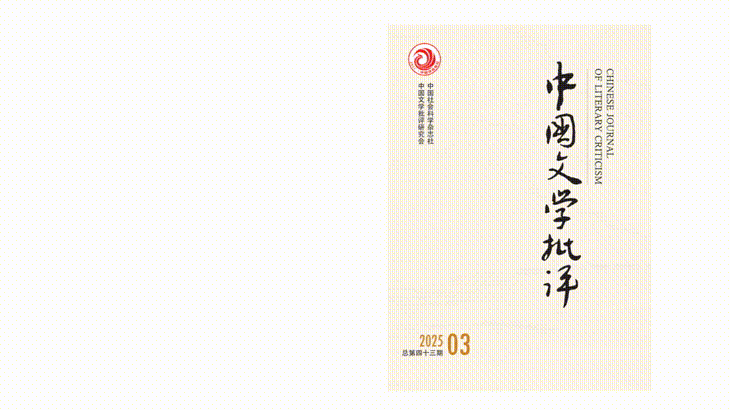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奇”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周朝时期就有“睹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识”(尹喜《关尹子》)的说法。南北朝时期,“奇”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观奇正”命题奠定了“奇”在文论和美学领域的发展基础,而历代诗论家们对“奇”的讨论更是使其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奇”在中国古代的演变不同,西方虽然没有与其直接对应的美学范畴,但却有着大量相似的诗论和美学观。亚里士多德、朗吉弩斯、马佐尼、缪越陀里、黑格尔、什克洛夫斯基、布莱希特、奥尔特加等人都曾提出相似的理论主张,由此形成西方美学“奇”论的发展脉络。借鉴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中西类似观念的比较思路,笔者以为,“奇”不仅是一个美学和文论范畴,而“逐奇”也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美学范式。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关于“奇”的思考体现出“逐奇”的审美范式,可以将这些讨论纳入“奇”的理论视域。
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奇”
何谓“奇”,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为:“奇,异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在这里,“奇”有两种内涵:一是“异”,即独特性;二是“不耦”,指单数或奇零。这两种意义虽然有所差别,但基本指向一致,都强调了“异”的内涵。
与刘勰赋予“奇”多重意义不同,钟嵘在《诗品》中赋予了“奇”更多正面色彩。钟嵘主张通过辞采体现“奇”,强调以“奇”达到直致之美和风骨之美。在钟嵘所评上品词人中,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祯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陆机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至于中下品的诗人,钟嵘也多以“奇”论之,如评张华诗“其体华艳,兴托不奇”,评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评任昉诗“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等等。在钟嵘那里,“奇”既是对文章风格的品评,又是对诗人天赋的品评。“奇”不再与儒家“宗经”传统联系在一起,也不再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转化为诗文品鉴的自主性审美范畴。
到了宋代,“奇”屡屡出现,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学批评和审美范畴,多用于文章的评论中,强调题材内容上的出奇。苏轼在评陶渊明诗时提出“奇趣”范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苏轼强调,诗在内容上要以“奇趣”为宗,要以“反常合道”为趣,“奇趣”是一种奇中有趣,奇中有理的审美体验。王安石提出“奇崛”概念,他在评张籍诗时写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指出,“奇崛”源于“寻常”,文章题材和内容只有“常”中见“奇”,才能实现“看似寻常最奇崛”的艺术效果。黄庭坚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提出“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的说法,认为“变”生“奇”,文章只有不断变化风格,才能有创新,才会形成“奇”的审美风格。
刘熙载将“奇”和“稳”并举:“文尚奇而稳,此旨本昌黎《答刘正夫书》。奇则所谓异也,稳则所谓是也。”与刘熙载类似,清人孙万春在《缙山书院文话》中也谈到“奇”与“稳”的关系,认为“奇辟之文,须从纯稳之思破露而出。纯稳之文,须从奇辟之意涵泳而成。”在孙万春看来,奇美之文需要纯稳之理,而纯稳之文需要奇辟之境。清人朱宗洛在《古文一隅》中也认为,“凡文章用意要稳,设势要奇。不稳则意与题隔,安能令阅者心肯;不奇则势涉平弱,一望徒令人心厌耳。”朱宗洛指出,文章需要在用意上求“稳”,同时也需要在设势上求“奇”,不稳则离题万里,不奇则过于平庸。
明清时期的“逐奇”倾向不仅体现在诗文中,也体现在画论、剧论和小说评点中,画论“尚奇”,古已有之。东晋画家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就以“奇骨”论画,提出“有奇骨而兼美好”“骨趣甚奇”“隽骨天奇”等说法。南朝谢赫有“一点一拂,动笔皆奇”“出入穷奇,纵横逸笔”“意思横逸,动笔新奇”“笔迹超越,亦有奇观”的说法。到了明清时期,画论家以“奇”论画,更是成为一种风尚。明人王樨登评唐寅画“画法沉郁,风骨奇峭”,清人方薰认为绘画“气格要奇,笔法须正”,都是强调绘画应当体现“奇”的审美风格。清人沈宗骞还提出绘画的“平中之奇”命题,认为不能因奇而求奇,他以米元章、倪云林、方方壶等人的绘画为例指出,虽然这些画家笔下的场景都很平常,但其中的“清和宕逸之趣”和“缥缈灵变之机”, “乃是真正之奇也”。
画论重“奇”,戏剧评论亦如此。虽然在元代,《录鬼簿》就有“移宫换羽,搜奇索怪”的说法,元人胡祗遹在《黄氏诗卷序》中也提出戏曲艺术“时出新奇”原则,但真正以“奇”论戏剧是汤显祖和李渔。汤显祖用“奇”来品评戏剧,认为“奇”是一种区别于戏剧程式化风格的新奇风格,“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李渔强调戏曲创作既要立意奇特,同时应当保证语言表意的妥帖和确切,“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李渔还以“新奇”追溯戏曲名称的由来。在李渔看来,“传奇”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所载之事奇特,无人所见或传播。
小说在明清时期蔚为大观,“奇”是当时小说批评的一个主要标准。明人徐如翰在《云合奇踪序》中认为,小说要写奇人、奇事和奇文,“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毛宗岗评《三国演义》认为“文有正笔、有奇笔”,其中“奇笔”通过插叙等手法,让小说产生悬念,引发读者形成好奇心理。金圣叹评《水浒传》和《西厢记》也将“奇笔”作为一个主要的审美原则,如“奇笔恣墨,读之叫绝”“写得险怪,真是奇笔”“奇笔妙笔,总出常人意外”“夫不遇难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便是此一副奇笔,便使通篇文字立地焕若神明”等。
在中国古代,“奇”最初是一个军事学术语,主要指用兵之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奇”开始进入美学与文学批评领域,成为一个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唐宋以来,“奇”主要用来表征文章风格和审美意境的奇特或怪异,诗论家们多用“奇”论诗,如司空图、殷璠等。“奇”开始与“境”“味”“清”“趣”等范畴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带有雅趣内涵的美学范畴。明清时期,“尚奇”风尚流行,“奇”不仅在文学批评、画论和剧论中得到广泛运用,也是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风尚,其审美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们在逐“奇”的同时,也注重“奇”的对立面“正”和“理”,强调奇不伤正、奇不违理,这也赋予了“奇”独特的审美意蕴。
二、西方美学中的“奇”
西方并没有出现与中国古代“奇”一样的范畴,但却有着与“奇”内涵相近的诸多范畴。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惊奇”和“新奇”等概念,德国古典美学时期,黑格尔也对“惊奇”范畴展开了深入讨论。在西方现代美学史上,什克洛夫斯基、奥尔特加和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非人化”“间离化”范畴,都是与“奇”相类似的范畴,体现了“尚奇”的思维模式。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从未知欲望的心理维度出发,论及了“好奇”心态。“求知和好奇,一般说来,是使人愉快的;好奇意味着求知的欲念,因此好奇的对象就成了欲念的对象;求知意味着使人恢复自然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中的变化是使人愉快的,变化意味着人们未知欲望的打开,意味着个体恢复到了自然状态。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从心理学维度出发,强调个体接受过程中的“新奇”心理,认为只有当熟悉的事物出现变化,才会与日常生活隔得较远,才会引起人们的未知欲望和“好奇”心理。
亚里士多德深入分析了悲剧情节所应当采用的“新奇”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应当通过“突转”和“发现”来组织和设计情节,其中“突转”强调“变化”的重要性,而“发现”则是对悲剧情节能引发“新奇”和“惊奇”效果的一种设定。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悲剧应当通过“发现”,形成“惊奇”的审美效果。“惊奇是悲剧所需要的……惊奇给人以快感,这一点可以这样看出来:每一个报告消息的人都添枝添叶,以为这样可以讨听者喜悦。”
除了在悲剧情节和审美效果上强调“奇”,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文章风格的时候,也强调通过对词语的“奇化”来达到“新奇”的审美效果。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装饰字和变体字等,认为这些“奇字”的混合使用,可以使文章风格产生奇特的审美效果, “它们因为和普通字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所以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普通词和奇异词,他主张在文章中使用与众不同的词汇,如具有异乡情调的词、无人使用的创新词、新添内容的变词体,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奇异词的使用,以及他所提到的“惊奇”“奇异”和“新奇”等说法,更多是局限于修辞学层面,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手法,使文章风格变得与众不同和富有新鲜感,进而迎合大众的“好奇”心理,并没有上升到美学与文学批评的范畴层面。
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重视文章的崇高效果,认为“诗的形象以使人惊心动魄为目的,演说的形象却是为了意思的明晰”。在朗吉弩斯看来,崇高是文章的一种新奇风格,能让接受者获得奇特和惊心动魄的审美效果。朗吉弩斯指出,崇高会形成惊奇效果,而这必须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需要通过“引人注目的措辞”和“惊心动魄的事物”形成文章的崇高风格,使接受者感受文章“惊人的威力”和“迷人的魅力”。
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马佐尼在《〈神曲〉的辩护》中强调诗是一种娱乐性的模仿艺术,诗的“格律”与“和谐”结合“可信而且可以引起惊奇的题材”,可以使人获得娱乐和教益。马佐尼对“惊奇”的论述可以说是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诗的题材应当“惊奇”,诗通过“新颖的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思想,来导致可信和惊奇”。“把可信的东西当做可以引起惊奇感的来看,它就变成适合于诗的题材,因为诗总是追求令人惊奇的题材”相对于亚里士多德,马佐尼从诗的题材讨论“惊奇”,无疑丰富了“惊奇”范畴的审美内涵。
17世纪,意大利美学家缪越陀里在《论意大利诗的完美化》中论及“新奇”,认为“诗人所描绘的事物或真实之所以能引起愉快,或是由于它们本身新奇,或是由于经过诗人的点染而显得新奇。这种(发见新奇或制造新奇的)功能同时属于理智和想象”。缪越陀里将“新奇”视为诗人的才能和天赋,优秀的诗人可以“发见新奇”与“制造新奇”。同时代的英国文学评论家爱笛生在《论洛克的巧智的定义》中写道:“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它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爱笛生认为不平常的事物能够使心灵产生“愉快的惊奇”,赋予了“惊奇”新的审美内涵,即“惊奇”是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爱笛生还提出“想象的乐趣”概念,认为它源于伟大、新奇、美的事物。
德国古典美学时期,黑格尔论述了审美过程中的“惊奇感”。在黑格尔看来,个体在认知过程中会因为对象的熟悉而熟视无睹,会因为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性而形成自动化接受心理。黑格尔强调,艺术观照源于惊奇感,“只有当人已摆脱了原始的直接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以及对迫切需要的事物的欲念了,他才能在精神上跳出自然和他自己的个体存在的框子,而在客观事物里只寻求和发见普遍的,如其本然的,永住的东西;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惊奇感才会发生”。在黑格尔看来,“惊奇感”是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因为“惊奇感”,艺术观照中的自然事物“不是以它们的零散的直接存在的面貌而为人所认识,而是上升为观念,观念的功能就获得一种绝对普遍存在的形式”。
黑格尔区分了诗和散文,认为散文要求表达的直白和通俗,而诗则要求摆脱日常的自动化和无意识表达方式,“诗有时可以用古字,即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字;有时也可以铸新词,从而显出大胆的创造性”。在黑格尔那里,诗追求“奇”,只有维持惊奇感,诗才能获得发展,因为“在过去时代里许多本来是新鲜的东西,经过重复地沿用,就变成了习惯,逐渐习以为常,转到散文领域里去了”。黑格尔认为,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诗歌语言就必须背离散文语言,要对散文语言进行奇化或更新,让语言时刻产生惊奇感。
1925年,西班牙艺术理论家奥尔特加提出“非人化”概念。奥尔特加认为,任何现代艺术都自发地形成一种新奇效果,它导致了现代艺术的陌生化。奥尔特加指出,现代艺术家“明目张胆地把现实加以变形,打碎人的形态,并使之非人化。……现代艺术家迫使我们即兴发明一些沟通的新形式,它们全然有别于同事物沟通的惯常方式”。奥尔特加认为,现代艺术家通过剥夺现实生活的外观,摧毁了通向日常现实的“桥梁和渡船”,同时也更新了现代艺术的感知经验。笔者以为,“非人化”通过把实在变形,将个体的艺术体验模式更换为一种陌生化的感知体验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奇化”的艺术处理方式。
20世纪30年代,德国戏剧美学家布莱希特提出“间离化”(也译为“陌生化”)概念。布莱希特通常将Verfremdung和 Effekt合在一起使用,强调“间离效果”。布莱希特指出:“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在布莱希特的理论中,“间离化”有间离、疏离、异化等含义,意味着把日常熟悉的事物处理成一种奇特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它强调戏剧的批判性效果,意味着主体认识论的完善,是实现社会批判的武器和策略。
在西方美学史上,理论家们对“奇”的讨论虽然没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路径,但却存在一条“奇”或“新奇”的诗论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朗吉弩斯、马佐尼、缪越陀里、爱笛生、伏尔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黑格尔,再到什克洛夫斯基、奥尔特加和布莱希特,求新趋异、趋奇走怪的审美心理期待成为“奇”范畴发展线索上艺术创作的动力源。需要指出的是,将什克洛夫斯基、奥尔特加和布莱希特的理论置于“奇”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说“陌生化”“非人化”“间离化”等范畴就是“奇”范畴的子范畴,只是说这些范畴体现了“奇”范畴的思维模式,即都强调艺术创作中的“奇化”或“难化”手法,重视接受主体“求奇逐异”的审美心理。
三、作为一种审美范式的“逐奇”
中西美学史上都有对于“奇”及其相关内容的讨论,它们散见于诗人、作家、评论家和美学家的著作中,形成“奇”的丰富内涵。需要指出的是,中西美学和诗论中与“奇”相关的思想资料,如惊奇、新奇、险奇、清奇、怪奇、奇辟、奇崛、陌生化、非人化、间离化等,是一些满足相似性属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组独特的家族相似范畴,构成中西美学与诗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题。
其次,中西都有“逐奇”倾向,但在“奇化”的策略上,中国以“奇化”为手段,西方则以“奇化”为目的。形式的“奇化”在中国古代诗论中表现为违背常理和习用之语。李渔写道:“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想不到”和“猜不着”即强调通过情节的变形来实现文本的“奇化”。在西方,艺术形式的“奇化”是为了延长审美感受的时值,强化接受者的审美体验。为了克服文学创作的自动化倾向,艺术家必须创新形式,使趋于“自动化”的形式重新“奇化”起来。因此,形式的“奇化”体现为文本语言和形式的变形,如什克洛夫斯基曾区分“故事”和“情节”,认为前者指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后者则是对事件的“变形”。
虽然中西都将“变形”视为一种“奇化”策略,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中国,诗论家们关注文本的社会关怀,强调文本的微言大义,“变形”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表现内容的手段。皎然写道:“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就是强调通过形式的“奇化”表达“真奥之思”。西方强调作品的可感性,强调文本自身的可感性。在西方不少“尚奇”的思想家那里,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他们并不关注读者是否理解文本,而关注文本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让读者所感受到,文本的内容及其所呈现的社会文化意义被他们所忽视或遮蔽,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
“逐奇”要适度,还应当看到“奇”与“常”的相辅相成关系。明人李贽说:“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清人叶燮说:“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可见,对“奇”的追求要做到“陈”中有“新”,“常”中见“奇”。
结语
在中国古代,“奇”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审美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刘勰将“新奇”视为文章八种风格的一种,认为“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在“尚奇”美学思想的影响下,诗论家们多用“奇”来评论诗文,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诗“奇之又奇”;评刘眘虚诗“思苦词奇”;评高适诗“甚有奇句”。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马佐尼、黑格尔、什克洛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人所提出的“新奇”“惊奇”“陌生化”“间离化”概念,提倡突破“文字之本”,创造与前在符号视野不同的“奇”符号,更新主体的感知体验,可以说都体现了“逐奇”的审美范式。基于此,突破中西语境的限制,将这些概念置于更为宽泛的视域中加以对比,不仅可能,也是当下文艺美学研究应有的理论姿态。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