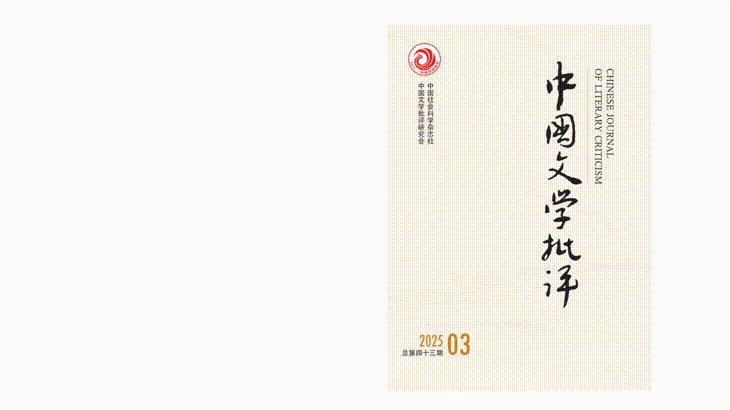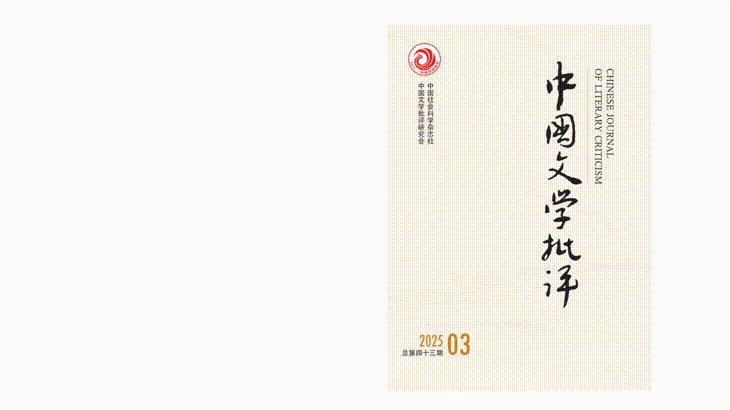
在汉语中,“奇”是一个多音多义词,包含奇特、异常、出人意料、变幻莫测等语义,也可指令人惊奇或诧异的事物。“奇”在中国美学和艺术领域大量出现,作为中华美学关键词的“奇”根基深厚,底蕴丰富,其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观念的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美学意蕴,随着现代美学学科意识的兴起,“奇”的理论价值不断被凸显。
在中国古典语境中,“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确立、唐宋之际发生嬗变、明清之际出现现代性转型萌芽。“奇”在魏晋南北朝出场频率较高,堪称艺术批评的重要术语之一。刘勰在褒贬兼顾的态度上使用该词,提出“以正驭奇”的说法,钟嵘也赋予“奇”以积极意义。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搜神述异、情节奇幻的传统延绵不绝。唐人刻意“好奇”,使“奇”这一关键意蕴发生嬗变。宋人话本近实而奇采渐失。此后,艺术结构之“奇”引起广泛关注。明清之际,“奇”的主体性因素不断突出,市民趣味发达,尚奇成风,出现了现代性转型萌芽,“以常出奇”“奇出于心”等观念深入文心,追求常中之奇,取材从鬼神怪异转向平凡的人情事理,展现世俗生活和日常情怀。以上是对“奇”在古典语境中演进历程的概述,本文旨在从整体上把握其古典意蕴,并结合中国现代美学对“奇”的阐发,管窥其现代理论拓展。
一、“以正驭奇”的审美理想
刘勰提倡“以正驭奇”,为“奇”这一美学关键词的意蕴生成奠定了基础。此后,谢榛“奇正参伍”、董其昌“似奇反正”等说法,也都贯穿着“以正驭奇”的审美理想。
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奇”出现数十次,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应根据具体语境而定。他肯定《离骚》作为“奇文”的价值,要求“酌奇而不失其贞”(《辨骚》),“即势以会奇”(《物色》),又把“新奇”列为八体之七,并释之为“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体性》)。儒家崇礼尚仁,排斥不合礼法的言行,以“奇”及其相关词语(如“诡”“怪”“异”等)指称非常、偶然或特别的事物,奇人、奇行、奇物等由于背离“常”(礼、法、道)而成为道德批判对象。概言之,儒家没有为“奇”提供积极评价的传统,刘勰论文以儒家思想为本,坚守“宗经”“征圣”立场,批判宋齐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序志》),偏离正统而求新奇。他不满形式主义盛行,批评近代辞风“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定势》)。“正”以五经为范式,属于典雅文风和正统法则。“奇”指向楚辞的虚构、夸张和想象,也批判背离典雅、精练、教化之道而追逐“新奇”之举,后者正是宋齐文坛求新求奇之势。刘勰针对怪异奇巧文风,主张“执正以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强调奇正虽反,应兼解俱通,随时应用,不可偏废。正如詹锳所言:“奇和正是一对矛盾。刘勰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新奇,只是叫人们不要专门地追逐新奇而失去正道。”这一看法符合刘勰以儒学为本的思想立场。
刘勰“以正驭奇”也与兵家之“奇”有关。兵家与老子思想相关,却并非老子思想的复制。老子指出“奇”“正”的作用领域有别,不离道法自然,孙子“奇”“正”并重,作为实战计策而存在。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正”是指作战的常法,“奇”是指作战的变法。孙子主张作战“以正合,以奇胜”,奇正如战势总纲,善奇是指变法无穷,用兵妙在奇正相生,作战既要遵照常法,又要随机变法,用兵有法而无定法。稳操胜券,必定奇正并重,使敌军捉摸不透而制胜。兵家承认奇与正既对立,又相互转化,对“奇”生成的影响主要在艺术构思、结构布局等方面。刘勰对奇正关系的思考受到兵家奇正论启发,且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根柢。中国艺术家论艺如兵家布阵,奇正不定,变化多端。项穆《书法雅言》论及奇正关系,认为书法如用兵,制胜相通,就像作战需要临阵决机,书法之前审势谋划,阵势、字形多变,行伍、体格不可乱,奇正互依,正而不奇,质而少文,奇不离正,文而尚雅,这与刘勰“以正驭奇”的脉理一致。
唐宋儒学复兴,奇正关系的探讨被纳入文以载道、艺以传理的背景之下,普遍追求“文奇”与“理正”的统一,“文奇”无妨“理正”成为共识。艺术构思、结构布局可独创风貌,不落常规,艺术法则和技巧可以多样化,但不能有悖于整体的美感,不能背离雅正之风和中和之美,这是儒家美学观的体现。因此,艺术要求立意深远,句法新颖,话语清新,常中藏变,正中含奇,从心所欲不逾矩。
明清文士重视艺术技法、法度,也使之与“奇”“正”联系起来。谢榛论诗:“譬诸诗,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执泥,隽伟而不险怪,此奇正参伍之法也。白乐天正而不奇,李长吉奇而不正,奇正参伍,李杜是也。” 谢榛把“奇正参伍”作为运法理想,并以此评价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等诗人,主张造语奇古,正奇相参,不入偏执歧路,而格调高古,气韵充盈,不失正宗。董其昌论书,提出“似奇反正”之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宕用笔处,无迹可寻。若形模相似,转去转远。”他要求书法创作突破形似模拟之风,展现个性风貌,王羲之书法似奇而反正,不离自起自倒,自收自束,故称典范。中国艺术讲究正奇并重,“正”是指顿挫、照应、威仪、节制和法度,“奇”在参差、起复、萧散、风姿和神妙,二者结合,方有奇作妙品。
晚清朱庭珍从反面揭示“以正驭奇”之理。他认为,“七律贵有奇句,然须奇而不诡于正,若奇而无理,殊伤雅音,所谓‘奇过则凡’也”。 他列举赵秋谷“客舍三千两鸡狗,岛人五百一头颅”,毫无余味,求奇太过,不合理致,不为佳构。换句话说,既在意料外,又在情理中,奇而有理,方为石破天惊之作。同列“奇伟”,韩愈与李贺诗风不一,这是“造奇”与“求奇”之别,从韩愈与李贺之别见证“奇过则凡”之理,卢仝辈无理而求奇过甚,背离风雅正道,也就是奇而诡正,故其诗风不足观。
可见,刘勰提倡“以正驭奇”为“奇”确立了核心意蕴,像谢榛“奇正参伍”、董其昌“似奇反正”、朱庭珍“奇过则凡”等说法,都是围绕奇正关系展开的,它们都把“以正驭奇”作为审美理想。
二、“以常出奇”的审美趣味
“以常出奇”的审美趣味是“奇”的又一古典意蕴。它围绕“常”与“奇”的关系而展开,是“奇”在艺术法则方面的体现。这层意蕴的生成与老庄思想、大乘佛学般若空观的滋养有关。
老庄思想蕴含“奇”的智慧。《道德经》认为“正”“奇”分别在治国、用兵领域发挥作用。老子还主张“有无相生”(《道德经》第二章),“正言若反”(《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为“奇”“正”相互转化提供了理据。与儒家的态度不同,庄子以“奇”“恑”“怪”等词指称奇特而不容于世之物,并赋予积极意义。庄子齐物论讲万物价值齐同,所谓“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齐物论》),破除对美/恶、奇/常等对立之见。一般人受世俗偏见或主观认知所限,产生“恢诡谲怪”之类的评判,而在庄子这里,齐物不是人为刻意地规整物之状态,使之规矩划一,“恢诡谲怪”喻示万物理殊而道通为一。齐物论超越事物的形状计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世俗认知的观物方式。按照庄子学派的理路,万物一气所化,“神奇”与“臭腐”并非定在,彼此可以相互转化。郭象注:“各以所美为神奇,所恶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恶也;我之所美,彼或恶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 事物本身并无美恶之分,由于人的情感所致,情之所美者为神奇,情之所恶者为臭腐。对此,应予以破除,毕竟“神奇”与“臭腐”均为万物之一。它们都不是固定的存在,而是不断地变幻生成。
随着大乘佛学东渡及其中国化,般若空观在文士阶层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渗透。般若空观认为,美/恶、奇/常等不过是人的幻妄之见,从般若空观看,其体性虚空,并非实在。随着禅宗兴起,庄子齐物论被激活,并与般若空观构成合流之势,共同促使“奇”的意蕴生成。
苏轼深明物极必反、奇常不二之理,论艺推重“奇趣”,不是刻意求奇,而是常中见奇。他称陶诗趣味奇特,评永禅师书时,称“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肯定渊明诗充满“奇趣”,二是以诗之“奇趣”类比永禅师书之“奇趣”。渊明诗初观散缓,细品识其奇趣。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皆话语质朴,意味深远,造语精到,平淡中见奇趣。
明清之际市民趣味勃兴,尚奇成风,以“奇”命名小说的现象普遍,如《拍案惊奇》《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由此满足市民的猎奇趣味。与唐宋之“奇”相比,晚明艺术尚奇之风从鬼神怪异转向人情事理,追求常中之奇,更注重世俗生活和日常情怀的展现。一些批评家为通俗小说作序时,强调它们之所以“奇”,并非出于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而是耳目之内的日用起居,生活细节蕴藏着谲诡幻怪的素材,绝非常理可测。这是对以往在耳目之外探索谲诡幻怪的反拨。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他把小说之“奇”划定为“无奇”之奇,与艺术真实性联系起来,回归日常生活的呼声强烈。以往志怪小说之“奇”多指不见经传之事、非同凡俗之人,与之相比,晚明小说之“奇”来源更广泛,也更日常化,像天理人伦、节孝忠义、因果报应之类皆可取材,突破了无从征实的鬼神怪异故事编造方式,也为艺术真实性的现代转型铺就了道路。
明清之际,艺术批评形成了“以常出奇”的风尚,一方面是“奇人奇事”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对“奇”的诉求趋于日常化、经验化,要求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深度挖掘“人情”,用心揣摩事理,以小切口作大文章,摆脱庸常琐碎的状态,显现世情蕴藏的意义,表达“以常出奇”的趣味。金圣叹认为,“奇妙文字”应以“平时道理”为根源:“一篇奇妙文字,却是一片平实道理。故先贤每教人,未提笔作文字,必须先将道理讲得烂熟于胸中。盖道理为文字之准衡,而平实乃奇妙之祖炁也。”或者说,奇妙文字是平实道理的自然流露。“奇”既可指取材不同凡俗,也可指艺术技法、构思布局等别出心裁。倘若刻意求奇,悖于情理,喧哗取宠,无理取闹,则会遭到批评。
中国艺术论强调“新奇”出于“平常”。至情至理之妙文,此为中国艺术之理想。世人厌恶平常,其实,天下最新奇者莫不出于平常,此有艺理存焉。日月千古而常新,与其在平常之外追逐新奇,骑驴觅驴,不如反求诸心,从平常之中发现并创造新奇。贺贻孙论诗:“吾尝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如飞星过水,人人曾见,多是错过,不能形容,亏他收拾点缀,遂成奇语。骇其奇者,以为百炼方就,而不知彼实得之无意耳。即如‘池塘生春草’,‘生’字极现成,却极灵幻。虽平平无奇,然较之‘园柳变鸣禽’更为自然。”“寻常”与“惊人”的转化取决于审美发现的眼光和艺术创造的能力,“极现成”是指得知自然,说得明白,貌似平常,实则通俗而不凡,“极灵幻”是指构思奇妙,诗语奇特,生灵活现。艺术家成就“惊人之句”,关键在于透悟人情事理,把握艺术创造真谛,至于题材选择、主题构思,倒不是决定性因素。
三、“奇由心生”的创造意识
老庄道家和禅宗心性论发达,对中华美学关键词的生成有直接作用。中国艺术论有论调认为,艺术无奇巧,唯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极力造作,不如师法自然,无心凑泊。老庄开启重视生命体验的传统,禅宗推重妙悟,讲究自证自悟,促成注重审美体验和当下感受的传统,“奇”的意蕴生成也深受道禅滋养。“奇由心生”的创造意识是“奇”的又一古典意蕴。这层意蕴是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起突出作用,可再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天资、禀赋和遭遇等较为奇特的主体素养;二是审美活动具有神思、妙悟等奇妙的特征,艺术创造需要开启心源。
先看第一个层次。在天资、禀赋和遭遇等方面较为奇特的主体素养,即所谓的“奇士”,其性情、禀赋、气质、遭遇区别于常人,且艺术才能突出。“奇”可读为ji,“单数,耦之对”。 《周易·系辞下》有“阳卦奇,阴卦偶”之说,阳卦以一阳为主,一阳为奇。奇是单数,古典语境中多以“奇士”指称文人不偶,或仕途不遇。“奇士”不合中庸之道,却与庄子学派的思想契合。庄子借助形态奇特的人物寄寓哲理,赞扬奇特而不甘流俗的人格精神,推崇符合天人合一理想的“天之君子”。如《大宗师》对“畸人”“畸于人而侔于天”的描述,就属于理想的人格形态,“畸人”非“中行”之士,更非常人,他们天机极深,翛然往来。此外,《庄子》语言有“奇”“怪”等特点,对后世艺术尚奇之风的形成也不无影响。
李贽深受庄子思想滋养,其审美观念弥漫着尚“奇”的气氛。他说:“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数奇”是指“不偶”,李贽以“数奇”自谓,强调个人的困苦经历、不幸遭遇是艺术精神的重要成因,这是韩愈“不平则鸣”的另一表达。袁宏道为徐渭作传,突出其“数奇”“好奇计”“然竟不偶”“无之而不奇者”等特征,袁宏道把徐渭塑造为仕途不遇、命运坎坷,却又禀赋奇异的形象,这种批评理路既是发挥“知人论世”的传统,又融入了“发愤著书”的观念,表现出以艺术浇注心中块垒的取向。此外,对《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的批评也能见出此一理路。
明清文坛把“奇”理解为摆脱庸常的个性风格,归于审美心胸和奇特性情所致,这是对以往把“奇”规定为取材和艺术法则的突破。汤显祖序称:“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如意则笔墨无滞,不落凡俗,自有奇格。明清艺术论批判刻意争奇之风,认为豪杰之士,当为奇士,有杰出才能,方可创造奇妙之文。何昌森《水石缘序》:“从来小说家言: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即事奇、人奇、遇奇矣,而无幽隽典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又何能供赏鉴?”何昌森把奇文归因于两方面:一是题材奇特,二是笔墨神奇。二者不可或缺,终归于文人“心有所触”,以性情胸臆为本,故应以静气戒除浮躁,不盲目趋新,表达冲淡平和之致。这是对小说之奇较为辩证的分析。
再看第二个层次。审美活动具有神思、妙悟等奇妙的特征,艺术创造需要开启心源。钟嵘反对诗中隶事用典,认为作诗贵于“直寻”,“诗不得奇”归因于博物、用事,违背了审美活动的规律。他有意识地把“奇”与“直寻”概念联系起来,如评陆机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此后,司空图主张“直致所得,以格自奇”,顺承钟嵘而来,“直致”与“直寻”内涵相通,开启直抒性灵的批评传统。晚明文坛标榜个性,反对形似工巧的造作行为,推重质朴自然的文风,不计较字句之奇。汤显祖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在此,“怪怪奇奇”是指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奇妙构思。汤显祖以画论文,苏轼所画枯木怪石风格奇异,不落画格程式。
中国艺术讲究品第境界,像《诗品》《画品》《书品》之类,都蕴含境界论内涵,其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清奇》、黄钺《二十四画品》之“奇辟”皆以奇为美。司空图写山中清奇、水边清奇之境,展现山林隐逸生活。可人神采奇异,不落俗调,迥然独立,美在脱俗。王士禛故而评之:“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澹不可收。’是品之最上者。”足见“清奇”一品地位崇高。“奇辟”之境需经历一番奇崛、艰辛的工夫,禅宗所谓渐修顿悟,正是洞开奇境之法门。“奇辟”与“清奇”都注重性情涵养之功,推崇妙悟自然。
唐宋以来,随着禅宗在文士阶层的传播和渗透,妙悟思想渗入“奇”这一关键词的生成当中。孙过庭把学书分为初求平正—务追险绝—复归平正三步,实质上可视为审美妙悟的过程,折射出禅宗思想的滋养。妙悟是禅宗的观物方式,通过摆脱世俗沾染、解除心灵障蔽,从而开启个人自性,起用生命智慧。妙悟前无主客二分,也无自我意识,妙悟后心灵处于澄明状态。因此,妙悟既是去蔽,也是敞亮,前者属于工夫,后者属于境界,二者相待而存。唐代青原惟信禅师有“见山见水”之说。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这段话融妙悟工夫和境界于一炉,涉及对世界的重新领会。妙悟破除对事物的遮蔽,又照亮真实的世界。妙悟后,山水依然是山水,却非悟前所见之山水,此时,山水灿烂如春,通透灵明,本真自在。这则禅宗公案表明,妙悟能激活人的本然觉性,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
妙悟突出个体心性的功能和作用,破除对知识理性对事物的认知边见,高扬当下真切的生命体验,这对于从主体角度理解“奇”及其意涵生成提供了依据。这就要求艺术家心无所滞,不加拣择,该奇则奇,当巧则巧,触缘造境,随物赋形。金圣叹评《水浒传》第四十一回:“何等奇妙!真乃天外飞来,却是当面拾得。”奇文出人意外,如怪峰飞来,又仿佛是眼前景色,这就是“拾得”,天衣无缝,妙手偶得。
明清艺术批评的“奇”“平”之论,延续孙过庭学书三步法而来,妙悟自然的观念贯穿其间,奇而不自以为奇,勿以平废奇,深明奇平不二之义。奇归于平,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或因或创,张弛有道,不可执着,根据审美情境而运法。沈德潜论诗:“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与“字”相比,“意”指意识、立意,以意胜则能从平常字句见出新奇和险绝。沈宗骞论画:“故吾尝谓因奇以求奇,奇未必即得,而牛鬼蛇神之状毕呈。董北苑空前绝后,其笔岂不奇崛。然独喜大江以南,山泽川原,委蛇绵密光景。且如米元章、倪云林、方方壶诸人,其所传之迹,皆不过平平之景。而其清和宕逸之趣,缥缈灵变之机,后人纵竭心力以拟之,鲜有合者。则诸人之所得臻于此者,乃是真正之奇也。”艺术不可动辄好奇,无一笔矜奇炫异,笔墨间奇气往来,令人玩味无尽。平中之奇才是真奇。此境具有偶然性,非刻意所得,非资学过人者易办。仿照中国艺术论“不似—似—不似”的说法,似可拈出“不奇—奇—不奇”的结构,表征尚奇而超越奇的境界,开启心源,任运自然,这是“奇”这一关键词注重创造意识的流露。
四、中国现代美学对“奇”的阐发
“奇”在古典语境中出场且不断生成,使之具备了美学关键词的核心意蕴和特征。对“奇”的把握,不能停留于古典形态,还要考察它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被阐发的情况。中国现代美学关于“奇”的论述并不系统,不过,宗白华、朱光潜在美学观念建构时触及了这方面。
五四运动促使知识阶层个性解放,宗白华有感于东方文明的现状,探寻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当时,他受进化论影响,宣扬民族文化创新,摆脱新旧文化的二元对立,主张融会东西方以创造新文化。他重视审美人生观建设,批判趋于达观厌世或流于纵欲享乐的旧式人生观,宣扬合群而富有个性的新型人格。“奇”虽蕴含审美人生观内涵,但在当时被纳入旧式人生观范围,尚未出现现代转化的迹象。
不过,“五四”反封建主潮毕竟为倡导“奇”的人格创造了机会。1927年,鲁迅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推崇魏晋名士风流。抗战期间,宗白华接续鲁迅的研究,发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深微阐述魏晋时代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精神。从魏晋名士的行为特征看,可归入“奇”的人格类型。后来,随着思想解放的到来,中国美学史叙述高扬精神自由,促使仰慕魏晋名士之风长期跟进,社会效应不容低估。
宗白华关于“奇”的直接论述,在于他对常人欣赏艺术形式的关注。他指出,第一流艺术多是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无妨其价值伟大、风格高尚、境界深邃和思想精微。常人天真朴实,并无艺术成见,他们喜好表现切身体验的生活,以及生活的缺陷和希盼,借助审美幻境表现人生,这是通俗艺术的奇特之处。他说:“今人的小说如果所描写的太新太奇而没有抓住我们生活的体验内容,就会不为一般人所了解与欢迎。”常人要求艺术真实地表现生命,使之共鸣同感,有些艺术虽能引发惊异,却无法使人满意。他们喜欢情节丰富、动作紧张、幻想诡奇、引人入胜的通俗艺术,既要求艺术写实,反映生活体验和憧憬,又要求创造“奇迹”,追求艺术内容真实与形式新奇的辩证统一。宗白华考虑到接受心理,发扬“奇正相生”“以常出奇”的古典传统,也留下了西方近代美学(如黑格尔)思想印记,为通俗艺术树立了新标准。
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多次触及对“奇”的思考,他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常态”概念。一是以“常态”为美。他认为自然无所谓美丑,美丑是观赏者性分和情趣的印证。自然界只有常态与变态之分,自然美是指事物符合常态,自然丑是指事物变态。自然美难在合式,即符合标准,或具有最普遍的性质,“超过常态”即不美,即丑,“稀奇古怪”即不美,即丑。如“山的常态是巍峨,所以巍峨最易显出山的美;水的常态是浩荡明媚,所以浩荡明媚最易显出水的美”。这些例证旨在解释自然美与自然丑的对象和成因,艺术之美丑与自然之美丑是两码事,他在自然美概念上使用“常态”,并未用于艺术美,由于过分强调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这两种美的共性。
二是“常态”遮蔽美。朱光潜分析心理距离时再次提到“常态”概念。这时“常态”是指实用经验完全占有人的意识,让人无法真切感知事物的美。与注重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的看法不同,朱光潜认为“常态”造成美感钝化或遏制美感,见物次数愈多,则所见物的美愈少,见闻与新奇体验成反比,故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观念受到叔本华影响,他赞赏叔本华“丢开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见出事物的不平常的一面,于是天天遇见的、素以为平淡无奇的东西,例如破墙角伸出来的一枝花,或是林间一片阴影,便陡然现出奇姿异彩,使我们惊讶它的美妙。”朱光潜接受叔本华思想时,也把审美距离说牵扯进来,认为常见的事物难以引发美感,是因为距离太近,实用牵绊太多。他宣扬审美距离,建议取旁观态度,超越实用功利的眼光,跳出习惯的认知圈套,从“平淡无奇”的事物见出“不平常”,观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感受世界的美妙存在。朱光潜发扬“奇出于心”的传统,主张摆脱“常态”思维和实用理性,以超功利态度感受事物的“奇姿异彩”,使之发展为一种审美态度,由此丰富审美距离说的内涵,他对“奇”与“常”关系的审美心理学分析,使“奇”的意蕴实现从平常到神奇(非常)的转化。
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奇”在浪漫主义等艺术观念、形象思维大讨论等领域时有露面,却未成为专题话语。“奇”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于理论领域:一是作为术语出现在古代文艺理论资料汇编及相关史论中,特别是“奇正”说受到重视,却未触及现代意义;二是在审美理论建构方面,出现了使“奇”的意蕴从“新奇”转向“审美惊奇”的趋势。从美学理论创新看,第二种方式更值得关注。
在此,以章利国、张晶的审美惊奇论建构为例。章利国把“惊奇”拆分为二:“奇”是审美客体的特征,“惊”是审美主体的反映。“审美惊奇是审美主体对于有着具体可感形式、趋向于完整统一和谐的突发性对立和冲突的即时反映”。审美惊奇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强烈性和趋迎性。审美惊奇以感知对象无害于主体为前提,这与朱光潜宣扬审美距离超越实用功利的特征相似。他概括审美惊奇的对象特征,受到亚里士多德惊奇论的启发。他还分析审美惊奇过程中主体身心状态、审美心理结构平衡,强调艺术品的“出奇”应该适度。此外,他对审美惊奇与新奇、怪诞、悲剧、崇高等范畴进行比较,总结审美惊奇的艺术功能和社会功能,通过对审美惊奇的审美心理学分析,体现出关注审美实践的取向,为“奇”的现代阐发和理论转化提供了思路。
张晶建构审美惊奇论体现出不同的理路和风貌。他把“惊奇”界定为一种审美发现,“惊奇”使片断、零碎的感受接通为一,心灵受到撼动,审美对象潜藏的意蕴突然被敞亮。与章利国相比,张晶更注重调用和整合中西惊奇论美学资源。他提及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沃兹沃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布莱希特、本雅明等人的话语,表明西方美学历来重视“惊奇”的美学意义。他又从中国艺术论爬梳惊奇论资源,强调诗文戏曲追求“惊人”效果。尽管上述资源的内涵有异,却无妨“惊奇”的意蕴构成。他辨析“审美惊奇”与“惊奇感”,前者的客观基础在于艺术或审美对象本身,后者属于审美心理范畴。“惊奇感是主体进入审美过程的关键性契机。在惊奇感中,世界如同被一道鲜亮的电光普照而变了模样,头脑中那些零碎的印象都豁然贯通为一整体,在惊奇感中,一切都从蒙昧的状态得以敞开。”他对审美惊奇的描绘似有接通天人之感,已开启使“奇”通往境界论美学之端绪,惜未进一步展开。
可见,审美惊奇论建构主要基于审美心理学视野,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较深入的论述,章利国侧重审美惊奇的原理建构,张晶注重发掘和整合中西惊奇论美学资源,都见证着“奇”的意蕴从“新奇”转向“惊奇”的趋势,顺应了人文学科主体性崛起之潮流。整体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对“奇”的阐发立足于西学东渐的背景,以西方近现代美学为基本参照,普遍关注艺术形式及其新奇效果,甚至把“奇”理解为形式主义,过分突出形式“新奇”的意义,造成形式与其他审美因素的矛盾和冲突,或过度注重艺术接受的感官刺激、情绪震荡效果。加之研究视野和方法趋同,导致“奇”的部分古典意蕴在阐发和转化过程中淡化、消散或失落,部分古典意蕴则因西方美学的强势介入而得以扩张、放大或弥漫,成为这一关键词意蕴的主体部分或核心要素。这既是社会和时代的影响所致,也与美学理论建构的目标和方法有关。对此,有必要稍作反思,并适度加以拓展。
余论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美学关键词的理论拓展既要加强中西方美学对话和文明互鉴,也要顾及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质,还要关注当代审美实践和艺术新潮,通过学术史反思和综合创新,使之实现深层次的理论融合。
其一,继续推进“奇”的意蕴从“新奇”到“惊奇”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中西惊奇论美学资源的支持。“惊奇”作为艺术意蕴传达的工具或手段,这类观点在古典语境中普遍存在,追求美善合一、意蕴与形式的统一,对于维护艺术内部的平衡和整体性美感传达有积极意义。
其二,“奇”提供了一种重建人与世界诗意联系的方式,有反思科学理性、超越实用功利的意义。“奇”突破常规,彰显个性,推重创造。当今时代,有必要反思科学理性对人性冷漠、情感麻木造成的负面影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存状态,重新感知世界,重建人与世界的诗意联系。这对于克服审美疲劳、防止感觉钝化、高扬感性生命、保持生活热情有矫正之功。
其三,突破艺术形式中心论藩篱,拓展“奇”的边界。对“奇”的理解不应限于形式主义,可以拓展到历史主义,重视艺术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关联。“奇”不只意味着形式新奇,吸引观众眼球,或令人惊奇震撼,它还应有助于心灵境界的提升。这对“奇”的意蕴重构及美育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奇”这一中华美学关键词思想根基深厚,其古典意蕴“以正驭奇”“以常出奇”“奇出于心”具有现代价值,从中国现代美学对“奇”的阐发看,这一关键词的拓展空间较为广阔。“奇”贯穿于审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到审美理想,再到艺术运法乃至审美境界,无不与此相关,今后可吸收审美心理学前沿成果,继续推进该领域研究,还应往哲学美学层面拓展。在理论阐释方面,应突破对艺术形式新奇的单向度关注,向人生、社会和艺术三位一体的审美境界论突围。深化“奇”这一关键词研究可为神奇、雄奇、奇伟、奇丽等审美范畴的建构提供支持,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美感经验,对于当今社会重建生活意义、重构心物关系有很大启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