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中国“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中,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具有重要地位,其诗学实践对这一谱系里的抒情传统更有重要的推进。就诗歌的体式探索而言,陕甘宁时期红色诗歌的诗体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将民歌民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歌体诗转化成现代中国的诗歌体式;二是以传统诗词创作促进了红色诗词创作的“中兴”,为现代诗学实践如何守正创新提供了新的启示;三是自觉推动抗战歌曲、歌词创作,使得一批具有现代音乐文学特征的“歌体诗”经典诞生。就诗歌审美特征讲,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建构了以“红”为颜色意象的基本诗歌象喻系统与时代风格,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特征。重释陕甘宁红色诗歌的诗学实践及抒情传统,对理解“红色革命文艺”历史构成谱系与延安文学艺术创新及其内在特质提供了新的理路,也对重写文学史具有深刻的启发。
关键词:延安文艺;陕甘宁红色诗歌;“红色革命文艺”谱系;诗体创新
作者程国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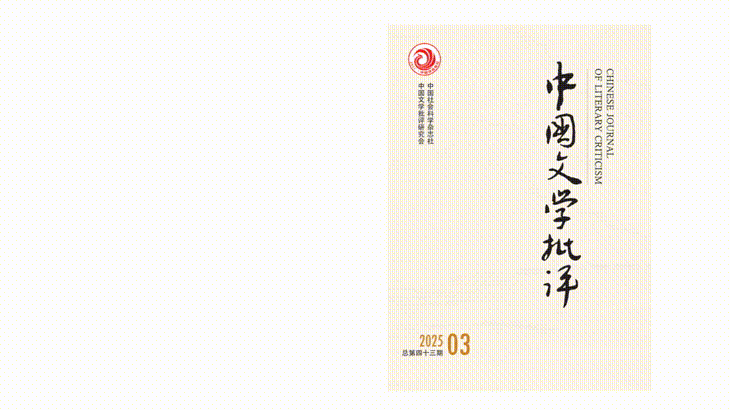
在现代文学史上,通常所说的陕甘宁边区的诗歌,主要是指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陇东南梁为主的革命根据地和宁夏不同解放区的诗歌创作。从目前具有代表性的选本来看,这些诗歌除了白话自由体诗外,主要有古体诗、词、曲、赋、宝塔诗、对联体诗、歌曲、民歌、民谣、顺口溜、快板诗、联体诗、传单诗、舞剧唱词、戏剧唱词、电影主题歌、语录诗、标语诗、口号诗、墙头诗等形式,也包括音乐学意义上的各种新民歌以及经典歌曲之歌词等诗歌形式30余种。这些当时盛传且被反复实践过的诗歌体裁形式,深刻影响了彼时彼地的诗歌形式变革。这种诗学形式变革,既开创了诗歌史上少有的古典诗歌、现代白话诗歌与民间诗歌等多种诗歌体式并存并兴、交融发展的崭新局面,又有效地吸收了古典诗歌与民间诗歌艺术形式的精华,体现出“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新风尚;既做到了“旧瓶装新酒”,为“新酒”找到了恰当的艺术形式,又丰富了20世纪诗歌艺术的形式内涵,颇有诗学研究价值。
事实上,由上述多样诗歌形式构成的20世纪中国红色诗歌抒情传统及其演变历程(谱系),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歌谣运动及其对民间、民众的“发现”实际上是红色诗歌创作的萌芽阶段。国内外工农革命运动及相关思潮的出现也深刻影响了这类红色诗歌的创作。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的红色诗歌创作,其内容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期传播密切相关,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红色诗歌。
第二个时期,是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红色诗歌的创作走向了艺术的自觉。在瑞金中央苏区、井冈山、闽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红色诗词、歌谣大量出现。一是革命领袖的创作,如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等诗词。二是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基于宣传工农革命思想的需要,发挥民歌“即兴创作”的特点,边唱边演,创作的大量作品,如《红军来到龙岩城》《哥哥你前方去打仗》等。三是在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对《国际歌》等外来红歌的翻译和倡导下,现代意义上的红色诗歌大量产生,如瞿秋白的《赤潮曲》、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系列歌词。
第三个时期,是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红色诗歌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在内涵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讲话》精神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人民性方向被确立。延安等地的“圣地”颂歌与人民英雄颂歌大量涌现;李有源、孙万福等老区农民的民歌、歌谣创作被鼓励、得到广泛传播,并与《讲话》后知识分子创作民歌的潮流汇合;红色诗歌的价值定位与“党的文学”的政治美学相统一;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的开展及其作为“下里巴人”的诗歌文体内涵提升,“体貌”特征凸显,《王贵与李香香》等人民文学诗歌的范本出现。
第四个时期,是1949年后。这一时期,红色诗歌文体向“国家文体”转化,其“体裁—体要—体貌”发生重大转化。以贺敬之、郭小川的创作为代表的民谣化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诗坛主流,也成了影响最大的诗体。红色诗词创作的“运动化”品格由此形成。
第五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的主题基本为“革命初心”的追寻及历史感的强化。怀旧性质的“红歌”大量出现,体现“主旋律”的诗歌,尤其是新的“革命歌曲”歌词融进了时代的主题;革命先辈诗词创作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旨趣”强化,大量烈士诗抄与悼词、挽联、回忆录的“初心”追寻主题凸显;老红军的红色诗词创作、口述红色歌谣得以整理,如《庆阳老区红色诗歌》等作品集的出版。
20世纪现代中国的红色诗歌抒情传统及其诗学实践有着历史跨度长、主题范围广、体式多样的特征,是现代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构成中不可被忽略的主体。这些红色诗歌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诗学实践,它们借鉴民族优秀诗歌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高度一致。
将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实践放在“红色革命文艺”历史构成谱系的框架下研究,一是可以凸显其特殊意义和价值,二是可以“以点带面”,从整体上梳理与认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纪面向。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不仅体式多样,艺术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红色诗词(包括自由体诗)、红色民歌及以“红歌”(音乐歌词)为主的“歌体诗”这三种形式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讲话》以后,这三类诗歌体式获得长足发展。
在红色诗词方面,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一是革命家对于古典诗词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在这一层面,延安革命家以“旧瓶装新酒”这一艺术策略进行诗词创作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如毛泽东等的诗词体式的创新尤为可贵,就是“在继承古典诗词艺术传统基础上努力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怀安诗社”为主体的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则以同样的诗学策略推动了新文学运动以来诗词创作的“中兴”。
其二是诗歌创作体式增多,形成独特的诗学新景观。像传统的诗词曲赋,戏剧的剧词、主题歌,民间的顺口溜、谜语、童谣、快板诗等形式已经被广泛实践并被巧妙化用在白话自由诗创作中,形成了新的诗歌文体。这些新形式诗歌的大量出现,与同时期的现代白话自由诗(如艾青、丁玲和一批“前线诗人”的创作)一道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多体式并行的繁杂局面。这种传统诗歌的多体实验和创作,既促进了红色诗歌创作实践的进程,使一些有生命力的其他文类(红军文告、标语、口号、传单等)转化成了“诗”的形式,也使诗的现实功能加强,有力引导了边区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解放及抗日爱国的革命激情。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这些独特的诗体创造,也为现代诗歌创作发展如何“守正创新”提供了深切的启示。
从20世纪中国诗歌创作实践的历程来看,“五四”以后诞生的自由体新诗,中经新月派的格律诗创作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以艾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达到成熟。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诗歌创作实践却使这种自由体诗歌的体式内涵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为自由体诗歌体式增加了新的形式,一种民歌体自由体诗诞生了。这种在广泛挖掘并吸收民歌艺术资源基础之上形成的诗体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熟悉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不仅在诗体试验上别具一格,而且主题与现代中国的思想主脉保持一致,还促使了红色诗歌象喻系统的确立,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特征,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延安经验及启示。
首先,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主题”的深化,引领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的思想转化。在这一时期,各类红色诗歌成为利用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多样形式来传播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和工农革命思想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在思想主题方面,举凡歌颂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及人民英雄、解放区劳动与新生活,表达对未来美好向往的内容都基本在陕甘宁边区定型。其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及新的英雄形象的主题成了主流。这些诗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也为日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些学者认为,在红色诗词(包括自由体诗)、红色歌谣(民歌)和红歌(歌体诗)这三类形式中,毛泽东等的红色诗词创作不仅继承、延续了中国抒情传统,也表现了文明史的连续性特点:“毛泽东诗词有意识地拒绝了白话,在音律、文字、格式乃至意象上都保持了古典诗歌的形态,使其更鲜明地表现了文明史的连续性特点”。换句话说,在陕甘宁边区,尤其是《讲话》以后,这种以古典诗词与民歌为基础的形式探索及现代转化,引领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的新的思想主题与文化方向。这些红色诗歌不仅具有丰富的主题与思想艺术价值,包含着更多历史真实,其“中国特色”更是显著,甚至构成了20世纪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底色”。
其次,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不仅表达了新的思想主题,也形成了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道统”。就整个20世纪中国红色诗歌诗学实践来看,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员的诗歌创作,已经明显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传播了与儒释道文化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陕甘宁时期的一些语录体、口号体、传单型诗歌,其内容本身就是历史真实。而像毛泽东等的诗词创作,则表现的是现代革命及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并以红色诗歌的形式构筑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脉,形成了一种新的“道统”,代表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也发挥了独特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现实功能。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诗歌创作有效地“反哺”了“抗战”、解放区建设等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力地推进、影响了现代中国革命,充分体现了其现实主义品格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这些红色诗歌还有效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大众化基因,区别于“五四”以来西化的自由诗,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
从意象使用的角度讲,《东方红》中的“东方”指涉中国,“太阳”隐喻毛泽东,而诗中的“红”象征着光明、正义与进步,而“升”作为解放、拯救的行动性意象,其积极和跃动的意涵也更为丰富。这种意象、比喻与象征构成的诗歌结构方式,显示了一种根本上有别于现代主义诗歌的隐喻、反“语法”式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新方向。每个时代的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辞风格,以表达时代的世界观。就比喻、意象而言,像《东方红》这种从歌谣美学原则脱胎而出创造出的诗歌歌词,影响了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创作的基本结构方法。而同时期或此后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绣金匾》等红色诗歌经典,都是如此被“制作”出来的。其以“红色”为核心的象喻系统自然被典型化了。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诗学实践在诗体创新、主题思想、象喻系统和文化审美特征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其诗学实践对20世纪“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传统有着重要的推进。从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来看,延安文艺及陕甘宁红色诗歌诗学实践的重要特点就是时代性、民族性与人民性。这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和“文艺要热爱人民”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关联,也影响着当代文艺的发展。因而,重识“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和陕甘宁边区诗学实践的重要品格对今日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时代需要我们对一些被“误读”的革命文学和文艺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坚守“革命初心”,是我们当今研究“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所必须坚守的学术立场,也是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代之问”的前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