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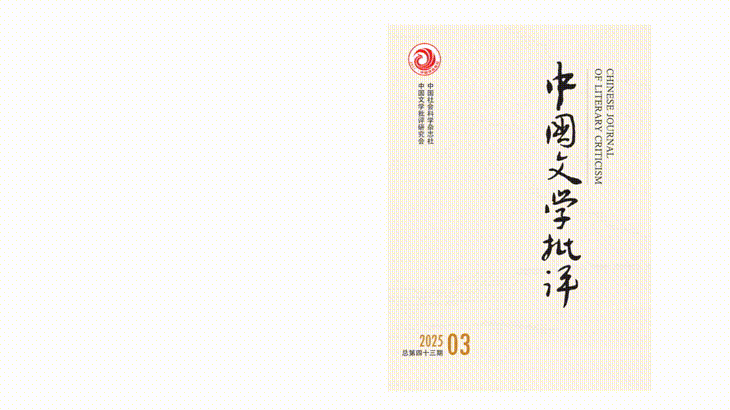
过去的几个月,我一直都在香港岭南大学当驻校作家。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对我来说,既感到十分陌生,又难免新鲜好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此期间,印象最深刻、感受最强烈的,竟然是每天的游泳。岭南大学有一个标准的露天游泳池,在这清澈的水池里仰泳,可以尽情仰望天空。仰望天空的感觉很好,天高地厚,香港的天空非常美丽,或许靠近大海的缘故,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我突然意识到太久没有这么仰望过天空。
仰泳时,不断地看见飞机从天上飞过,划出一道长长的白线。作为一名作家,一名蜗居的室内动物,我很少有闲情去注意天空,至多也就是往远处看上几眼。平时是住在高楼之上,可以远望,远望和仰望属于不同的观看方式,仰望更容易产生幻想。香港的天空真的很特别,不由地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到达香港,当时最强烈的印象,就是飞机突然从城市低空掠过,飞得非常低,无法想象得低,紧贴着房顶,直接就是从房顶上飞过去。
当然不是在今天的香港机场,如果要和别人说起自己的香港记忆,说起对香港的最初印象,首先就是那种从高空往下看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显得非常不真实,仿佛一下子扎进了香港的怀抱,那个曾在电影上看过无数遍的花花世界,没有任何过渡,你突然就投入其中。转眼之间,你到了香港,这里就是香港,这就是你印象中香港最初的模样。
在游泳池里仰望天空,产生的联想则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在天上往人间看,一个是在地上往天上看。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三十多年前,要到一次香港,非常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我只要说起香港,一定会首先想到那个破旧的老机场,想到那种从屋顶上掠过的神奇感觉。
后来的很多年,又来过好多次香港。每次感觉差不多,大同小异。尤其是过去的这几个月,因为驻校,飞了七次香港,来回就是十四次。有趣的是十四次飞行,飞机总是晚点晚飞,又基本上都会提前到达。航空公司显然放了余量,这么做的好处,是先让你有点失望,然后呢,然后又忍不住暗自窃喜。有时候,小说就应该这么写,就应该这么设计。人生往往会有许多说不清楚,有曲折才好玩,有意外才有意思。想当年,只是从下降的飞机上,看了几眼翅膀下的香港城,就感觉自己已见识到了真正的香港。
无论是从下往上仰望天空,还是从上往下俯瞰人间,这种感觉都仿佛是在写小说。你看到的只是一点点,只是一部分,联想却可以带出来一大堆。我总是很容易就拥有了太多的想象空间,幻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现实。坦白说,在岭南大学校园这几个月,生活十分单调,来去匆匆,除了教学,谈不上有多大收获。上课、散步、游泳、去食堂,从不同的学生身边经过,学生也不断地出现在面前。我这人脸盲,记不住别人的面孔,有的看着好像熟悉,可能是班上的学生,也可能不是。总之一句话,并没有因为在这待了好几个月,就比以往更了解香港。
我并没有完全融入,对于这个神秘的东方之都,过去不太了解它,现在生活了几个月,仍然还是不太了解。一直都不太相信体验生活,生活有时候可以用来体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享受它。生活无处不在,不过要靠有意识地体验才能写作的教条,对于我来说,起码是有些蒙人。你经历的一切,和你的写作有关,但是未必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没有生活写不好小说,有生活也未必就能写好。依靠所谓的体验,就凭着这两个字,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深入体验听上去堂而皇之,却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你凭什么去体验别人的生活。
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往事,想起自己的一位朋友,他与我一样,也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个岁数的人,对香港都会有种莫名其妙的误会。朋友是位遗腹子,起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这么认为,大家也都这么相信。我们被告知,在他还没有出生时,父亲便死了。后来我们又知道,是被人打死的。他母亲我们都见过,应该是一位大家闺秀,也可以说是出身书香门第,高中刚毕业,嫁给了年轻有为的国民党军官,然后呢,1949年以后,改嫁给了一位搬运工。
我这位朋友自然不会喜欢继父,母亲又生了弟妹,夫妻关系非常一般。有一天,时间进入80年代,他突然兴奋地对大家宣布,说父亲没有死,而是去了台湾,母亲一直对他隐瞒了这个真相。接下来,朋友开始了寻找父亲之路,打听清楚父亲身世,跟母亲一样,父亲本是个文化人,抗日时投笔从戎,还是位不大不小的军官,去了台湾,从此渺无音讯。
再接下来,朋友开始走火入魔,研究了所能找到的各种地图,最后决定去台湾寻找亲生父亲。结果当时历经艰辛曲折,寻找父亲也没能成功。
再接下来,妻离子散的台湾老兵纷纷回乡探亲。他父亲没有回,只是写封信过来,说自己再婚了,在台湾那边有了新家,又有了几个子女。往事不堪回首,他觉得对不起留在南京的亲人,不过事已如此,也没什么办法。信写得很感人,十分无奈。我的朋友放不下心里的那个结,揣着这封信,辗转去了一次台湾,见到了亲生父亲。结局呢,并不是很好,不太理想,大家见是见了,都觉得十分隔膜。
最失望的当然还是这位朋友,从小他觉得应该痛恨自己的父亲,父亲给儿子带来耻辱。现在父亲死而复生,又给了他从未有过的荣耀。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成了抗日英雄,是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幸存者,在别人写的回忆抗战的文章中,竟然见到了父亲的名字。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没想到真正见面后,耻辱感和骄傲感突然都不复存在了。他发现父亲只是个陌生人,更爱更关心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这一点,跟自己的继父如出一辙。
朋友希望我能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我们不止一次聊过这话题。事实上,我一直在想应该写谁,应该先为谁动笔,是写朋友的母亲,还是写他的生身父亲。当年我在台湾,曾见到几位转业的军官太太,她们说着地道的南京话,都是当年去台湾的军人家眷,知道我是从南京过来,又是生长在南京,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朋友的母亲也跟随丈夫去了台湾,她显然就是其中一位。
记不清自己写了谁,好像都写过,又好像都没写。其实就算写了,也不能算是真正写好。写作的秘辛就在这,有些事会始终萦绕在你的心头,让人久久不得平静,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写,这个可以写,这个必须要写。我忘不了朋友冒险越境,临行前,神秘地跟我说,他要去某个地方,但是,但是现在还不能告诉我,反正他是要去的,只是暂时不能说,再难,再危险,他也要去。
我这位朋友喜欢说某某是父亲黄埔的同期生,是好朋友。他父亲离开了军界,做生意挣了些钱。要说故事都是故事,悲欢离合总无情,我忘不了在台湾遇见的一位太太,拉着我的手使劲摇晃,说她就是那什么学校毕业,我们还是校友,说当年读书时真好玩,没想到自己高中一毕业,就嫁了男人,成了少奶奶阔太太。
感觉我把他们的故事都写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写。耿耿于怀的,只是那些寻找真相的欲望。实际上,我有兴趣的不仅仅是真相,有时候真相解密,反倒索然无味。人生最不应该失去的,是寻找真相的初心,然而寻找的乐趣,如果没有想象去加持,没有假设和虚构去补充,可能最后也就没有文学。
最终结果常常不了了之,排空驭气奔如电,上穷碧落下黄泉,真相能否找到,找到了又怎么样,对于写作者来说,可能重要,更可能不重要。关键还是得去寻找,带着想象和虚构的翅膀,要能上天,也要能入地,俯仰两不愧。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