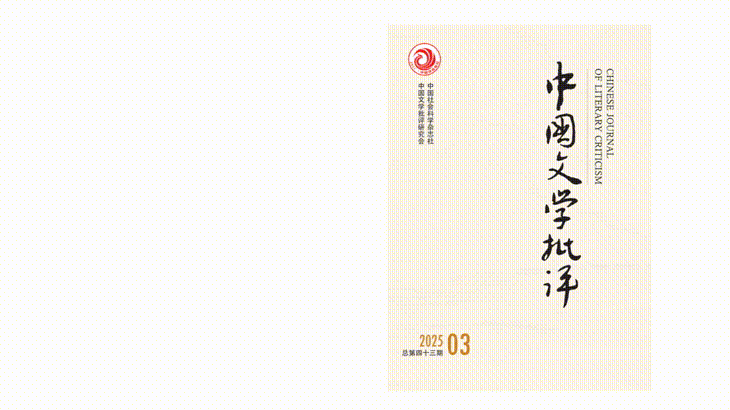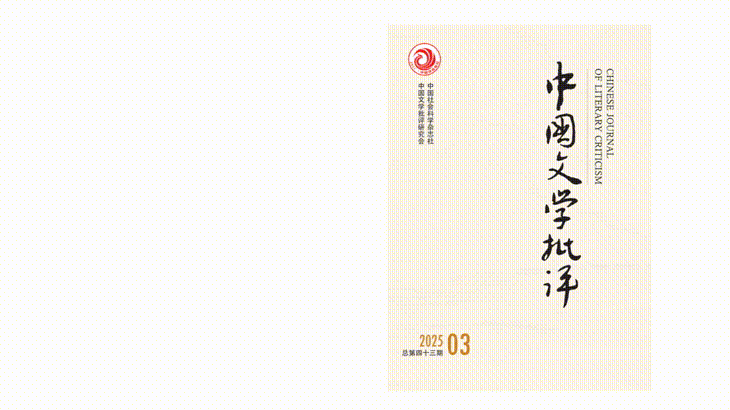
一、平民化的文学书写
继非虚构作品《南京传》和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后,2024年,以“文坛劳模”著称的叶兆言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璩家花园》,广受好评。在新闻媒体、作家访谈和相关评论中,人们对《璩家花园》的意义与特点作过不少讨论,但我以为,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作家以其非常自觉的平民意识书写了平民,为我们的时代贡献了一部相当杰出的平民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主要以先锋小说创作闻名,但从80年代末起,他便开始了平民文学创作。比如有论者指出其发表于《钟山》1989年第2期的《红房子酒店》“和同一时期的《五月的黄昏》《绿色咖啡馆》更关注当下社会,人物也更加平民化,表明此时的叶兆言已经从着重强调外在形式转向关注作品精神内蕴。他开始更多地描写世俗生活的细节”,“这种对现实和世俗的回归也预示着叶兆言在下一个阶段即将回归传统的倾向”。很显然,叶兆言从彼时开始回归的传统,正是这位论者所指出的注重社会现实、世俗生活和“人物也更加平民化”的平民文学传统。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如《花影》《别人的爱情》《马文的战争》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此意义上,《璩家花园》正是叶兆言平民文学创作的最新收获。
关于平民文学,新文学之初的周作人就在其《平民的文学》中大力倡导,认为平民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所以,只是在题材的意义上,《璩家花园》便可称之为平民文学。但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璩家花园》中描写的平民和平民生活,却是经过作家特意地“平民化”处理才得以实现。
这种平民化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将祖上曾经很辉煌的璩家三代“转化”为平民。以璩民有、璩天井、璩达为人物谱系的璩家三代的故事,是《璩家花园》的主要内容。正如作品中所写的,璩家的祖上曾经有过极度辉煌的光辉业绩,拥有上百间房屋,因为做皮货生意,在当时的官家那里,并不很看得起,所以璩家虽然很富有,也并不敢太过炫富。直到后来璩民有的曾祖父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拥有了更被看重的文化与功名,“才开始堂而皇之大兴土木,亭台楼阁想怎么修便怎么修,璩家花园的显赫名声,也就是那时候落下的”。这里所讲述的,显然是璩家祖上由“非常有钱”的“生意人”而到努力争取功名、拥有文化的过程。但是很快,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丁兴旺的璩氏家族迅速败落,丧了元气,只幸存下天井的高祖父这一支人脉, “这以后,接连几代都是单传,一直传到了天井”。“老太爷死后,照例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民有的父亲手上,也就是天井爷爷当家,拆东墙补西墙,早已是惨不忍睹。他老人家聊以自慰,可以夸夸口的成绩,就是让自己儿子民有,也就是让天井的父亲念了大学”。
实际上,小说将璩氏家族“转化”为平民,还不唯如此。《璩家花园》的故事,正是开始于“念了大学”以后的璩民有。小说主体性的故事结构,就是璩民有—璩天井—璩达祖孙三代进一步地变为普通人的过程。除了个性特征如璩民有的游戏人生、璩天井的老实巴交、璩达的平庸无奇以及他们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普通平常,尤有意味的是,作家还为天井和璩达的血脉设置了疑点。小说的第二章“1954年:母亲,天井不知道那些往事”,主要讲述了璩民有和天井生母江慕莲的婚恋故事,写到了民有对其母身孕的怀疑:“民有觉得这个事很可疑,不会那么简单。他并不觉得江慕莲的身孕,一定是与自己有关。怎么就会那么巧呢,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呢,他怀疑自己被下了套,当了冤大头”。天井一岁时,其母投河身亡,他的血脉问题,从此便一直存疑;而小说中璩家第三代即天井之子、民有之孙璩达,也被设置为来路可疑,被怀疑为其母阿四与李学东的一次出轨,这恰如阿四对后者所说的:“我跟你说李学东,也不知道怎么的,有时候我看着璩达,越看越像,越看越像你,真的是有点像”……这些疑点,无疑在根本上实现了天井与璩达的平民化。
《璩家花园》平民化的第二种方式,则是对小说人物的去精英化。在《璩家花园》的诸多人物中,费教授、郝银花和岳维谷等,都是拥有精英身份的人物,但是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去精英化,还原为普通人。比如本名费怀瑾的费教授,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去德国留学并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各个大学,且有部聘二级教授的身份与地位,每个月工资高达当时的旧币两百万,分明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但是在小说中,他却被塑造为一个谨小慎微、疑虑重重、不无算计的普通人。他先是在处理自己与江慕莲、李择佳两位女性的关系上颇多疑虑与谨慎,甚至不无荒唐与俗恶地将中意于自己的江慕莲“转手”于璩民有。对于这一点,连风流成性、人品堪忧的璩民有也觉得他干的不是“人事”,认为“天底下再也不会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多少年以后,民有跟儿子天井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想不通,想不明白,觉得有些滑稽,同时又有些愤怒。他说儿子你想想,这老家伙干的是他妈人事吗。”而后来的政治运动,则更是将费教授改造得更加普通——“费教授变得小心翼翼。说他变得小心翼翼也不太准确,费教授向来就是个谨慎小心之人,只能说他是更加谨慎,更加小心”,经过运动中的受冲击、被批斗,按照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胡教授所笑话他的,他的“胆子比常人更小了,或者说不是更小,是索性就没了”。当然,在这之外,小说中的费教授日记,也很充分地显示了其普通人的本性。在作品的最后一章“2019年……”,作家还对一位曾经显得“一本正经”和“高高在上”的主任医生去精英化地打回原形,还原为普通人。正是这位在阿四的心目中有着“神话光环”的医生偷偷来到阿四的音像店,近乎猥琐地淘购淫秽黄碟:“主任医生在黑塑料袋里,慌慌张张挑了三张碟片,匆匆付了钱,头也不抬地就走了。他这是以一位普通淘碟者的身份出现在阿四的店里。阿四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差点要笑出声来。现在,主任医生的神话光环终于被他自己给打破了。阿四看清了他的嘴脸”。
二、“平等”与“共情”的叙事伦理
叶兆言以“去精英化”等方式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平民化的处理,使得《璩家花园》呈现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平民生活景观,具有十分浓郁的市井气息。《璩家花园》的世界,就是一个平民世界,而且是一个非常本真的平民世界。这一世界的建构,明显有赖于作家平民化的文学观念。在谈到《璩家花园》的创作时,叶兆言就曾说过:“我不愿意在一部小说中表现出对什么人的同情,或者对什么人的讽刺、批判,我更愿意把自己也投入进去。因为我觉得作者与作者所写的人物是完全平等的,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想象成这样的一个人,人物所经历的疼痛、苦涩、温情等同于你所经历的,而不是说你在描述别人的疼痛、苦涩、温情”,他“甚至还希望包括读者来共同经历,作者、读者和书中人物共同触摸、感受那样的疼痛、苦涩和温情,实现一种共情”。“平等”与“共情”的文学/叙事伦理,体现在《璩家花园》中,就是突出的平民性。这种平民性的文学/叙事伦理,创作主体已经不再高于作品中的对象主体,从而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讽刺、批判”或启蒙,甚至也没有如叶兆言所说的“同情”。这种平民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叙事伦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和文学/叙事伦理之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潮流与现象,特别是在以池莉、刘震云等作家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在《平民的文学》中,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的精神根底与文学伦理,实际上也是“平等”,指出我们也不过是平民文学所记载的世间普通男女中的一员,“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在此意义上,叶兆言的《璩家花园》显然是“五四”以来平民文学的最新实践和重要成果。
叶兆言的实践,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在于书写了当代中国历史中城市平民的生存与命运。叶兆言多次说过,在他的创作中,民国题材与当代题材各自参半,并且基本上交替进行,《璩家花园》便是其民国题材《南京传》和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后的当代题材作品,书写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七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在回应一位记者“《璩家花园》被誉为1949年后的‘南京传’。它和非虚构的《南京传》既是一种接续,也构成一种互文”的说法时,叶兆言说:“我觉得它跟《南京传》首先在感情上是共通的”,“无论是《南京传》还是《璩家花园》,我无非是借南京这个窗口来看中国。通过这座城市、这个平台描写的中国历史,是和很多人理解的中国历史不太一样的一种中国历史。因为从南京这个窗口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和从北京、西安或郑州这样的窗口所看到的中国历史是不一样的”。我以为这里的“不太一样”,自然包含有如其所云的诸多不同,但更重要的,还应该是指他对历史的平民性表现与理解。
叶兆言曾经说过,《璩家花园》对平民生活和对历史的书写“两者好像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一架飞机的两个翅膀,没有它们就飞不了。我就想把人间烟火和历史融合在一起,光说人间烟火没有历史就没有意义,光说历史没有烟火气也不行,所以这两者是并重的,人间烟火反映了历史,历史又折射出人间烟火”。所以在作品中,从20世纪50年代之初的“俄语热”到后来的恢复高考、企业改制、下海潮和工人下岗等,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均有所反映,而这一切,又都水乳交融般地融合于小说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中。正因如此,只有那些紧紧融合于人物的历史,才会被涉及和书写。像“俄语热”和“缉毒”这样的历史现象,其实并没有重大到无可回避、非写不可,但由于对人物设置和人物命运的影响,均得到了具体和生动的书写,而有些大历史事件,哪怕再怎么重大,由于并未融合于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反而被作家所忽略。这些被“忽略”了的大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叙事空缺”,实际上倒是象征性地表征了平民世界对于大历史的遮蔽与遗忘。对此,叶兆言曾经结合自身的经历、体会与作品实际作过这样的阐释:“就像天井一样,我也是等到父亲平反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右派’。但知道的时候,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甚至反而成了一种光荣的历史标签。天井过去只隐约知道父亲犯过错误,但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历史似乎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我自己对这点有很深的体会。1974年,我高中毕业进工厂做工人。按理说,我厂里的那些老工人,距离抗战并不远,但他们对南京被日军侵占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这非常奇怪。但有时候,历史就像费教授的日记,可能会在时间里消失、被掩盖,仿佛从未存在过。所以我这部小说会很强调历史,同时也想表明,历史的消失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方面“很强调历史”,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历史的消失其实是非常容易”,这既是《璩家花园》历史书写和历史理解的平民性特点,也是作品中的平民对待历史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叶兆言的历史观并不相异或高于其笔下的平民,从而对后者历史记忆的淡漠与消失进行启蒙主义意义上的批判与揭示,而是将自己作为老百姓、作为平民,进而也形成了《璩家花园》平民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
三、城市平民的精神与道德
《璩家花园》平民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展现出当代中国70余年社会历史变迁中城市平民的精神与生存。其中,无论是被作者平民化了的璩家三代和被“去精英化”的费教授、岳维谷等人,还是李择佳一家,以及与他们有诸多关联的江慕莲、倪英文、甜甜、于静和胡正碧等人,他们作为一介平民和“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与成败,都得到了非常生动与丰富的书写。在《璩家花园》的“后记”中,作家曾说“小说中照例会有很多痛,很多苦涩,很多不可言说,我无意展示它们,渲染它们,只是在轻轻地抚摸,带着含笑的眼泪继续写”,“有时候感觉写得很爽,想怎么落笔就怎么落笔,有时候又忍不住流眼泪,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别人读了这篇小说,会不会和我一样,内心也有那种难言的忧伤”。作家的“痛”与“苦涩”、泪与笑与忧伤,显然是有感于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精神与生存、性格与命运,确实让我们感慨万端,其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他们作为“普通男女”的不完美,应合了一个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人生是个不完美的花园”。
在个体人生与命运的意义上,《璩家花园》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难说成功。如费教授,虽为留洋博士,贵为二级教授和省政协委员,薪水颇高,却因爱妻早逝,形影相吊、谨小慎微地度过漫长余生,后来又在政治运动中遭到冲击,颇受凌辱,却在将要迎来新时期的1976年7月,于病痛中孤凄离世。而璩民有,这一明确具有璩家血统的子弟,所度过的却是跌宕起伏、悲欣交集的一生。璩民有毕业于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又攻俄语,在小说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之初,便担任干部学院俄语速成班的老师,具有明显的优越感,但是,莫测难料的命运却使他频遭打击,先是妻子江慕莲生子一年后投河自尽,后又历经变故,家破人亡。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头上戴有一顶特殊“帽子”的璩民有,“一改往日习惯性的认错认罪,突然变得神气活现”,“突然也成了革命群众,而且还是造反派”,可是旋即,又被隔离审查,沦为贱民,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就是璩民有“这二十年,一直过得很憋屈。憋屈就是不痛快,过去二十年,真他妈太憋屈,真他妈太不痛快”。改革开放后,璩民有时来运转,不仅恢复教职,还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因为其所主抓的高考补习班和推出的高考复习资料的成功,复又荣任校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璩民有下海,开张民天文化公司,却又由于嫖娼被抓,颜面扫地,加之经营不善,退出市场,起起落落地终至老境……实际上,除了费教授和璩民有,《璩家花园》中很难找出哪一位人物,能够拥有完美人生。
当然,《璩家花园》中人生之不完美,还在于它对平民道德的书写。平民文学中的道德,“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世上既虽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璩家花园》中,作家正是以其如前所述“平等”与“共情”的文学/叙事伦理,叙述了平民世界中的一种“一律平等”和“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即不务高远、讲求实际的平民道德。这样的道德,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作品之初围绕着费教授和璩民有所发生的婚恋故事。比如在费教授和江慕莲之间,江慕莲参加俄语速成班,其实就是想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异性,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在摸清已单身多年的费教授的底牌后,便把目标锁定了他。江慕莲认为,像费教授这样的老男人,自然需要女人照顾他,而以费教授这样的地位与身份,其所需要的,显然应该是有文化的知识女性。而且她从费教授对她“仰慕的目光”,也“察觉到了自己对他的吸引力”,因此,她接着便颇具心机与他交往,甚至不惜编造故事。而费教授这厢,却又不无清醒地怀疑她的动机。他在相信江慕莲对自己有好感的同时,又很怀疑她好感的动机,而且“一想到江慕莲有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真的要结合,她把女儿和儿子接过来一起住,眼前突然多出来这么多人,他脑袋立刻就疼了,立刻要打退堂鼓,想与她进一步发展的念头顿时打消。江慕莲的美艳绝伦足以让费教授心猿意马,可是现实的各种问题,不得不让他考虑止步”。由于“现实”的考虑而“止步”的费教授,便很荒唐甚至不无俗恶地将江慕莲转手于璩民有。
然而在道德上,璩民有与费教授相比并不高尚。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检点”:“民有风流潇洒,很擅于和女人打交道。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无师自通,是个天才,拈花惹草的一把好手”,“喜欢生活中来点小插曲,喜欢女人罩着他”。他对江慕莲,起初“确实抱着儿戏心态,说白了,无非想占点便宜,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约会、开房,像他以往和其他女人一样,故伎重演,终至步入后者的陷阱。即使后来与倪英文成婚,也未断了风流本性,做了书商后,“开始了不可救药的堕落之路”,“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开始寻花问柳”。当然,在两性道德问题上,《璩家花园》中的大多数人物,都难经得起道德拷问,不光是民有,阿四、阿五、岳维谷、李学东、郝银花等很多人,都曾“出轨”,特别是阿四,更是多次“出轨”。
叶兆言以“平等”与“共情”的方式书写了平民道德,揭示了人性的不完美,对于这些不完美,他并未据持某种道德理想主义话语进行高高在上的道德评判,他说“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在小说中间‘爹味’太重,不要有太多评判在里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小说中书写了李择佳和璩天井两位体现出一定道德理想的人物。李择佳早年丧夫,先是经历了“从家庭妇女到缝纫小组的‘七仙女’之一,到大集体性质的永红服装厂的工人,再到厂办幼儿园园长,最后又变成家庭妇女”的轮回,后又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为人帮佣和为街坊邻居倒马桶谋生,艰难拉扯和养活着五个孩子,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李择佳也深怀善良,不仅从未责怪当年差点致她于死命的天井,道出天井当年的秘密,而且还将自己对民有的情感,深埋内心,弥留之际,才有表露;而天井这位少年时代不无“劣迹”的人物,却对阿四痴心不改,并且为家庭无怨无悔承担一切。作品中的阿四,是一个较为风流的女性,青年时期频换男友,恋爱很随便,婚后又多次“出轨”,但是天井或者是并不计较,或者是可能并不知情,却始终痴心不改、不离不弃地深爱着阿四。天井的爱、天井的情感选择,很像是努斯鲍姆讨论奥德修斯在女神卡吕普索和妻子佩涅洛佩之间所做选择后,所突出强调的人的卓越性与超越性。努斯鲍姆指出:“人的限度构成人的卓越,并赋予卓越的行动以意义”,而“对我们日常人性的超越”“把对这种超越的渴望作为完整的人类善的图景的核心是极其重要的”。天井的情感选择,显然是对平民人物并不完美的平民道德——这些“人的限度”和“日常人性”——的超越,是作家从平民内部发掘和展现出的“卓越的行动”和道德理想。正如叶兆言在谈到天井这一人物形象塑造时所一再指出的:“我想写一个有爱的男人,成功与否对他来说不重要。他爱一个人,可以爱一辈子。他的爱有着落,他是最幸福的人”;“我清楚地知道璩天井是个理想人物。现代人很少会有人像他那样去痴迷、踏实、不计回报地只爱一个人。但就算99%的人不是这样,也还是会有那1%的人存在。璩天井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爱”与“幸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多么重要却又稀缺的情感、价值与体验,多么美好的“人类善的图景”,作家在他的平民世界中发现和塑造了这个人物,或许正是为了烛照和映衬出同样存在的人生与人性的不甚完美。他的“含笑”与“眼泪”,他的“难言的忧伤”,或许正源于此?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