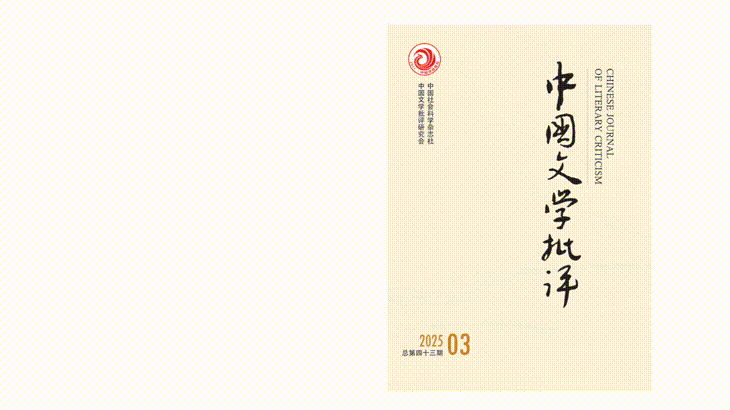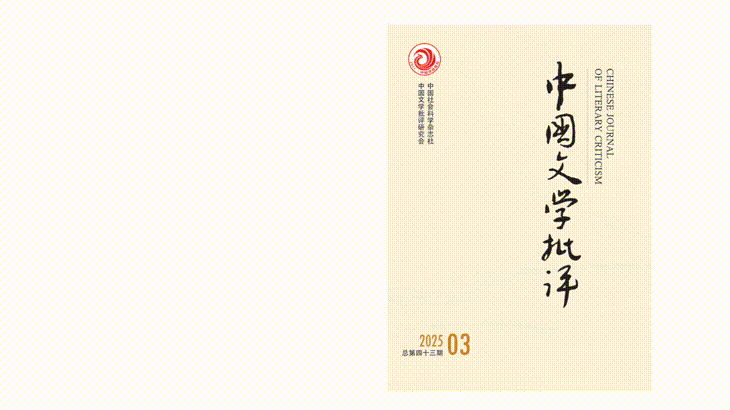
叶兆言在一次访谈中谈及《璩家花园》的创作缘起:“我曾经写过一本《南京传》,非虚构的写法,我想通过南京这座城市,把中国历史说一遍”,“《南京传》只写到1949年,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通过南京历史来讲述”。从这个意义上说,《璩家花园》是叶兆言在《南京传》之后续写南京历史的作品。不过,与《南京传》选择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的宏阔视野中写南京不同,《璩家花园》将叙述锚定在南京城的一个具体街区中,通过普通人的命运周折和人生悲喜透视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巴赫金在讨论小说形式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借用巴赫金对“时空体”的描述,我们可以说璩家花园是浓缩中国历史“一隅”的那个具体空间,在此空间中活跃的是一个个平头百姓,他们的悲喜人生相互交织,成就了一部市井传奇,也绘出了一幅南京侧影。
一、璩家花园里的市井传奇
叶兆言在《璩家花园》中为南京打造了一个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曾是一片荒地,璩家靠皮货生意起家,在此处建起了一座大宅,后来一些暴发户也纷纷在璩家附近置办产业,形成了一条屋宇连绵的长长老街。然而世事变幻,富贵繁华转瞬而逝,小说开始的时候,这片聚集了大户人家的高门宅邸已经变成了拥挤的棚户区,大小杂院一个连着一个。住户里有做工的、有教书的、有革命群众也有家庭妇女。这些人家的日常生活扩充了璩家花园原本的空间功能,除了留存下来的祖宗阁和藏书楼,这片街区里也出现了工厂、饭馆、派出所,当然也有了幼儿园和中小学。活跃在璩家花园里的各色人等构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市井社会,他们依靠亲缘或契约关系彼此连接,开启了各自的市井人生,也碰撞出一段段市井传奇。
作为历史的一隅,璩家花园里的人物命运始终随时代风潮起起落落。1893年出生的费教授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随后去德国深造,获得了柏林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只因学的专业于彼时的中国现实毫无用处,只好在20世纪50年代凭着精通的几门外语,从知名的经济学教授改行做了普通的外语专业老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省里的政协委员,费教授主动降过工资,享受过政协委员的各种福利,藏过日记,在巷子里受过小孩的捉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璩民有在一所中学里当英语老师,1957年成了右派被下放劳动,后来当过几天造反派,很快又成了革命对象。随着高考的恢复,有业务能力又有实干精神的璩民有带着学校老师编印复习资料,成了市场经济大潮中最早“下海”办公司的文化人。和璩民有同龄的李择佳出身富贵,嫁入的侯家也是个大户,“大跃进”时期她加入了缝纫组成了光荣的劳动妇女,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她的身份使其失去继续成为劳动妇女的可能,中年丧夫的侯太太在生活的压力下开始给人帮佣、倒马桶,拉扯大了五个女儿,直到“文革”结束政府落实政策,侯家分到了房子和一笔现钱才让李择佳过上衣食无忧、安享天伦的晚年生活。对于璩民有和李择佳这辈人,社会运动带来的混乱、动荡和变革是形塑他们人生的主要力量。
随着《璩家花园》的叙述靠近当下,人物命运的控制权也逐渐由时代让渡给个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天井、阿四、李学东度过了相似的青少年时期,他们在初中毕业后没有上山下乡而是进了工厂。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带动的社会转型,他们随后的人生轨迹也大致相同。当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后,璩家花园的年轻人们也开始尝试改变既定的人生道路。天井守着工厂直到下岗;阿四辞职进了民营公司,公司倒闭后又改做音像制品生意;李学东成了片区派出所的民警。三个人分别代表了这一辈人在经历社会转型后的三种人生选择,而岳维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准了中国改革的节奏,一跃进入人生的快车道,一路顺风顺水。叶兆言用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记录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具象地表达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对这一代人的影响。至于再晚一辈的陆路萱、璩达则是在更加开放的年代里长大的“80后”,他们并没有按照父辈的意志生活,也没有太多的情感负担。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长辈保持着恰当的生活距离。璩家花园里的几代人在矛盾中相互妥协,也相互尊重,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日常。
几代人基本的人生走向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性叙述,然而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在相互的命运碰撞中也制造出无数个小小的传奇。这些市井传奇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大势,甚至也没能影响个人命运,却成就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的丰富性。《璩家花园》以两种方式来造就传奇,一是通过偶发事件,制造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故事走向。李择佳和璩民有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引发的入室“盗窃案”终止了这场可能到来的婚姻。岳维谷由单位领导做媒娶了省领导的千金于静,没承想于静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两人历经周折终于离了婚,一向谨慎周到且官运亨通的岳维谷再婚后竟然出了轨,对方是一个长得很像于静的姑娘。天井偶然爬进祖宗阁,撞见了郝银花的隐私,也被郝银花抓了个现行,虽然天井幻想过跟郝银花可能发生的若干个故事,但事实上也只是若干年后见到阿四的师父,被她酷似郝银花的长相吓了一跳。这些事件的“意料之外”并非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而是借助“情理之中”的机缘巧合和矛盾冲突,实现了常中见奇的叙事效果。
二是通过建立多重因果关联,让事件走向悬而未决、似是而非的结局。江慕莲为了找到稳定的生活来源,千方百计要嫁给费教授,费教授虽贪念江慕莲美色,却不想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于是极力撮合她跟璩民有的婚姻,并承诺给予经济资助,三人之间因此形成了颇为复杂的情感关系网。还有关于阿五的分尸案,尸块推断出来的特征指向了失踪的阿五,能找到的证据也都指向了阿五的男友——那个曾经杀过猪、卖过猪肉的黎明晖。虽然北京来的刑侦专家洗脱了黎明晖的嫌疑,但一家人心里仍然认定他是凶手,直到许多年后阿五的突然出现。阿四和天井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在与李学东的一次偶然出轨之后竟然怀孕,阿四一会儿看儿子像天井,一会儿又觉得像李学东,这个问题困扰了阿四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不了了之。小说里的刑侦专家说:“我们做什么事,要以认真和努力做到为止,有些案子,靠行政命令解决不了,有些案子,很可能就是破不了的,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可是,由于我们是依据确定性来理解世界、设计生活的,这种悬而未决或似是而非的情节设定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也成就了常中见奇的叙事效果。
对历史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认知形塑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历史本身却包含着诸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形象地描述出人在遭遇不确定时需要以某种确定性来重建生命的存在感,如果说她是在不确定的时代以“古老的记忆”书写《传奇》,那么《璩家花园》更像一部在既定的历史大潮中通过个体可能遭遇到的不确定来书写的传奇。
二、“合传之体”的叙事特征
叶兆言选择以市井传奇书写南京的历史,与他对历史的认知有关,他说“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从小市民、小人物出发的历史书写,让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中短篇小说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而近些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比如《仪凤之门》和《璩家花园》,虽然仍是从小人物出发的“小故事”,却一改“新历史小说”对逸闻轶事、偶然事件的执着兴趣,转而正面呈现历史大潮中的人世沉浮,写的是人生,也是历史。
海登·怀特曾说:“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个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无论它们最终在故事里是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我们姑且使用福莱的范畴——这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从这样的视角看《璩家花园》,这个将小人物植入大历史,容纳了地方风物、世俗生活和市井传奇的小说文本,同样也是历史文本。
小说家眼中的历史是一个个故事的串联。叶兆言说:“我觉得自己成长的历史、所经历的历史包括阅读其实都是碎片化的历史”,“其实碎片化的阅读才是最真实的阅读,那唐诗、宋词从来就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基于这样的理解,叶兆言在《璩家花园》中以打乱的年代建立起讲述历史的基本结构。全书十二章,每章围绕一个核心故事展开,同时牵连出相关的人物,生长出不同的故事枝蔓,而每章也都是一片等待缝合的历史碎片。小说的第一章以李择佳和璩民有的谈婚论嫁开场,牵出费教授的生活日常和天井在祖宗阁上的“偷窥事件”。这一章的主体故事发生在1970年,但其关联到的故事枝蔓会突破这个时间限定。第二章回到1954年,讲费教授、璩民有和江慕莲三人的关系纠葛,顺便也分别交代了费教授和璩民有的身世背景。第三章重新回到1971年,故事的主人公过渡到了天井和阿四,在讲述年轻人的工厂生活的同时,也给第一章的“偷窥事件”收了尾。由是,《璩家花园》关于历史的叙述在这种环环嵌套的结构中滚动向前。
叶兆言将碎片化的历史与碎片化的阅读联系起来,并以此来理解文本的结构。他说:“碎片化的阅读其实给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比我略早的一代人会有那种颠覆性的反应,你可以想象一个人阅读一本书,他很可能是从中间开始的”,“我读到中间这一段,确实觉得好玩,我就有可能往前看,也可能往后看。我想知道前面怎么回事,我想知道后面怎么回事,但是这种视角、这种目光其实就很可能是一种写作的一种线索,那书就可以开始这么写,我就可以把中间这一段作为开头”。《璩家花园》描写了七十年的历史,却是从1970年开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部“把中间一段作为开头”的作品。串联起前前后后故事的,是生活在璩家花园这一具体空间中的一众人物,他们互为师生、同事、同学、朋友、情人、家人……他们彼此交错结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的交往活动成为碎片化历史的有效黏合剂。
可以说叶兆言是以“穿插”“藏闪”之法,整合了碎片化的历史,让《璩家花园》呈现出“合传之体”的叙事特征。《璩家花园》在整体结构以时间为单位实现了年代的穿插之后,又在具体章节中通过人物关系完成故事线索的穿插,每一章都围绕某几个核心人物展开,笔力集中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上,偶尔漾开的一处闲笔提及了其他人物,他们的故事也会在随后的章节中徐徐展开。这种处理方式比较接近胡适对《海上花列传》“合传之体”的解释。胡适说:“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又说:“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东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海上花列传》没有时间上的延展,叙述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单位中,以“合传之体”将许多“不相干的故事”组成一个复杂的机构。《璩家花园》处理的虽然是相干的人和相干的事,但由于时间跨度大,“合传之体”同样成为解决结构问题的有效方式。
《璩家花园》中的人物关系牵牵连连,组织成长篇小说的完整结构。叶兆言在使用“穿插”或“藏闪”之法时,拉长了人物活动的时间范围。如璩达参加高考时,岳维谷已是省教育厅的领导,他利用职权之便为璩达提供读书上的便利就将这两个相差近二十岁的人物连接在了一起;跟璩民有合作开公司的龚政策去深圳后,阿四辞职成了公司在南京的代理人,血缘之外的两代人之间的连接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合传之体”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连接自然地过渡到了时间代际,实现了历史的讲述。不仅如此,《璩家花园》对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交代,包括米米被卖到内蒙古后的杳无音讯、陆晓明跟阿五离婚后还与女儿有旁人不知的联系、龚政策在公司倒闭十多年后突然成了大老板出现在电视上,等等。这些交代一方面很好地解决了“无挂漏”的“合传之难”,显示出作家谋篇布局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呼应了叶兆言对历史的理解。
叶兆言在《璩家花园》中沿用了他熟稔的借助小人物和世俗生活来叙述历史的方式,但他对文本中人与历史的关系做了新的处理。主人公们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中顺势而为还是随波逐流,取决于性格和机遇的相互作用。璩民有和阿四的性格中都有不安于现状的元素,一旦既定的社会秩序出现松动,他们就会尝试改变。于是我们看到,恢复高考后不久,璩民有就察觉了其中的机会,他带着老师们编制复习资料,让学校赚得盆满钵满,为自己后来下海开公司打下了基础。阿四做事从不瞻前顾后,一股风似的,她不想待在工厂里,先是扯着天井上夜校复习备考,后来去了民营的公司,公司破产又自己折腾个音像店,还因为贪图小利卷进了藏毒案。李择佳和天井则是不管遇到什么都是本本分分、按部就班的性格。李择佳富贵的时候做侯太太,潦倒的时候也能给人帮佣、倒马桶;天井只愿守着工厂,守着阿四,下岗后就待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璩家花园》没有像英雄叙事那样让人物在历史中成长,最终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也没有按照“新历史小说”的叙述逻辑让人物疏离重大历史事件,只专注于个人的情感、欲望和内心生活,而是将人物处理成历史的参与者,他们无法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却也能有限度地做自己的主人。
《璩家花园》中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人生轨迹正是一个个平头百姓参与历史的现实状态,只不过小说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将众多相近的轨迹浓缩到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不仅如此,入室行窃的小偷被主家撞见、躲在隐秘角落里的偷窥者被抓个现行、公寓楼里的碎尸案、音像店成了藏毒点、遭遇车祸的不幸者捐赠了遗体……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社会新闻,同样也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浓缩进璩家花园几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海登·怀特说:“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小说创作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可以看出《璩家花园》很好地平衡了虚构与写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让文学文本有了历史的质感,也组合出了一个更符合写作者叙述目的的“历史境遇”。
三、城市性格的独特把握
《璩家花园》中活跃的众多“小人物”身上具有鲜明的市井特征。“因井为市”“处市必就市井”,已然表明了市井与商贾买卖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市井关联的是务实、重利、圆通,市井中人有坚韧豁达的一面,也有趋利狡黠的另一面。但是,如何写出一座城市里的特有市井人生,如何从具有普遍性的市井中提炼出带有特殊性的传奇,则取决于写作者对城市的认知和对城市性格的理解。
叶兆言对南京城市性格的把握或许可以从他对南京历史的理解中看出端倪。他说:“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种偏安的形式,一种接受北方失败的形式”,“南京经常见证兴亡,一个失败者到了南京以后就觉得人生坎坷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地方给胜利者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给失败者一种抚慰”。对胜利者的接纳和对失败者的宽慰赋予了南京城一种大气磅礴又柔肠百转的侠义感,而《璩家花园》里的小人物身上也显现出这种超越了功利色彩的“义”。江慕莲自杀后,璩民有竭尽所能承担起照顾甜甜和米米的责任,费教授也一直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直到他自身难保;李择佳撞见天井在费教授的书房里翻抽屉,但她认定天井是个好孩子,对此一直守口如瓶;阿四入狱十年,天井每月都准时去探监;陆路萱生前就表示过如遭遇意外愿意捐献遗体……小说中蕴含着一种虽然并非毫不犹豫、义无反顾,但仍然能超越功利的相互照拂,其中当然有彼此之间的情分,有人性中本来的善意,只是建立在道德和良知层面上的“义”让这种基于感性的“情”和基于本性的“善”变得持久而稳定。
作为一部书写南京经验、体现南京气质的力作,《璩家花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通过小人物之间的“义”刻画出南京的城市性格。可以说,“南京制造”是叶兆言文本序列始终带有的深刻烙印,而南京也因为叶兆言的书写,成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叶兆言的南京叙述显然意图不止于此,他说:“我是一个绝对反对地方主义的作家,我觉得地方主义毫无意思”。换言之,叶兆言并不是为了写南京而写南京,而是想要通过写南京来写中国,如同《璩家花园》是要通过南京历史讲中国历史一样。
事实上,虽然近些年颇受关注的地方写作,比如“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文学现象多与城市文学相关,但当下的城市样貌和城市生活本身却是去地方化的。一方面,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所带来的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和品牌文化使城市的品相越来越趋同。尤其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被深刻地卷入全球市场之后,城市的外观更是大同小异,不管我们身处哪个城市,看到的往往是类似的城市景观,每天经历的也基本是类似的衣食住行。
另一方面,商业化带来的不断膨胀的交往和消费需求又让城市变得混杂多元。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们根据籍贯乡音、教育背景、消费习惯、生活经历、兴趣喜好甚至休闲方式建立起数量众多、大小不一、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中心明确却边界流动的文化群落,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同时跻身不同的文化群落。这些相互叠加的文化群落借助城市的包容和扩张,衍生出各自的文化品格,同时也使城市本身无法再保持文化上的均质和统一。换言之,如果今天的乡土仍然可以在“传统”所蕴含的符号意义中得到多重解读,那么当代城市内部的混杂多元却让其很难再被单一地概括为文明、进步或颓废、趋利,现代性的多重面孔呈现出重叠并置的状态,使今天的城市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意义空间。“千城一面”的城市表象让写作者不再刻意描摹城市景观,“一城千面”的内在肌理则为城市文学提供了多重表达的可能。这使当下的城市书写得以超越具体地理的限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述空间。
不过,尽管城市是超越地方性的存在,我们仍然能从城市文学中看到不同城市清晰可辨的身影。叶兆言笔下是小人物不断上演市民传奇,有情有义的南京;贾平凹笔下是带着乡土的生存逻辑却与现代社会迎面相撞,不得不对付日子里“破烦琐碎”的西安;王安忆笔下是不管出现在哪个历史阶段,都是充满市井活力的上海;迟子建笔下是天寒地冻却烟火漫卷,守着人性中的善,过寻常日子的哈尔滨;石一枫笔下是以幽默和温情应对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中各种社会问题的北京;张欣笔下是在消费社会中守望诗情,充满韧性的广州……文学中不同的城市之所以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取决于写作者书写城市的立场、视角、眼光,以及将城市作为文化符号的精神寄寓,这与作家的文学观念相关而不完全受制于城市的地理空间。当然,说“不完全”也是因为城市文学不能脱离具体的城市生活,毕竟作家对城市的书写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他熟稔的身边人和身边事。
现代城市“千城一面”与“一城千面”的特性,使文学中的每一个城市既是独特的个案,也是中国城市普遍性的代表,一如《璩家花园》书写的既是七十年的南京城,也是中国本身;既是南京当代史也是中国当代史。叶兆言说:“中国还有个城市可以叙述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是南京,它可以把中国很曲折的历史说出来”。这意味着他是在尊重南京城之特殊性的前提下突出南京参与中国大历史的另一面。这种谈论“地方”的思路非常接近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论预设。“地方性知识”是与“普遍性知识”相对应的概念,意在通过对地方文化的经验性阐释,凸显出被普遍性规律或共同性结构遮蔽了的特殊性,还原对地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观念认知。吉尔兹在处理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时,强调尊重地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认为将研究对象“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这也意味着对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地方”的研究,不是为了删繁就简、合并同类项,最终抵达标准化和普遍性,而是充分尊重、认识和理解“地方”所携带的差异性信息,让每一个“地方”彼此相加,形成多元而统一的整体。从这个角度理解《璩家花园》的历史书写,璩家花园作为中国历史“一隅”的价值得以凸显。
结语
作为南京书写,《璩家花园》延续了叶兆言借助小人物的市井传奇呈现城市经验、塑造城市形象的写作方式,写出了南京城的“义”;作为历史书写,《璩家花园》以城市一角的历史变迁勾勒出中国七十年风云际会的整体走势,实现了作家想要通过南京历史讲述中国历史的写作目标。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为我们借助“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资源理解城市文学中地方性与中国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事实上,当下的城市文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北京、上海,或者南京、广州。不同的城市书写聚焦城市文化不同的侧面,形塑出一个个独特的城市,这些自带普遍性的异质经验互相衬托,彼此叠加,共同构筑了中国城市文学的丰富版图,体现出多元而统一的特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片乡土都能够用来讲述中国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隅”。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