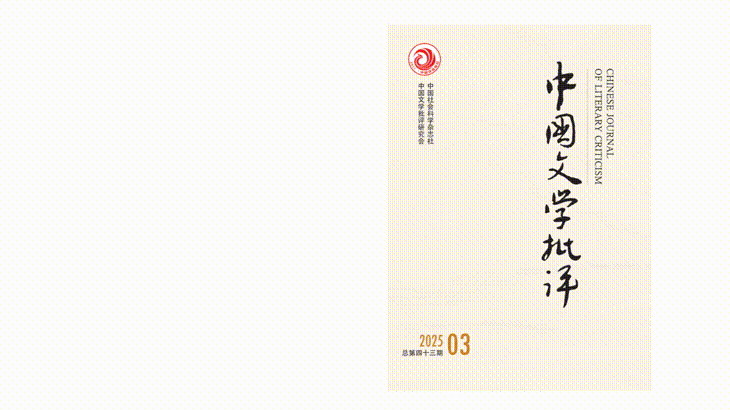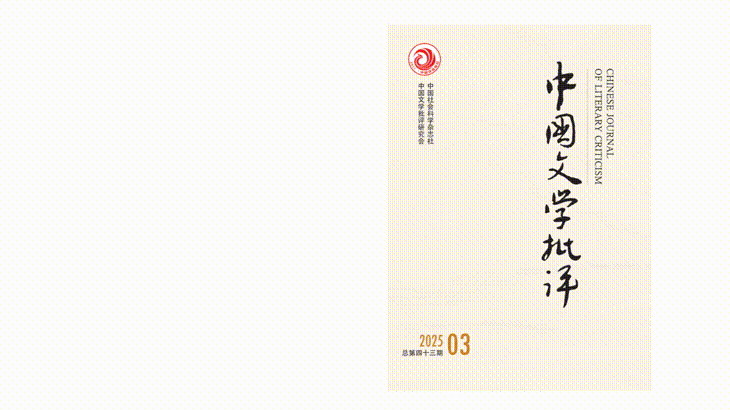
《璩家花园》围绕南京璩家花园一带璩、侯两家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展现了一幅生动可感、悲欣交集的历史画卷。叶兆言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对南京风物的摹写与雕琢,正如西安之于贾平凹、高密之于莫言那样,深沉厚重的南京城为叶兆言建构“合乎自我生命节奏的空间”提供了重要原型。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叶兆言在写作《夜泊秦淮》《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等作品时,尚游走于南京城的今昔与虚实之中,那么近些年《很久以来》《南京传》《仪凤之门》的出版则显示了叶兆言有意识地为南京“立传”的努力,标志着叶兆言从原来“梅城”这一暧昧的虚构空间走向了对南京历史空间、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真实再现。《璩家花园》自然是其“南京传系列”的又一力作。不同于《仪凤之门》对城市史细节的偏重,叶兆言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向虚构性叙事回归的鲜明姿态,在城市空间与历史事件所构筑的叙事框架之下,充盈着人物群像及世情世态的细节摹写,深刻表现了小人物与大历史对话中可能发生的裹挟与反抗、错位与嵌合、欣悦与悲凉。小说以方寸之地,写尽人情世态与历史沉浮,其格局之宏大、立意之厚重、心态之悲悯,在在令人赞叹。
一、时空与个人的交错合流
《璩家花园》以璩、侯两家人半个多世纪的际遇沉浮为线索,围绕璩民有父子与李择佳母女间的爱恨纠葛,串联起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前夕璩家花园的历史变迁。故事及人物的短聚焦非但没有削弱小说的深度,相反,空间之狭小有限在漫漫时间长河及宏大国家话语的映衬与浸润下呈现出格外清晰的历史厚重感。作为独立个体的民有或天井既有独属于自己的性格及经历,而他们的际遇沉浮又勾勒出璩氏家族自晚清以来的盛衰图景。璩氏一族令人叹嗟的命运在一定层面上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重大社会变革及历史进程相呼应。杨庆祥认为,以家族史写当代史是“50后”作家的普遍特点,而叶兆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隐忍”,“‘隐’是隐藏大历史,所有大历史小说里都涉及”,但是又都巧妙地被藏在人物经历之后,而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忍受着“不正义的生活”,并在这种忍受中表现出“他们自己的姿态”。如此这般,个人、家族与国家三者命运交错,构成了《璩家花园》疏密有度且错落有致的叙事肌理。
为城市而非人物立传的写作动机,决定了叶兆言在处理人物、时间与空间关系时践行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观,即在空间化或结构化的时间框架之下将人物命运不着痕迹地镶嵌进历史轨迹的“叶氏美学”。在《璩家花园》中,空间与时间不仅是人物行动所必要的背景,更与人物经历构成彼此应和的三个声部,共同演绎出一曲别样顿挫的命运交响,主旋律虽是璩氏父子起落无常的人生轨迹,而南京城市风貌的变迁与当代中国历史的起伏也同样混声其中。尤其是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的交错嵌合,一隐一显地穿行于城市空间之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让看似偶然、独立的个人事件犹如彼此咬合的时间齿轮一般环环相扣,使小说叙事形散而神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故事从璩、李二人隐秘的情感纠葛说起,璩民有与李择佳在艰难岁月中因彼此帮扶而产生了感情,准备结婚。李择佳随口提出要一台缝纫机作为聘礼,事实上双方都清楚结婚是一个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结果,李择佳并不真的指望璩民有能为自己买一台缝纫机,但璩民有的承诺不是空口无凭,而是真心实意。可是这桩原本“水到渠成”的婚事却出了意外,璩民有因急于拿回费教授拖欠自己的报酬而指使儿子去后者家中盗取欠款,不料被帮佣的李择佳撞见,慌乱之中璩天井不慎将李择佳推下楼梯。李择佳虽未揭发璩氏父子,却因此看清了璩民有的人品,姻缘之事就此作罢。二人潦草缘分的终结又阴差阳错地在多年后成就了天井与阿四相濡以沫的婚姻。天井怀着愧疚与感激照顾了岳母李择佳的后半生,一度被中断的母子缘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绵延,事件的偶然在其微末之处与命运之必然枝蔓交错、彼此呼应。
作者不仅借小说开端的这段冲突牵扯出璩、侯两家自晚清以来的代际更迭,交代了璩、李二人前半生的身世沉浮,而且点明了历史话语之于个人际遇的影响,因此,小说第一句话“1970年某月的某一天”就绝非无关紧要的闲来之笔,故事的因果都与它息息相关。在物资匮乏的1970年,一台全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几乎算得上奢侈品——一百五十元一台,而且要凭票才能购买。正因为如此,璩民有才迫不得已教唆儿子犯下偷盗罪行。因为是形势缓和的1970年,璩民有凭借对政策的了解帮助费教授提前讨回了被扣发的工资七千元,而对方也答应给他两百元的“辛苦费”,不过要按每个月十块钱的方式支付,民有在与其协商一次性支付购买缝纫机数额遭拒之后才策划了拿回自己应得报酬的行动。在这里,反复出现的1970年,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时间。对于璩民有与李择佳而言,两人萌生结婚的念头状似无意,实在也与多年的磨合与扶持有关,但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却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出现了相对和缓的转机,民有不仅为费教授讨回了补发的工资,而且他和李择佳的处境也大为改善,这才是两人这一年放下戒备与顾虑考虑结婚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政治风向与历史车轮的变化深彻而又悄悄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这再次显示了人类个体在历史潮流面前的被动性,诚如王春林在评论《仪凤之门》时所说,“历史人质”在“被劫持状态下的束手无策”,“所有的人类个体,在足够强大剧烈的历史潮流面前,除了被裹挟而去做一个万般无奈的历史人质之外,恐怕并无别的出路可供选择”。
叶兆言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这一点的同时又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即个人命运尽管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洪流所裹挟,却并非仅仅是后者的傀儡,人生轨迹固然难以逾越时代的限制,真正的走向却与个人选择更加休戚相关。正如璩、李二人的缘起缘灭当然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两人的缘分并非出于真心实意,而是乱世中迫于无奈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的自我放逐之举。偷情也好,结婚也罢,他们习惯了苟活于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下,被动地承受重压与剧变,毫无选择的权利,直到那顺水推舟的婚约出现变故,两人才突然从盲目与麻木中清醒过来,为彼此的关系——单纯而不掺杂其他因素或利益考量的关系——盖棺论定,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从被历史话语叙述/遮蔽的状态中短暂逃离出来,重拾叙述者的身份。
然而这种逃逸并非总是出于自觉,命运沉浮在漫长而无形的时间洪流之中往往行踪难辨,一如璩氏父子面对命运之裹挟的态度,决难以乖从或滞钝而一言蔽之,相较之下,稳固而具象的空间变化无疑更能够清晰地勾勒历史变迁。小说以“璩家花园”命名,所述之人事皆聚焦于此,或者以此为原点出走、回返或离散,而璩家花园自身也在此聚散离合之中数度兴衰。在这里,私有空间向公共记忆的过渡一方面与历史的线性走向高度重合,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轮回轨迹,比如作为璩氏后人的天井其实对曾经奢靡富丽的祖宅毫无印象,早在他出生前这里就已面目全非,经过一次次战乱,璩家花园这一片地区,早就成了大大小小的杂院。正如对“祖宗阁”的无知,他对家族史的盛衰亦漠不关心。与父亲的频频回望不同,他始终生活在当下并对未来充满期待。有意思的是,恰恰是看似家族异类或璩氏“不肖子孙”的天井彻底摆脱了历史过分浓重的阴影,在坚定地奔向未来之时却在无意中守住了历史——晚年的天井与刑满出狱的妻子阿四辗转住回了儿时生长的璩家花园,于简陋而又簇新的斗室之中重温旧梦,“复活”为一对新人。与此同时,又在游客所象征的他者眼中作为历史街区的一部分与历史叠合,实现了个人、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合流,璩家花园也便具有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所谓“璩家花园”,显然并非花木扶疏、曲径回廊的园林空间,而是历史空间与人间戏台。璩家花园的方寸之地,寄寓了这片土地上三代人数十年的恩怨沧桑。
二、千姿百态的市井人物群像
璩家花园不仅仅是时间化的空间意象,更是人物的存在空间。叶兆言以微观镜头记述人物的行为与心理,将他所属意的历史之真,隐藏于生活日常之下,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形态各异而又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沉郁的人文精神是叶兆言小说叙事的重要基调,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这种关注甚至早于“新写实主义”对日常叙事形态的重新发现。他的小说创作始终擅长直接切入生活的肌理,着力揭示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下的人性面目。尽管《璩家花园》叙述视角不断切换,但小说叙事总是围绕璩氏父子展开,故事发展也在两人渐渐走向分歧与疏离的线索中缓缓推进,致使父子殊途的不仅仅是代际差异,更是性格差异。璩民有父子身上不仅印刻着时代更迭的辙迹,更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璩民有无疑是《璩家花园》中性格最为复杂多面的人物。作为经历过社会剧变以及宦海沉浮的一代,他身上既有天真理想的一面,也有自私怯懦的一面,兼具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双重人格特征。璩民有年轻时上过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做了中学英语老师,虽然没有野心,安于现状,却不乏求学进取的精神。对知识本身的热爱始终伴随着他,成为其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多年以后璩民有将半生所学用于记录不堪的狎妓经历,但这种沉沦的肉体欲望某种意义上同美好的知识渴求一样,或许源自对被压抑以及缺失的某种生命权利的不自觉且注定徒劳的追寻。
正是这点仅存的知识分子情怀,令璩民有在改革开放之初爆发了人生中罕见的理想与热情,成就了后半生一段真正辉煌的岁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六十九中副校长,彼时正赶上高考热,怀着露一手的迫切愿望,璩民有率先为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开设补习班,一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第308页),一时声名显赫,也因此参加了民主促进会并当选区政协委员。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潮下,怀揣“做点实事”理想的璩民有又先后通过刊印售卖复习资料、盖宿舍楼这两件事为学校及教职工谋取了切实的福利。后来受人怂恿下海经商,也并非完全源自对金钱的贪婪。正因为如此,他能坚守原则不以权谋利,也能在失去权力金钱时安之若素。这与其说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气度,不如说更多地源自得过且过的小市民习性,一如他习惯讨女性喜欢,却从未有过真情,缺乏深思熟虑的恋情与婚姻,几乎伤害了所有真心待他的女性。除去晚年那一段对英文日记的短暂狂热,璩民有几乎不曾对这个世界怀有过浓烈而持久的爱意,这种薄情而不寡义的性格中和了善与恶的冲突,让他游走在人性的中立地带,成为一个读者无法投射爱恨的另类“真人”形象。
批判的阙如表明了作者带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写作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璩氏父子之间的性格对比。如果说作者从一开始便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璩民有性格中的矛盾性,着意将其刻画为怯懦庸常的“真人”,那么作者对天井这个人物的塑造则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技巧,即欲扬先抑地写了他的迟钝、笨拙甚至冷漠,不着痕迹地勾勒出一个“愚人”形象。作者先是这样写道:“十六岁的天井,个头已大人模样,已经和成年人一般高,嘴边也有了毛茸茸的小胡子,心智上仍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仍然没有完全明白事理,仍然没心没肺”(第5页);继而解释说,其童年时期曾两次遭受意外,“智力受了影响,与其他孩子思维不一样”,被人戏称为“二呆子”(第48页)。但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发现,他读书成绩不算坏,后来甚至还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可见智力并没有问题,其人之愚乃是对利益得失、阴谋算计甚至人情世故的无知无觉。和父亲的轻佻寡情相反,对阿四坚定不移的爱,构成了天井行为逻辑的起点。这份爱是如此真诚而纯粹,以至于他从来不指望这个“心高气傲”的漂亮女孩会喜欢“缺心眼的”自己,并愿意为她放弃读书机会与大好前程。对于天井而言,“爱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无须权衡或抉择。当其他人在一次次的选择中走上歧路,他却因为留在原地得以和迷途知返的阿四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他对妻子婚前堕落行为的包容以及婚后不忠的迟钝不察,最终彻底感化了这个不贞的女人,令她蜕变成他理想中的模样。一定意义上,天井的执着近乎清静无为的道家精神,他的愚顽未尝不能视作大智若愚、大成若缺的一个注脚,看似随波逐流、软弱可欺,却带着孩童般的一派天真完成了对现实的反抗。
除了璩氏父子所象征的“真人”与“愚人”,小说中还描写了一群形态各异的“庸人”,比如善良平凡的李择佳、谨小慎微的费教授、泼辣率真的阿四、风流纨绔的章明等,他们身上既有自私、贪婪等人性的弱点,也表现出真诚、善良、坚忍等可贵的一面。作者以远近交错、主次分明的长短聚焦讲述了他们平凡又跌宕的悲欢离合,这些庸庸碌碌的小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差错落地穿行于璩家花园的街巷楼阁之间,和主人公一道组成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市井生活图景。无论是“真人”“愚人”还是“庸人”,这些人物群像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晋书·嵇康传》),小说由此写出了大时代洪流中载沉载浮的个人命运。
三、以点带面、以人代事的叙事手法
虽然叶兆言说《璩家花园》是他“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第536页),但相较于故事广阔的时间跨度,小说的篇幅并不算长。在有限的篇幅中,小说清晰而完整地勾勒出了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除了明确的空间聚焦之外,还得益于作者状似随意实则精巧的谋篇布局,即串珠式以点带面、以人代事的叙事手法,有机融合了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简约灵活与西方现代的破碎象征及空间隐喻。正如论者所说,时间是理解叶兆言小说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小说形式框架的所有秘密几乎都在时间”之中,时间不仅是隐藏在内容之中,也蕴含于形式之中。
在叙事结构方面,《璩家花园》最明显的特征即在于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以明确的时间节点为章节命名统摄全篇。前五章分别以天井和民有两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双线交叉地讲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璩家花园一带的人物故事。从1970年的某一日天井误入祖宗阁初懂人事开始讲起,接着引出了天井出生的1954年及其母亲江慕莲的往事,之后又回到他初中毕业成为工人的1971年,在讲述1979年天井与阿四的婚礼之前,又回顾了1957年璩民有即将跌入人生谷底的种种经历。此后两章为转折,以费教授的经历承前启后,第六章“1964”在时间上接续了璩民有的1957,第七章“1976”则补叙了他与璩民有、李择佳的纠葛。小说从此处开始双线合流,回到传统的直叙模式,选取“1983”“1986”“1989”“1999”和“2019”五个时间点讲述了改革开放后的世事变迁。不同的时间节点对应不同的人物轨迹,小说的十二章以天井、民有、费教授、李择佳、阿四、阿五与璩达等人的重要人生经历为切入点,从某一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延伸至人物置身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境遇,串联起整整几代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数次社会大变革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时间节点的陡转与切换割断了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条,悲与喜、苦与乐、生与死、父与子的轨迹或并置或交错,故事由此呈现出一定的破碎感,也令小说前半段的叙述节奏略带几分阻滞,然而随着更多叙事拼图不断被抛出,故事也如百川归海般渐次流畅与开阔起来。很显然,作者刻意使用了这种叙事结构以便最大程度地容纳时空。小说第五章阿四因被章明抛弃,心血来潮地想要通过读书“提升自己”时这么写道:“阿四和章明分手了,有一股要向上的力量产生了。她突然想到要去夜校上课,要去夜校补习”,“阿四要去夜校读书的念头,与唐山的大地震几乎同时爆发。”(第198页)唐山地震的爆发和阿四想要读书的念头之间,不仅仅构成了本体与喻体的修辞关联,更将儿女情长之琐事与历史伤痛、民族创伤巧妙并置,于小人物经历之间埋下了大历史脉络。然而作者对后者的叙述仅仅点到为止,以一句充满暗示性的“这一年,1976年,这样那样的事特别多”(第198页)再次将叙述视角转回璩家花园的动荡与变迁,转回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凡,直到第七章末尾结束对费教授故事的叙述时才悄然与此处接榫。彼时糊涂不已的费教授在“1976年7月7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精神状态不正常的费教授死前已经对一些事件毫无记忆,这也许暗示了时代的变迁以及历史被遗忘的某种可能。一个老人临死前的胡言乱语也就不露痕迹地被赋予了历史的沉重与厚重。
与此同时,人物视角的自然转换也让很多看似松散的叙事场景之间巧妙衔接,完全没有传统笔记体小说那样的粗疏。比如小说开头在描写李择佳因撞见天井偷盗而被后者不小心推下楼梯这段情节时,就使用了交替的视角来解释人物关系、铺展叙事线索。作者先是寥寥几笔交代了李择佳看到天井、发生拉扯、不慎坠楼晕死过去的过程,然后以“李择佳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第23页)开启她对天井幼年时的回忆,引出璩民有因下放改造而将天井送至侯家“搭伙”的经历。李择佳的记忆碎片之后是一段视角模糊的描写,从前面近乎静止的细节描写,突然转而加快节奏,时间飞逝着从过去抵达现在,在重新回到“李择佳从二楼摔下去的那一刻之前”(第24页)也同时完成了人物视角的转换,和“李择佳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便昏死过去”(第22—23页)一样,“天井根本没时间去想后果有多严重”,惊慌失措的他只能“逃之夭夭”(第24页)。短暂的逃亡中他不无怨恨地想到了父亲,如果不是父亲让自己去费教授家偷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么继而解释“民有为什么要让儿子去偷钱”也就顺理成章;叙述视角在这里也就自然地转到璩民有身上,不但交代了这件“荒唐事”的来龙去脉,也照应了开头他与李择佳谈婚论嫁时埋下的伏笔。
人物视角的转换造成了叙事的停顿,同时也赋予作者在停顿与裂隙之间随意穿插回忆或引出新叙事线索的多种可能性,有时一处情节可能遭遇数次中断,而作者甚至会刻意强调这种停顿,将视角从人物身上稍微拉远至一个全能的叙述者,如“三天以后,我们看见李择佳正迎面走过来”(第9页),或者“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打打岔,说点别的什么,整理整理头绪”(第14页),又或者“我们不妨把时间拨回到1975年”(第188页),等等。大部分情况下,具体事件中的这些小停顿都会重新被接续,那些看似完整的事件不过是整体故事中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小片段而已。它们之间的省略与跳跃,为读者钩沉历史事件与勾勒人物轨迹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通过这种现代与传统相混杂的叙事手法,作者有效改变了“传奇故事的线性发展逻辑,将一切客观性的叙事转化为具有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文本”,在写实精神之外融合了含蓄蕴藉的审美趣味。
需要指出的是,故事情节貌似的松散与空间背景的紧凑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当晚年一无所有的天井夫妇搬回璩家花园那间逼仄的小房子,蹉跎的人生一定程度上似乎得到了补偿,生命也同时走向终结与新生。他们在这里出生和长大,是彻头彻尾的原住民。他们曾经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万万没想到在搬离三十多年后又会回来,尽管现在的璩家花园早已今非昔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如今成为符号化的可供游览的文化街区,那些切切实实的砖瓦墙垣变成有点模糊和变形的老照片,甚至天井和阿四本人,也从璩家花园的居民变成了“原住民标本”与“活化石”(第533页)。他们从璩家花园中走出来,再走进璩家花园深处,已然众生百相,俱现裂璺。正是在“璩家花园”这一空间意象中,小说以近似回环的叙事结构表达了作者浓郁的家园意识和深沉的历史观。诚如戈达尔所说,“无论书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到工作和日子总让我们失去的一些感受:人生的复杂,我们对价值的需要,我们在寻找价值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不确定性,还有最根本的,对我们存在于世的震惊。”
四、反复出现的物意象
在刻意淡化的历史话语和着意虚化的空间书写之上,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物意象不免被凸显,如缝纫机、日记和照片等,这些微观之物或是时代的模糊象征,或是个人的生命印记,不仅浓缩着宏观的时间或空间隐喻,也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黏合叙事的作用。“缝纫机”是小说中出现得最频繁、几乎可以说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意象。它首先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起点,李择佳和璩氏父子的恩怨纠葛由此而起:
天下万物多少都会有联系,好像“蝴蝶牌”缝纫机,只是开了个头,为后面的故事推开一扇窗,打开了一道门。没有“蝴蝶牌”缝纫机,就没有天井偷钱这事,天井不偷钱不还钱,就不会把李择佳拉下楼。一环套着一环,“蝴蝶牌”缝纫机产生了蝴蝶效应,李择佳不被拉下楼,天井就不会东躲西藏,不会从永红小学的围墙翻过去,进入那个防火通道。不进入防火通道,天井不会想到要往高处攀登,进入黑暗的落满时间灰尘的祖宗阁。不进入祖宗阁,他不可能从祖宗阁木板的缝隙中,看到郝银花这个女人。(第62—63页)
此后的种种故事其实都是这段话的漫长延续:如果没撞见郝银花和奎保的男欢女爱,天井不会以“羞耻”“痛苦和不安”的方式步入成人世界的大门,而这种内疚感伴随了他一生,令他不自觉地拒绝了“成人法则”而能保有精神童贞,并最终以寓言般的姿态重返虚实参半的童年时空。
“缝纫机”是社会变迁的见证,李择佳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缝纫机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改善生活水平的目的,更多的是对曾经的火热生活的怀念。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前,家境殷实的她拥有整条巷子唯一的一台缝纫机,丈夫死后,李择佳被迫自食其力,靠着这台缝纫机在“大跃进”时期和附近的家庭妇女组织合办了一个七人缝纫小组,很快发展成“永红服装厂”。“文革”开始又做回家庭妇女的李择佳,同时也失掉了那台缝纫机。随着家庭条件每况愈下,不仅购置一台缝纫机的愿望遥不可及,摆脱“家庭妇女”身份的愿望更加渺茫。然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生活冲击是如此之大,等到70年代末女儿阿四结婚时终于如愿拥有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作为嫁妆,但它不过是婚嫁风尚的附属品,“作为缝纫机,这玩意几乎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第525页),直到在老房子改造中其他老物什都遭到淘汰之时,作为嫁妆的缝纫机因为特殊的“纪念意义”而成为唯一保留之物。“缝纫机”从财富象征到自立资本再到“无用之物”的演变,正从最细微处表征了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和缝纫机背后所蕴含的时代话语不同,日记代表了隐秘的自我声音。小说中只有费教授和璩民有写日记,后者又完全受了前者的影响。费教授最初记日记是为了锻炼外语能力,日记中充斥着英文、德文和文言文。日记成了个人史的记录,也是他无数的情感寄托的所在。当晚年他重新阅读这些日记时,“失去的历史”与“消失的场景”便纷纷“复活”或“再现”。这些“再现”的事件、情感、思想在誊抄者璩民有眼里却在语言与时间的双重陌生化之下,模糊了“历史之真”与“文学虚构”的边界。费教授的英文自称是效法于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讲究文思晓畅,追求隽永淡雅”,很多地方,璩民有是当作故事来读的。甚至在费教授精神状态不太正常的最后时光,他回忆起的大多不是经历本身,而是日记中所记录的自己的故事,于是“时间开始颠倒,空间变得混乱,他能想起的,偶尔能想到的,日记里记的一些事,各式各样的碎片,仿佛漂浮在海面上的杂物,完全不是原来的形状”(第294页)。
历史和故事一样,都需要被讲述,“对于阿四和天井这一代人来说,渐渐远去的历史从来就是用来聊天的,都是靠聊天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才存在”(第363页),即使亲身经历过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伤痛,天井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直到时过境迁后,他被人事处叫去销毁相关的档案材料,才听故事一般了解了这段历史,了解了父亲和自己的那段经历。至于日记的被偷,也颇有象征性:费教授对日记的过分珍视让歹人误以为是值钱的东西,偷走后发现都是看不懂的文字,一时为了掩盖罪证,在一个夜晚骑上车满大街乱窜,垃圾箱、大院围墙、秦淮河,走到哪儿就丢到哪儿,最后甚至把旅行包连同零零碎碎的日记纸片一起扔了。于是赃物不复存在,费教授令人唏嘘的一生也就被如此轻易地抹去,被历史遗忘。
相较之下,照片对历史时刻的再现更加直观。阿四和天井聊起早逝的父亲母亲时,不禁为缺失的记忆而感伤,让天井羡慕的是,阿四好歹还有一张照片,知道自己爸爸长什么模样,而他的母亲江慕莲却在自杀前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照片,一张都没有给他留下,他也就对母亲毫无印象。他对生活了一辈子的璩家花园同样知之甚少,直到它成为电脑喷绘的老照片被贴在巷子两侧的青砖墙上,当现实与历史并置,图片与文字讲述中的璩家花园才终于被天井真正认识:
很多老照片都太过久远,属于爷爷奶奶和太爷太奶的年代,不加上文字说明,根本不知道是在璩家花园。照片上的辉煌时期与天井毫无关系,他熟悉的场景当然也有一些,并不算太多,天井看到了老房子边上那棵自己熟悉的榉树,看到了老房子里的祖宗阁,看到了费教授住的小楼,看到了永红小学,看到了永红服装厂,永红服装厂的围墙那边,就是天井的家。(第534页)
可视的历史仍然是一种讲述,而那些没有被讲述的真相,“永远地就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第431页),有如岳维谷拍的那些照片,天井看到他脖子上挂着一台流行的傻瓜相机,拍个不停,却不知他究竟想要捕捉什么,也不知为何要讳莫如深地将照片寄放在这位并不熟悉的小舅家,又缘何会在一个极不适宜的场合(李择佳的葬礼)匆匆取走。他看到了什么?又为何沉默不语?我们当然明白岳维谷那些照片的不合时宜,但叙述者天井却糊里糊涂,他好奇心的缺乏导致了叙述空白的出现,也带来了历史图绘中令人遐想的留白。小说中历史真相与被书写的历史同时被讲述,正如叶兆言在非虚构与虚构文学两个方面的探索,既有对人性的温厚的探寻,也有对时代的深刻的反省,既有对历史真实的呈现,也有对历史混沌的留白,两者共同构成了叶兆言历史书写的丰富维度。借用厄休拉·勒古恩评论肯特·哈鲁夫的一段话来说,叶兆言的历史书写“不故作姿态,也不提高嗓门。他安静而亲密地、同时也有所保留地诉说,就像一个成年人对另一个成年人诉说一样。他小心地让故事以正确的方式被讲述。他做到了,正确无误;他的故事听上去如此真实”。
可以说,《璩家花园》作为一部别出心裁的南京断代史,为城市立传的同时也为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歌哭。作者对人物、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超妙处理,展现出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叙事艺术。小说笔记体的古典趣味与流畅简约的语言风格彼此交融,其笔力遒劲处若老松盘根,纤柔处似春蚕吐丝。历史与城市的浮光掠影看似是虚化了的故事背景,却带有厚重的时空纵深感,与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交错嵌合,显隐虚实之间,回荡着小人物与大历史寂静无言而又声嘶力竭的对话,其动人处,不在奇巧而在悲悯。诚如叶兆言自己所说,“小说中照例会有很多痛,很多苦涩,很多不可言说,我无意展示它们,渲染它们,只是在轻轻地抚摸,带着含笑的眼泪继续写”(第536页)。总之,《璩家花园》写尽了一个时代余韵绵长的感觉结构,踏过玉阶苔痕,行经百年风雨,一座城,几代人,半世纪,尽付笔端,欲说还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