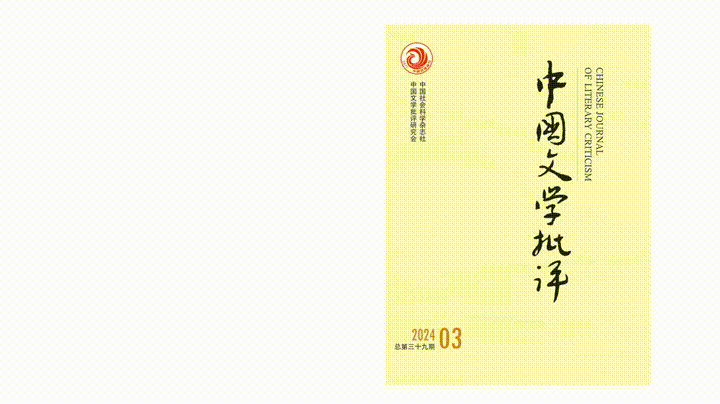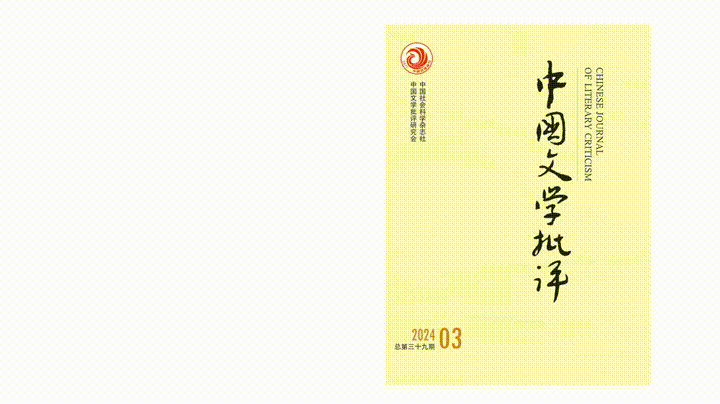
理论与文学关系的紧张由来已久。一个为文学辩护的知识生产领域,不断遭到辩护对象的攻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理论何为,理论的合法性何在,理论如何生产关于文学的知识?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澄清。
一、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文学的在场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应有之义。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文学,何来文学理论?然而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命题的讨论都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找到一种“如其所是”与“何以所是”的深层理据,防止先入为主或过早给出意义的冲动。所以,对任何一个文学的理论命题,我们不能遽下判断,而应当进一步追问:这一命题究竟是在说什么?
历史地看,文学在先,理论在后,理论是对文学的总结、描述、说明和评价。早期的文学理论的确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如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布瓦洛《诗的艺术》,以及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都是关于文学(诗)的理论。我们离开文学的在场无法讨论文学理论的意义,更不可能设想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理论与文学一起构成文学存在的两个维度,并都受时代精神的感召和现实情境的激发。
但是,文学理论一旦形成,与文学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它既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又可以跳出文学的制约而独立发挥理论的功能。众所周知,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也有着政治关怀,向着时代大胆发言。例如,席勒不仅是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审美教育书简》与其说是讨论审美的游戏冲动,不如说是对社会改造的思考。在席勒看来,暴力不可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由本能和自然的物质世界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道德世界,必须经过审美教育的中介。因此,《审美教育书简》是一个实践的文本、革命的文本,向着他所处的世界不断发难的批判性文本,而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或美学著作。马克思曾在《评普鲁士当局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里,马克思的政治家、思想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的身份是统一的,他对于文艺的批评并不止于文艺本身,而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和道义精神。恩格斯批评玛·哈克奈斯《城市姑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实地写出她的时代,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主张:“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强调文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作用于现实,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显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是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性,审美现代性又称批判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理论与美学、文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对文学审美价值的思考,也有对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与运用,是美学与文学理论介入社会而形成的一种言说方式或理论文本。
如果把这种言说方式或理论文本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本然存在形态,以为可以丢掉“文学”的文学理论,进而还能化解文学理论危机。显然,这是有悖于文学理论逻辑和旨趣的。毋庸讳言,文学理论可以溢出文学而独立发挥社会批判的功能,但这只是文学理论公共性的一个特点,如果作为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显然言过其实。因为,一旦将这种理论称之为文学理论,令人担忧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一种不受文学制约的理论话语就会膨胀起来——明明是“没有了文学”却又偏偏以“文学理论”命名,当今文学理论的危机,既体现为本体论的,又表现为功能论的。本体论的危机,即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严重脱节,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最为根本的源头活水隔断了,导致了文学理论自说自话,空转空耗。正由于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的严重脱节,带来了文学理论功能的弱化——文学理论介入社会能力的弱化。如果承认文学理论危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么,功能论意义上的溢出文学的文学理论能否使文学理论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这仍然是一个问题。高建平指出,如果把理论离开文学,说一些包括政治、社会、性别、青年亚文化或者关于社会焦点的话,视为文学理论新方式或者文学理论化解危机的路径,则无异于耕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文学理论走出文学,面对社会发言并成为一种理论的形态,这种理论可能是社会批判理论或别的什么理论,但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学理论。因为“文学理论不管如何扩容,不能背离三点:首先,这种研究要从文学出发;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围绕着文学;第三,这种研究要以文学为目的。否则的话,就不能叫作文学理论,而可叫作别的什么理论”。这个观点道出了文学理论存在的文学基础,也为审视各种理论提出了一个基于文学性的视角。
李春青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概念生成的另一种情况。他发现,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有很多概念比如气、清、远、风、玄、妙、神等,一开始并不是从文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文论的概念,而是属于先秦子学的一部分。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些概念伴随着人物品藻而逐渐成为诗文评、书评、画论中的基本概念。如果从起源上看,这些概念当然早于特定的文学实践,不是从特定文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李春青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子学概念生成文论概念,实际也是经过了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的检验和提炼,并被赋予了新的文学性内涵。这里又涉及中国哲学、美学与文学艺术的相通性问题。中国哲学、美学不是在纯粹思辨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哲学中的许多命题、范畴、概念的诞生,受制于它所属的哲学世界观。不把世界看成静止的存在,而是鲜活有生命力的、被体验的对象,这是中国哲学面对存在的一种生存论智慧。这种智慧催生了中国哲学、美学命题中的诗性言说,而诗性言说与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又是相通的。因此,中国哲学、子学中的一些概念具备转化为文学理论概念的潜质。随着时代风气和文学观念的发展,这些概念走进了文学,成为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走进文学不是拿来即用,而是经由文学实践的检验和提炼,并被赋予了文学性内涵的。唯其如此,这些概念向文学、文论概念的转化是自然而然,并且是在文学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质言之,无论怎样的概念,成为文学理论的概念,都需要经过文学经验的验证和文学实践的检验,这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出场说到底是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社会文化现实——文学的图像化、视觉化、世俗化,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边界模糊等。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新理论,如果文学研究还止步于审美范式或单纯的文学研究,不顾新的社会文化现实,自说自话,只会远离文学与文化的现场。所以,文化研究应运而生。文化研究的出场不是要埋葬文学理论,而是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可以并行不悖,它们之间彼此的对话远比互相抵制更具有建设性。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化研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一些文化研究者关注文学之外的一切领域,唯独对文学漠不关心。对此,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不留情面地嘲讽道:“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由此,伊格尔顿断言“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瓦伦丁·卡宁汉对文化研究忽视文本的审美品质而空发议论表示了担忧:“60年代引进的‘理论’无疑对英文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可是我们从那里究竟应该走向何处去呢?难道我们应该重新去读解经典吗?难道我们应该像从超市的货架上拣取商品或从异国风味的后现代主义‘大拼盘’中选择食物那样去选择一个又一个的文本并把它们混杂起来吗?”他希望“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的传统”。文学理论在发挥介入功能的时候,需要文学性机制来保障。否则,溢出了文学性,文学理论就会在芜杂纷乱的社会文化现实面前迷失自己,何谈功能的发挥?西方文化研究命运的起伏跌宕也许昭示了离开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尴尬处境。文学理论可以暂时不讨论具体的文学问题,可以溢出文学的制约而讨论一切社会问题。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中的。离开了文学,理论创新也就失去了最为关键的源头活水。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文学)理论一定是关涉文学、有文学性的 。
二、好的理论是有文学性的
好的理论是有文学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动力源自许多方面,但无论哪个方面,最终都离不开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是检验理论好坏的唯一尺度,也是生成文学理论知识的本源性路径。一种理论能够有效地介入文学的经验、文学的事实和文学的实践,那就是好的理论;一种理论不能够有效地介入文学的经验、文学的事实和文学的实践,那就是坏的理论。
坏的(蹩脚的)理论没有灵魂,没有视界,也没有与思想能量相匹配的话语生产方式。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坏的理论的泛滥。坏的理论习惯于从活生生的文学世界中抽绎出思想、总结出观点,习惯于用一套大理论(大概念、大叙事、大体系)规约文学,习惯于用总体性的思维讨论具体的文学问题,习惯于一般性地回答文学的起源、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传承、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这种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就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结果竟是这样,理论喋喋不休,文本却缄默不语。
文学理论不只是对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的总结和归纳,依靠总结和归纳不可能产生深刻的理论。因为,理论是有谱系的,有自身的转化和生成机制的,理论不同于总结和归纳,就是因为理论探寻对文学的本质性理解。但是,无论理论如何谋求深刻,文学性始终在场。例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是通过美学上的现实主义而进入文学的,一旦美学的现实主义建立起来,理论对文学的解释就产生出强大的辐射效能。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对文学艺术特殊性尊重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特色之一就是对于社会文化现实的强烈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修养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有深刻的关联。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专门讨论了文学作品谜一般的结构,认为正是这种谜一般的结构向理论家、批评者提出了解谜的要求,而解谜的前提是要承认艺术作品的不可解析性。在这样的美学视野下,文学解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成为理论借助于文学而抵达的现实批判之路。相反,如果一种理论不与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相结合,不自觉接受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的检验,这种理论即使在社会文化现实面前振臂高呼、慷慨陈词,也不过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因为,缺乏文学精神的理论言说是干瘪的、没有底气的。所以,理论要坚决纠正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谦卑地听从文学的召唤。否则,文学的缺席会带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泛滥。这种理论看似讨论了许多文学的问题,但文学究竟是什么仍然处于一个晦暗不明的状态。
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理论不能包打一切。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正是因为理论意识到自身的限度和边界,是理论自觉的体现。反思性研究致力于对理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机制、条件、语境和谱系的探究,是一种回溯性、本根性的研究。理论言说的限度何在,谁为理论的合法性辩护,这是反思性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重建文学理论的声誉,提升文学理论的阐释效力,反思性是一项基本要求。文学理论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知识生产活动,但这种知识生产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寻找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结论或者对对象的客观性陈述,而是描述、解释、阐发和评价,是最大限度地逼近文学意义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主义立场不同,文学研究是高度主体性的,是同情的,身与物化的,是带着特定视域和丰富感性而与文学的照面。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研究需要有一种回到内心经验的能力。在内心经验层面,文学精神与反思气质不谋而合,成为一种愉快的、有难度的人文发现之旅。体验在这里不是被动地去经历、去认知,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在之中”。这个过程充满着灵动的发现、会心的默契,是一种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遭遇。
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由谁来保证自身的合法性,答案毫无疑问是文学,包括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等。文学可以不留情面地质询理论的狂妄和自大,提醒理论面对不确定的文本始终保持敞开的状态。理论远离了文本,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空转之中,其枯竭消亡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一旦进入文本,那些动人的理论仿佛一下子不起作用了。理论在文本面前的失效,正是新理论萌动的开始,这看似是理论的局限,其实是理论葆有活力的关键之所在。
好的理论是有文学性的,文学性在这里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表面看,理论与文学操持着不同的话语方式,理论是概念的、思辨的、推理的、论证的和理论形态的,而文学是感性的、形象的、结构的、意蕴内涵其中的,话语方式的差别带来了两者的分别。这种差异其实是表面的。在精神深处,理论和文学其实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对人类生存经验的最为深沉的抚摸,是对人的存在的最为切己的关怀,是对爱、自由、幸福和可能性憧憬的表达,是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抗争和批判,理论和文学在精神方面是深度契合的。更何况,现代文学的叙述结构里,理性判断、哲学思考是其基本内容。甚至,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理论的思考。而理论,特别是晚近的理论,文学性弥漫是其基本特点。作为发现问题的视角和文本分析的工具,文学性使理论超越概念的局限,实现对不可言说之域的抵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认为文学性“是对言词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是抵制那种粗浅的、标题式的、摘要式的直奔主题阅读的最好方式。
自从“文学性”一词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笔下诞生以来,“文学性”成了文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别于将文学性定位为“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基本规定,如今文学性的内涵已远远超出文学本身,而成为理论的一个特点。推动理论的文学性生成的重要力量,是各种文本——戏剧、电影、互联网、短视频、电子游戏等文学性的蔓延。辛普森基于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性蔓延这一事实,认为一切书写都是文学性的,卡勒则提出了“理论的文学性”命题。作为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方式,理论的文学性特质不仅表现为文学修辞手段的运用,更包含着唯有文学性视界才能发现的对不可言说的体验以及无法被命名的事物的一种尊重意识——如法国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与雅克·朗西埃所强调的那样,文学性是颠覆常识、凸显差异性的方式。
仔细分析,“去文学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理论化”这些提法实际带有某种噱头的意味。理论真的要将文学逐出地盘,要和文学做一个了断?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历史上,几乎所有出色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对文学有深度理解,对语言、形式高度敏感的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他相信,在文本的解读与理论的生产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张力关系。没有对于作品语言的敏感,所谓文学的讨论就会无的放矢,不得要领。对文学的关注不是对文学之外的现实的关注,而是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关注。文学之为文学,正是语言的力量、形式的力量作用的结果。在理论的生产中,具体的文学文本可能隐去了,但文学性的旗帜高高飘扬。
没有人规定理论的书写必须是“理论式”的。理论同样可以使用多种反思性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在文学的世界里,事实和虚构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分歧,文学的事实不是真实,而是富有人文性的价值事实;虚构也不是背离现实的凌空虚高,而是拨开云雾抵达本真,向着可能性趋赴的过程。以语言为媒介,事实与虚构的结构性关系得以建立。文学性之于理论,不是一个技巧、策略的问题,实际是理论走进文学、最大限度秉持对文学善意的努力。理论如何穿梭于文学的世界,讲述文学的故事,而不是傲慢地、居高临下地对文学实施宰制和剥夺,文学性是一个基本的制衡机制。不难发现,随着文学与理论深度关联的揭示,理论书写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已经来临,一种融合了概念、逻辑、实证、参悟、体味、叙述等多种致思方式的理论跨文体写作将流行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人文的、意义的、回到内心的精神世界。
三、在阐释中生成的文学理论知识
文学的意义并非自动产生,而是依赖于阐释。文学是沉默的,阐释则是对沉默文本的激活。所以,阐释不仅是实现文学意义的手段,也是升华为文学理论知识的基本途径。
文学阐释的要旨并不在于寻找一个唯一确定性的答案,哪怕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创作意图,哪怕文本对解释者发出按照文本逻辑去解读文本的呼唤,阐释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运思。依赖于作者意图的确定性或文本结构的稳定性建立起来的文学阐释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并不能给人足够的说服力。毫无疑问,文本结构的先在性、稳固性对于任何一个阐释者来说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制约因素,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尽管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毕竟都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堂吉诃德或贾宝玉,这就说明阐释不是离开文本结构的天马行空,不是我行我素的任意行为,没有哪个批评家会无视文本结构的制约因素而听任意识的信马由缰。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功能结构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这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阐释的公正性、权威性与其说是文本结构确定性使然,不如说来自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阐释的有效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阐释文本需要有精湛的细读能力。文本细读不是一般的经验性的阅读,不是感性的直观浏览,而是基于专业知识积累和特定的阅读训练的一种走进文本的能力。按照结构主义诗学的观点,文本是独立的,自有逻辑、自有关联的,对文本意义的阐释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这决定了文学阐释的权威性。普通读者基于经验的阅读和批评家基于训练的专业阅读之间是存在着识见和分析方面的差别的。一旦专业阅读进入文本,那么,文学阐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就建立起来了。第二,基于细读的文学阐释之所以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发现一般读者不曾发现的意义,是因为在这种阐释中理论发挥了积极意义。这里,理论与其说是某种概念体系,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或者,借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一种工具箱。视角不同,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同。视角的介入不是观念先行,不是强制阐释,而是阐释进入文本的先行理解,它本身就构成了阐释的一部分。人就是凭借经验积累、文化选择、知识传承所建立起来的(理论)视角进行文学阐释的。一定意义上说,是理论以及理论所特有的视角照亮了文本的意义。
阐释的有效性体现为视角和对象的高度契合。只有在蹩脚的阐释中,视角与文本才是分离的,观念才会成为一种宰制文本的力量。在有效的阐释中,视角是理解文学的先行筹划。伊格尔顿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理论——无论其如何不自觉其为理论或隐而不显——我们首先就不会知道‘文学作品’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阅读它。”视角有时是显豁的,有时是隐匿的,无论哪种视角,都会给解读文本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我们以艺术史家高居翰的中国绘画研究为例来略作说明。在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历史上,作为一个“他者”,海外学者高度重视视角的选择。尽管这些视角可能囿于西方文化的偏见,但客观地说,这种高度重视视角选择的文本研究是值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阐释特别重视的。高居翰对中国传统画论重视并依赖文献分析,研究了绘画之外的一切因素,却唯独没有研究绘画本身的倾向提出了质疑。因此,这种研究属于没有绘画的绘画研究。他提出绘画研究要以视觉为中心,高居翰努力做的工作就是要为读者提供一条“如何看画”的经验,力求把以“看”为中心的读画机制揭示出来,为读者培养一双“看画的眼睛”,为读者“打开头脑中的新的感知领域”。试想,如果没有以视觉为中心的强调,中国画论何以发现并超越自身的局限?视觉经验具有文化的意义,“视觉所见”绝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靠近和发现。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中认为,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看”方式的变化带来了世界意义上的变化。他举例说,文艺复兴早期发展起来的构成欧洲艺术特点的透视法将独一无二的眼睛强调为世界万象的中心,世间万物是观看者安排的。但是,照相机发明之后,透视法的矛盾逐渐显露:“我是一只眼睛,一只机械的眼睛。我——这部机器——用我观察世界的特有方式,把世界显示给你看。从今以后,我永远地从人类凝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在不断地运动。我凑近各种物体,然后拉开彼此的距离。我钻在它们底下爬行。我同奔马的嘴巴并驾齐驱。我与人们同沉浮共升降。这就是我,一部机器,在混乱的运动中调遣部署,在最复杂的组合中记录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照相机带来了观看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你见到什么,取决于你在何时何地。”借助于照相机,我们眼中的事物逐渐有了新的含义。所以,在印象派画家那里,可见物在不断流动的变化之中成了难以捉摸的东西,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眼睛原来的对象。约翰·伯格这里虽然是就图像生产机制而言的,实际也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被人看见的,看是选择、看是发现、看是视为。一句话,看是主动性行为。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对文本的阐释行为。阐释不是被动的,阐释是主动的。阐释的效果如何,取决于阐释者所处的历史境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阐释者以何等方式打开(看)文本。
在阐释中通向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这是文学理论发展至今的一种强烈的呼声。这里的阐释包含多重意涵:首先,文学理论知识生成机制的动力源来自文学的召唤,是文学存在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性质,引发阐释者何以如此的惊讶与追问。文学理论的合法性、有效性、公正性、权威性都不是依靠对自身的辩护而获得的,而是经由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检验而实现的。在阐释中通向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意味着它的逻辑起点是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而不是哲学、社会学或其他相关学科。文学经验、文学事实、文学实践对于文学的哲学阐释、社会学阐释、心理学阐释、语言学阐释、人类学阐释等具有优先性、本体性和渗透性。而对文学的哲学阐释、社会学阐释、心理学阐释、语言学阐释以及人类学阐释之所以也可以构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路径,重要原因在于这些理论经过了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的检验,且表现出溢出经验、常识的“理论”优越性。其次,在阐释中通向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意味着一种文学精神的确立。在相互包容、理解基础上产生的对话、论争是文学阐释别具个性的精神气质,倾听永远比单方面输出、独白更为重要。最后,阐释也是文学存在的方式,阐释之于文学既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方法论旨在强调文学理论的知识生成来源于文学经验、文学事实和文学实践,只要阐释的方法适合于文学。阐释,就是根据现象存在的理由理解现象,这与从作品中抽绎出思想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作为本体论,阐释就是文学存在的方式。在阐释中理解,在理解中阐释。如此循环往复,无有终结。人在“认识”文学之前,早就与文学融为一体了。人所能认识的,正是人与文学融为一体的世界。阐释,意味着文学存在着、活动着、生成着,意味着人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彼此渗透、融合和相互生成。
以理解为核心、为目标、为视域的文学阐释学,是通向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途径。首先,文学阐释不是《圣经》阐释,不是典籍阐释,不是理论文本阐释。文学阐释意味着对于阐释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双重体悟和认同,由文学阐释可以引发一系列不同于一般阐释学的核心命题、范畴、概念,这些命题、范畴、概念是我们言说文学的理论工具。从文学阐释中提炼的命题、范畴、概念具有走进文学文本的理论优先性,对这些命题、范畴、概念的娴熟掌握和运用,是丰富文学理论和批评知识工具的重要方式。其次,文学阐释学意味着细读和形式分析的批评方式仍然有效,细读和形式分析仍然是意义建构的基础性工作或环节,所谓反讽、肌质、张力、陌生化等,不仅作为封闭阅读的工具活跃在文本分析之中,同时也是通向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手段。伊格尔顿认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都从事细致认真的细读。”细读,不只是细读,还是形式意义的发现者;而形式,也不只是形式,还是历史的达成。以细读和形式分析为抓手,一方面,文学源源不断地为阐释提供素材、灵感和言说的概念工具;另一方面,阐释也反哺文学,文学因阐释而变得丰富起来。以文本为纽带,阐释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共同实现意义世界的敞开。当然,文学阐释不能止于审美解读和文学性体悟,还应该向广袤的人类精神世界进发,发现在语言敏感性基础上的社会、历史、文化讯息,从审美解读、文学性体悟走向文化诗学、社会历史批评以及意识形态分析,从而实现对理性主义识见无法抵达之域的洞察、捕捉和呈现。
在阐释中生成的文学理论知识是否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阐释呢?这里涉及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起点问题。我们当然反对那种把文学理论知识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反对从一个思辨的本质、规律出发去推演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反对以一种立法者的心态进行文学理论的言说,抵制文学理论言说当中唯一正确性的图谋。事实上,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反思,这类体现理性虚妄的文学理论知识大厦早已经轰然倒塌。但是,在如何重建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上,目前学术界还有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的文学理论应该是一种走向阐释学的文学理论。走向阐释学的文学理论意味着理论除了对“基本问题”感兴趣外,更关注“具体问题”。基本问题指那些本质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基本问题源于某种理论预设,其论证逻辑是从理论到理论。作为前提的理论,一般是自明的,论证也是像断语式的。而具体问题是研究对象本身呈现出来的问题,存在于研究对象各种构成的因素关系之中。具体问题的呈现是剥茧抽丝式的、条分缕析式的,使结论渐渐明朗起来。这里,走向阐释学的文学理论实际是针对过去理论的独断性质而产生的一种建构设想。笔者虽然理解论者的初衷,但在具体概念的理解上却不尽相同。“基本问题”是否就是那些本质性的、自明性的、断语式的问题?这还有讨论的空间。笔者以为,“基本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构成文学理论知识根据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得以建构的本源性问题。讨论基本问题并不必然走向本质化的道路,并不必然以揭示本质和规律为目标。基本问题也可以是具体问题。我们需要在追问基本问题的同时保持一种与当下文学语境和走势相呼应的状态,而在解释具体文学现象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回到基本问题。这样,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就像是一个不断上路又不断回归的过程。上路,即向着新的文学问题保持敞开姿态;回归,即回到基本问题。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魅力即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因此,取消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是有缺陷的,甚至是无根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理论,不如说是文学理论的一种功能。理论的价值和生命,来自对问题的阐释以及阐释的效力。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文学阐释学等同于文学理论。因为,阐释不过是理论的一种能力,一种介入文学问题的力量,最终是要走向文学理论的。阐释中的概念演绎、命题表达和工具使用,最终都会化成文学理论的知识和知识体系。经由阐释得来的文学理论知识是活的、有生命力的知识,但文学阐释学不是文学理论。
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文学理论的知识问题。文学理论提供的是关于文学的知识,但是这知识不是实然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一种关涉意义和价值的人文的知识。在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里,实然与应然之间、事实陈述与价值评价之间处于高度的契合状态。知识包含价值理想和价值评价,这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知识的特殊之处。其实,严格讲,文学作为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决定了它的理论高度的个人化、隐喻性和多质性的特征。正如石中英所言:“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人文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没有个体独特的生命遭遇和内心经验,人文学科的许多概念、命题都不过是僵硬的东西。唯其如此,我们强调人文学科习得弥足珍贵的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复制性,强调对独特个别的经验的珍视,也强调知识的可磋商性、对话性以及“间性”或“兼性”性质。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不会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终结,而是永远向着多种多样的体验和多种多样的回答开放。明乎此,我们就不会把维护确当性作为阐释的最高目标,而应该以理解之同情的姿态参与到文学阐释多声部的大合唱之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 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