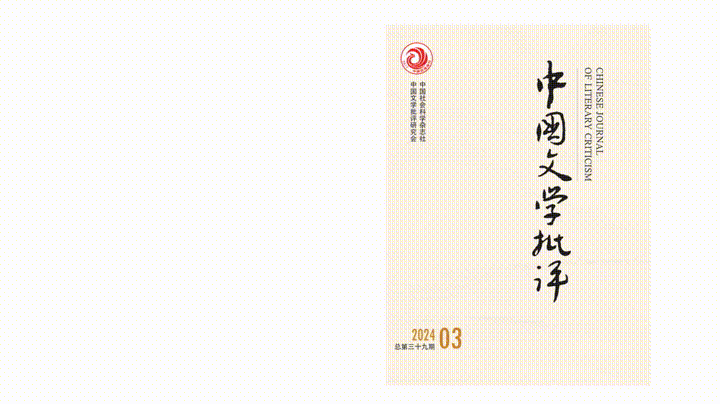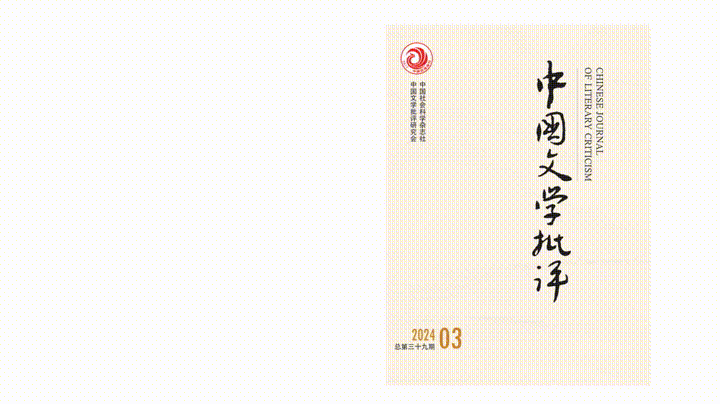
在中西美学和艺术领域中,艺术和美能否表达客观真理的问题始终是核心论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对“虚拟”“虚构”“想象”等问题的讨论,辨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由于《周易》和老庄哲学关于“虚”有过深入且系统的阐述,故而有众多重要的词汇、概念、思想与之相关。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和阴阳哲学的发达,使“虚”一开始就与“实”组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整体,古代艺术家和哲学家始终在“虚—实”并列的关系中讨论艺术和美学的基本问题。在西方,关于虚拟的讨论,由摹仿问题衍生而出。自柏拉图将诗和艺术看作一种“假话”(pseudos)之后,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诗(艺术)可以表现普遍真理的观点,自此形成西方美学关于艺术真理观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两翼。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现代美学关于“摹仿”“虚构”“想象”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人注意到,中国美学中以“虚”为核心所形成的话语词汇,可与前者形成比较和对话关系,遂将之纳入该体系,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建构,宗白华艺术意境论的建构,是这种努力的代表。
一、“虚”的中国语境:由神圣而达真实
在中国美学话语体系中,“虚拟”一词使用较少,一般用以指称无法考证、确定的事物,带有“推测”之意。例如,《红楼梦》第九十四回写贾府发配出二十四个女孩子,“那个不想。究竟那些人能够回家,未知着落,亦难虚拟”。现代艺术和美学领域中常使用的“虚拟”一词由现代学者对fiction等词汇的翻译所形成。中国古人也有词汇专门表达没有根据的想象和虚构的行为,即许慎所说的“乡壁虚造”,具有否定性内涵:“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根据许慎的文意,“乡壁虚造”是指有些人为迎合人们的好奇心理而毫无根据胡编乱造以夸耀世人的造字行为。“虚”在这里是指没有根据,用以修辞“造”的行为。“虚”亦可表示虚假之意,如“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等,但这层含义在中国古代不占主流,在《周易》和老庄哲学的影响下,“虚”具有更多正面意义。在古人著述中,“虚拟”一词偶有出现,但由“虚”和“拟”两个各具独立内涵的词语组成,这两个词是相互独立的话语概念,同时二者皆与摹仿紧密相关,须单独论述,方可呈现其全部内涵。
在中国美学和艺术领域,“虚”很少指向虚幻(虚假)层面,而更多是指一种更高的真实;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审美境界。作为思维方式,“虚”首先代表宇宙及其客观实在的本源性存在方式。由于“虚”带有对“实”的否定性倾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又将之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真实存在的想象活动联系在一起,用“神思”称之,这一点亦类似于西方现代美学中的“想象”。作为审美境界,“虚”不是指一无所有,而是通过对“有”的超越、舍弃,通达对万物本体的认识,带有本体论意义,而“拟”则是主体通过文化艺术创制、呈现前者的手段。支撑“虚”这一内涵的,是中国古老而特有的、充满辩证法意味的阴阳哲学,由此使与“虚”有关的问题变得极为复杂:“虚—实”“真—假”“有—无”“黑—白”等相反相成的思想观念或话语词汇,都含有以“虚”求“实”的倾向,这里的“实”不仅包括现实、真实,而且更多是指真理性、本体性内容,真实可感而无固定形制,或可变化为各种形制而存在,可用“真”来表达,古人常用“象”表达这种难以固定而复杂的状态。
正因如此,“虚”作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内在特征之一,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前人和今人已有很多研究,代表性成果和观点是宗白华和叶朗的论著。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及其批评在老庄哲学关于道与空、无关系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强调虚实相生的艺术特点和本体结构,可用“道”“舞”和“空白”界定之,其中“道”乃艺术之真境,而“舞”则是艺术最高的旋律、节奏、秩序,是宇宙创化过程的形象化、肉身化,宗白华用《庄子》“象罔得珠”神话说明“象”与“虚”之间的辩证关系:“‘象’是景象,‘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景象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景象与虚幻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中国艺术颇重虚实相生艺术特点的传统,这一特点的哲学基础是庄子提出的“虚室生白”“唯道集虚”等观念和命题:“中国诗词文章里都着重这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使诗境、词境里面有空间,有荡漾。……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宗白华指出,古人所谓“无字处皆其意也”(王船山)、“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正是中国人对“道”的体验,“‘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与宗白华的本体性阐释不同,叶朗十分重视从史的角度阐发“虚”对中国美学史和艺术批评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针对《老子》第五章提出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十六章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以及第十一章提出的“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器之用”“当其无,有室之用”,叶朗认为,老子关于“虚”的思想形成了中国艺术和美学中“虚实结合”的原则:“‘虚实结合’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一条重要的原则,概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的美学特点。这条原则认为,艺术形象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同时,老子的思想,与荀子提出的“虚壹而静”、韩非子提出的“思虑静则故德不去”等思想观念一起,形成了中国美学的“虚静”观,作为审美观照,“虚静”的实质是对宇宙本体和生命(“道”)的观照。叶朗指出,这一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意境论的形成影响巨大,因为“境”本身就是“象”和象外虚空的统一。
宗白华、叶朗关于中国艺术和美学精神中“虚”的本体性意义和价值的阐释影响深远,后来诸多成果都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需要说明的是,“虚”在老庄、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其含义固然已较为确定,但从语义发展角度看,一个字一般实指意义诞生在前而虚指意义在后,他们著作中的“虚”所指的可能并非其本义,用“虚”指称主体心胸、心理的纯净状态,还应有过渡环节。《老子》第十六章讨论的万物虚空部分的“无之以为用”,应是“虚”的实指意义向虚指意义发展的中间环节之一。换言之,“虚”所指的事物存在的空无状态、主体精神的虚静状态,可能有更古老的来源。
根据《说文解字》等字书的解释,可以知道,“虚”本义为“丘”,即自然形成的高山,在中国文化中,这座高山在某一时期专指昆仑山,故昆仑山又称“昆仑虚”“昆仑丘”等。故可推测,“虚”所指的虚空等义项,可能源于较为古老的以昆仑信仰为基础的圣山崇拜:昆仑山高耸入云,不可究竟,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从而使其含义产生由实到虚的转换。《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从丘虍声。”《说文解字》释“丘”云:“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所谓“丘”,即自然形成的高山,“虚”则是高山中的高山,故古人称昆仑山为“昆仑虚”。需要说明的是,“四邑为丘”中的“丘”乃井田制的产物,表示土地之多,属于其本义的引申义。以昆仑虚为代表的圣山崇拜,是早期中国文明、文化、思想的基石和集中体现。在《山海经》的记述中,昆仑山是“帝之下都”,也是众神的居所,高耸入云,无法探测其高度,下面有弱水环绕,又有各种神奇怪物把守,凡人、恶人无法接近。据袁珂统计,《山海经》提到“昆仑”“昆仑虚”“昆仑之虚”“昆仑之丘”凡18处。对昆仑丘记述最详细的,是《西山经》:“(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除了各种神奇畏兽,昆仑丘下有四水分流,分别为河水、赤水、洋水和黑水。《海内西经》记“昆仑之虚”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正是以此类神话记述为基础,人们对高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崇拜与想象。同样,与“虚”诞生于圣山崇拜类似,“太极”(“道”)观念亦与之密切相关。“太极”原为“太亟”,“太极”之“极”非为《说文解字》所谓“驴上负也”,其本字为“亟”。在甲骨文中,“亟”为,像人立于天地之间,人的头顶(天)和脚下(地)即为两“亟”,由此引申出最古老的起源或本源之义,形成“太亟”一词。人头顶最高的是天,天有多高多远不可测量,古人便以高耸入云、不可究竟的高山表征之,以说明天之高乃两极之一;人立于大地之上,大地离自己最近最亲,可成为另一极。因此,“太极”的概念或观念与久远的圣山崇拜、大地崇拜有关。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各大名山大川都是想像中神仙的住处和凡人隐化的最好去处。……山高云深,外人无法寻找,正是隐化者理想的栖身场所。山的巍峨挺拔、高耸入云、白云缭绕、神秘莫测,给人以升仙的丰富联想。山高,最接近天,站在山顶上,离天就不远了。而天,就是天堂,就是想像中美妙的神仙世界,是求仙者梦寐以求的地方。”这种以想象建构而成的“虚境”就是仙境,也是理想化的、美好的存在。
因此,以“虚”为基础的圣山崇拜,对中国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就直接影响看,昆仑崇拜催生了神仙崇拜以及众多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就潜在影响看,这种由自然之山而引发对虚无之境的想象与追求,更多转移为一种追求虚空之境的艺术理想。顾彬提出:“所有中国艺术可能都起源于宗教——祖庙就如同生殖细胞一般,因为从实质上看,舞蹈、歌曲、文字、卜问、升天等都是在这里同时出现的。但其世俗化进程也很早,最迟到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一些思想和其他创作中的直接相关的宗教成分被祛除。接近‘太极’不再需要通过直接的洞‘观’或宗教仪式,也就是说,不再是在自然界或宗庙里,而是可以用一种反思的方式进行。艺术就是这方面最高尚、最主要的形式。”顾彬此论大体准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艺术源于宗教的形式是多样的,无论其场所在宗庙、山巅、圣地,其形式为舞蹈、歌曲、文字、卜问,其根本都为升天(仙)服务。同样,由于中国早期文明世俗化进程展开较早,自然界或宗庙作为艺术起源的基础被迅速祛除,转化为精神反思的方式,这致使以老庄为代表的“虚静”“心斋”“象罔”等思想得以产生。这也导致中国美学话语体系中“虚”“太极”等重要概念中的神圣崇拜思想被进一步过滤而成为单纯的哲学或美学概念。因此,“虚”来自古老而悠久的圣山崇拜,作为自然界实存的山,让人产生了无限向往,打开了人们的思维和想象空间,造成由“实”向“虚”的伸展;在神话思维转向艺术和审美思维之后,这种由实生虚、由虚生实的思维便成为中国艺术家创作的一种基本方式。这里有个例子正是此种情况的生动写照。顾彬曾在1993年看到过清代画家汪士慎一套题名为“空山一片影”的草图册页,然而根据这一题目观看画作,却给他带来一片茫然和困惑:“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画家为我们呈现的只是一株从左向右伸向空旷画面的梅花。我们看不到任何山或任何风景。因为不仅山为‘空’的,即在眼之外,而且景从字面来说,也只是一片‘影’,是其他更大的但却又未被细究讲明的(事物)所投射的轮廓。我将之称为积极正面的‘空’,因为它使得人的精神思想有了活跃空间。”顾彬的疑惑正验证了“虚”在中国艺术和美学中的重要作用:汪士慎虽在题名中标出了“山”的重要性,但同时使用了“空”字,而且他还进一步告诉观者,你所看到的是“空山”之“影”。这个简短标题蕴含着双重“虚”的内涵指涉:那株从左向右在空旷画面中呈现的梅花的“实”,正向人们说明了“山”“影”之“虚”,也说明“山”不“空”、“影”不“虚”——正是梅花的存在,使山无处不在,山之媚影愈加摇曳生姿。顾彬说这正是中国艺术和美学中的“积极正面的‘空’”,这“积极正面的‘空’”也正是“积极正面的‘虚’”。汪士慎的创造和顾彬的欣赏实践凸显了中国艺术和美学中虚实转化的奥秘。
综上可见,中国美学和艺术偏重“虚实相生”,除阴阳哲学之奠基外,可能还有更古老的宗教基础。根据“虚”字之本义推测,“虚”与“实”的辩证关系、由“实”向“虚”的转化进而过渡到主体精神空间的观念,可能来自更为古老而久远的圣山崇拜。在神圣宗教信仰的支撑下,“虚”不是虚幻、虚假的存在,而是充满神性的真实空间,这是中国艺术由“实”入“虚”、借“虚境”表达生命真实的根本所在。宗白华等关于“虚”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本体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分析,奠定了现代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美学中的“虚”不是单独存在的概念或观念,它始终与“无”“实”“有”“象”等话语词汇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美学和艺术偏重虚实转化的特点,中国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体验与感悟往往借“虚境”以表出。
二、“拟”而不虚:以“准拟观”为基础的艺术创作
如前所述,与西方历史悠久的虚拟传统不同,在中国语境中,“虚拟”由“虚”和“拟”两个词组成。这两个词语指称的内容有较大区别。《说文解字》:“拟,度也。从手疑声。”而“度”,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法制也”。在《周易》哲学的系列语汇中,“拟”(“擬”)实际上是指伏羲创制易象的行动,即“拟诸其形容”和“象其物宜”两个阶段。所谓“拟诸其形容”,是指伏羲所绘制的易象是对天地万物“形容”的摹拟,其本质是“象其物宜”,即易象不仅是对万物“形容”的摹拟,而且它所摹拟的是万物“形容”背后的“宜”(“天下之赜”),即万物存在运行的根本法则。与此相关,“拟”往往与“准”和“议”两字同时使用,形成“准拟”和“拟议”两个词语。这两个词语所指称的均是《周易》易象体系及其功用,故而人们也常用“拟象”称之。《周易》易象学语境中的“拟象”观与西方现代美学中的“拟像”(simulacrum)理论有可供比较之处。
所谓“准拟”,即准确之摹拟,是圣人摹拟、表现天地万物之真理的方式之一。圣人作易“以与天地准”,“准”谓“准拟”之义。孔颖达疏云:“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谓准拟天地,则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是也。”在此语境中,“拟”不是中西语境中带否定意义的虚构或虚拟,而是一种通过摹拟与万物之理、宇宙之道相契合的行为,其结果是人类各种文化制度,艺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易象可以实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功能。由于“拟”可准确呈现宇宙之道并与“法”或“法度”紧密相关,这进一步形成了“拟”与“法”相互借用的情况:与“拟”一样,“法”不仅有法则、法度之意,而且它也可表示学习、借鉴、摹拟之意。古代艺术家在题跋自己作品时常用“拟元人笔意”之类标题,其中“拟”不仅仅指摹拟古人之作这一层含义,它更多是指通过对古人作品的摹拟以实现对古人意趣和宇宙精神的再次传达,从而打破悠久时空的限制而使之在当下复活,艺术家的创作可达到“拟议神明”的境界。这使“拟”具备了颇为丰厚的神圣性、生产性和创造性特征。《毛诗序》指出,诗(颂)可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王微《叙画》亦云:“披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神明”更多是指隐藏在自然造化中的最高的隐秘存在,画家可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之,以与自然造化相呼应,人们常用“焕然神明”指称这种境界。批评家还从技法角度指出,师法古人可称为“拟议神明”,认为能够领悟古人技法之精髓才能超越古人,形成自己的面目。这与歌德认为通过虚拟而形成个人风格的观点截然不同。恽寿平认为,今人学画应先从古人笔法入手,但是摹仿古人笔法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要揣摩古人之用心,无技法处才是古人用心处,领悟这层含义才能学到古人的精髓,形成自己的特点:“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技矣。”因此,真正的绘画创作既要师法古人技法,又要超越技法的限制,领悟古人技法背后的宇宙精神,做到“拟议神明,通于造化”,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由于“准拟观”的存在,中国艺术家认为摹拟之作亦是新的创作,是通过摹拟行为建立新作与旧作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其本身属于创造行为,旧作对于新作来说只是提供灵感、素材、技法等创造所需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件先前的作品促进、刺激了另一件新作的产生,因此“拟”是一种新的生产行为,具有创造性。这种以“拟”为重要手段和工具的艺术创造,成为古人与今人、主体与自然和谐共振、息息相通的中介。清初“四王”中的王翚在82岁高龄时,以宋神宗驸马都尉王诜的《采菱图》为蓝本创作了一幅同名作品并在画上题跋:“观王驸马真迹,笔法严重,全是摹仿唐人,设色古淡,不以秾丽为工,山麓小树,水面菱叶,点缀疏密,一一入妙,真墨苑之奇珍也。又见白石翁抚本,绝不露本家笔,皴法精简,用重色极清润,深见古人临摹苦心,所谓绚烂之极,仍归自然。”根据王翚的题跋,可以看出,后人摹拟之作与原作之间不存在精神上的对立,在摹拟创作的基础上,古人与今人之间反而形成一种脉络清晰、精神与共的发展线索;换言之,古人和今人的作品本身就处于一个整体之中。而在王原祁的论述中,“拟”不仅使古人与今人气韵相通,而且今人对古人作品的摹拟、学习,要摆脱形迹、技法的束缚,有意无意之间“与古人气运相为合撰”。王原祁指出,对于古人用心处,今人不能过于“用心”而导致“误用”其心,这样一来古人与今人之间就无法形成“合撰”。换言之,古人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自我与自然融通的范例,而今人通过摹拟亦可实现,这种实现不仅复活了古人与自然之精神,而且使之具有当代性和当下性,成为一种“典范”而存在,其绘制之方法也成为“法”而值得后人效法、摹拟。这是一种通过摹拟而重造经典的过程,所以包华石说,摹仿“不是中国人顺从心态的表现,而是树立经典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传统中,摹仿之作不仅不是“仿本”或“赝品”,反而因为后人对古人精神的传承和重新创造而不断塑造了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从而使艺术史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有机整体而存在。
因此,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区分真实与虚拟是没有意义的,古代艺术家也无意进行这种区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转化关系消解了二者可能存在的对立,宇宙万物得以存在的最后根据“道”“太极”或“一”才是最终的实在。苏轼的艺术批评是将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融合最好的例子,在他看来,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艺术创作,二者本质是一致的:艺术形象或境界看起来变化万端,但最终呈现的都是“一”或“妙理”“法度”,艺术家只要不执着于物就能与“万物交”,他的创作就能与万物自然相合。他曾以李龙眠创作《山庄图》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
苏轼又以吴道子所作华严佛像为例论证李龙眠作画的根本遵循:吴道子作佛像,虽“以意造”却能“与佛合”,更何况李龙眠是亲眼所见山水人物然后作画,自然更能与造化丝毫不爽。苏轼认为,吴道子画人物,无论技法如何变化,但均能“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题孔宗翰所观南康城各种景致而作《八境图》中,苏轼指出,所谓“八境”本为一境,之所以会有“八境”的区别乃是观者“自观”所造成,自然寒暑朝夕的变化,自我坐行息怒的变化,“接于吾目而感于吾心者,有不可胜数者矣,岂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则四海之外,诙诡谲怪,《禹贡》之所书,邹衍之所谈,相如之所赋,虽至千万未有不一者也”。“一”即“太极”,即“妙理”与“法度”,它的存在使真实与摹拟、虚幻的区分失去了意义:如果仅在是否实有方面区分真假,显然是囿于表象的看法,中国艺术家从来不拘泥于形象之真假而致力于寻求最好的方式以实现对“一”或“妙理”“法度”的呈现,从而在形上层面保证了艺术的真实性和真理性。
总之,除极少数日常用语外,“虚”在中国美学语境中不仅没有虚假之意,而且还为更高更真实的真理提供居所;与此相同,“拟”虽有柏拉图意义上的“摹仿”之义,但其结果不仅不产生包含虚假意义的幻象,而且还与客观真理同质同构。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以《周易》易象观为基础的同时性哲学。就艺术创作而言,创作活动及其结果只是这个不断循环的整体性结构中的构成环节之一,这个环节内部所包含的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及其结果,同样构成这一环节中的一个子环节。这样一来,艺术与审美想象虽然也以摹仿、虚拟、想象等方式展开,但其结果同样包含了艺术家和审美主体对客观真理的体验和认识。
三、“虚拟”在西方:“摹仿”的衍生问题
在西方,人们对虚拟问题(包括艺术幻象、想象、虚构等)的讨论,是伴随着对摹仿(mimesis)问题的讨论而出现的。摹仿与虚构关系的复杂性来自摹仿本身所涉及的众多因素,这引起无数理论家从各种角度展开讨论,同时也产生了无尽的争论,以至于理查德·沃什不得不将问题的解决方案回归到摹仿之上,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虚拟问题与摹仿的亲缘关系:“尽管从逻辑和相关性角度看,语言修辞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解释虚拟与我们理解的生活之关系时,它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摹仿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在表达这种关系方面,其效用是有限的。但是,摹仿概念被证明已被人们持久地使用,这说明它对于解决虚拟的实用性可提供一些帮助。如果抛开其他因素,那么摹仿就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来理解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把密匙。”虚拟问题是摹仿问题的衍生物,直到康德美学才在正面意义上确立其合法地位。关于现实生活与虚拟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论注定没有唯一结果,而摹仿则是将问题化繁为简的捷径。我们仍需回到问题的最初起源。
关于这一问题,影响最大的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关于摹仿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此后讨论中始终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即使就柏拉图本人的思想来说,也存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朱光潜指出,柏拉图“对艺术和美就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艺术只能摹仿幻相,见不到真理(理式),另一种看法是美的境界是理式世界中的最高境界,真正的诗人可以见到最高的真理,而这最高的真理也就是美。”柏拉图用“理式”(eidos)改造了流传已久的摹仿论,在关于艺术与最高真理之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等命题和思想,虚拟问题由此与摹仿、艺术和真理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这一矛盾思想中的后者,一方面建立了艺术虚构与普遍真理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柏拉图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性。在漫长的中世纪,虚拟问题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天堂、地狱、天使、魔鬼等,不仅不是虚构的,而且是真实的,诞生于柏拉图摹仿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层级式的摹仿关系,被衍生到关于天堂、人间与地狱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在宗教强大力量的压制下,这种固定而无法改变的摹仿关系被进一步强化、凝固化。直到文艺复兴和狂飙突进运动时期,这种关系才开始出现松动,虚拟问题的正向价值开始提升。在康德美学中,他对想象和虚拟问题的讨论,也是结合摹仿问题而展开的。康德美学以后,摹仿与虚拟则渐行渐远:在康德天才观和艺术独创性观点的影响下,此前漫长历史时期中若隐若现的对摹仿的否定性观点逐渐清晰化、凝固化,艺术创造与摹仿彻底被对立起来,这样一来,摹仿与想象、虚拟的关系便也变得对立起来,成为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在这过程中,有三个关键人物或节点须特别关注。
首先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对柏拉图观点的修正。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性修正一样,后世理论家基本上也是在批评柏拉图观点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虚拟问题的看法。此后不久,普鲁塔克将出现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假话”(pseudos)阐述为一种良性的虚构概念,故事的发明和创造对于诗歌来讲至关重要:“在一幅图画当中,鲜明的色彩使得作品更为生动,创造出一种幻觉,比起素描的线条更能刺激人的感官。诗中的狂言妄语结合巧妙的词句更能醒目,让人获得更大的满足;那些在韵律和措辞方面享有盛名的作品,由于避开神话和传奇的题材,面临夸耀的意境就会感到自叹不如。”普鲁塔克为诗歌和绘画使用虚拟进行正名,指出它们使用虚拟所产生的逼真性可以引人入胜,使观者产生愉悦,而且在欣赏过程中,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虚拟所产生的真实只是依靠技法,如诗歌使用韵律和修辞、绘画使用色彩和线条,只要稍加注意便不会因此受到腐蚀:“诗艺对年轻人的心灵带来欢乐和滋补,除非在聆听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监督,否则会使他们的情绪不安而且误入歧途。”与柏拉图一样,普鲁塔克也承认虚拟会对人类心灵产生影响,但他并未对诗歌采取柏拉图式的审查模式,而希望人们能“自我审查”:人们应清楚地意识到诗歌的虚构性及其道德属性,不能无条件全部接受,也无需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建立强关联性,进而实现诗与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普鲁塔克观点的哲学基础仍是摹仿说。哈利维尔指出,摹仿艺术始终会涉及观众的评价问题,无论诗歌是如何虚构或想象的,诗歌读者对艺术世界的反应都是真实的,这会反作用于他们对现实世界真善美标准的评定,摹仿植根于对不同生活形式的想象和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伦理学问题。朗吉努斯也指出,一切伟大崇高的作品均与自然本身的伟大相通,摹仿可以实现人类思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创造性接触,所以他用摹仿的方式来定义想象:“当你在灵感和热情感发之下仿佛目睹你所描述的事物,而且使它呈现在听众的眼前。”在朗吉努斯看来,是诗人的灵感与情感保证了虚拟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使对象得以逼真呈现。
其次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重新阐释,关于艺术真理性和逼真性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人们对虚拟与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虚拟、想象或幻想被提升到很高地位。弗拉卡斯特罗、帕特里奇等人带有对立性的观点,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更为系统的理论高度。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这些学者也是结合摹仿问题讨论诗人摹仿的独特性,即诗是对事物现实性、普遍性和最高理念的摹仿。克罗齐指出:“在17世纪的意大利,想象或幻想的用法也达到了顶峰。”这里所谓“顶峰”,是指长久以来受柏拉图观点摧残的虚拟和想象问题总算能够被人们客观地看待了。即使人们仍在真实与虚假的两极摇摆,但已有人指出,如果诗的虚构是虚假的,是一种谎言,自然的法则和神的法则也不会允许其存在,人们宣称:“一首诗的美只有和那个被描述的东西的种类相比才能被理解;它不是至上的、最高的美,而是那个种类的最高美。”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第31页。这是从类比角度将诗与它描述的对象之间的真实关系作为标准。此后不久,人们就毫无避讳地对诗的幻想和想象进行赞美:“诗寓言的唯一目的就是‘以想象或者说以富丽的、新奇的、可赞赏的、光辉的直觉来美化我们的知性。诗由于对人类有益处而为人类所接受;所以,人类要以高于任何职业的光荣来酬劳诗人,要以比保护任何其他科学更精心地保护诗人的作品,以使其免遭几百年以来遇到的凌辱,并以神祇的意见来加冕诗人的名字。’”到维柯时代,他对诗与哲学、历史,对知性与幻想的讨论,几乎完全抛开了摹仿,对柏拉图的观点进行彻底否定,进而将虚拟和想象作为诗的根本原则。克罗齐说维柯“反对所有以前的诗学理论”,就是指维柯为诗找到了新的根据。
到了狂飙突进时代,虚拟与想象问题已作为艺术和美学领域的核心论题之一而被深入讨论,形成了诸多系统性的思想,这其中,歌德关于摹仿(Nachahmung)、虚拟(Manier)与风格问题的观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歌德宣称,他“是怀着高尚和崇敬的感情”使用“虚拟”一词的。这一宣称实质上是对柏拉图贬抑虚拟和想象观点的回应。1788年歌德考察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所收藏的古希腊时期的大量艺术品,返回德国后创作了《对自然的简单摹仿,虚拟与风格》(“Einfache Nachahmung der Natur, Manier, Stil”)一文。该文于次年发表,是歌德晚年集中表达自己文艺观和美学观的重要文章之一。在文章中,歌德提出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三种方式,集中讨论了摹仿与虚拟的关系。
关于Manier一词是否应译为“虚拟”还需进一步明确。在三种描写方式中,“对自然的简单摹仿”(Einfache Nachahmung der Natur)和“风格”(Still)各家翻译基本一致,但对Manier的翻译差异较大。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译法有四种:其一,译为“式样”。1935年,宗白华将这篇文章译出并在《文学月刊》第5卷第1期上发表,篇名为“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将之译为“式样”。这一译法属于直译。其二,译为“特别作风”。朱光潜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将篇名译为“对自然的单纯摹仿,特别作风和风格”,其中“特别作风”的含义是指艺术家创作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由艺术家‘自出心裁地找到一种方式,创造一种语言,以便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把他所心领神会的东西表现出来’,由于偏重主观方面的作用,所以这种作风因人而异。”其三,译为“作风”。王元化将歌德这篇文章与维克纳格、柯勒律治、昆西等四人关于风格的四篇文章译出,以“文学风格论”为名出版,篇名译为“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这一译法与朱光潜较为类似。其四,译为“虚拟”。在中文版《歌德文集》第10卷,范大灿将篇名译为“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虚拟,独特风格”。可以看出,宗白华的译法更忠实于Manier的本义,他对文章篇名的翻译稍显僵硬且易引起误解。朱光潜和王元化则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而稍作变化,将Nachahmung译为“摹仿(模仿)”、将Manier译为“作风”,这一译法较符合西方哲学的摹仿传统和艺术语境,以及歌德文章上下文的语境。范大灿则根据文意将之译为“虚拟”,进一步明确了三种描写方式之间逐渐层深的关系。就文意看,歌德使用Manier一词意在强调作家、艺术家本人内心体验和情感的主观性,而且在歌德时代,关于摹仿与虚拟(想象)问题的讨论已成为一个新问题而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一翻译更符合歌德本义。
就摹仿与虚拟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歌德关于虚拟与摹仿关系的讨论,带有总结性意义。歌德晚年的意大利之行始于1786年,于1788年6月返回魏玛,本文即创作于这一时期。接近三年的游历历程,在歌德晚年的写作中首先被命名为“我的自传”,“意大利游记”是其副标题,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实际是歌德关于艺术创作的总结性思想和观点。学术界认为,这段游历过程和文章撰写,是歌德“通过对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的观赏来展现观赏者歌德自己在精神上的‘再生’过程”。所谓“再生”,即指歌德所表达的并不是意大利艺术本身而是他在这些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中体验到的自己。因此,歌德提出的三种创作方式,其根本在强调作家、艺术家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正是对重新找回自我的学理表达。所谓“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是指艺术家通过技法训练,严格根据自然尤其是静止的自然进行创作,其作品的逼真程度可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歌德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达到高度的完美”。可以看出,歌德对摹仿的看法已有较明显的贬义,这种态度在西方现代美学中逐渐成为主流。采用这种创作方法的人未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因而也无法表现自己的精神,故需要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即“虚拟”:艺术家“为自己臆造了一种方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语言,用以把自己用灵魂捕捉到的东西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赋予他们一再重复的某种对象一种特有的表征性的形式,当他们再重复这一对象时,就不再去管眼前的自然,甚至根本就不去想它”。根据文意可知,歌德所说的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虚拟”。歌德在同时期撰写的讨论拉奥孔雕像的文章中说:“艺术大师如能把他的美感注入到静止的和简单的对象中去,他也就表现出了他的美感的最大能量和最高价值,因为这种美感有助于各种不同性格的形成,能遏制和调节人的天性在艺术模仿中过激的爆发。”同样强调艺术家独特的美感体验对人类摹仿天性的抑制作用,使用“虚拟”可将“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提升到对事物普遍性的表现,而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就会使艺术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歌德最后对三者的关系总结道:“因此,简单的模仿仿佛是在进入独特风格的前厅。……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虚拟,那就会看到,根据这个词的最高和最纯正的意义,它是简单模仿和独特风格之间的一个中间体。”“虚拟”作为“中间体”,虽具主观性但可表现真实,是艺术家创作由摹仿自然通达自我风格的必经之路。
歌德的经历和观点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实践和批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在对摹仿与虚拟之关系问题上积累了丰富遗产。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批评家和学者们拥有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艺术创作的盛行促进人们对摹仿与虚拟问题的再思考。在此影响下,歌德从意大利旅行归来后撰写了这篇著名论文。比较有趣的是,与康德一样,歌德虽然对摹仿持贬抑态度,但仍认识到它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从而体现出摹仿传统的强大影响力,这也是十年后他在《雅典娜神殿入口》发刊词中反复强调艺术家应了解、掌握自然及其知识的原因。因此,歌德的观点可以看作西方美学关于摹仿与虚拟之间关系讨论的总结。
结语
综上可见,关于虚拟问题,中西古今均积累了大量资料,这一问题也始终是哲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核心论题之一。在中国,人们除了在日常用语中偶尔赋予“虚拟”以否定性意义,在哲学和艺术领域,无论是“虚”还是“拟”,均可通过摹拟而通达对真理的呈现和认识,这一点延续久远,几未变化,其内涵与后现代美学中的“拟像”(simulacrum)观可进行比较。在西方,艺术虚构是摹仿说的衍生问题之一,其与真理的正向关系,虽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被提出,但首先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柏拉图的观点,直到浪漫主义美学兴起后,虚拟才获得正面价值,康德、歌德等人的体系化著作使之固定下来,影响至今。当下时代,“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发达,各种VR产品被生产出来,极大影响了人们关于虚拟与真实关系的看法,人们的虚拟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西虚拟观的比较,可为我们深入、全面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