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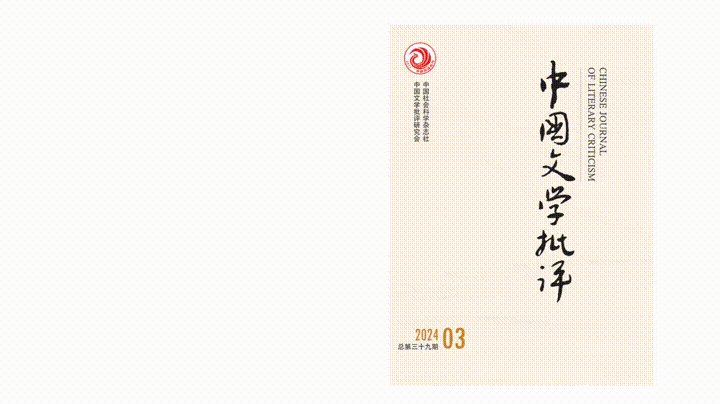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创作都是在写自己。写什么?身世终有写穷之时,而感悟是个每日新、日日新的变数,只要不闭目塞听,只要走出书房,感悟总会有的,怎么写也写不完。
所有人对客观的感悟皆为碎片呈现,作家当然不能例外,只不过作家的感悟会习惯性具象化,始于某种说不清的灵感。作家的感悟像云中落下的雨滴,像耳边掠过的软风,
小说可以讲心里话
众所周知,生活中有些话是不能讲的。季羡林先生曾感慨说人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讲不全。季先生的话里充满了儒家思想中对“度”的把握,的确,现实生活中一味地揭示真相,大概率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但真话憋在胸腔里不吐不快怎么办?小说便是一个不错的出口。小说给作家提供了一个讲心里话的载体,作家可以借助人物之口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而且只要处理得好,不会有人自讨没趣去对号入座。有人说小说能让人活出双倍的人生,这句话不无道理,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可以恢复做人的天性,能卸掉后天戴上的所有镣铐。
作家的心里话可以讲,但一定要讲得符合文学规律,喊口号、骂大街、撒泼耍横,那不是小说,用文字砌成的渠将感悟加以引流,润物无声感染读者,心语就成了悄悄话、入耳的话,效果自然会更好。应该说作家是幸运的,至少比其他从业者多了个讲心里话的出口,而有的职业就不然,只能唯唯诺诺地随帮唱影、鹦鹉学舌。既然作家有这样的便利,那就不要浪费了这个难得的条件,当自己没有心里话要讲的时候,可以替那些需要讲的读者去讲,这样,文学的大众性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读者也就有可能喜欢上你的作品。有的作家不讲自己的心里话,也不替别人去讲,喜欢在那里自顾自地讲不着边际的漂亮话、风凉话,讲一些自己都不信的假话,这是对作家心血和笔墨的浪费。
巴金先生说作家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说出了心里话,这是可信的。当时读过这篇小说的中年知识分子,无不感到小说中的陆文婷、傅家杰身上多少有些自己的影子,两个主人公说出了许多读者想说的话。作家在作品里是不是讲了心里话是瞒不住读者的,真与假不难鉴别,千万不要小看读者的鉴赏力。一部作品好不好,初始评价权也许在专家,但最终裁判权属于读者,属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提出,应该是充分考虑了这一本质因素。
既求真实,亦分雅俗
虚构是另一种真实
毋庸置疑,小说一定是虚构的艺术,每个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那么作家是否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杜撰故事呢?对于从事科幻、惊悚等小说创作的作家我不敢妄言,但就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家来说,他讲述的心里话一定是真实的影子。
虚构往往比真实更真实,这里说的真实含义不同,第一个真实是生活的真实,第二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是作家虚构故事的素材,而艺术的真实揭示的却是事物的本质。心里话无疑是作家的感悟,这些感悟需要形象地呈现,而如何虚构这个要呈现的故事则要看作家的本事。前文提到的作家谌容,她虚构了一个《减去十岁》的故事,把一干人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生活中肯定不会有哪个机关敢发一个让干部普遍减去十岁的文件,但这样一个需求却合乎特定时代的世情,契合很多人的心理,于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就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
那么如何来创造艺术的真实呢?这其实涉及底色、氛围、情绪等几个问题,底色是基础,氛围是底色的折射,而情绪是作家要传递给读者的效果。就像画家作画,材质用的是纸版、木版或瓷版,对画风影响很大。艺术真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小说的底色或者说调性,因为底色和调性决定着氛围,而氛围又影响着情绪,底色、氛围、情绪三者统一起来,艺术真实的“小周天”就打通了。有的故事在生活中是真实的,但并不符合艺术的真实,问题就出在这个“小周天”没有打通,结果有了生涩感、违和感。
抱怨是审美之敌
有人说心里话总是充满抱怨,好像有诉不完的苦和怨,这样的心里话可以理解,如同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被狼叼走的孩子,她特别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不幸,因为这不幸不能总是憋在心里。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倾听这种分享?尤其是当分享得不到任何思想上的启迪时,倾听就成了一种负担。正常生活中,没有谁愿意成为别人不良情绪的垃圾桶,人们读小说是为了审美和愉悦而读,如果读后郁闷压抑,对前景充满暗淡,那岂不是自讨苦吃。
不可否认,怨妇式的抱怨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佳作,但从整体上看,个例构不成普遍意义。写小说倾诉心语,倾诉的是独特的发现和思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文学美学特征,而文学美学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语言美,而抱怨无疑会冲淡语言上的美感,就像两人街头冲突骂大街,没有哪一方还会字斟句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