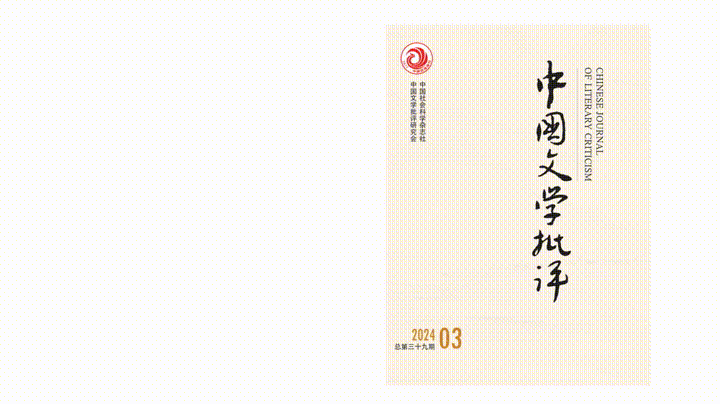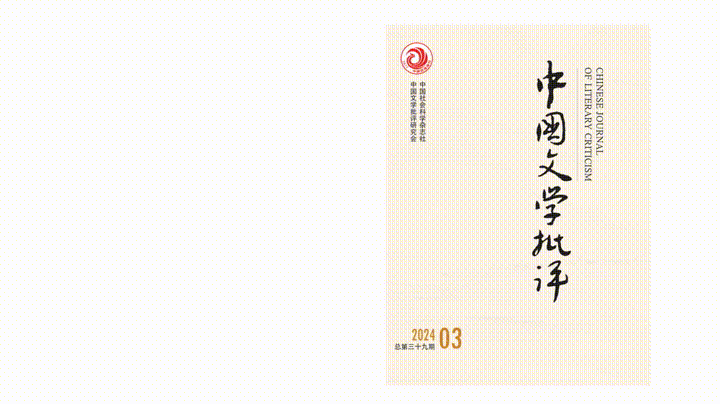
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宏大社会实践,是当下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伴随着这场覆盖中国大地的“山乡巨变”,诞生了《经山海》《金墟》《陌上》《莫道君行早》《海边春秋》《白洋淀上》等一批与时代同构,对国家决策和乡村振兴实践作出迅速反应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一些表述中被称为“主题创作”,也有人将其称之为“乡建小说”——以区别于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不管如何称呼、归类,这些作品鲜明的共性是,以“地方性”乡村为叙事对象,通过对若干个“独特的这一个”的乡村正在发生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系列事件进行场景式描绘,在重建乡村有机生活的整体性的同时正面回应“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进而实现从局部辐射整体,从乡村指认“中国”的意指。在历史延长线上,新时代乡土叙事赓续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理性意识,具有积极的创造历史的乐观主义精神。
作家老藤发表于2019年的长篇小说《战国红》也属于前述写作类型。小说叙写了辽西贫困山村柳城在驻村工作队带领下,大胆启用村里有锐气的年轻人,破除陋习,植树造林恢复生态,整治村容村貌,发展特色经济,摘掉贫困帽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故事。2024年,老藤出版反映乡村振兴实践的长篇小说《草木志》,故事背景搬到了黑龙江边陲,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美风光的村庄墟里因经济落后,面临被其他村合并的风险,村主任和驻村书记从村里“小环境”和村外“大环境”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共同发力,逐一化解村里的历史矛盾,发展乡村经济,保住了墟里。《草木志》与《战国红》可以视为姐妹篇,一方面,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东北,在主题创作的规定框架内展开新时代乡土叙事,无论是思想内蕴、价值取向,还是美学风格上,两者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进阶”的政策背景下,从《战国红》到《草木志》,呈现出服膺于创造历史的理性意识,完成既定意识形态诉求,到尊重乡土世界的复杂性,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生活、整体目标与地方经验之间建立有效勾连的认知迭代路径。这种认知路径的变化,反映在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与人物关系的设置,也反映在乡村的重构、乡村“风景”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何为乡村、如何巨变的思考。
一、“青年到何处去”
《草木志》在开篇第一章用形象生动的笔法描绘了城市机关单位中的几副面孔和日常工作中的几个场景。第一个是郑高,一个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人缘好,擅长讲段子的干部;第二个是老雷,和郑高相反,是一个深谙官场规则、沉默寡言,擅长写报告的“大笔杆子”;最后是“我”,也就是小说主人公,一个大学毕业进入机关工作时间不算长的年轻职员。三个人的组合,有点像传统小说中“刘关张”的三角结构,在墟里“起死回生”的过程中,“我”和郑高、老雷都积极出人出力,缺一不可;单拎出郑高和老雷,一动一静、一热一冷,又颇有“哼哈二将”的意味。在“我”从省城机关到墟里驻村的过程中,郑高和老雷是推动“我”的决定性力量。小说用一段对话交代了驻村的缘起:
参加工作第三年的夏日,老雷叼着电子烟来到我办公桌前对我说,组织部门有明确规定,干部提职必须有基层工作经历,没有的要补课,问我怎么想。我说听领导的,我什么时候补课都成,反正我单身,轻手利脚。老雷说你这样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这课非补不可,早补比晚补强。
老雷的这番建议促使“我”决定到墟里驻村。临走前,“我”和老雷又有一段对话:
我问:“去了之后我该做点什么呢?”
老雷沉吟片刻,然后用食指在电子烟上做着弹烟灰的动作说:“多做无形之事吧。”
……老雷又补充了一句:“比方说吧,见证者本身也是建设者,很多时候见证比建设重要,你就两年时间,多见证、多学习,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个不停。”
这两段对话既淋漓尽致地传递了老雷对下属真诚的关心与呵护,又不动声色地强化了老雷精明老练的形象。对于《草木志》这样一部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的主题创作,如此直白地处理驻村干部的动机“看上去”似乎并不是最佳选择,且不说老雷劝说“我”去驻村的理由似乎并非纯粹出于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愿望;之后老雷传授给“我”的工作方法建议也值得思考,“多做无形之事”“你就两年时间,多见证、多学习”的说辞似乎不够积极。这样的动机和态度貌似无法匹配乡村振兴实践的宏远意旨,更无法为小说主题的后续展开提供足够合理性,甚至早早地消解了主题的重大意义。换而言之,小说的主体内容是“我”参与墟里乡建的过程,第一章如果只是为了交代“我”驻村的缘起,完全可以几句话带过,并不用叙述得如此意味深长,不合常理。但是,当我们不只是在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场共时性地考察《草木志》的叙事意图与叙事效果之间的张力,而是把小说放置在当代历史和文学史的历时性语境中,便会对小说第一章的用意有更深广的理解。
回望文学史,1946年夏天,从东北松江省珠河县驶出一挂四轱辘马车,拉着工作队进了元茂屯,从此元茂屯翻天覆地(《暴风骤雨》);而在华北平原桑干河畔,一辆漂亮的胶皮大车扯出了暖水屯陈年老皇历,工作队的到来翻开了暖水屯历史新的一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史在这里转折,工作队的到来开启了乡村叙事的“创世纪”神话,在承载革命理想和历史冲动的乡村世界,“太阳”普照大地,一批农村青年和革命青年一起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成长,确立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在这种乡土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嫁接”中,革命理想的“大远景”拉近为当下生活的美好“特写”,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相互激荡中,建立了一种属于革命年代的明快的、积极的乡土叙事美学。青年人也成为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最具感召力、最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学“新人”形象。
来到“革命的第二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正如所有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革命的第二天”是另一场革命的开始。“革命的第二天”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提供了不同的现实场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现实场景之一。当狂飙突进的激情褪去,“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理想主义、朝气蓬勃的林震与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的工作环境之间的冲突是“革命的第二天”必然遭遇的历史难题。相比较批判官僚主义、特权意识的意图,小说更深刻的意义是对“青年到何处去”问题的敏感与警惕。二十多年后,王蒙在《〈冬雨〉后记》里再次重申了这一问题的核心意义:“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真诚、追求、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历史经验证明,“青年到何处去”既是革命“前夜”最活跃、突奔的动力,也是“革命的第二天”必须直面、重视的问题之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之所以引起重视,即在于林震所遭遇的个人精神危机,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刘世吾与林震互为镜像,林震是年轻时的刘世吾,刘世吾可能是未来的林震。作为“革命的第二天”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林震的迷茫和刘世吾的倦怠,是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症候意义的精神动向。虽然小说的尾声,林震坚定信念,要与不良风气持续作斗争,但在现实没有为无数个“林震”的理想和情怀提供有效的社会出口之前,林震的抗争只能是一厢情愿。
马烽创作于1958年的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革命的第二天”的现实场景之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烽在山西汾阳挂职县委副书记时经常到贾家庄体验生活,亲眼所见村里年轻人“百把镢头闹革命,治水改碱拔穷根”的生动场景,以贾家庄退伍军人、团支部书记吴士雄、青年木工技术革新能手宋连生和妇女主任赵玉芳等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影片故事发生在常年缺水干旱的山区农村孔家庄,村里的年轻人敢为人先、敢于挑战,大胆提出要凿通山洞、劈山引水,但是这项前无古人、造福于民的壮举在当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以高占武、孔淑贞为代表的年轻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在悬崖峭壁上打通了夹鼻山,让清澈甘甜的泉水流进了干渴多年的孔家庄。影片上映后,万人空巷,反响热烈。许多都市青年都热切盼望参加改变农村面貌的生动实践,更多的农村青年也立志将青春奉献给自己的家乡建设,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高占武突击队”“孔淑贞姐妹组”。
如果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提出了具有时代共性的“青年到何处去”问题,那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则提供了一种解决“到何处去”的可能方案与方向。同样是“年轻人”,“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和“村里”的年轻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力和精神状态。作为象征性空间,小说中“组织部”与“村里”所表征的并非是二元对立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判断;而是两套不同的机制运作系统,以及相应的秩序和规则。成熟、优越的“组织部”渐趋板结、僵化,在墨守成规、按部就班中丧失了吐故纳新、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发展、变革中的“村里”恰恰提供了容纳创造力、创新力的可能。《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为两个互文性文本,共同搭建起在社会整体结构与运作中思考、解决“青年到何处去”的流动视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和我一起,到中国的乡下去”,依稀可见国家层面对“青年到何处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性发展、区域资源配置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及至20世纪80年代,《人生》《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再次探讨青年发展的问题,依然没有脱离这种结构性的流动视野。
历史提供了重新辨析《草木志》叙事意图的更广阔的视野,也打开了解读“非常规”的第一章与后面主体章节之间复杂关联的空间。第一章除了塑造了郑高、老雷两个“老机关”的人物,也在虚虚实实、欲说还休的叙述中掀开了冰山一角。老雷“没有市县工作经历,但对市县的情况了如指掌,人不下去,调研报告却一篇篇像模像样地提交”。这种工作“本领”纵然也是一种个人能力的体现,但又何尝不是某种“机关病”的症状。那些细枝末节中隐约透露出的氛围,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的“组织部”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或进步,年轻的“我”又何尝不是那个走进组织部的林震。留给“我”的选择,或者加入“内卷”的赛道;或者主动“躺平”,自我边缘化;或者去驻村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中成长,在时代的主旋律中确认自我的位置,成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草木志》通过只有十一页的第一章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两个文本合二为一,连接贯通起来,在当代化与历史化的双重语境中把“青年到何处去”和社会区域结构性问题统筹处理。故此,从《战国红》到《草木志》,驻村书记人选的变化——陈放是即将退休的机关干部,“我”是事业刚起步的机关职员,折射的是作者对乡村振兴社会实践认知上的变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实践,之于《战国红》的陈放,意味着个人职业生涯的完美谢幕;之于《草木志》的“我”,是探索普遍性社会问题“青年到何处去”的破解之道;之于国家,是在局部出现“板结”“固化”“内卷”趋势的机制中重新激发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调整中探索发展之路。
“青年到何处去”的现实路径疏通之后,《草木志》的叙事焦点推向青年的思想层面,即像“我”一样的青年来到农村后如何丢掉靠政治“镀金”的思想,脚踏实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淬炼成钢。历史经验再次出场,金子逆时代而行的选择向“我”昭示了一种在历史风潮中遵从内心和自我意志的生命历程。于是,“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完成了从功利到非功利的精神蜕变,克服了“多做无形之事”的惯性,坚定“做一个建设者”,在“有形之事”中成长为与时代主潮“共名”的新人。通过“我”的精神成长,小说在“大我”与“小我”、乡村振兴国策与“青年到何处去”历史命题等多个层面完成了交互叙事。因此,在主题创作的“外壳”下,《草木志》既是一部成长小说,塑造了兼具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青年新人;也是一部问题小说,在看似简单的“驻村”事件中融入了对青年问题、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深度思考。
二、乡村“风景”的发现与再造
毋庸置疑,文学中的“风景”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在时间中形成的社会历史性产物。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对风景的现代“装置论”阐释广为接受,“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构起一种稳定的、貌似自然的关系。文学叙事中无论以多么自然、多么客观、多么中立出现的“风景”描绘,实际上都是与作者、与“看风景的人”的认知方式密切相关的,是经过了认知滤镜层层透视的风景。文学地理学研究进而把这种主客体间的投射关系放大到一个地域甚至整个世界。如著名文学地理学学者米歇尔·柯罗所言:“世界总是从一个主体的角度被看、被阅读、被体验和被写作,而这个主体只能存在于和世界的关联性之中:‘地理’(géo)必以‘自我’(égo)为前提,反之亦然。文学地理学从某种角度说,仍然是一部‘自我的地理学’……它(景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想象空间,因为它毕竟是基于一种主观上对真实世界的敏感体验。”自然属性的风景或景观在不同的“装置”中,呈现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重面貌。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而言,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现代性”这个巨型认知装置,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行”置于其中所带来的情感结构与复杂经验。在“现代性”认知装置中,传统文学中的常见之物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被彻底颠覆。新文学之初,古典文学中朴素恬淡、怡然自乐的田园诗文转向基调阴暗、沉重的乡土文学,“乡土生活作为一个景观是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一次带入表现领域的”,随即被放置于“他者”“被看”的视域中。当“现代性”的时光机褪去了京派文学审美滤镜下乡土生活的诗性光晕,黯淡了革命美学赋予乡土的明亮色调,20世纪80年代已降的乡土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扩张挤压下,日益走向空心化、边缘化,“传统的乡村氛围不复存在”,乡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无法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承担绝对的“动力源”的角色。社会空间结构的转移,直接影响到文学表达的焦点,“当下小说创作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追踪性的文学‘报道’。这一趋向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21世纪后,作为“风景”的传统乡村和传统乡村的“风景”一道,在《秦腔》《后上塘书》《望春风》等文学作品中经历了“象征性死亡”,隐隐地伫立在时代的落日余晖下。因此,大规模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社会实践,既是对乡村现实困境的破解与回应,“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也是在总体性上重塑作为“风景”的乡村和乡村的“风景”,其中也包含着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等治理理念上的调整。在很多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小说中,作为“风景”的乡村和乡村的“风景”也成为叙事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视野中的乡村“风景”不会、也不可能会倒退回传统农耕文明的原始、古典、静穆,也不是田园牧歌、桃花源式的纯粹精神审美对象。
老藤在创作谈中曾说:“一个作家在写人有了审美疲劳之后,可以把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这样会给其创作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门。”“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是作者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从对“人为万物之灵”的过度尊崇到万物生灵、众生有道的平视。在另外一篇创作谈中,老藤曾描述过一幅散发着古典美学意味的乡村“风景画”:
我一直认为炊烟是人间烟火的标志,袅袅炊烟是乡村生活的旋律。炊烟的味道令人沉醉,当你站在高坡上,看着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炊烟时,你会感到生活的真实和温暖。当年,黄昏里我扛着鱼竿从讷谟尔河畔回村,看到的就是一缕缕炊烟。尤其无风的傍晚,远远看着条条炊烟笔直上升,缓缓融化在晚霞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油画。
……
我来自农村,炊烟是脑际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这愁绪会像纤细的电炉丝,遇有机缘,就会充电发热变红,带来寻根的温暖。
这种对乡村的深厚情感眷恋与万物生灵、众生有道的文学观在《草木志》中叠加、发酵为对乡村“风景”的多重想象与塑造。《草木志》所塑造的乡村“风景”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是小说中对北方乡村自然植物世界的翔实而细腻的书写,塑造了一个生机盎然、葱郁丰茂、有机共生的植物王国;第二层是基于墟里山川、江河、植被、地理、地貌开发的乡村景观,这些景观既美化了乡村风貌,又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物质依托;第三层是乡村振兴实践激发的饱满、向上的人的精神状态和行动力,构成了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的“风景”。自然风景—人造风景—人的风景,是新的总体性想象逐步重塑的表征,乡村“风景”重新发现与再造的渐次展开构建起新时代乡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空间关系,由此乡村世界全新的秩序及逻辑逐步建构起来。
《草木志》文体上一个醒目的特征是大量植物的出现。小说借鉴古典文学比兴的技法,以植物作为比兴的载体,章节篇目以植物命名,在对植物生物属性的描绘中开始每一章的叙述,每种植物的生物属性又对应着小说中一个人物的性格、行为方式,进而铺陈开小说环环相扣、互相观照的情节与人物。《诗经》《离骚》中都大量运用比兴技法,但又各有不同。《诗经》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客体,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的片段;《离骚》把物我、情景交融起来,使物具有象征的性质,情具有更具体的寄托指向,构成一种庞大完整的象征体系。《草木志》以植物譬喻人物的技法借鉴并融合了《诗经》《离骚》的技巧形式。单独篇章借鉴《诗经》,以植物起兴,联想到人物,如由牵牛花的花形姿态联想到郑高,由默默无闻的拉拉秧联想到会计石小东。小说中出现了三十四种主要植物,分别对应三十四个小说主要人物。把全书所有篇章归为一体,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离骚》式的草木象征体系,把植物世界与乡村世界、植物属性与人的品性完美地融于一体。
《草木志》中的植物构成一个自然世界,人物构成了一个乡村世界,一个村就像一个植物生态,不同的人就像不同的植物,各有各的脾气秉性,各有各的喜好。把村里的生态处理好了,就会像植物生态一样,多姿、繁茂、和谐。因此,小说中驳杂、多样、共生的植物,以及都柿滩三道湾、白桦林,既是对北方丰茂葳蕤的自然生态景观的写实,更是把当下文学叙事中正在逐渐消失的“风景”归还给乡村,虚实交错中恢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和谐共生的乡村景观。
《草木志》中另一种乡村“风景”,是墟里在开发改造过程中依托自然资源修造的景观,如“驿路·遇见”景观带、都柿桥、小龙山红松天然林自然保护区、小龙庙等。这些“风景”赋予乡村现代文明气息,让传统乡村享有现代化的便捷,共享现代经济的红利。这也是当下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着力推进的举措。如果说《草木志》对几十种自然植物的抒情描写是用审美的眼光重新发现了乡村自然之美,成为疗愈“城市病”的审美慰藉;那么对乡村资源的现代化开发,则是为乡村再造并增添了一道道优美的“风景”,在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激发、重塑乡村的内在活力。自然风景与人工景观的叠加,不仅是提供了一幅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充满自然生机与人文诗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图景,更是重新焕发了乡村的人文活力和烟火气,把萧条、凋敝、濒临“并村”的落后山村打造成慰藉乡愁的城市后花园。
《草木志》中最后一道风景是乡村人的“风景”。在墟里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历史遗留的家族仇恨得以弥合,留在村里的和走出村的墟里人都激发出建设家乡的实干热情,在乡村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墟里有了欢快的鼓乐之声,“鼓乐队让打蔫的方大珍又支棱了起来”;“沿江的三道湾上,木刻楞建筑正在崛起”;都柿桥建设筹集资金,世代积怨的方石两家“赞助了等额资金”。乡村开发建设的“勃勃生机也切实地体现为一种乡村公共性的重建”。《草木志》生动呈现了“在当下越来越原子化、空心化的中国农村,如何调动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整合村庄多方面的文化资源,发掘与激活农民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意愿”。
三、乡土·乡愁·乡建
黄子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当代中国文学主题曾做过这样的判断:“作家的总主题总是在一时代民族的总主题制约下展开的,这一点具有普遍意义。我认为‘五四’以来六十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它的总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每一个作家自己的总主题都是在这一时代的总主题制约下展开的。”不管当代文学现场如何“乱花渐欲迷人眼”,或隐或显地总浮现着一种国家想象、一套国家逻辑,执着地指向“向何处去”——不妨说前文所讨论的“青年到何处去”也是这个总主题下面的一个分章。而在所有的文学题材中,乡土小说所描绘的各种社会形态、审美旨趣又最能充分展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总主题所蕴含的所有的国家想象和国家逻辑。
乡土之于中国,不仅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结构,更在于其中寄寓着深远的政治理想和精神乌托邦。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承担了在“山乡巨变”中解释中国、理解中国的使命。而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始终是贯穿于百年乡土小说、也是百年现代文学的“惘惘的威胁”和诱惑。沿着现代化的指向和目标,乡土小说在文化视域和革命视域中分别展开现代国家想象。
在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有学者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力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因此,乡土在鲁迅、沈从文等“返乡者”文化批判的观照中,既氤氲漫漶为回不去的故乡,寄寓着化不开的乡愁,又在“挽歌”和“牧歌”的二重奏中内含着文化“涅槃”的期待。这种期待一直到革命力量的介入,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落实为改变自身的具体行动。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对乡土社会的想象和塑造平衡了“中国乡土文学中文化批判思想多,却少有对乡村的建设性思考”的“弱行动性”,在革命的逻辑中呈现出绝对的力量感和翻天覆地的行动力。随后的《创业史》《山乡巨变》在历史理性的介入下展开了新生现代国家的想象,乡土在革命视域中具有了建构性的面目。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一次大的转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文学对乡村振兴实践的表达赓续了革命文学与社会实践同步、同构的传统,历史运动和社会实践在文学叙事中“道成肉身”,获得赋形。文学叙事也因此具有了国家文化战略的意义,再次启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国家想象。
新时代乡土小说的难题,也是乡土社会遭遇的难题:在现代化、现代文明的福利与病症一目了然的背景下如何重建乡土社会的主体性,进而重建新时代的国家想象。于是,曾经被新文学“现代”话语所压抑的“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重新被认识、辨识,成为凝聚乡村共同体的文化共识,并由此展开政治与文化叠加的国家想象的逻辑。这种叙事策略近似20世纪80年代语境中寻根文学从民族历史文化出发构筑国家的宏伟叙事。因此,在老藤乡土小说中,地方性民风民俗、传统文化伦理得到充分呈现,乡土社会的“本土性”、复杂性得到尊重。任时间流逝,《熬鹰》《遣蛇》中的乡村世界自有一套岿然不动、默默运转的规则和秩序。老藤从不“用一种‘改造’过的先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书写农村和农民”,反而是“外来者”被乡村社会规则所改造,上至军队高官、心高气傲的挂职干部,下到落魄的“右派”、被开除的干部,都被一个村主任用最简单的道理“熬”得通透、释然(《熬鹰》)。
即便是主题性的观念和主旨也并非超越于乡土社会自身运作规则之上,而是在与乡村运行规则的有机融合中潜移默化为乡村社会“本土性”的一部分,进而发挥效用。《草木志》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沿着村主任哨花吹和驻村书记“我”的所见所知所行分头展开小说叙事,两个人一个主内,管村里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日常琐事、人情世故;一个对外,谋求乡村发展,振兴经济。两个人的角色分工、行为方式、工作思路,是乡村内部与外部、地方性与国家性的平衡与整合,也是新时代历史语境中对何以“乡村”、如何“振兴”、何谓“巨变”的书写策略。
村主任是老藤乡土小说中最接地气、最鲜活的独特存在,也是老藤为当代乡土小说贡献的重要人物形象。村主任穿梭于文本内外,穿针引线,盘活叙事,在故事内,他们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润滑剂”,是连通基层乡村与上级机关、外部世界的“天线”;故事外,他们是作家借以破解迷津、勘透乡村的“抓手”。《熬鹰》中的金兆天、《战国红》中的老村主任柳奎,等等,概莫能外。不妨说,村主任是独属于老藤的人物,是老藤深入乡村世界的眼睛和耳朵,代替作家行走在乡间四野,品山鉴水,阅尽人间觅归处。《草木志》中的村主任哨花吹延续了老藤既往塑造的村主任形象的共性,又增添了充满乡土气息的幽默、风趣、诙谐的一面。哨花吹是土生土长的墟里农民,能说会道,熟悉乡村生活的内里,深谙乡土伦理。哨花吹担任村主任后,在墟里经济发展上似乎没有什么作为,工作都是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沟沟坎坎的矛盾。但这一部分在小说中占据的篇幅并不比对挂职书记的叙述少,甚至更多,更鲜活,更接地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哨花吹处理墟里邻里纠纷、化解家族矛盾的方式不是一味采用法制化的现代管理方式,而是借鉴沿袭传统的礼制。哨花吹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表明传统乡土文化依然左右着乡村生活,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草木志》中的村主任哨花吹是小说塑造得最生动的人物,也是一个具有典型人物特质的乡村“能人”,既能在盘根错节的纠纷、争端、恩怨中条分缕析地拎出关键所在,又能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维系乡土社会稳定有序的运转。小说并非意图强化特定人物的重要性,而是借村主任“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特殊身份和贴近土地的近距离视角,剖析乡村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哨花吹提前化解了制约墟里发展的宗族矛盾,驻村书记“我”的文旅开发计划才得以推进实施。
如果说村主任是内生于乡村社会的“内视角”,那么驻村书记“我”则是一种与土地、与乡村拉开距离的“外视角”。“我”从省城来到墟里,不同于哨花吹与墟里融为一体的属性和立场,“我”,当然也是作者,把乡村视为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政治结构乃至全球化格局中的一环,思考乡土社会的命运。“我”带给墟里的是发展经济的方案,是重建乡村生态的观念,是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外视角的加入既在思想层面上把国家主义话语和主题创作的意旨落实为实际行动,在叙事层面上与内视角构成对话、补充,又开阔、丰富了作品的维度空间,从而架构起文本“有意味”的叙事形式。小说结尾,墟里的文旅开发项目成功落地,吸引了更多城市的人走进乡村,走进自然,不仅打通了城乡的边界,也打开了交流的通道,实现了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生态文明与科技文明联动发展的“山乡巨变”。
2022年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对乡村振兴实践进行同步书写。与此同时,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清溪村开展了一系列文学实践,建立遍布全村的二十多间农家书屋,建设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文学景观散布在田野村落。文学对乡村振兴实践的赋形已经超越了静态叙事的层面,更直接参与并“反哺”于乡村振兴实践,书屋、珍藏馆等文学景观作为文学的“活态化”样本,成为清溪村的文化地标。乡村成为文学叙事中的“风景”,文学也成为乡村中的“风景”。从《山乡巨变》的清溪村到新时代的清溪村,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乡村振兴与国家想象的多重互动落实为具体的生活实感,也构成了新时代文学独特的实践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