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品的可读性由自身品质同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所形成,是其政治与美学功能实现的基础,在当代媒介融合的语境中变得尤为重要。老藤《北爱》《铜行里》《草木志》等长篇小说是探讨小说可读性问题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切入口,通过对其作品在娱乐性、知识性和观念创造性上实践途径的总结,进而也对“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的区分进行重新辨析与思考:可读性自然蕴含了可写性的潜质,是可写性的基础。
关键词:可读性;主题写作;小说形式;观念创新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北京102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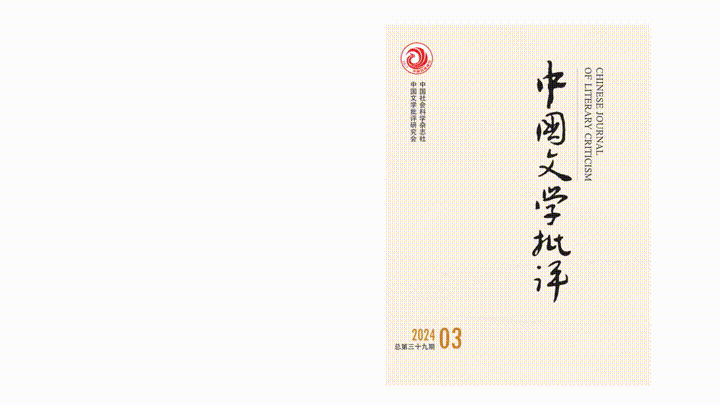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的可读性问题常常被忽视,可能缘于人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之事,仿佛学理上无须进行讨论。文学史研究者考镜源流,试图将作品、作者、事件、现象、流派、思潮等史料确证为知识,文学批评在理论的烛照下或者从外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或者借助语言风格与形式技巧的工具进行解剖,很少有人讨论可读性问题。可读性通常意味着受众层面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是鉴赏的开始与批评的起点,在普及与提高的辩证中获得其合法性的证明,指向传播与接受的效果,至于何谓可读性以及什么样的途径通向可读性则语焉未详。
之所以由这个话题引入,是因为笔者读到老藤(滕贞甫)的小说。如果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古典文本”——那些小说大多数为“主题写作”,有着目标明确的所指,并且语言力图谋求一种透明性,这让意义产生了封闭,也就排斥了含混暧昧的多样解读可能性。那些作品确实不是那种可写的文本,但是“可读”与“可写”有着明确的指涉,倒未必是作品等级高低的唯一评判标准,可读性本身同样值得再作发掘。对于主题写作而言,它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议程,其目标则需要依托于传播与受众才能得以实现。回到常识与基础层面,作品只有具备可读性,才能达到主题所诉求的反响与效果。从这个维度上来说,老藤的小说是探讨小说可读性问题的一个切入口。
一
老藤无疑是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写作者,他总是在追踪那些最为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议题。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看似讨巧,其实充满难度,甚至带有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因为缺乏审美距离,“同时代人”必得对所处现实葆有一种审视的眼光与心态,否则很容易让写作者沦为蹩脚的摄影机角色;另一方面,当下纷至沓来的信息泥沙俱下,写作者需要学会取舍、拣选、提炼和改造,从而萃取出核心命题,并且赋予议题以“有意味的形式”和行文推进中的筋骨血肉,不然他就会走向一种对信息和细节活力的过度追求而导致歇斯底里,而“细节一般是想象出来的,不是拘泥地‘记录’下来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命题,对于“新时代”而言,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是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键词。时代的命题作用于文学,虽然未必那么直接,但必然会潜移默化带来创作从题材到观念和形式上的更新,近些年来关于工业和科技发展的作品明显增多,科幻文学成为热议的话题,显然同整体性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老藤的《北爱》聚焦的就是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前沿题材,并且由此编织了一个戏剧化的“逆行”故事。
《北爱》由人物经历入手,敷写了从2012年到2021年十年间国产飞行器曲折演进的侧面。小说从上海交通大学女博士苗青“逆行”的毕业选择开始。所谓“逆行”就是她放弃了与男友南下深圳从事地产业,而是追随自己的志向,北上前往大连,进入专门从事飞行器研制的鲲鹏集团下属科研单位909所工作。因而,这个“逆行”实际上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地理空间上从南到北,从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南方逆向到发展亟待转型的北方;二是价值目标上从现实到理想,从欣欣向荣、前景(钱景)似乎更好的地产业,逆向到需要坐冷板凳的科技研发。这两重含义可以归结为从世俗的金钱、名利、物质和个人利益的追逐,逆行向知识、精神、梦想和国家利益的探求。
苗青从909所的学习生活开始,到飞鹰公司挂职,设计出小型低空航拍无人机创收,再到领衔国家级的G31项目,设计出隐形超音速飞机并试飞成功。这十年的经历包括了爱情与友情、科研与创业、经营与管理,联结了学院、职场、商场乃至战场,可以说是成长的十年。支撑她在低谷中始终没有颓废的是“一个人的计划”:“她心头的灯是一个人的计划,具体就是喷气式商用大飞机,目标是让国内干线、支线商飞国产化。” 这是将个人志趣和家国情怀关联在一起的计划,因而并不孤独,而是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同行者。苗青的成长与导师、朋友、同事、组织的关心与帮助密切相关,从新型无人机到隐形特种飞行器,再到小说结尾接到研制大型多用途远程运输机的国家级项目任务,无不显示出一种在文学书写中久违了的集体主义协作精神。
正是在集体精神的笼罩下,《北爱》虽然颇具所谓时下颇为流行的“大女主”叙事色彩,却并非性别视角的作品。它不乏爱情的情节,但并没有陷入到儿女情长中去,而是将素朴的志同道合、共同进步作为爱情的基础——坚守信念,不懈奋斗才是小说真正的主题。这种情感结构区别于狭隘个人主义的爱情婚恋话题,而将个人情感同更广阔的事业与人生统一到了一起。因而,情感与事业、个人与社会家国交织为一,形成了“南人北上”、南北交融、男女合作和多行业协作的暗喻,念兹在兹的是东北振兴。小说中多次出现对“亲爱的东北”的构想、蓝图和实践,从曾经在东北工作过的苗青父母和导师,到正在东北生活工作的科学家、商人和艺术家,都对这块土地充满感情和美好的愿景,并且在实际中投入到建设这块土地的工作生活之中。
如果从结构上来分析,《北爱》改造了一种常见的启蒙式叙事模式:外来者进入某处并使之发生改变。苗青作为外来者到东北,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生态,而是创造出新的生态,并将自己融入进去。外来者视角被置换为内部人视角,并且是女性的角色,从而让冲突化为融合,外部启蒙转为自我成长。东北振兴在这里凸显为坚守本心又自我创新,从而也就超越地方性,具有了普遍性的中国故事意味。所以,个人的“逆行”其实是对整体性时代主题的“顺流”,顺应着的是国家总体上的科技与经济转型的大潮流。苗青的父亲本身也是心怀大志、身负才华,却没有机会得到施展,对比两代人的不同际遇,更可以看出个人的能力和成绩正是在特定时代的适当语境与平台上才能得以展示和实现。
《北爱》的题材是颇为硬核的高科技行业,为了可读性,在写法上巧妙地用画家吴逸仙送给苗青的十二幅画来暗示人物对未来的憧憬、徘徊期的彷徨、奋进中的激情与收获时的喜悦,并且通过苗青静默时在日记上写下的小诗,对画作和自身的认知进行提点和总结。通过这种刻意的虚构设置,艺术与科技、商业与人文融合在一起,标识了一种经过反省、沉着精进的人生,让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召唤与表达。
不过,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观念的展开过程中,《北爱》较之《战国红》有所推进,但为了阅读上的“爽感”,还是导致整体叙述的节奏过于平坦和迅疾,缺乏富于质感的细节铺陈和细腻的情感演绎。
到《铜行里》这部聚焦铜艺传承与匠人精神的作品中,老藤逐渐找到了题材与叙事之间的平衡。此前,脱贫攻坚与大国重工这类题材离他的经验有点远,事物的内在复杂运行机制通过采风、采访与想象也难以完全弥补。《铜行里》不一样,这个发生在沈阳市井铜行胡同并且与现当代历史进程同轨的人物与故事是他所熟悉的,因而从语感到表述都要熨帖许多。
《铜行里》的情节主线框架并不复杂,即铜行里富发诚响器店的第三代传人石洪祥在为父亲石国卿准备九十九岁生辰礼物的过程中,发现父亲的日记“软铜册”,并在同父亲以及永和兴的传人、青梅竹马的令狐可的交流中,逐渐了解铜行里的历史、形形色色的匠人和两家的过往,最终决定在由父亲创办的富发诚铜雕艺术公司兴建一座浮雕墙,将铜行里工匠们的故事镌刻上去。小说的主体内容包含了晚清石洪祥爷爷的师兄“九佬”、民国初年爷爷的三个门外徒、抗日战争时期铜行里其他铜器店的“十八匠”,以及奉天解放到抗美援朝时期父亲一代的经历。人物繁多,情节复杂,但每个阶段的故事几乎都可以独立成章,它们通过日记、回忆与讲述,拼贴为一幅完整的铜行里历史画卷。
这种结构形式同王方晨的《老实街》(2018)类似,以某个统一的空间组织起沿着时间线发生的众多驳杂的人物故事,脱胎于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1919)和冯骥才的《俗世奇人》(2008)那样的短篇小说集,是一种便于容纳杂多内容的操作形式。追溯起中国古代小说尤其近代小说,就是常见的“串珠式”结构的变形。《铜行里》的好处是以空间容纳时间,讲述的是时代的变迁,以小人物的人生史贯通起宏大的政治史与社会史,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历史,有时如同攀爬的藤萝生长在坊间墙角,这也是为什么说最早的历史是方志的缘故。民间记忆往往更贴近真相,尽管墙上的藤萝不免添枝加叶,但根茎大都在原位”。贴近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与传奇讲述,形成了顺畅通达、亲近读者的风格。
二
顺畅通达正是老藤小说的特点,它未必指向某种高深的理念,或者复杂的人情世故,而是回归到小说原初的可读性。从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读物,到“革命”之后的“为体其易入人”“为用之易感人”的现代小说,所有的审美效果都来自作品同读者亲近的可读性,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所提倡的“大众化”要求。老藤最新作品《草木志》作为乡村振兴主题的写作,显示出在上述作品经验积累基础上的统合性尝试,下文就以其为中心略作分析。
首先,娱乐性。从故事情节来说,《草木志》同样采用了外来者进入某地的模式,但具体经验是老藤所熟悉乃至亲历的。“我”作为省自然资源厅的一名小公务员,参与省里的一项驻村工作计划,到小兴安岭东麓沿江镇墟里村担任第一书记,帮助规划协调这个由驿站演变而来的古村改造和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因而,外来者进入某地促成某地的变化这一母题,在《草木志》中就转化为某个曾经兴盛、后来衰败老朽的地方,在某种契机下,重获新生的复兴叙事。复兴叙事有着悠久传承的神话原型:元亨利贞,成住坏空,无论在传统的儒家还是佛教思想中,都有此种萌芽—兴盛—衰落—重振的循环演化的生物学式结构,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内化到一般人的集体记忆和思维方式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因势利导的格式塔完型心理。
小说在复兴叙事中加入了戏剧性元素。其戏剧性直接体现在每个人都被冠以一种植物的绰号或代称,从而让他们的性格特征得以凸显。村中“一金三老” 与《铜行里》的“九佬十八匠”相似,都是类型化的刻绘。这些乡村人物群像,让墟里村内部自身即是一个舞台。墟里村中方、石两大家族三代人的恩怨及其化解,同样是一种戏剧化的结构,不仅制造了矛盾冲突,增添了情节的起伏,也使得线性叙事的脉络不再单一,而掺入了村中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
与墟里村复兴之路并行的,是“我”的成长历程。作为一个并无多少基层工作经验的小公务员,“我”在墟里村的调研,同村中人物的接触,设计项目时遇到的困难与化解,不断地加深了对村子的历史、地理、风物、人情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居于省厅研究室的同事老雷抽象概括的“纸上谈兵”,与村中事务、村民纠纷、村庄发展的现实复杂性和丰富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促进了“我”的反思,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上,“我”都逐渐走向成熟。外来者不再是启蒙的主角,而成为与村民们共同成长的一员。
复兴结构、戏剧化元素、外来者模式、成长叙事,全部都是有着深厚历史传承的故事形式,对于阅读期待而言,读者接受起来水到渠成,构成了轻易便捷的娱乐性。
其次,知识性。《草木志》的29章用了34种植物来命名,实际文中涉及的植物至少有上百种。那些主要的植物被用来与人物性格外貌特征相对应,有着刻意设计的痕迹,如同戏曲中的脸谱,给读者造成直观的前理解。同时,“存在通过见证而呈现”,正是这种多介绍、说明和议论,而少叙述与描写的设计,叙述者“我”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让墟里和都柿滩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得以呈现。如果从文学传统而言,它接续的是草木比兴、感物兴发的诗骚传统。
老藤并非要进行一种博物志书写,但《草木志》客观上起到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效果。这既是通行的一般知识,也因为同人的关联,而成为带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识。自然地理、水土气候决定了物产、景色和风俗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才出现了诸如打松塔、捉飞龙、吹唢呐、养鱼头、杀猪菜之类生产与生活的形态,客观上对东北地方文化起到了宣传普及的作用,也是阅读兴味的一个来源。
语言作为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在行文中以方言土语的化用表现出来。不仅表现在日常词语、歇后语、谚语之上,更主要的是,语言同文化联结在一起,赋予了叙述者与讲话人声口毕肖的形象。高度凝练的方言显示的是民间智慧与乡土生存法则,渗透在社会交往与风俗仪式之中,成为认识一个地方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草木志》可以视为小兴安岭东麓的风物志。
最后,观念表达的开拓。在晚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的小说中,利用地方资源发展文旅几乎成了一个叙事上的俗套窠臼。在那种俗套中,常见的是干部带头,乡民跟随的“风行草上”模式。同时,乡村成为一个自我风情化的处所,它将自身打造为一个供游客休闲、养息、汲取新鲜感与体验文化消费的客体,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的他者。
《草木志》则通过共同成长,以新任村主任哨花吹(邵震天)的言语和行事,展示出农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内生力量、原生智慧。小说中一再通过“我”的感悟指出“农民式智慧的可爱,这种智慧的特点是直奔主题,隐蔽性不强却十分高效”,“农民式智慧能够复原所有的高等智慧”。事实上,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方石家族恩仇、督导组进村封灶的问题,都是哨花吹巧妙地通过个人能力、运用本地习惯才有效得以解决,“我”只是在开发建设上协调引进了资源,而这个资源也同样来自从村里走出去的各方人才。如此一来,乡村振兴的叙述,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倡导与自下而上的创造相结合的产物,让乡村振兴的主题得以摆脱带头人策划方针、村民执行的个人英雄模式,走向了干部设计、能人实践与村民集体参与的水乳交融、彼此互动的多元集体模式,从而拓展了乡村振兴观念的表达空间。
三
此种情形之下,“严肃文学”必然要改弦更张,或者与类型文学进行嫁接、移植,就像在麦家《暗算》、全勇先《悬崖之上》、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等作品中所显示的那样,增进自己的娱乐性;或者提供新鲜的认知经验,也即以稀缺性知识或地方性文化作为卖点;或者进一步精英化,在审美形式和理念创造上走向启示、启发与启迪,也即观念性创新——当然,这并不是一般作者或者主题创作所能达致的。这些探索与尝试往往融合在一起,共同指向可读性。
老藤的小说从审美上来说即便不是乏善可陈,却也谈不上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文学的大众层面和主题传输的层面来说,他依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对他的小说的述评,可以初步进行一些经验总结。
作品的娱乐性是阅读的本能需要,因而需要在语意、修辞、框架中做到读者喜闻乐见的形象化,通过形象把含混、不确定与抽象事物和理念的“不可见性”变得“可见”,避免读者隔着一段距离来把捉被传播的事物,便于读者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
作品的知识性则源于求知的内在激情,但读者并不是学生与信徒,并不专为受教诲与训导而来。小说的“寓教于乐”不同于教科书和教义指令之处就在于,专业知识、默会知识与地方知识,经过书面语言的声音化、情节故事的日常化处理之后,具有了通俗性和普遍性,让传递的信息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作品的观念性来自叙事本身逻辑自洽的潜移默化感染力而不是皮下注射式的灌输。生活本身并无逻辑可言,是书写赋予芜杂的信息、人物、事情和细节以形式与意义,现实中诡异离奇之事必须通过叙述的剪裁和整饬,以叙事的说服力通向可信和可接受性。
至于作品意义阐释空间是否有可能走向阻塞,也即是否具备可写性,在可读性中倒不再形成困扰。无论是观念先导的理想型写作,还是以商业目的与娱乐消遣为旨归的写作,主题与观念都需要细化到具体的人、事、时、地、物。一旦进入具体的人、事、时、地、物,也就必然蕴含了意义打开的可能性。因为,就作品本身而言,我们不能假想任何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符码同意义之间有着无障碍的直接对应关系,在词语与句子组合、形象与情节的生成过程中,意义的流失、增殖、歪曲和转化无可避免。就流通与阅读而言,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一种单向度的传播,内容、形式与理念由作品通向被动而毫无作为的受众读者。读者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使得作品产生之后,就必然成为开放、多向的存在物。可读性自然蕴含了可写性的潜质,并且是可写性的基础。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