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路遥的写作,根植于他的故乡陕北农村。他的创作受到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乡土苦恋”是他作品主要的底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他通过对乡村风景、人物、天气的书写,甚至于整体叙事框架的建构,描绘出心中完整的农村样态。陕北的乡村空间在路遥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关键词:恋地情结;路遥;乡村;空间
作者杨艺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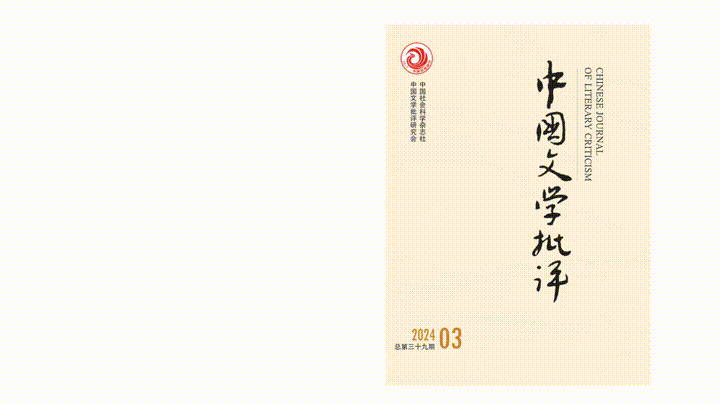
出生于陕北的路遥,在陕北农村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陕北黄土地上的无限风光和困苦生活,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路遥在陕北的人生经历是复杂的,年少时家境的贫寒,摆脱不掉的农民身份,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他养成了敏感和自卑的性格。在激荡的岁月里,他时而被送到荣耀的巅峰,时而掉落耻辱的谷底。因此,路遥对陕北的情感也是复杂的。陕北的土地与风物将路遥塑造成一个特征明显的陕北人,而他的创作也具有显著的高原文化气质。
一、审美视域下的乡村景观
路遥对乡村的体验是完整的。从乡村地理事物以及乡村人际关系的图式中,路遥绘制了乡村空间的整体性,并将这样一个世界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体验到了个体与集体、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路遥对农村近乎全景式的展现中,自然风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在面对乡村景观时,路遥总是流露出爱的态度和喜悦的感情,以一种审美式的经验,来描摹陕北农村的自然景物。
对某地风物的审美式评价,在段义孚看来,往往更多来源于外来者。相较于我们熟悉的场域,人对于陌生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所以就外来者而言,他们往往采用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通过视觉构筑图景,欣赏新颖的风光,与此同时,体验陌生景致的新鲜感也促使他们抒发自己的情感。与之相反,本地人由于长期浸润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他们对环境的理解更加深刻,态度也更加复杂,导致他们鲜有需求去表达自己的环境价值观,或对家园作出评论。
路遥在书写乡村自然风貌时,叙述中充斥着对美好景致的审美式表达,赞颂着陕北农村的田园风光和四季景色。这一方面凸显了路遥对陕北农村的满腔热忱,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路遥极佳的艺术感受力和语言表现力。他兼具外来者的审美视角和本地人与自然环境长期交流互动的经验,所以他对陕北风景的刻画更加鲜活生动,经常能捕捉到常人难以关注到的细微变化。
在《人生》中,因为“卖蒸馍”高加林与刘巧珍在路途中邂逅。他们一起相约回家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路遥描绘了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图: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天上飞起了一大片红色的霞朵。除过山尖上染着一抹淡淡的桔黄色的光芒,川两边大山浓重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川道,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马河两岸所有的高秆作物现在都在出穗吐缨。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远处的山坡上,羊群正在下沟,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富丽的夏日的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
在这段景物描写中,显示着由远及近,再由近到远的结构布局。从夕阳时分晚霞的绮丽,写到更近处山尖上落日投下的光芒,暖色调的视觉效果,带给人温暖柔和的感觉。在描写川道时,他又着重勾勒了大山“浓重的阴影”,加上凉森森的空气带来的触觉感受,与前文的暖色调叙事既相衬又调和,在温暖的基调下又添了几分舒适凉爽的意味。接着,路遥描绘了近处庄稼出穗开花的盛景,清淡芬芳的嗅觉感受,引人进入如诗如画的意境。最后,他笔锋一转,又写到远处山坡上的羊群,以大地“宁静而庄严”的审美判断,结束了这一长段的景物描写。
路遥在建构乡村的景物空间时,从远处的视觉到近处的触觉、嗅觉,形成了立体综合的写景效果。段义孚认为,“眼睛会观察可视区域,从中抽象出一些特定的目标、焦点和视角。”因此,从眼中看到的世界是更加抽象的,去“看”的人仅仅是旁观者和目击者。而“柠檬的味道、皮肤上的暖意,还有树叶的沙沙响声,给予我们的却是感觉本身”。路遥在写景时综合运用多种感受系统,景物也从抽象转变到具体。这在制造氛围、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也完成了对陕北农村风貌的深度把握,带给读者完整而优美的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在写作中选择使用一种肯定性的风景修辞,即无论人物的情绪是高涨还是低落,无论情节的发展是顺利还是波折,他坚持“单一地描写那些明媚的,充满诗意的风景”。这是路遥最为突出的写作特色之一,在他构筑乡村图景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赵学勇认为,路遥的乡恋并不是对故乡自然景观的简单赞颂,“而是由故乡景物和童年记忆凝结而成的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包含着他对乡村的整体感受。尽管路遥的童年是在饥饿与穷困中度过,但是他对乡村的感情依然深厚而真挚,在他眼中,乡村永远是一片熠熠生辉的土地,因此他所刻画的乡村风物也永远是优美动人的。
如高加林刚刚经历了民办教师资格被剥夺的痛苦之后,他在院子里刷牙,就看到了一幅美好的乡村风景:
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川道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向阳的山坡大部分是麦田,有的已经翻过,土是深棕色的;有的没有翻过,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像刚熟过的羊皮。所有麦田里复种的糜子和荞麦都已经出齐,泛出一层淡淡的浅绿。川道上下的几个村庄,全都罩在枣树的绿荫中,很少看得见房屋;只看见每个村前的打麦场上,都立着密集的麦秸垛,远远望去像黄色的蘑菇一般。
路遥在描绘高加林眼中的景物时,一改在环境描写时层次分明、有条有理的方式。这里的景物描写,表面上看似乎显得有些凌乱,远景与近景的跳跃性较强。然而,这种描写方式也正好契合了人物内心的焦虑与波动,外在表现为视觉上的跳跃不定,上一刻还在看湛蓝天空上的白云,下一刻就看到了川道里的玉米,接着又张望起了更远天边的雾霭。但人物眼中隽美如画的景象,又降低了情节的悲伤色调,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品的感受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路遥在描绘“明媚的,充满诗意的”风景时,通常都喜欢描写远景,这一方面构建了人物与风景的疏离,削弱了风景与人物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作品的悲剧感;另一方面密集的视觉描写是对景物最好的刻画方式,集中了主人公的感受系统,完成了对陕北风物的审美式书写。段义孚认为,视觉所能穷尽的空间更加广阔,“‘远’的东西只能被看见,所以我们说能看见的东西离我们有多‘远’,即使它们可能离我们很近,这也就无法唤起强烈的情感体验。”路遥对远景的刻画,唤起的是对陕北风物的爱怜之情。他仅仅使用视觉描写,在视觉空间上建构农村的景象,弱化了情感体验,因此尽管这种描写冲淡了故事本身的感伤色彩,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叙事结构。
后来,高加林下定决心要和刘巧珍分手。他们诀别之后,高加林在草地上痛哭了一场,在水沟了洗了脸,又重新上路,“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稍微轻松了一些。眼前,阳光下的青山绿水,一片鲜明;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彩。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了一会,便像箭似地飞向了遥远的天边……”同样的,路遥通过远景描摹,描画了陕北农村的隽美风光,也稀释了分别的忧伤。阳光、蓝天、青山绿水,还有天空中飞过的鹰,这些审美式的景物描写,形成了自足的体系,削弱了叙述中的悲剧性力量。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风景本身就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特殊符号,而风景描写则是体现着自觉目的的修辞行为。路遥在审美视角下对陕北风貌的描述,自然有着独特的风格与效果,李建军认为,路遥笔下的风景描写和风景修辞“不是与情节和人物的心情相一致,而是与之相分离”。在这里,“不是相一致,而是相分离”可谓一语中的。仔细阅读后会发现,路遥对农村景物的描写,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甚至于和情节发展、人物状态都没有直接的联系。笔者认为,这一点正是路遥写作的独到之处,即对乡村风景、天气、事物的描写,并不是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服务,而是独立自足的审美式书写。
二、心理意义上的乡村空间
路遥对陕北农村风景土地的直接描写,完整地寄托了他对故土的眷恋与热爱。但路遥对农村的真实态度,却是复杂的。路遥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一生都在试图逃离乡村,但是内心深处对故土的眷恋,却又始终在精神上将他拉回陕北农村。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有了这样的思考:“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得太多了,思考得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在接受教育的农村青年心中,乡村是缺乏意义、缺乏价值的,他们的思想已与父辈迥异,在他们的心理层面建构起的乡村空间,是缺乏工作机会和生活资源,却有着社会无形的束缚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地方。这与路遥笔下美好的、风景如画的乡村自然风物形成了矛盾和张力。人物在乡村体验的是极致优美的环境,但他们的人生价值只有离开乡村、在远方,才有可能实现。
在《人生》的开头,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身份被顶替之后,他想到的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曾经在路遥笔下熠熠生辉的乡村美景,在这一刻变成了“贫瘠的山区”,主人公高加林拼命读书十几年,也终究是为了不当农民,不成为土地的奴隶。乡村的青年受过教育,在县城里读完了高中,接触到了另一种生活的样态,他们在心灵深处都会对城市里的生活充满向往,而变得对农村日复一日的劳作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满腹厌弃。
当高加林因为叔父的升职,终于又被马占胜安排到县上做一名通讯干事的时候,他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对生活的希望,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了。在做第一次关于暴雨的报道时,他晚上冒雨赶去,渴了伏在路边水坑里喝水,脚也被碰破了。但他无所畏惧,一到地方立刻展开工作,帮助大家抢险救灾,晚上还彻夜赶通讯稿。知识青年进入城市,他们心中的激情和力量就被激发出来了。尽管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可能更加艰苦,但是一方面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可以从事知识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褪去农民的身份,成为吃“公家饭”的人,这种转变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执念。只有这种执念获得了满足,他们才会觉得生命有了向往。
无论是高加林和薛峰,还是同时代的许许多多青年人,都把留在城市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不愿意成为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承认乡村美好的一面,但是乡村的匮乏和封闭,却是他们难以忍受的。路遥在构筑乡村自然风物时采用的肯定性修辞,与人物在心理层面接受的真实的乡村空间样态,有着极大的矛盾,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描写中,乡村空间在多个层次上同时延展开来,对乡村的描摹更加深刻全面。
三、返乡的叙述模型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路遥最终选择了“返乡”。在认可城市空间的基础上,又重新返回、重新定义了乡村空间的价值,在这样的叙述结构中,路遥把握了乡村在他生命中真实的意义。路遥一方面认同乡村的价值观,崇敬赞扬乡村的美景风物;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理解乡村的苦难,有急切地想要逃离乡村的渴望。当这两种意识相争斗时,还是对故土的眷恋热爱占据了上风,在小说中的体现就是一种“返乡”的叙述模式。这样的叙述模式,为乡村空间的最终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乡村不再仅仅关乎物质的条件,也囊括了一种情感的牵连。这是路遥对自身逃离故乡的人生奋斗历程的反叛,也是对童年经历与生活境遇的回归。他在描写城市优渥生活之余,往往充满深情地展现对乡村的惆怅苦恋,也使得作品建构的乡村空间具有了更加复杂深刻的内蕴。
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路遥塑造了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郑小芳。她大学报考水土保持专业,就是为了回到家乡,为了把那里的山山水水变得更加美好。她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崇高的生活,永远要有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因此她也身体力行,自愿回到了比家乡更北的地区。那里一半是山区、一半是毛乌素大沙漠。她选择到沙漠农场种植固沙花棒。她忍受着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毫无疑问,这一形象是路遥依据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创造出来的,是他由“乡土苦恋”而生发出来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信念,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具有的。在这部小说中,她的出场一方面调和了薛峰过于“物质”和“圆滑”的行径,另一方面也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生命的选择。
郑小芳所代表的是一种固化的精神气质,无畏、无私、勇于奉献,有牺牲精神。她对自己的理想主义信念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当意识到薛峰想要留在省城时,她自觉地认为一定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渗入了他的意识。她还想到,“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投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薛峰希望留在省城,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可在郑小芳看来他的眼睛已经“混混浊浊”了,还有可能变成投机钻营的市侩。这种对比强烈的描写表露了路遥自身的道德立场和他对于还乡的坚决信念。在小说中,路遥描写了薛峰内心的纠结和沉重,但郑小芳一直是坚定的,对自己的选择和人生道路毫不怀疑。小说以薛峰在火车站的矛盾和痛苦结尾,最终是理性暂时性地败给了信念和激情。
李建军认为,“对故土的过于浓烈的情感,严重干扰了路遥的小说叙事,让他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浪漫的精神还乡仪式”。同时,这也反映了“‘恋地情结’与‘现代意识’在路遥内心的尖锐冲突。当‘恋地情结’压倒了‘现代意识’的时候,路遥就会选择高调的道德浪漫主义叙事模式”。路遥的这种“精神还乡”的情结,饱含着他的人生态度和道德选择。城市和乡村作为生活的两极,往往使人物的生活和生命有一种撕裂感,而路遥选择农村作为故事的归处,将小说叙事的根脉扎在了乡村的土壤之中。人物或主动或被动,都回到了养育他们的故土,人与乡村的互动也形成了首尾相应的环形结构。这样,乡村空间就真正被完整、深刻地建构起来了。
对乡村的执念,不仅仅体现在路遥这里。贾平凹《浮躁》的结尾,金狗娶了小水,带着福运的儿子,在州河上做起了正当的水上运输生意,回到了他年少时的起点。与路遥的创作不同的是,《浮躁》中的乡村空间没有与作者形成精神上的联系,小说中无论何种场域,都只是为了提供主人公活动的轨迹,也就无所谓情感的羁绊了。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才暂时性地跳出了精神还乡的冲动。孙少平希望追求一种“抱负”和“梦想”,他不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通过和田晓霞的交流、阅读各种书籍,他摆脱了小农意识,他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天地里遨游。后来他也逃离了农村,但他还是被抑制在了城市边缘的煤矿,成为一名工人,最终也未曾到达过远方。这其实与《人生》中的高加林类似,一直在县城和乡村之间徘徊,跟随黄亚萍去南京,去往更广阔天地的愿望永远地落空了。这表明从路遥自身的精神而言,他一直没有脱离农村,也一直没能走进城市。他的精神和生命,永恒地停留在乡村之中,短暂的超越也只是抵达了“城乡交叉带”。
由于路遥的创作与中国特殊时代的经验结合相对紧密,在路遥研究中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叙述话语强加在路遥作品的叙事中,如石天强曾提到,他认为在路遥小说的三种空间——乡土空间、都市空间以及城乡结合部中,乡土空间意味着一种过去,一种记忆。同时,路遥的乡土空间是始终处于都市空间的压力下的。而事实上,我们考察路遥的文本结构会发现,在路遥的创作中,他最熟悉的、养育他培养他的乡村,才是作品中永恒的主体。都市对路遥来说,仍旧是处于陌生的他者的位置。
作家所坚持的叙述方式,都是作家自身生活、思想和态度的反映。路遥对于农村的真实感受评价,隐含在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自然的语言流露中,隐藏在他对农村热忱的感情表达的更深处。他深切地认识到农村空间对个人发展的限制,因此他常常在农村与城市、故土和远方之间举棋不定。在几部中篇小说中,路遥都坚定地选择了乡村作为故事的终点和归宿,一直到《平凡的世界》,他才暂时性地跳出了这种精神还乡的冲动。路遥的作品隐喻着特殊的空间感和空间焦虑,他对乡村深情的牵挂始终萦绕在作品的叙事氛围中,因此,在乡村空间的剖判上,除了自然风貌和物质条件的坐标轴之外,又加入了情感的坐标轴,使得乡村空间被完整地界定出来。
结语
路遥在陕北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岁,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深厚的情谊。陕北塑造了路遥的精神气质,他在创作中也不断抒发着对陕北的一往情深。
路遥的“乡土苦恋”,表现在他对农村风貌的肯定性书写中,也表现在他深刻理解农村生活的艰辛后依然选择精神还乡的叙事策略中。路遥对故乡的热爱,不仅仅是对故乡风景的赞美,也包含着故土的人群、景物、味道以及留在故乡的记忆构建的整体氛围,是与故乡离别之后的郁郁苦恋。从单纯的景物描写到整体的叙述策略,路遥的写作无一不呈现着对陕北农村的深切情感。他的乡土叙事,自然而又真实,有着美好的情感和温暖的生活体验。
路遥对陕北农村的刻画,影响了很多陕西作家。在海波的《高原落日》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中,都流淌着对黄土高原的热爱,也充满着与路遥相似的“肯定性的风景修辞”。路遥对乡村的绘制,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他所建构的乡村空间,也以其完整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成为文学史上的丰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