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忠实与路遥,是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两位杰出代表,从新时期陕西文学的版图和成就观察,两人可谓双峰并峙,难分伯仲。路遥与陈忠实,由同行变为同事,陈忠实多次谈到路遥对他创作上的影响,一是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和态度,坚定了陈忠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信念,二是路遥的《人生》促使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构成一种“集体性共创”现象,陈忠实谈到路遥的创作对他的创作有“摧毁与新生”的作用,这是一种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路遥;陈忠实;影响;集体性共创
作者邢小利,陕西省作家协会编审(西安71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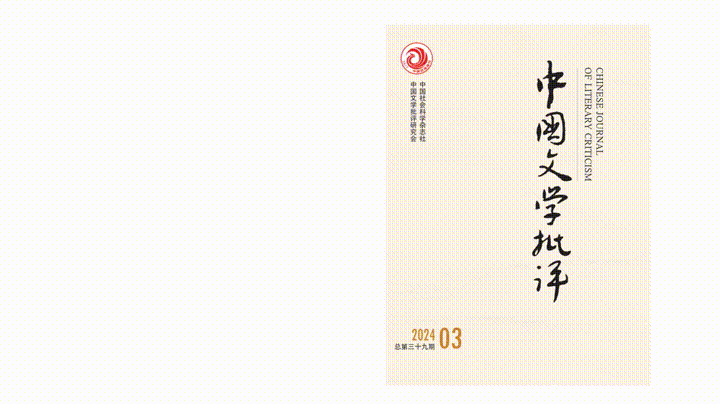
陈忠实与路遥,是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两位杰出代表,从新时期陕西文学的版图和成就观察,两人可谓双峰并峙,难分伯仲。路遥以1982年问世的中篇小说《人生》和1986年至1989年间陆续问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享誉文坛,影响广泛,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也确立了他在陕西文学格局中的大家地位。陈忠实则以1983年问世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和1984年问世的中篇小说《初夏》特别是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享誉全国,影响深远,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不朽地位,也确立了他在陕西文学格局中的又一大家地位。
陈忠实与路遥,前者是陕西关中人,1942年生,后者是陕西陕北人,1949年生,两人当年同在一个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又在同一部门——作协创作组共同从事文学创作。这种单位、这种工作,一般而言,两人应该是彼此敬重而又我行我素的状况。但在两人当年共事而又各行其是的创作过程中,据陈忠实多次文中自述和口头回忆,路遥对他的创作有过很大的影响。
这种同时代特别是同一地区同一单位共同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互相切磋,彼此影响,特别是陈忠实能向同辈同行虚心学习,是文坛佳话。其中也有文学创作中一些值得深思并值得探讨的问题。
创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创作并不是说个人可以不学习前人和他人的创作经验,不受前人和他人的影响。即使是天才作家,他也要学习前人,也要或多或少接受他人的影响。从文学史看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古代和现代作家都有结为诗社或文学社团的。他们因为文学主张比较一致,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比较相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进而自由结社、互相切磋、彼此影响,在“集体性共创”的艺术环境中创作出一些佳作巨构。文学史多有此类佳话。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环境更有其时代特点,有作家协会这样的文学组织和单位。以陕西作协来说,20世纪50年代,柯仲平、马健翎、柳青、胡采、王汶石、杜鹏程等有延安时期经历的作家齐聚于此。80年代,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这些主要从陕西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先后调入,并齐聚于陕西作协创作组。1976年9月,路遥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陕西文艺》(该刊由陕西省文化局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编辑部任小说组编辑,1977年《陕西文艺》恢复《延河》刊名,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延河》复归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办,路遥由《陕西文艺》编辑成为《延河》编辑,并随《延河》成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工作人员。1982年12月,路遥由《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转到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1月,陈忠实由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该区文化馆副馆长任上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与路遥在同一单位同一部门成为同事。
路遥与陈忠实,由同行变为同事。曹丕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认为相轻者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有人分析“文人相轻”现象,认为中国作家的文人相轻,多出于嫉妒心。西方作家也有“文人相轻”现象。笔者是1988年4月调入陕西作协的,以多年的接触和观察看,从性格上说,路遥沉雄、陈忠实刚毅,两人都是强者。这样的两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又在同一个部门,比较容易形成矛盾甚至冲突的关系,至少是内在的矛盾。但陈忠实与路遥之间,后来他们至少有十年的共事时间(路遥于1992年11月去世),两个人未见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亦未见“相轻”现象。相反,二人互敬互重,陈忠实后来多次深情回忆路遥,而且具体谈到路遥对他创作上的影响。在此,陈忠实一方面道出了他由一个学历不高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不断进步并有创作上非凡超越的某些秘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作家谦虚的美德。也正是因为谦虚并以谦虚的态度敢于学习善于学习,陈忠实不断丰富壮大,终成一代大家。
01
路遥和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写小说,写农村题材,他们秉持的创作方法也主要是现实主义。从直接的文学影响上来说,路遥和陈忠实都奉柳青为师,路遥称柳青为文学上的“教父”,陈忠实则称呼柳青为文学上的“老师”。颇有意味也合乎逻辑的是,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是陕西人,先后同在一个单位——陕西作协工作,他们文学上的影响自然而且显然有内在关联性。他们文学上的认同和相互影响既有地理意义上的,也有文化意义上的,当然更多的是文学意义上的,因为他们都尊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柳青是陕北榆林地区的吴堡人,1952年落户关中的长安县,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题材是陕北,《创业史》题材则是关中长安县农村;路遥生于陕北榆林地区的清涧县,七岁被家人送到延安地区的延川县,他的代表性作品《人生》写的是陕北,《平凡的世界》主要写陕北,同时也延伸到关中地区的铜川和西安等地。柳青的创作特别是他的《创业史》侧重写集体中的个人,并以集体中的个人来反映时代和社会。他的创作代表着“十七年”文学的高度。路遥也以柳青为师,但他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有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社会经验和生命体验。他的文学观念属于另一个时代——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精神和创造激情的时代。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写的正是中国社会由70年代向80年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他的创作与柳青小说中那种集体中的个人不同,他突出了个人,并把个人与时代紧密结合,代表着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主要写陕西关中平原渭河两岸特别是南岸地区,小说的地理、文化以及民俗背景虽与前两位不同,但有共通之处。他以前辈柳青为师,并谦虚地从同辈路遥那里汲取创作经验,寻找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写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白鹿原》,代表了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
路遥对陈忠实的影响之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和态度,坚定了陈忠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信念。2011年5月,作家张炜到访白鹿书院,陈忠实、葛水平和笔者陪张炜在书院的四合院里喝茶聊天。张炜和陈忠实共同忆起了路遥,说到了1984年3月,他们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路遥在会上的发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张炜回忆,路遥在大会上说“万元户中也有坏人”,写万元户,可以写他们的好,也可以写他们的坏,这个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陈忠实说,他当年对路遥在大会上的发言印象最深的,是“我不相信全世界都要养澳大利亚长毛羊”。因为澳大利亚有一种长毛羊,品种好,正在推广,路遥借“澳大利亚长毛羊”这个比喻,来说当年文学上的现代派主张。他认为现代派可以搞,但现实主义也应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能“全世界都要养澳大利亚长毛羊”,让“澳大利亚长毛羊”一个品种独行,而扼杀世界上一切羊的品种。这个说法在当时文学界的现代派呼声甚高、行情看好的时候,一方面给人提供了关于文学走向上的另一种思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路遥独立思考、敢于发言、不怕别人说他“土”的艺术勇气。陈忠实强调,路遥这个发言引起他的深思。1984年,新时期文学从伤痕、反思、改革等潮流到现代派的种种试验和表现,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新”与“奇”竞相炫技并狂欢。有人认为文坛已经没有主流,并以“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概括当时文坛。陈忠实说他写的是农村题材,用的又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面对文坛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和新潮,多少有些惶惑和不安。但是听了路遥会上自信而且幽默的发言,他受到启发,也受到震动,在心中坚定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信心。
1984年3月11日,陈忠实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编辑何启治,谈到他参加涿县会议的收获:“这次农村题材讨论会是开得不错的。几年来,在农村题材的创作中,面对变化着的新的生活潮流,我不至(止)一次感到困惑,甚至痛苦。这种困惑,首先是对复杂的生活现象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至于作品从怎样的角度去反映现实,以避免图解政策的前车之鉴,又当别论,而作者总应该搞清楚当前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困惑,因为我缺乏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又长期囚于比较狭隘的一隅,因而导致如此。所以这次会议,我是从内心感到踊跃的,企图得到启示特别是活跃于当今文坛的农村题材的名家蜂拥而至,我想我会受益的。会上,绝大多数的作家都谈到困惑了。困惑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了。我心里踏实了,看来大家面对新的生活现象都有类似的思考、类似的苦恼,我甚至想,严肃的作家对变化着的农村生活的思考是必然的。而对这种新的生活现象觉得轻易可以认识,可以表现,往往使人感到了某种图解的简单化作品。我这次主要是带着耳朵去的,我达到了目的,听到了许多长期保持着与生活联系的新老名家的精彩发言……”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陈忠实当时面对新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颇多困惑,对自己的某些局限也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参加这个会,“主要是带着耳朵去的”,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的也是多听意见,以图打开眼界,解除困惑。
2015年 3月27日,陈忠实在《文艺报》发表《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这篇文章中他再一次谈到涿县会议路遥那个精警的发言留给他的深刻印象:“路遥在大会交流发言中阐释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末了有一句让我至今不忘的警句:‘我不相信全世界都养一种澳大利亚羊。’”陈忠实还从《平凡的世界》被改编为电视剧并热播谈到作品的史诗品格,评价《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性作品”,认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丰富并开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路遥始终不渝的艺术创造理想”。陈忠实还引用路遥的话,“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然后发挥说“这种精神在我理解就是依循现实的客观逻辑,再现和表现生活直面人生”。在这段话中,陈忠实不仅充分肯定了路遥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而且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发。
路遥、陈忠实两位现实主义大家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持、理解和阐释,既是一段文坛佳话,也对我们充分理解和研究现实主义创作有所启示。
02
路遥对陈忠实的影响之二,是路遥的创作促使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真实当然与事实有关,但在文学创作以及作品阅读中,所谓真实不真实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经验感知。它虽然可以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真实事件与真实的人联系起来,但一般来说,无法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直接对应起来,更不要说一一对应起来。所谓真实性只能是作家和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理性认知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对于现实主义作品来说,真实性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本质性的要求。真实性与写实手法是两个概念,用写实手法写出来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现实主义作品。反之,现实主义也可以用夸张、浪漫甚至一些魔幻的手法。
陈忠实的创作,是从自学起步,用他致何启治的话说,“缺乏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又长期囚于比较狭隘的一隅”。他从1958年16岁发表第一首诗《钢、粮颂》,到1973年至1976年每年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其中《接班以后》改编成电影,1979年写的小说《信任》后来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虽然他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但在80年代前期,他的创作思想还未完全摆脱多年以来形成的某些桎梏。尽管他有着比许多作家更为真实、深刻和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他此刻仍未完全摆脱小说主题“图解政策”、人物塑造概念化等从“十七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就形成的某些创作窠臼。这从他写中篇小说《初夏》的艰难过程可以充分看出。陈忠实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写于1981年1月,寄给了《当代》杂志编辑何启治。何启治认为“有基础”,对小说中冯景藩和彩彩两个人物很感兴趣,希望能“充分”写他们,退稿让修改。陈忠实认真修改了一次,《当代》主编秦兆阳看后又指出“冯景藩等人物身上有很大潜力可挖掘”,让再改。陈忠实后来用了三年多时间,又反复修改了多次,才得以通过,后刊于1984年《当代》第4期。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这部中篇从初稿到定稿,大约写过四次,从最初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再到最后发表出来的大约十一万多字。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
陈忠实写于1981年的《初夏》,至1984年8月发表,历时三年多,初稿写成后《当代》负责人和编辑秦兆阳、何启治、朱盛昌、龙世辉等反复提出修改意见,陈忠实后来意识到问题在于“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陈忠实在当时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概念化描写人物的桎梏。换句话说,他没有真实地面对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也没有完全写出《初夏》这部小说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矛盾故事,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50年代以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当年把一个进城机会让给了别人,把一切都献给了农村的集体化事业。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醒悟之后,他走后门让儿子到城里当司机,不料儿子冯马驹却放弃了他多方奔走弄到的进城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创办农办工厂,带领大伙“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也正在转变过程中。陈忠实所谓“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在新时期初期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陈忠实写在历史转变时期冯景藩这个人物情绪的“失落”和“思想负担”,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冯景藩这个形象不仅有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且有时代的典型意义。但是,陈忠实过去长期形成的艺术思维和心理定势还未完全突破,他以习惯用的对比手法,塑造了同冯景藩相对立的另一个人物,这就是乡村新人冯马驹。这样的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显然缺乏时代的典型性和历史的真实感,他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的一个想象式人物。
就在陈忠实为反复改写《初夏》而煎熬的时候,他读到了路遥的《人生》。陈忠实在《摧毁与新生——我的读书故事之五》中说,1982年5月,他到延安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开会期间,来自陕西各地的青年作家聚在一个房间交流创作信息,议论新发表的小说。有一天晚上,路遥说他的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将在《收获》第3期发表,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陈忠实记住了《人生》,他从延安一回到灞桥镇就拿到《收获》第3期,一口气读完。陈忠实回忆,读完之后,他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此种感觉并不是被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故事所触动,而是因为《人生》“完美的艺术境界”,使他受到了强烈的艺术打击。陈忠实说他当时创作激情高涨,读罢《人生》,却是一种“几乎彻底的摧毁”。此后连续几天,他一有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思绪翻腾,不断地反思着他的创作。他认识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他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全新的人物形象。他感叹高加林的生命历程和心理情感,是包括他在内的读了书又回到乡村的青年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所以引发了他强烈的共鸣。他真诚地认为,《人生》是路遥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他在灞河沙滩以及长堤上不断走着、不断反思,他重新思考怎样写人。他想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是作品的生命,没有真实性就没有现实主义,没有真实性作品也就没有艺术性,更无法打动人。如何真实而准确地写人,陈忠实自述:“我在灞河沙滩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我重新理解关于写人的创作宗旨。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准确了才真实。一个首先是真实的人的形象,是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而与世界上的一切种族的人都可以完成交流的。”陈忠实这里所言,是说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具有时空的超越性。陈忠实关于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的思考,特别有意义。真实的东西,特别是真实的人,往往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丰富性包含着多,复杂性还包含着自身的对立和冲突。真实的人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和对与错,更不是简单的所谓“先进”与“落后”。由陈忠实所谓的“摧毁与新生”一说可见,路遥《人生》对陈忠实的“摧毁”性冲击所形成的思想和艺术的“新生”启示,使陈忠实对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刻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由此出发,陈忠实更是逐渐形成他自己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这从《初夏》到《康家小院》到《蓝袍先生》再到《白鹿原》人物形象描写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出。
陈忠实还回忆,《人生》发表后,有一个老同学问他为什么没写出《人生》那样的作品?陈忠实说他无言以对。他深刻反思:高加林的那些愿望和想法,比如进城,当个城里人,咱也有呢,怎么就没有写,而且,为什么咱还要批判这种思想?《人生》发表的此刻,陈忠实正在改写《初夏》,《初夏》中的复员军人冯马驹,回到村里,他父亲走后门给他弄了一个进城工作——当汽车司机的机会,他居然拒绝了,还批评他父亲这种做法是自私、落后。陈忠实回忆,那时候他也认为这种思想是自私和落后的:我都想进城,我年轻时明明也想进城当工人,我为什么总是写不出也不敢写这种真实的思想,反而总是按照一种社会既定的思想来写冯马驹这样的人物,还要把他写得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这种明明虚假的人物,怎么能够立得住,怎么能够有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陈忠实说他被《人生》“完美的艺术境界”击倒,这个“完美的艺术境界”有很多方面,也应该包括真实性。真实性是艺术性——艺术魅力的基础。好的作品因为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以及由真实性生发出来的丰富性,所以才有巨大的艺术性。陈忠实从早期的观念化写作到体验性写作,所谓“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这个转变过程与路遥的《人生》对他的冲击有一定的关系。《人生》的冲击、《初夏》的艰难写作,特别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1983年,王蒙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其前提是清理反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突破表现在“文学真实性的恢复”“我们的文学的审美功能有所提高,文学更加多样化,文学不再简单地、片面地从属于政治”等方面。在这种时代和文学背景下,陈忠实明白,他自身需要一个蜕变,一个文化心理上的和艺术思维上的深刻蜕变。“剥离”的同时还要“寻找”,这是陈忠实80年代前期必要的思想和艺术的蜕变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也就没有《白鹿原》。此后,陈忠实在创作中,开始自觉地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写作,摒弃从某种宏大的理念出发的概念化写作模式,进而一步一步形成陈忠实自己的更为独特的文学个性和文学风格。
从文学真实性的震动到对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深刻思考,陈忠实产生了一个他后来反复提到的问题,这就是“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白鹿原》问世以后,陈忠实多次谈到他的创作体会,他有一个主要而且重要的观点就是“生命体验”,他特别强调“生命体验”对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的重要性。他说:“过去大家谈生活体验的多,谈生命体验的少。我在生活、阅读和创作过程中,意识到生命体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极为重要。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读了米兰·昆德拉译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把昆德拉的《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阅读,发现这两部作品在题旨上有相近之处,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从写作角度探寻其中奥秘,认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如同生命形态蚕茧里的‘蚕蛹’羽化成‘飞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有了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蚕蛹’才能羽化成‘飞蛾’。‘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写作《白鹿原》之前,我在农村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现的能力。”陈忠实后来还对“生命体验”有所阐发,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前一句讲的是生活体验,后一句讲的是生命体验。仔细辨析陈忠实这两个概念,他所谓的“生活体验”实际上就是外在的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而“生命体验”则指人内在的生命感受、心灵震颤、理性自觉和心灵的自由丰富。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这种“生命体验”尤其表现在对生活“真实性”的感受、认知和理解上。
从陈忠实的创作经历看,都是在他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理念指导下进行创作,但是仅就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而言,他的认识和深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他写于1974年的短篇小说《高家兄弟》,写和睦友爱的高家兄弟围绕着推荐谁去上大学产生了矛盾冲突。哥哥是党支部成员,先公后私,力主推荐认真经管医疗站、热心为社员服务的乡村医生秀珍去,而不同意有着“不健康思想”一心想成名当专家的弟弟去,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家内外相关人之间思想感情上的斗争。这个小说在当年那种文化观念和文学环境中,内容虚假似乎可以理解。但1984年发表的《初夏》,其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就令人有些难以置信了。在集体(家庭、单位、社会和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更强调前者。如果说,路遥和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创作都写集体中的个人,那么路遥更重视更突出集体中的个人。他的《人生》放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来看,都是人的个性复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陈忠实的创作更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如果仅从真实性和人的个性复活角度考察陈忠实的创作,似乎到了他1984年写成的《十八岁的哥哥》(刊《长城》1985年第1期)这部并不引人广泛关注的中篇小说,才凸显了陈忠实写真实的扎实功底,突出了他写人的个性美的魅力。在笔者看来,《十八岁的哥哥》似乎就是陈忠实的《人生》,此作也是笔者看到的唯一多少具有陈忠实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作品。该作写的也是青年人高中毕业以后回乡的人生经历,从中能看到路遥《人生》的些许影响。另外,似乎只有到了《白鹿原》这部小说,陈忠实通过白孝文、白灵、黑娃、鹿兆鹏、鹿兆海以及田小娥这些子女一辈才实现了“集体叛逆”和“个性的集体复活”,让这部作品突出了每一个人的个性。
03
作家是以其个性立足的,创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工作。但是,个人化并不等于作家之间不交流,不受他人的影响。作家之间的交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互相影响也是必然的。从消极的方面看,影响固然有所谓的“影响的焦虑”,文学后来者面对先驱者的鸿篇巨制,同行者面对他人的技高一筹甚至光芒四射,既想摆脱影响,又想超越创新,有时候产生一定的焦虑在所难免,有的还可能踌躇不前。但从积极的方面看,影响既能激发一个作家前进甚至超越的动力,更能让一个作家汲取更多的艺术养分,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互相拥挤,志在天空”。更重要的是,文学艺术的创新和创造,自古到今,即使是一个天才的创造,也绝非天马行空的独立行为,他总要汲取前人和他人的养分。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艺术作品的创造和完成都有“集体性共创”的成分。
“集体性共创”是评论家李建军创造的一个概念。李建军说:“集体性共创是我整合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内涵是: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
笔者以为,“集体性共创”这个概念可以涵纳作家之间艺术思维上和创作上的积极性影响,包括对前人和他人创作经验、方法和技巧上的学习、借鉴,也包括显在与隐在的启示。陈忠实后来的创作不仅受到路遥这样的作家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陈忠实是一个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人,他生前曾对笔者说,他没见过也不相信的东西都不写,他不信鬼神,也不写佛道。他不像有的作家那样,作品中喜欢“装神弄鬼”,谈佛说道。但他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受到震动,也受到影响,影响之一就是接受了“魔幻”手法。他后来在《白鹿原》中写的田小娥被鹿三刺死后,她的冤魂化作千万只各色的蛾子在天空中飞舞;鹿三也疯了,似乎被田小娥鬼魂附体,说话和动作都像田小娥。这样的描写,在陈忠实《白鹿原》之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白鹿原》中的这些描写,既写出了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历史与文化的某种神秘性,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家创作中这种“集体性共创”现象非一人所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陈忠实后来把作家之间这种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包括互相竞争和互相激励,称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他说:“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阔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陈忠实后来在一篇答问里又说:“《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这里所说的“志趣相投”恐怕只是就共同爱好文学而言,非指艺术趣味和审美取向,而“竞争”与“激励”两个词,实为核心概念,也应该看作陈忠实数十年身处中国文学团体之内,对同行关系在积极意义上产生的真切感受。共在一个团体,比如在陕西作协,陈忠实和路遥互相之间的“竞争”与“激励”,与对方的人格和思想有关,更与作品有关。陈忠实阅读同行特别是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用他的说法,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就具有某种“摧毁与新生”的积极作用。
良性的“竞争”与“激励”作用很大。路遥对陈忠实的影响,还表现在陈忠实既要“寻找自己的句子”,还需要把自己的“句子”打磨好,磨得漂亮。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评论家李星得到消息后一见到陈忠实就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楼上跳下去!陈忠实分明感到了文学朋友在为他着急,但他心里想,人家都得了茅奖了,我还急什么,不急,一定要弄好再说。这也促使他下决心把正在创作的《白鹿原》打磨得更精到些。
陈忠实和路遥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都以现实主义创作小说,其互相影响,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势所必然。路遥当年在陕北的时候,他的成长包括思想的、精神的和艺术的诸方面,都与他当时接触结识了大量北京知青颇有关系。当年在陕北包括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很多是清华附中和人大附中的学生,他们对路遥很有影响。在与林达、林虹、陶正这样的北京知青相处特别是交流、讨论过程中,他的思维与思路得以开启。这对他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知识以及提高艺术鉴赏力都有极大的帮助作用。陈忠实后来与路遥在一个单位共同从事创作,相互间的影响既是必然的,也是日常的。陈忠实后来回忆:他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省作协开会,或是买面粉买蜂窝煤,他才进城。“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坐在床沿上聊天”。“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总是会令我大开眼界;更有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力度和角度都要深过一般庸常的说法;他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此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便用观胜的‘球不顶’的话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不是贬义,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业已喜欢到成为惯性地在此聚合,成为交流信息、抒怀见解而又可以无所顾忌的一方自由且自在的小小空间”。陕西作协大院内的作家们在这里以聊天的方式交流见闻、议论新作佳作、介绍国外文学,以及品藻人物。笔者当年就住在大院内,与王观胜毗邻,也是常客,所以对陈忠实此段描述感到既真实又亲切。陈忠实在陕西作协大院内这个“闲话店”和“二流堂”得到其他作家特别是路遥的一些启示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影响是日常的,不经意的,看似闲淡,但如有所得,却一定是深刻的。
简单比较一下路遥和陈忠实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情况,可以发现他们早年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和创作,后来则有不同的发展,既合乎逻辑,也颇有意味。两人的早期作品,都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个人被时代风潮淹没,此后随着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加上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砥砺同行,两人都形成自己的文学个性和艺术风格,长成文学的大树。仅从作品的影响而言,《人生》是路遥的里程碑,路遥沿着《人生》顺理成章走向了《平凡的世界》;《人生》则是陈忠实的分水岭,陈忠实由《人生》的“打击”开始寻回文学的“自我”,由此走向《白鹿原》。而路遥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踞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高度,陈忠实则以《白鹿原》踞于90年代文学的高度,两个人、三部作品交相辉映。
陈忠实比路遥年长七岁,一般来讲,承认向年长者学习既不失面子也会赢得虚心好学的好名声,而公开承认曾受一位比自己年轻的人的影响,何况是同行,同是搞创作的作家,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谦虚、宽阔而又自信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陈忠实在《摧毁与新生》中说,“路遥写出了《人生》,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摆列出来,他已经拉开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茬跃上新时期文坛的作者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的被摧毁的感觉源自这种感觉,却不是嫉妒。”在这里,陈忠实固然讲了他的被“摧毁”,更讲到了他的“新生”。陈忠实在这里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谦虚、宽阔而又自信的人格。因为这样的人格,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陈忠实这样一位靠自学成为大家的作家。
陈忠实认真地阅读过路遥的不少作品,而且深有体会和心得。他在八集纪录片《路遥》第四集《夏至》中接受采访时说,路遥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就艺术而言,不亚于《人生》。他对人在困难中的那种情感、心理、行为,那种准确的把握,那个生活氛围的准确把握和表述,我是也很震撼”。陈忠实比路遥年长,但基本上同属一个时代,他对路遥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时代和生活非常熟悉,特别是对《在困难的日子里》所写的“饥饿”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因此他对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饥饿”的艺术表现有着高度的认同,他知道路遥的价值在哪里。
路遥1992年去世,陈忠实在悼念大会上以《别路遥》为题致悼词,这个悼词充满感情也充满理性,它有陈忠实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对路遥的评价,也表达了陈忠实对路遥的个人认知。陈忠实评价路遥是“中国文学的天宇”中“一颗璀璨的星”,“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绚烂的篇章”;他认为路遥“智慧的头颅”曾经“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有“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有“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的气魄”,有“朝着创造的目标”“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他评价路遥“热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的进程,热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他认为“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路遥是“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
陈忠实对路遥的评价和认知,得之于他们多年的交往,真实、准确,也充分表现出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是文坛佳话,也是研究者得以窥视他们关系和他们创作的一把钥匙。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