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几大主要文脉,发端于延安文艺传统的陕西经验,包含着自延安时期以来,陕西作家逐步形成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拓展的现实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等多方面的重要实践。陕西经验生成于延安时期以来留在陕西的第一代文学陕军,发扬光大于集中书写乡村社会文化变革的第二代、第三代文学陕军,并正在作为X世代和Y世代的第四代、第五代文学陕军中延续和传承。由当今城市时尚文化和网络虚拟空间所构成的时代境遇,与陕西文化原色之间的错位,所引发的不是文学陕军的“断代”和陕西经验的失传,而是当代文坛上陕西的“70后”“80后”和“90后”等新的文学群体孕育的可能。
关键词:陕西经验;文学陕军;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
作者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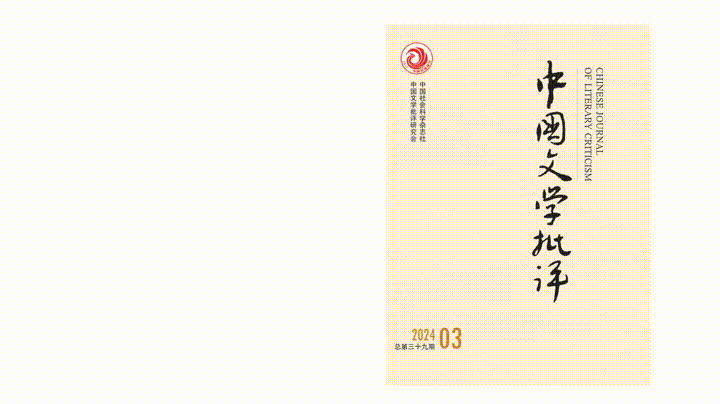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上较为独特的地方。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陕西不仅是始发地,而且也是较具代表性的实践区域。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陕西经验,绝非一个地方性话题,而是一个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文学主流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艺术现象。陕西的作家不仅为中国当代文艺贡献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其文学实践所生成的陕西经验,还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生成与陕西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层面、不同形态的传统和经验。但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传统是从陕西开始并延续下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西延安展开的文艺实践,以及作为延安文艺实践指导思想和理论总结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讲话》精神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从此,中国文学艺术各领域基本上是沿着《讲话》精神在发展。尽管其间经历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以来的多种思潮的冲击,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流传统依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贯穿始终。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传统一以贯之,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实践中,陕西作家一直是备受瞩目的一支劲旅。究其历史渊源,显然是延安文艺传统在陕西当代文学中的延续。其直接根源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延安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机构留在了陕西,成为这一传统的火种,点燃了陕西当代文学的热潮。延安时期民族化、大众化文艺实践的践行者、狂飙诗人柯仲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同时,还先后担任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等职务,其间他始终坚持写作,作品包括最终因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完成的现代史诗巨作《刘志丹》;延安时期的陕北籍作家、曾以《种谷记》《铜墙铁壁》著称的柳青,于1952年回到陕西长安县黄埔村,逐渐开始了后来成为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创业史》的写作;延安时期西北野战军的随军记者杜鹏程,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于1954年出版了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延安时期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编剧、团长的王汶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秘书长、陕西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从1953年起先后在渭南、咸阳农村深入生活,发表了《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村医》等小说,成为新中国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延安时期在鲁艺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以《七月的战争》《大进军》著称的“七月派”诗人胡征,经由西南军区、《解放军文艺》杂志辗转回到陕西;延安鲁艺学员、诗人戈壁舟,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留在陕西,在西北文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任职;延安时期参加过革命和文艺实践的作家李若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文联担任领导职务,长期深入西部矿区,完成了《柴达木手记》《在勘探的道路上》等一批散文作品,成为新中国散文代表作家之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评论家胡采,以评论集《从生活到艺术》直接将延安文艺精神传递到了当代陕西文坛,影响了几代陕西作家。这一批从延安来的作家和评论家后来被认为是第一代文学陕军的代表。此外,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主要编剧马健翎、画家石鲁等一批艺术家也都留在了陕西,成为陕西文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西北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机构留在了陕西,发展为后来的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与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陕西日报》与延安时期的《群众日报》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
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等一批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为代表的第一代文学陕军,将延安文艺的种子,直接播入三秦大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践行延安文艺精神的典范,也成为陕西经验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们的作品《创业史》《保卫延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从生活到艺术》等,被列入中国当代文学最早的一批代表作名录,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在新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延续和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也是陕西经验生成的奠基之作。这些作品直接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文学陕军,以及后来的陕西戏剧、影视、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发展。
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学陕军,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于八九十年代。他们的文学实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的。尽管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时代氛围,与第一代文学陕军有着很大差异,但从文学观念和创作道路上,依然是沿着第一代文学陕军的路线前行的。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实践是第一代文学陕军的文学道路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特别是柳青及其《创业史》,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影响是直接的、全方位的。这一点已被很多史料所证实,此处无需赘述。他们在观念和方法上所取得的诸多进步与发展,是新的时代内涵和新注入的中外文学经验所赋予的,但所延续的第一代文学陕军的文学道路却并没有改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等一系列作品,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是新的历史时期陕西经验走出的一行扎实而深厚的足迹。
以杨争光、红柯、陈彦等一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陕军,起步于20世纪九十年代,成长于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尽管第三代文学陕军引入了更多的时代因素,在观念和方法上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但陕西经验的核心因素依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延续。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从两个蛋开始》,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太阳深处的火焰》,陈彦的《装台》《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等一系列作品,携带着陕西经验,进入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新异的写法和更加深入的反思领域。杨争光有着深厚的诗歌写作和影视编剧经验,陈彦有着丰富的戏曲编剧和行业经验,红柯有着多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经验。他们为文学陕军注入了与前两代作家不同的体验方式和叙事方法,但这些方式与方法并没有与前两代作家相悖逆,而是以不同的时代精神、文化特色和行业经验,以及更加新锐的观念,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陕西经验的内涵。
由20世纪70—90年代出生的作家组成的第四代、第五代文学陕军,正在争议和选择中成长。他们的写作尽管遭遇着城市流行的时尚文化、网络原住民和Z世代的生存与写作方式等一系列冲击,但却与文坛上代表性的“70后”“80后”“90后”有着明显差异,形成“陕西的70后”“陕西的80后”“陕西的90后”等独特现象。之所以会构成这样一些独特现象,正是由于他们背后有着强大的陕西经验在形塑着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终将以不同代际的方式赓续和丰富陕西经验的深厚内涵。
经历了几代作家的接力,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生成,文学陕军的文学实践已经形成了自己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的陕西经验,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重要标识。
二、陕西经验:内涵与启示
缘起于延安时期,经过几代文学陕军前赴后继的实践而形成的陕西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传统的重要标识,是因为陕西经验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启示意义。概括来看,文学上的陕西经验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自《讲话》以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文艺发展、文艺主体改造与建构的核心问题。经由几代党的领导人的不断强调和深入论述,几代作家艺术家的自觉实践,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并由此形成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下简称“深扎”)的实践,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和重要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各地的作家中都在延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和几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当普遍,如赵树理长期住在山西老家、李季举家迁到玉门油田等。但在陕西,“深扎”现象更为集中典型。柳青“深扎”长安县皇甫村14年写出《创业史》、杜鹏程深入西北野战军战地采访写出《保卫延安》、陈忠实在白鹿原老家西蒋村居住几十年写出《白鹿原》。路遥、贾平凹本身自幼有着艰辛的乡村生活体验,即使在进城成为专业作家后,依然每年坚持行走在家乡的山山水水、家家户户间,才有了《平凡的世界》《秦腔》等这样一批典型的“深扎”事例。并且,陕西已经将“深扎”制度化、习惯化、长期化。绝大多数陕西作家都有到区县、企业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高建群在西安高新区、叶广芩在周至县、红柯在宝鸡金台区、冯积岐在凤翔县、方英文在汉阴县、冷梦在米脂县、朱鸿在长安区等。有的作家甚至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作家艺术家在“深扎”中拉近了与老百姓的关系,亲身感知了民生疾苦、具体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学习到了大量地方性知识、行业性知识,获得了在书斋里想象不到的生活体验。这就是陕西作家能够佳作迭出的真正原因,也是最重要的陕西经验。
2.始终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在文艺思想中的直接表现,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传统。作家能否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尊重生活真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被确立为评价当代文学的重要准则。
走现实主义道路,是几代文学陕军的基本共识。从《创业史》《保卫延安》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再到《装台》《主角》,当代文学各个阶段最主要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集中出自陕西。这足见走现实主义道路是陕西当代文学的基本经验,也足可证明陕西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区域。尽管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现实主义从精神到方法都在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但其反映真实生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柳青在《创业史》中面对的是中国农民到底该集体创业,还是个人创业的矛盾;路遥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反映的是中国农民该留守土地,还是走向城市、走向外面的世界的矛盾。所不同的是,柳青的结论是确定的、肯定性的,而路遥的结论是反思性的。而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中国农民又一次回到集体创业与个人创业的艰难抉择之中,但与柳青不同的是,杨争光的结论是批判性的。尽管作家们因面对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不同而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断,采用了不同的写法,但他们直面现实、力求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现实主义原则却是一致的。同时,随着作家们的文化视野、个人经验和文学体验的流变,现实主义在不同代际的陕西作家笔下,融入了不同的元素和写法。陈忠实的现实主义融入了一部分魔幻色彩;杨争光的现实主义融入了较多的荒诞色彩;贾平凹、红柯的现实主义融入了更多的浪漫气质;陈彦的现实主义则更多地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喜剧化;而陕西的“90后”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时代》则又将乡村社会现实的书写延伸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写法。陕西经验在告诉人们,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而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作家对现实所做出的不同感知和体验,以及所采用的不同写法,正是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塑造出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典型形象。在陕西作家越走越宽广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大批典型形象。梁生宝、梁三老汉、高家林、孙少安、孙少平、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庄之蝶、引生、刘高兴、刁顺子、忆秦娥等都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其中有的形象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同时,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也在不断地被延伸到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陕西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陆续被搬上舞台和银幕,《人生》被改编为电影;《平凡的世界》两次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年又被改编为话剧;《白鹿原》被改编为秦腔现代戏、舞剧和话剧,以及电影和电视剧;《鸡窝洼的人家》被改编为电影《野山》;悲剧色彩浓重的《高兴》被改编为同名喜剧电影;《装台》被改编为电视剧;《主角》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近年来,陕西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柳青、路遥也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先后出现了话剧《柳青》、电影《柳青》、话剧《路遥》等。这些改编作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扩展版,将文学中的一批典型形象扩展到了舞台和荧屏,并通过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送入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
几代陕西作家艺术家连续不断地推出反映不同时代现实生活的力作,塑造出不同时代、不同特质的典型形象,共同延续并拓展了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使现实主义成为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三秦大地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肥沃土壤。
3.始终保持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众所周知,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集散地。因此,陕西作家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是天然的,且在其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首先表现为陕西作家充分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禀赋。这种禀赋是中国传统文人数千年来在绵延不断的“文”“道”关系中形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关学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这种精神禀赋的准确表述。在陕西的当代文学中,无论是第一代文学陕军的代表柳青的《创业史》,第二代文学陕军的代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还是第三代文学陕军的代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陈彦的《主角》,都立足于书写社会历史的史诗式巨变,都是对乡土中国及其人的生命和命运的深重关切、对“时”与“事”的讴歌和书写,都是道义担当、文脉延续、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真实写照。
在作家们的写作中,直接书写、延续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陕西作家的突出优势和特色,也是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阐释,但归根到底是一部文化小说。其所讲述的是以关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社会变革的冲击下,如何一步步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该作讲出了作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其中有赞赏、有反思、有惋惜、有批判、有期待,是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审视。截至《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如此集中而深入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还比较少见。
贾平凹的写作始终是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进行的。他对佛、禅、道,以及金石、书法和文人画的浓厚兴趣人尽皆知。他生长于陕南商洛,其性格中本身延续着复杂的文化基因,融合了楚文化的灵性和秦文化的坚韧。贾平凹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他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自觉沿用。无论是从汉字、汉语到汉诗的“立象尽意”的象征传统,佛道哲学中的静观美学与空间叙事,还是志怪、笔记、史志,以及古代的白话世情小说、文人小说等,中国传统叙事中的种种传统,都能在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中找到尝试的痕迹。在当代作家中,始终自觉延续中国叙事传统者,非贾平凹莫属。
陈彦自幼进入戏剧院团,从演员到编剧,再到团长、院长,一直到中国剧协领导,其对传统戏曲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其代表剧作“西京三部曲”是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标志性作品。尽管进入小说写作较晚,但其小说“戏曲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不仅以密集的行业性知识书写了当下社会中梨园行里的人生百态,而且将戏曲这一最精粹、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到了当代小说的视阈之中,绽放出独异的光彩,且以《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
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作家,在陕西非独上述几位,还有众多作家以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风格和叙事方式呈现着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血脉联系。与此同时,陕西的画家、音乐家、导演大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怀。例如,长安画派明确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为艺术宗旨,并以此将传统国画现代化;赵季平等在陕西工作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几乎都与传统戏曲音乐、民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之所以如此集中地出现了这么多关注并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陕西,在中国传统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必然会成为陕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始终坚持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之路
陕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起始地。史料和传说中记载的神农氏炎帝、“治五气,艺五种”的黄帝,以及作为炎黄后人和周部落祖先、“教民稼穑”的农神后稷等农耕文明的始祖,都是在陕西的土地上开始耕种的。即使在当今中国,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之一,以及被誉为“中国农业奥林匹克盛会”、定期举办的“中国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都落地陕西杨凌。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陕西应该是乡土中国的腹地。因此,几代文学陕军大多以乡村叙事为主。有人甚至由此认为文学陕军是一支农民大军,缺乏现代性。但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文坛,文学陕军真正集中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尤其表现在乡村叙事方面。从鲁迅、沈从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陕军构成了现代乡土叙事的一条主线。仅就文学陕军而言,如果将其书写的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按照时间顺序连接在一起,便可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陈忠实的《白鹿原》从废除帝制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革写起,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柳青的《创业史》从新中国农村变革写起,书写了乡土中国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过程;贾平凹的《古炉》和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书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境况;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青年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奋斗史;贾平凹的《秦腔》《高兴》等书写了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农民与城市的关系;而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则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作家们书写的这条道路尽管弯弯曲曲,但却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一步步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完整历史。这正是一条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其中揭示的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历程蕴含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因此可以说,真正完整书写了乡土中国现代化、接续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恰恰是被视为“乡土作家”的文学陕军。
三、陕西经验生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陕西经验生成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前述的延安文艺和《讲话》精神,而文学陕军整体上所接续的精神禀赋和传统文脉则更加深远。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大重要文学传统,几乎都淤积在陕西的厚土之中,像岩矿一样一层一层深埋在地下,却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
首先,无论是从史料还是从传说中都可获知,我们今天书写文学作品,从古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其诞生与陕西颇有渊源。在史料和传说中,最早造字的仓颉,是黄帝的左史官,出生于陕西白水史官村。“仓颉造字”尽管是传说,却也是史料中记载的关于汉字诞生的历史依据,也是汉字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而汉字发展的第二块里程碑也立在陕西,那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即所谓“书同文”,完成了文字国家化、规范化的过程。
用汉字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书写文学作品则是从西周开始的。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建都镐京(今西安市内),周公旦在这里制礼、作乐、修史,便有了后来被孔子编辑成书的《诗经》《尚书》《周礼》《乐经》《易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其中,设“大司乐”,立民间采诗制度,使《诗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第一大文脉,并由此开启了中华文脉。
以《楚辞》为代表的另一条文脉缘起于长江流域,但以楚人为首的多支秦末农民起义大军,先后涌入关中,占领咸阳,最终由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楚人入主关中,自然将缘起于长江流域的楚歌楚舞引入长安,一时长安城里、汉帝宫中,楚歌楚舞弥漫,这一情景被刻在汉画像石中,至今可见。更有甚者,当地文人纷纷仿作《楚辞》,实则是将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与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汉赋。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事实上,汉赋受《楚辞》影响,从宋人朱熹到近人郭沫若、陆侃如也有论述。由此可见,即使形成于长江流域的《楚辞》传统也汇入了关中长安,并促成了汉赋的诞生。
汉朝延续并扩大了周朝的民间采诗制度和秦朝的乐府,又加设了“太乐府”,大量从民间采集歌谣,并与文人诗歌融合,形成了乐府诗歌传统。这一传统赖以生成的“采诗制度”,尽管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观察民情所设,但在客观上为文人创作开辟了源头活水。这种文人创作汲取民间文艺的传统,直到延安时期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文艺思想,成为文人创作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一条坦途。由此可以发现,文人创作与民间文艺相互融合之路的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都树立在陕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汉朝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开辟的又一条重要文脉,便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尽管是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却对文学叙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让后世的小说、戏剧、影视的叙事艺术较难超越。而司马迁则是生长于陕西韩城,其任职、撰述《史记》均在长安。
及至唐朝,中国的几大文脉均臻于成熟,且又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吸纳了外来的佛教和西域文化的诸多元素,以及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养分,最终融合为一座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学高峰——唐诗。仅据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完成编校的《全唐诗》收录,就有诗歌48900余首,诗人2200余位,共计900余卷,仅目录就有12卷。这些诗人当然出自各地,但大多云集长安,使长安成为人类诗歌文明的重镇。
唐以后的陕西尽管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不再孕育新的文脉,但以宋代的张载、蓝田四吕,明代的冯从吾,清代的李二曲,以及近代的刘古愚、牛兆濂等为代表的关学,不仅发展了儒家学说,还开启并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发展。他们提出并践行了“横渠四句”所倡导的中国文人的责任担当和精神禀赋,制订了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乡村自治方略,为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对陕西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了近现代。近代的于右任、张季鸾、吴宓、李仪祉等重要历史人物,都同出于关学大儒刘古愚门下。关学对当代的文学陕军的影响既是深层次的,也是直接的。陕西作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和书写、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担当,以及陕西经验中的“深扎”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都与关学有着深层次的、潜在的联系。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受到“蓝田四吕”的《吕氏乡约》的直接启示,才萌发了写作动机的。《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更是以关学大儒牛兆濂为原型的。
这些一层又一层的文学、文化传统,淤积在陕西的沃土之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文学气场,直接或间接地形塑着当代陕西的作家、艺术家,成为陕西经验形成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渊源。
四、关于陕西经验的赓续与发展问题
时代在流变,历史文化语境在不断转场,陕西经验作为在数千年历史文化演进,以及延安文艺背景下形成的稳定而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能否得到赓续和延伸,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随着邹志安、路遥、陈忠实、红柯等一批文学陕军主将的相继离世,陕西文坛的上空阴云密布,人们也在为文学陕军的未来感到担忧。同时,随着中国文坛上“70后”“80后”“90后”相继登场,又有人在多地报刊发文讨论文学陕军会否“断代”的问题。这些担忧和疑问,除了对文学陕军意外减员的惋惜和关切外,也包含着对陕西经验能否在后几代作家中延续下去的问题的担忧。
意外减员当然是一件让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关于“断代”的问题,笔者认为是由文化错位造成的。
在中国文坛,“70后”真正引起人们关注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代表作家有付秀莹、乔叶、盛可以、鲁敏、魏微、弋舟、田耳、石一枫等。其中一些女作家,以惊世骇俗的身体写作、隐私写作震动文坛,标志着与上几代以乡村叙事为主导、以严肃的社会问题为文学主题的作家们的根本区别。她们多居住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繁华都市,沉迷于对都市时尚生活和感官体验的书写,渲染出与上几代作家所面对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气息,因而给人们造成了对“70后”的固定认知:比“60后”更加开放的、时尚的一代。稍后继起的“80后”,被称为网络原住民,抬脚就踏入了网络写作的历史,其代表作家韩寒、郭敬明等以强烈的青春气息和叛逆姿态,以及天然的媒介驾驭能力和旋即转战影视娱乐圈的行动,展现出与前代作家迥然不同的风貌。
这两代作家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环境多为城市时尚文化和网络虚拟空间,与陕西的文化原色——农耕文化和传统文化——有着巨大距离和本质差异。陕西不大可能成为书写城市时尚文化和营造网络虚拟空间的代表区域,因此,也就不大可能出现被文坛定性的“70后”“80后”代表作家。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陕军所面临的不是“断代”问题,而是文化错位问题,是陕西的文化土壤与文坛固定认知的“70后”“80后”作家成长的文化空间之间的文化错位问题。事实上,文学陕军并没有“断代”,陕西有自己的“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而且有着与文坛上被固定认知的“70后”“80后”“90后”作家完全不同的特质。这种不同便源于在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陕西经验。
陕西的“70后”“80后”“90后”与国内文坛的同代作家有着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和相近的感知方式,也大多生活在城市,浸染着程度不等的时尚生活和相似的新兴媒介环境。但他们同时生长在以农耕文明为原色、积累了深厚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他们的前辈作家已经在这块沃土上耕耘出了一条深远的文学传统,积累起厚重的文学经验,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学气场。他们只要在这块土地上写作,就不可能不受这个气场影响。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一批作家,在网络上被称为X世代,在陕西文学格局中,应该被叫做第四代文学陕军。其中仅以小说见长的就有寇挥、侯波、杜文娟、王妹英、周瑄璞、吴文莉、陈仓、贝西西、范怀智、陈毓、冯北仲、黄朴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近年来,弋舟以专业作家身份加盟陕西,进一步加强了第四代文学陕军的阵容。这批作家的书写既有文坛上X世代作家的共同特征,如更加注重越出大历史观的个体经验、感知世界更加丰富细微、写法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同时,又延续了陕西经验中的种种传统,与文坛上其他区域的同代作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譬如,他们中间很多人依然深耕乡村生活;他们也写城市,但很少写城市的时尚文化,而是写城市的底层生活、城市人的奋斗史;他们可以写刻骨铭心的苦难、饥饿,写农耕、写中药、写戏班子、写木匠活儿、写移民史、写援藏生活、写打油井、写老年人的孤独,写其他地方的同代作家很少触及的生活和体验。他们和前几代陕西作家一样“深扎”在村庄、矿井、移民族群、援藏队伍、知识分子、孤独老人的群体中,尽管他们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集中“深扎”在乡村,但不管“深扎”在哪里,都是“深扎”在了生活之中,“深扎”在了老百姓之中。他们不全是在观照乡村的现实,但不管是乡村的、城市的还是过往的现实,都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重要的是陕西经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没有被改变。
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陕西,从管理层到社会公众,高度重视作家后备队伍的成长。近年来,陕西省实施的专门资助中青年作家、艺术家的“双百计划”,在加强上述“60后”“70后”作家队伍的同时,也在扶持“80后”“90后”作家群体。这批被称为Y世代的作家可以整体上被视为文学陕军的第五代,其中以小说见长的就有“80后”的杨则纬、张炜炜、丁小龙、周子湘、风圣大鹏,“90后”的范墩子、王闷闷、高一宜、杨可欣、王安忆佳、孙雨婷、献乐谋、安心对阳等。第五代文学陕军尚在成长过程中,而且不断有新人加入,特别是从事网络小说写作的作家已形成了一个较大群体,并组建了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这批作家没有涌现出韩寒、郭敬明式的网络写作的代表作家,也很少有人从文学转战影视圈,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Y世代,他们的体验和感知方式比前几代作家更加轻松自由,想象力和表达方式更加开阔。他们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活或网络虚拟世界,写作习惯更多地适应网络,有的甚至喜欢在咖啡馆写作。这些都是与前几代文学陕军不一样之处。然而,他们对陕西经验的接续依然具有自觉意识。“80后”作家杨则纬在接受“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采访时,明确表示:“在陕西这片土地上,我学习着前辈作家的写作精神,同样我也坚守着自己的写作理想。”“90后”作家范墩子依然在写乡村,写大变革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生百态,他依然像前几代陕西作家一样在关注着乡村现实,但写法上却执着于对超现实主义的探索。
无论是X世代还是Y世代,第四、第五代作家都还是文学陕军的新生代,他们中间尽管还没有出现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那样的标志性作家,但也都已经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有的已经频频走上了各类文学大奖的领奖台。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经表现出强大的潜力和后发优势。特别是他们作为文学陕军的后备力量和陕西经验的传承者,在新的时代境遇和历史文化语境中,依然天然地携带着与中国文坛上被人们广泛认知的“70后”“80后”“90后”不同的风貌与特质,预示着陕西经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的文学实践,将会在后几代陕西作家们的写作中进一步延续、发酵,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独特而富有代表性的景观。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