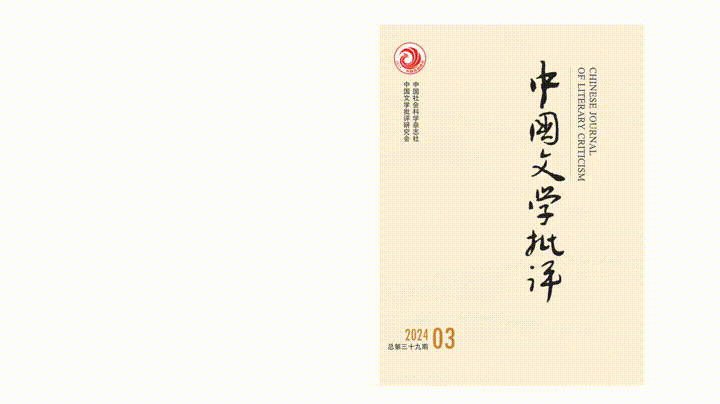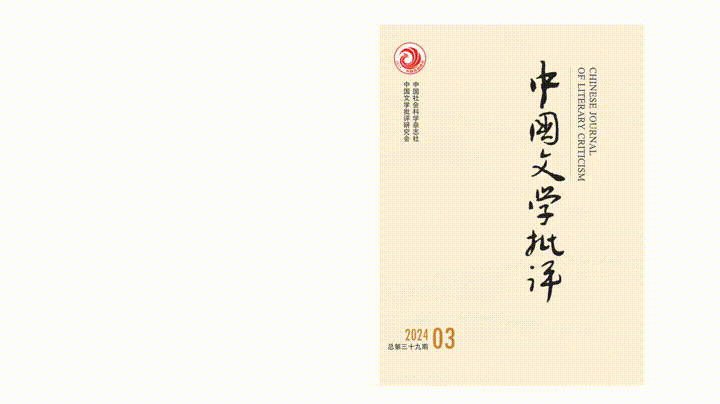
“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近几年成为热门话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地方化”“空间叙事”“作家群”“文学流派”等相关概念不再单纯以文化习俗、行政区划、写作风格划分,而是与“区域化经济”高度重合,其反映的文学现实也与该区域的发展形态相关。如“新南方写作”与粤港澳大湾区气质相通,有着思想开放、认知前沿、文化多样性等特征;“新东北文学”有着东北老工业区坚韧、执着、丰饶的印象。过去学术界将这些问题笼统归入“区域文学”“文学地理学”等体系中研究。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地方作家群现象更加动态化、跨学科化,不仅反映了文学与地理空间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更意味着数字时代的传播路径、经济特征、文化传统复兴等多种新要素的参与。文学以地方化命名的方式出圈、破圈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多维度视角分析,这个议题也成为文学学科新的研究热点。
新的文学的地方化命名的形式、功能、传播方式均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一是中国文学的地方化命名的分类标识规则发生变化,二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文学标识分类的转型,三是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建构与社会发展如何同步。
一、中国文学的地方化命名的分类标识规则
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内核是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某种属性上的归类,其形成和发展在文学史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频繁更迭的文学思潮属于时间性结构,是一种先验的直觉形式,而流派作为地域性、空间性的产物,更容易被固定和凝视。通过对这类文学现象的归类总结,可以找到文学的某些发展规律。而被符号化的文学标识概念在信息时代更易于传播,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追溯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历史化过程,从大量的文学史例证中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艺术群体的出现有其社会总体性因素,其内部成员既有显著的相似风格,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其中常常有文学高峰的出现。杰出文艺家往往有一个群体来映衬。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做过大量研究,发现人类杰出的作家、画家都有其地方性和社会总体性因素起作用。以莎士比亚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莎士比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而丹纳发现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同地区就有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具有同样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表达:“同样暴烈与可怕的人物,同样的凶杀和离奇的结局,同样突如其来和放纵的情欲,同样混乱,奇特,过火而又辉煌的文体”。丹纳同时还列举了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例子,只要去比利时多参观几座教堂就会发现,鲁本斯并非人们所说的前无师承、后无来者,而是“有整批的画家才具都和卢本斯相仿”。他们的画作有着相近的题材和表现形式,甚至连画中人物服饰的铺绣盘花、衣料、绸缎与红布的反光都相似。
中国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杨义认为文学研究与地理结缘是“为了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将地域的独特气质作为全书的结构,如“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等,他认为“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属‘北方文化’,又濒临黄海,与‘东部’有缘,所以山东作家群既富于凝重的道义感,又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创作自近代以来开始形成潮流,但中国文学史上地域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神话《山海经》时代开启,下经十五国风、汉魏人物志、两晋先贤耆旧传、宋元方志、明清志书等,直到民国府县志、当代分省域文化史和文学史著等,代不绝书”。
中国古代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其地方化命名以某一风格或流派的文坛领袖为标杆,并以该领袖的籍贯为名称,其影响也不限于一时一地。如江西诗派因黄庭坚为江西人而得名,而赞成和追随“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诗歌理念的该派诗人却并不都是江西人。南宋末年,日本的五山禅林学习借鉴江西诗派的句法、用词等技巧,并做出香谱注释,此时离黄庭坚时代已过100多年。桐城派以其“四祖”的籍贯而命名,以其相似的文学风格和艺术观念影响深远。
五四时期的文学团体多以文学社团的形式出现,不拘泥于地域性的影响,侧重于文学趣味、理念和风格。“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些文学社团有的注重强烈的现实主义,有的倾向表达个人情感和内心体验,均不是以地域为纽带。京派、海派虽然有地域性特征,但总体上却以文学风格和群体认同为依托。
当代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是将特定地理区域发生的文学现象、风格、流派或思潮,形成凝练的标识语。真正以地域为纽带的文学地方化命名在“十七年文学”体现得比较充分。这一时期的作家处于相对自足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作家的流动性也较弱,其创作地方性特征较强,流派也往往以地方命名。
在“山药蛋派”的核心人物赵树理的影响下,一批山西青年作家承袭朴素生动的写作风格,被简称为“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其写作关注当时中国社会重大问题,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妇女新生活等。其作品以农民为描写对象和阅读受众,采用口语和简洁生动的句式。
同样描写北方农村,“荷花淀派”亦有强烈的地域风格。其代表作家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是河北人,其书写对象和写作主体都有特定的空间性质。该派作品整体上呈现着朴素的情感、明丽的格调与清新的文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浪漫精神也得以继承。其名“荷花淀派”更有着自然写作和生态关怀方面的艺术探索。
“‘茶子花派’的氤氲和形成,只是一种非组织、非自觉的文学见解、创作思想、题材内容和艺术韵味上的默契。”艾斐列举的作家除了旗帜性人物周立波以外,主要有叶蔚林、张步真等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学湘军”。被称为“茶子花派”的作家作品风格、题材各异,但都以湖南为书写对象,深入基层、把握现实,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以“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为典型的文学地方化命名的文学群体,初步实现了文学地方化命名的转型。以区域为纽带的精神个体,在思想、题材、创作手法大体相似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写作群体,使得该地区的文学风气日盛。三个典型的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写作群体注重小说干预现实,其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社会变革。在表现了生活的美的同时也揭示了矛盾和问题,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理解生活。其现实主义创作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标准的很好的诠释。
二、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
文学的地方化命名就是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种体现。近几年出现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其概念背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气象,与共建“一带一路”、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乡村振兴战略、经济全球化现象等有深刻的关联。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地方化命名参与了文学研究方法重构和精神文化重建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的勃发、西方文化的大量引入的同时,国人将目光返还自身传统。“寻根文学”的潮流推动着文学地方化的发展,对文明、文化风俗的反思朝更理性更深入的层面推进。文学研究也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新时期,学术界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作家群、文学流派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对较为突出的作家群进行命名,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并产生一系列文学研究的话题。
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有着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国际交流中的对话能力需要文化加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受到重视,本土文化传承放在全球语境下更凸显其价值,更容易落到实处。因此,文学分类标识发生了转型,出现了“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文学新浙派”等各种以“新”命名的文学分类标识。“新南方写作”拓展了地域范围,不仅包括了国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和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等地区,还延伸到了海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文化背景。“新东北文学”(或称“新东北作家群”)的前身“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抗战’,那么当下 ‘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 ‘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艾伟在“文学新浙派”研讨会上致辞:“浙江是诞生文学的一块土地”,他回顾了现当代浙江文学史,“以鲁迅、茅盾、郁达夫为代表的浙江现代作家光芒闪耀”。“文学新浙派”的提出,是对浙江现代文学作家的致敬,也是对他们精神的传承。这一地方性命名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对浙江文学史、文化传统的再确认。
由于批评家和作家的双向参与,每一个地方性命名最终都上升到普遍性。以往的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概念由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提出,而新的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概念是由批评家与作家共同促成的。如2023年5月14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杂志联合主办的以“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为主题的论坛上,与会者除了批评家外,还有东西、周洁茹、林森、王威廉、霍香结、陈崇正等多位作家参与。批评家与作家共同讨论、丰富和发展“新南方写作”概念。“文学新浙派”由浙江省作家协会艾伟、钟求是、哲贵等作家发起,由孟繁华、贺绍俊、谢有顺、张燕玲、张莉、杨庆祥、刘大先、曾攀、行超等批评家进行概念阐释。虽然文学的地方化命名强调的是地方性的文学概念,立足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和文学发展,但本质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为当下文学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探索出一条路径,朝向整体的人类意识、人类文明大方向发展。每一个文学的地方性命名都有其抑制不住的向外进取的力量。
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的认识论基础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崛起。民族精神落到实处就会凸显其地域性。中国各地长期形成了各自的区域文化特征,每个作家作品的呈现方式都带有地域性特征。即使是以普遍事物和现象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也是基于各自的地方经验与生活视角。而文学本质上也正是经过概括和提炼的、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精神符号。“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家在描写地方文化方面已经不同于老一辈作家。他们已不满足于地区风俗的介绍、神秘或特色文化的呈现,而是以广阔的世界性视野进行深刻而辩证的反思,其作品体现出自身文化在人类文明中所处的位置和所作的贡献。潮汕文化是粤语文化的一座宝库,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写潮汕侨商郑梦梅“下南洋”的奋斗史,年轻人沿着韩江的任一条支流去了马六甲、暹罗、安南等,而“平安批”这个特殊物件在小说中承载了家与国的意义。厚圃的长篇小说《拖神》通过潮汕商人陈鹤寿及其商帮的命运来展现樟树埠的崛起与没落,以人、神、鬼的多重视角展现潮汕平原的人民自近代以来的精神追求。熊育群的《金墟》则以赤坎古镇的变迁描绘广东侨乡文化、讲述当地乡村振兴的故事。林白的《北流》以极具个人化的写作风格,展现了一座南方小县城丰富驳杂的生活史,同时通过附加一部语言词典,凝练地呈现了粤语的文化价值与美学价值。林森的《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描写了一群租住老旧房屋的年轻人想要突破困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折射出全世界现代年轻人共同面临的情感和生活困境。朱山坡将目光投向非洲,创作了一系列援非题材小说。《萨赫勒荒原》中援非的中国医生提倡对尼日利亚的野生动物、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索马里骆驼》中的“我”决定继承父母的遗志,为当地饱受海盗和战火蹂躏的老百姓送去帮助与爱。“新南方写作”作家群体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既挖掘了自身文化、聚焦地方发展,又将目光投向远方,关注人类总体发展趋势,在文明向度上呈现以世界为中心的视野。
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有着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特定地理区域的文化生态、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等因素,无疑影响作家的审美观念、创作手法以及作品主题。在强调文学的地方特色的同时,超越地域限制所蕴含的普遍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是作品是否具有更高层面意义的关键。地方文学不仅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也是全人类共通情感和经验的表现形式。东北作家的标签既不按风格、题材,也不按思想倾向,而是按东北自身的地域因素。东北作家早期影响较大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马加等被称为“东北作家群”。而“新东北作家群”囊括了“70后”作家贾行家、赵松,“80后”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无论是老“东北作家群”还“新东北作家群”,都并没有刻意要形成某个群体,作家内部也没有像其他群体一样有特定的核心人物或发起者。东北作家自发地遵从文学本身的规律,一批优秀作家涌现后,批评家后知后觉地进行了地方化命名。被称为“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各有特色。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在悬疑小说中折射出东北甚至中国的时代景象;《刺杀小说家》以现实与玄幻两条线索的复杂交错,探讨了勇气、正义、爱与牺牲的永恒主题。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探讨了东北老工人后代的人生困境与生活态度,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关注国企下岗工人如何生活的问题。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以悬疑手法展现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权力斗争、人性扭曲;其短篇小说《仙症》通过吃“刺猬肉”等魔幻现实主义的情节,反映了东北的社会历史与乡土民俗,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成长的艰辛过程。除了“铁西三剑客”这一批年轻作家,还有迟子建、老藤、鲍尔吉·原野等活跃的老作家。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以草喻人、别具一格,将人与草木气息相通、精神关联的那种不可捉摸的灵性,用语言和结构表现出来,灵动而厚重。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既接地气又有空灵的诗意,与其他描写现实的东北作家风格迥异。由于东北经济的活跃度较弱,作家本能地坚守文学本身。
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与文化经济化的内在冲动有着一定关联。为打开旅游市场,扩大地方知名度,作家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出于文联、作协、文化旅游部门的工作需要,以及地方的经济发展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作家以团体的形式出现,更具有地方化效应。21世纪以后,文学地方化命名已经开始被纳入文化资源,《2011—2012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将当代作家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介绍,并将当下活跃的北京作家命名为“新北京第三代作家”。文章认为以老舍为代表的新北京第一代作家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变化。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等第二代作家则关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代作家指大致出生于1948—1958年间的北京作家,如史铁生等,是当代文坛的重要群体。“新北京第三代作家”在学术上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其命名缺少学理支撑和概念阐发。但就地方政府决策参考的智库报告而言,研究者整理了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材料。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化发展报告都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角度重新盘活作家资源,文学杂志也着力推进地方化命名。《北京文学》从2023年第1期开始推出“新北京作家群”栏目。该信息的传播引发了集体效应,各地“作家群”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河池作家群”“昭通作家群”“阿坝作家群”“百色女作家群”“汨罗江作家群”“温州作家群”等。历史文化名人与新兴作家群的联合也是文化经济化的趋势。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成为社会发展趋势,文学的地方化命名也带有强烈的经济属性,文学也在地方文旅中扮演着形象代言的角色。这也表明,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各地珍视和传承自己独特的文学遗产,方能创造新的发展路径。
文学批评视野的拓展,促进着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研究者考察地方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现代化语境下如何保持地方特色,地域文学如何提升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能力,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跨学科视角在文学中的应用也激励文学分类标识的转型。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文学地方化命名的研究中,如通过空间理论(文学地理学)来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地域空间构建,运用族群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来剖析不同地区文学的群体性和差异性,探索历史文化名人(历史学)的文脉传承与作家群体的生成的关联性,全球视野中的文化交往(传播学)对地方化命名的参照(国别文学属于广义上的一种“地方文学”)。多学科融合为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视野。文学本质是他者与自我的镜像关系,文学的分类标识转型的轨迹,包括变动、解散、重组等都真实地映照着社会发展轨迹。
三、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发明与构建
文学的地方化命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作品反映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掌故、民俗文化、方言俗语等。作家在地域文化熏陶下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生活经验、个人感知、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虽然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审美特征,但其群体效应与标识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作家和批评家发明与构建的。文学研究者将这种具有独特标识性的文学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从符号化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度关联及其规律性,以及文学创作的空间分布、叙事策略的基本规律。
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有着随时可能发生的聚合与离散。西方理论界有“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但西方国家的作家频繁迁徙流动,跨国界比较常见。因此,西方文学很少有地方化命名。研究者为了方便研究,作出“俄国作家”“法国作家”等国别划分。而在中国读者看来,西方作家鲜明的标识符号不是地域,而是宗教信仰、艺术流派和主题精神。同为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在艺术风格和题材上区分并不明显,而同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卡夫卡、普鲁斯特的作品却一眼能分别。中国文学的情形则不一样。鲁迅、陈忠实、柳青、沈从文、周立波等都是乡土文学作家的代表,被指定为各自地域文化的精神领袖,其乡土是由地方文化风俗构筑起来的乡土。“新南方写作”中的作家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地区,如:邓一光的作品有湖北的风俗和语言特色,熊育群承接的是屈原的汨罗江传统,葛亮有掩盖不住的江南文人气质。他们作品中偶尔掺杂的一些方言也是经过“翻译”和锤炼的。蔡东、王威廉、南翔等作家的作品地方印记淡薄,倾向于时尚与创新,与他们身居具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城市深圳有关。新的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更具有包容性,模糊了作家籍贯、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艺术手法,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有着很大关联。国内的粤港澳大湾区、福建、广西、台湾,海外的东南亚地区,是人才流动频繁的地域,其作家来自五湖四海,这一情况反而成为新的地方化命名优势。一种文化被他者的眼光审视后,才有真实感和本质感,这也是为什么外地作家写粤语区文化反而更加生动、厚重。被西北黄土地养育的陈继明来到广东后,潮汕文化对他的文学生命恰好形成互补。他的《平安批》中的语言在粤语区以外的读者看来具有浓郁潮汕文化和广东地方韵味,而在粤语区本地人看来则是被改良的粤语,更易于理解和传播。生长于荆楚文化里的邓一光,其文学视野跨越了地域的范畴。《人,或所有的士兵》虽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香港战俘为题材,但其精神向度却在人性探寻、存在本质、文明发展逻辑等基本问题,把区域文化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审视。
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与旧的区域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由多种文化背景组成的对话系统。它有着多重的话语模式、价值体系、文化系统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解散和重组。“新东北文学”的“新”也来源于“70后”“80后”作家的广阔视野和多重文化积淀:双雪涛既能写《刺杀小说家》这样的玄幻小说,也能写《平原上的摩西》这样的现实小说;班宇成为湖北作家后,会不会用《逍遥游》的风格续写南方城市的人和事,“新东北作家群”的动态更是值得期待;陈春成作为“新南方写作”成员,其《夜晚的潜水艇》本身不具有任何地域特色,从小说中看不出他是一位福建作家,他入职武汉文联后,也不会因地域问题造成困扰。
地方化命名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的地方化命名容易陷入一种封闭的功能性文化保守主义。但这里要分清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地方化命名。一是“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作为跨省际、跨行政区域的文学团体,其优势不为一时一地之利。作家写作出于自觉,学术评论也是自发,文学团体的命名、文学现象的批评、文学史的书写,都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立场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它们没有财政和行政力量,而是有批评界和传媒机构进行宣传推动。研究者和宣传者形成一种默契,将其作为新的话题和文化增长点。二是省籍化文学地方化命名,如“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文学湘军”“文学陕军”“文学桂军”等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文学地方化符号。省籍化文学命名一直很活跃,各省的文学团体有体制力量保驾护航。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各地文旅部门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地方文化的振兴方面不遗余力地挖掘整理、提炼提升,也是一种文化繁荣的表现,但也容易陷入文化保守主义和视野的局限。而“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这种没有具体的机构出面支持的文学派别,其兴盛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处于文化边缘区域的作家敢于对文化中心区域的作家生发出一种竞争意识,有着区域文化自我意识觉醒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显示,民国时期的作家往往进入北平和上海两地,才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例如沈从文和丁玲。而在当下的中国,四川、广西、新疆、陕西、东北等非中心地区都不乏一流作家。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命名,它们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是以人为核心的作家群具有流动性。“新南方写作”成员陈春成和“新东北作家群”的班宇都入职武汉文联,如果单纯从地方化命名的角度研究其作品,就会出现困难。二是其开放包容的姿态缺少明显的边界,甚至成员内部的认定也存在分歧。文化区域化命名与省籍化命名不同,具有强大的收编能力,在中国的岭南地区及海外的东南亚地区使用着多种方言或语言,生长在这些区域的作家大多都能使用其中的两三种语言。以语言为界限显然有概念归纳上的缺陷,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化开放程度众所周知,它吸纳了岭南以北的方言区(包括湘方言、赣方言、吴越方言、北方方言等方言区)的作家,而在提到“新南方写作”的核心作家时,往往将这些方言区的作家排除在外。三是容易掩盖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林白与林棹同样是探索异质文体、进行实验性写作,但其一个将触角伸向传统,一个将感知投向未来;葛亮与魏微同是岭南以北的文化身份,但一个深厚温润,一个细腻绵长;邓一光与熊育群同受楚地和粤地的文化熏陶,一个向历史纵深开掘,一个向社会现实进发。如果把文学地方化命名看成一种文学集结号,其功能之一便是使个性趋同化。四是共享一种理论框架、思想资源和精神气质。地区观念容易保守陈旧、僵化审美,导致固步自封。正如文学批评界流行的简单代际归纳,抹杀了创作主体审美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谓“70后”“80后”作家的归类,只不过是方便叙述的无内涵的空壳概念。
地域文化是文学的重要资源。通过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或许能建构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文化主体。而如何超越文学地方化命名的局限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是要将展现地域特色与彰显中国色彩、发扬世界面向相结合。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概念,文学的地方化命名往往暗含着与中心的审美对峙。文学表达涉及器物、制度、观念等多层次的文化概念,需要区分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把握和认识其流动的空间性。优秀的作品尽管带有地方气质,却包含着人类共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世界意识与地域特色相结合,才能使地方文化焕然一新。那些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学写作,总是有突出的、强烈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情感。
二是要勇于创新,认识和把握随时流动与变化的观念,打破“文化就是传统”的刻板印象。文学创作的同质化是地方文学发展的顽疾,便捷粗暴的命名,容易掩盖深刻细腻的文化内涵。同类作品之间缺乏思想和审美差异,显得雷同而乏味。这需要打破僵化的模式,挖掘新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新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的融入,能够使地方文学既保持地域特色,又具有时代感,在借鉴和吸收其他地域、民族的文化的同时,与现代化建设保持同频共振。
三是创作主体需要进行自我挑战。作品的优劣取决于作家的视野和精神的高度,作家的主体意识决定了作品的精神向度。而在文化挖掘与创新表达方面的超越,取决于该地区的文化开放度。如在经济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作家不断深入挖掘岭南文化与海洋文化,其产生的文化自信又反过来帮助提升该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在东南亚的多元文化资源中,创作者通过吸收异质文化,探索新的叙事模式,发展出新的艺术手法。“新东北文学”则可能继续深入剖析东北地区的历史变迁、工业遗产、社会生态和人文精神,同时结合新时代背景,寻找并展现东北地区的崭新面貌和转型力量。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是一种流动性的、未来性的、全球视野下的本土书写。
结语
文学的地方化命名作为一种被发明、被构建的地域性精神文化,对地方的文化风气有激励作用。作家通过作品塑造鲜明的地方特色、地方化符号,传承和弘扬了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反过来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独特的素材,激发读者的想象,使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以陌生化的审美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提升精神文化,文学的地方化命名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提供凝练的精神文化符号,在信息化时代方便传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有利于在文学传承中聚拢和发展新的文学力量,以新概念、新方法激发文学创作,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是一种品牌标识,也是某种精神气质和艺术性格的体现。在全球语境中坚守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一大贡献。数字化时代信息弥漫,在文学日益类型化、精细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地方化命名以一种团体的面目出现,突破旧的文学地方化命名的窠臼,有利于将被遮蔽的文学样式彰显出来。
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正在重塑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愿望,并积极转变为重要角色。在全球化语境下,新的文学地方化命名还可能通过翻译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走向世界,为中国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贡献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这一现象表明文学正朝着个性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路径发展,与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互动,共同构建中国文学多样而富有活力的版图,从精神文化层面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