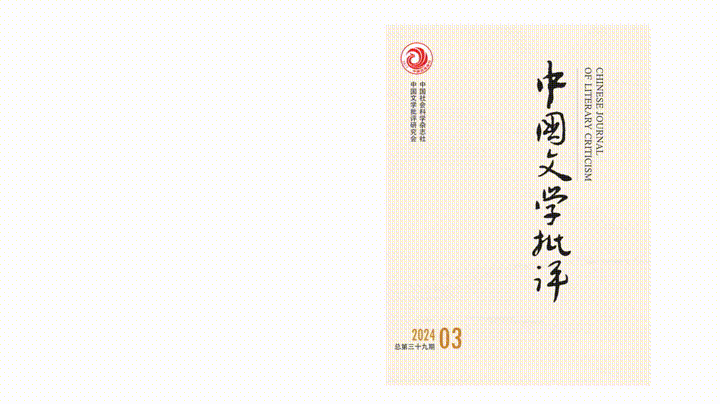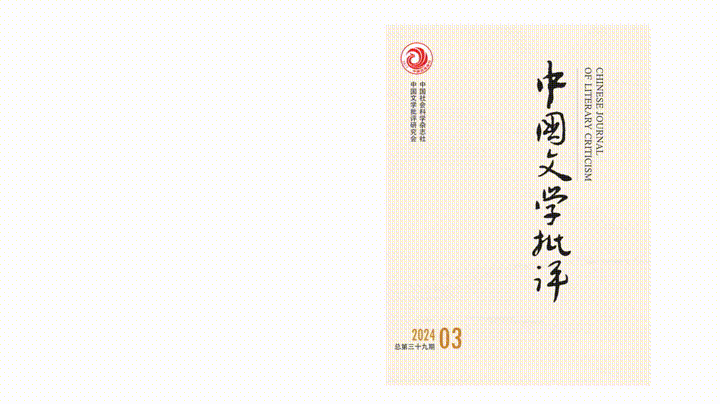
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地方性”话题自古皆然,至今更成为自我凸显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老话题中不断酝酿出新的动向。近年来持续讨论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两大热点。其论述和探讨早已经超出了本地域发声的层面,而发展成了一种全国性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汉学界与华文创作圈的文学动向、批评动向。在这里,本文无意直接加入对“南北文学”的讨论,而是希望通过梳理这一批评新动向的来龙去脉,对由来已久的地方性的资源价值再作反思。
01
中国文学有南北之议或各区域地理的概念,是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辞约而旨丰”的《诗经》,“耀艳而深华”的《楚辞》,都为刘勰所辨明。《汉书》《隋书》辟有“地理志”,讨论了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与当地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讨论已经出现了“南北”“江左”“河朔”等重要的文学地方视野:“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近现代以后,引进的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空间理论,使论述更上一层楼,文学的区域研究、地域考察不断结出重要的果实。在新时代的今天,东北与南方问题的再度提出,令人想起一百年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至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一批学者也让中国文学的南北论隆重出场。这既是对文学发展史实的陈述,也包含了自我辨认、清理思想根脉,以激发文化的活力之义。那么,这一百年以后的议题,有着什么样的思想意义,是不是亦有同样的历史效应呢?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系统的地方性的观察和总结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于1995年开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该丛书全面展示和挖掘了文学的地方经验与地方路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然也是百年来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与地方文化内在关系的第一次系统性梳理总结。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国文学的地方性研究几乎都是生长或长期居住在当地的学者完成的。具体可见下表:

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作者,除了朱晓进、刘洪涛因为前期分别从事山药蛋派与沈从文研究而参加了相应编纂外,其他所有的学者都具有深刻的“本乡本土”渊源。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自我感受,学术的表达也具有自我开掘、自我说明的鲜明意图。笔者关于现代四川文学的著作就在“后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表述:“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出生的这个地方在那些时候是多么的热闹……当然,童年还有过小伙伴的游戏,有过小河边的捕鱼,有过防空洞里的‘历险’,有过小饭铺里二角一碗的大汤元。”“我知道我向往北方!那荒远而淳厚、从容而坚强的北方,就像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先辈那样,但是一旦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它,又当如何呢?难道就不会有郭沫若、何其芳那样的乡情?”在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绩还有待全面总结和彰显的时候,这种地方性的开掘和展示几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他们解释的是“走向世界”的文学主流叙事所需要的细节,也是对“中国文学”主体叙述所难以顾及的地方内容的放大呈现。除了地方性的学者及其对“地方”有特别研究的基础,似乎也难以熟悉这些特定地域的被遮蔽的陌生的内容。
不过,这样一来,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除了对主流文学细节的补充与完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凸显自己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最后的意义又不仅仅属于“地方”,而是指向对整个文学格局的再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工作属于中国文学地方性研究的第一阶段,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无比丰富的地方性。这些地方性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它的历史实绩。因为有了不同地方的文学成果,我们百年文学的建构才是充实的和多样化的。当然,在大量扎实的奠基性的工作之外,这一阶段的努力基本上还没有展开新的追问,即这些地方性的文学有没有贡献出一种独特又具有整体性指向的可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对各区域文学的解剖、分析新见迭出,不过似乎都没有刻意挖掘那些地方性文学创作中蕴含的导向未来文学发展的律动和线索,也没有放大性地揭示“当下地方”中暗藏的“通达中国”“激活世界”的机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出版至今已有20多年,中国学者对文学地方性问题的研究依然在持续推进。这种推进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系列相关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例如文化地理学、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三元论、段义孚关于“空间与地方”的论述、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所谓“地方与无地方性”的论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超空间”概念、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的“全球地方感”等理论使得我们的学术视野更为深邃,从过去的感性总结上升到更为理性的概括与分析。其次是对地方性考察迈向更为广阔的领域,除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的分析,也进一步扩展到了古代文学领域,使古今中外的文学相比较,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更大范围的文学地方性问题。“文学地理学”的充分阐发和广泛运用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进行的。最后,对中国新文学的考察、研究也开始超越了主流思想的“补充”这一层面,努力通过对“地方”独特文化资源的再发现重新定义现代,洞见中国现代性的自我生成路径。“地方路径”概念的提出、阐发和讨论可以被看作这一努力的理论性尝试,而陈方竞1999年出版的《鲁迅与浙东文化》则是学术超越的较早的成果。
作为一位浙江籍的学者,陈方竞致力于鲁迅与浙江文化关系的阐发并不奇怪,这十分符合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地方性研究的动向,从总体上说还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的脉络。但是,陈方竞却以自己细腻的梳理和深入的思考展示了地方性研究的新的可能,从而实现了对同一时期的学术模式的某种超越。《鲁迅与浙东文化》不是在鲁迅的文学中寻找时人关于浙东文化的常识性概括,从而迅速地总结出鲁迅文学中的浙东“基因”或“元素”,最终证明一个不受人质疑却也并不令人兴奋的事实:鲁迅的确属于浙东文化。这样的地方性阐发仅仅是对文学史“常识”的一次侧面的印证,它本身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能够发现新问题,因此对学术思想的启发和推动也十分有限。陈方竞却是将对浙东文化传统的发现与对鲁迅内在精神特质的挖掘紧密结合。他不是企图对尽人皆知的常识展开别样材料的印证,而是在重新发现鲁迅思想构成的意义上挖掘出了被人们所忽视的浙东文化的存在。无论是对于鲁迅还是对于浙东文化传统,这里的发现都是深刻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例如著作对鲁迅所“复活”的浙东地缘血缘传统的论述就始终在多层面多维度中展开,不断作出个体性的比较和时间性追踪,从而呈现了这种地方性传统延续承袭的复杂和变异。而所谓文化传统的影响也从来都不可能是本质化的、理所当然的,它们都得在历史的转换中被重新选择。所以,“发现”传统绝非易事,“继承”文化需要付出:
鲁迅作为破落户子弟,反叛于他“熟识的本阶级”,这样,血缘性地缘文化在他身上的“复活”又并非是顺其自然的。显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主体意识的“认同”过程,由“认同”而“复活”。
鲁迅与瞿秋白同为士大夫家族子弟,血缘性的地缘文化影响,他们身上都表现出某种根深蒂固的“名士气”。但瞿秋白身上的“名士气”表现为“洁身自好”;鲁迅则不同,他仰慕浙东先贤而表现出近于“魏晋名士”愤世嫉俗的硬气与骨气。
周作人又不能不正视他与乃兄鲁迅之间互有濡染又泾渭分明的不同文风……周作人的文风不无“深刻”但更显“飘逸”;鲁迅的文风则是,不无“飘逸”但却更见“深刻”。
这样的鲁迅精神也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再发现”,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新文学内在精神的创造性提炼。由此被阐发的浙东文化,也就不再属于历史的陈迹,而理所当然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参与者、激发者。这里的鲁迅和浙东既蜿蜒生长在地方性的土壤里,但又最终超越了具体乡土的狭隘性,与更为广大的世界性和更为深刻的人类性沟通关联在了一起,从而给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启发。
02
今天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从创作到批评也都呈现了中国文学地方性意识的一种深化。
作为创作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已经超过了地方彰显的意图,写作和作家本人的跨区域性向我们表明,地方本身已经不是他们集中表达的内容,超出地方的更深的关切可能是他们更有意包含的主题。有人统计过,这些活跃的“新东北”与“新南方”作家未必都固守在东北和南方,故乡也并非就是他们唯一关注的焦点,文学的故土更不等于就是现实的刻绘。“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文学代表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其实是在北京书写东北”,“广西籍作家林白,她的长居地是武汉和北京,她的写作很多时候与故乡和区域并不直接相关。但《北流》却无疑动用了故乡的精神文化资源,浓厚的地方性叙事、野气横生的方言叙事为人所津津乐道。与林白相近的还有霍香结。桂林人氏,走遍中国,定居京城近二十年的霍香结近年以《灵的编年史》《铜座全集》颇受瞩目。霍香结无疑是自觉将‘地方性知识’导入当代文学的作家。”书写“新东北”的班宇在南昌市青苑书店书友会上说过,他现在写的东北,其实并不是90年代真实存在的东北。他还表示,“即便今天经济情况不再一样,但精神困境也许一样,所以会有感同身受。读者和我不是寻找记忆,而是对照当下处境”。双雪涛则称“艳粉街是我虚构的场域”。“新南方”的东西表示要拒绝“根据地”般的原乡、寻根公式。梁晓阳十几年间辗转于广西和新疆,没有新疆这个北方异域的参照也无所谓独特的广西。他的长篇小说《出塞书》的主人公梁小羊因为一次次的出塞,才得以从本土的空间中挣脱而出。“新南方”作家朱山坡说得好:“我们只是在南方,写南方,经营南方,但我们的格局和目标绝对不仅仅是南方。过去不少作家沉迷于地方性写作,挖掘地方奇特的风土人情,耸人听闻的怪人怪事。这是伪乡土写作。这不是写作的目的,也不是文学的目的。写作必然在世界中发生,在世界中进行,在世界中完成,在世界中获得意义。一个有志向有雄心的作家必须面向世界,是世界性的写作。”朱山坡自己不仅书写了“米庄”和“蛋镇”这样的南方小镇,他其实已经走出了国境,走向荒凉的非洲,索马里、萨赫勒、尼日尔,在不同文化中探究人性的幽微。“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
批评也是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性文学研究不同,参与“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研讨的批评家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地方的代言人”,“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问题引起普遍参与的热忱。黄平是东北人,但长期求学、生活、工作在上海。杨庆祥是安徽人,长期求学、生活、工作在北京,“新南方”只是他远眺的方向。这恰恰说明,“新东北”与“新南方”都不再是地方对主流文化发展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它们本身的问题已经足以引发全局性的思考。正如“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论述者都已经达成了的普遍认识一样:所谓的“新东北文学”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这里的写作并不是地方的,其中隐藏着的是社会的思考。“新南方写作”则标志着由地域诗学向文化诗学、未来诗学的演变,这样的“写作”在世界时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新南方写作”“尽管发轫于地方性书写,却具备一种跨区域、跨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品格”。
与某些地方文学倡导者的“自恋”式地方彰显有异,“新东北”与“新南方”的论述者都在跳出自设主题的束缚,在更大的框架中建构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同时也不无反省。例如黄平就曾以“新东北写作”为参照,对照性地来讨论“新南方写作”。他认为两者创作表现的差异有五:
第一点是边界,“新东北写作”的地域边界很清晰,但“新南方”指的是哪个“南方”,边界还不够清晰,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同一个区域内部也不够清晰,所以庆祥等评论家还在继续区别“在南方写作”和“新南方写作”;第二点是题材,“新东北写作”普遍以下岗为重要背景,但“新南方写作”并不共享相近的题材;第三点是形式,“新东北写作”往往采用“子一代”与“父一代”双线叙事的结构展开,以此承载两个时代的对话,但“新南方写作”在叙述形式上更为繁复多样;第四点是语言,“新东北写作”的语言立足于东北话,但“新南方写作”内部包含着多种甚至彼此无法交流的方言,比如两广粤语与福建方言的差异,而且多位作家的写作没有任何方言色彩;第五点是传播,“新东北写作”依赖于市场出版、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短视频以及影视改编,“新南方写作”整体上还不够“破圈”。故而,在思潮的意义上,“新东北写作”比较清晰,“新南方写作”还有些模糊。
这样的反省无疑将推动中国文学地方意识的发展。
03
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地方视野的系统展现到今天文学批评中南北话题的深化发展,我们可以见出中国文学创作地方意识的兴起和自觉,也可以看到学术思想日趋成熟的一种态势。不过,严格说来,学术发展和文学创作一样,归根结底并不是一种进化式的跃迁,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力表达最独特的感受,或者努力解决这一阶段的思想文化问题。它们最终的价值取决于感受的不可替代性或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面对中国文学地方性问题的学术态度既不能与古代中国的“地理志”简单类比,也无法因为数十年前简易的区域研究而满怀自信。译介自西方的各种“空间”理论好像更不能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归根到底,今天的地方性讨论和未来的其他文学讨论一样,都还得通过本时代我们批评的有效性来检验。
于是,透过当前中国文学批评对“南北”问题的关注,我们都有责任来继续探讨和提高理论的效力。我认为,这种理论的效力至少还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捕捉文学现象独特性的能力,即相关的概念和阐释是不是切中了相关文学现象的核心和根本,可否在与相似现象的区隔中透视其中最独有的精神秘密;二是它参与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也就是通过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能否升华出一种更大的思想文化的启示。
当代文学的“南北”命名及讨论显然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有价值的捕捉和发现。例如“新东北文学”由“下岗”主题而重述文学对普通人民群众的关怀,进而引发关于“复兴现实主义”的猜想。“新南方写作”由“一路向南”的版图的扩展打破国境线,将海内外的汉语写作囊括到一个观察体系中,甚至挑战“华语语系文学”所暗含的文化抵牾……这都是一些令人激动的文学批评的未来前景。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前景在目前尚不是触手可及,我们依然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创作现实:写作的活力总是体现为不断变化,这些“狡黠”的媒介时代的精灵并不愿意乖乖就范。事实上,“新东北”的几位作家本来就置身在比过去纸质出版时代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之中,他们并不甘受制于某一“古典”的程式。语言和行动上脱离“被定义”,在逃逸批评家指称的道路上自由而行,同样是这个时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特点。正如有评论指出:“这样立意宏大的批评路径似乎并未和小说家的自我指认之间达成顺滑的对接,在阐释者一方试图将‘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圈定在预设的阶级话语框架,从而完成对其文学价值的确认之际,创作者一方却往往不甘于被外界给定的标签所束缚,不断寻找着‘逃逸’的出口。”在命名的争论当中,也有以“新东北作家群”人数有限,不足以匹敌历史上有过的“东北作家群”而颇多质疑。其实,对于一个新兴的文学现象,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它所包含的问题的不可代替性。如果“新东北作家群”揭示的创作问题前所未有,数个作家也值得认真考察。这里可以深入探究的东西其实不少——无论他们对弱势群体命运的披露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传统的普罗文艺,也无论“现实主义”的概括还是否恰当,我们都不能否认其中所存在的深刻的左翼思想背景,还有那种曾经淡化了的现实批判的追求。当然,历史并不会出现简单的重复,新时代的“普罗文艺”肯定另有一番景象。一种综合性的对普罗大众的关怀混杂于新媒介文化的形态正在蓬勃生长,这可能是我们既有的文学思潮难以概括的,也亟待我们的批评家认真勘察,准确命名。我们不仅需要流派的命名,也需要艺术形态的命名,一种跨越精英/底层、主流/边缘、雅/俗的融媒介式的艺术概括。
“新南方”的跨境向南是鼓舞人心的学术前景。当中国作家林森、陈崇正、朱山坡、吴明益、夏曼·蓝波安、董启章、黄碧云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都被置放在“南方”的大背景下予以呈现,我们可以洞悉多少新鲜的景致!不过,在这里,迫切需要我们思索的可能还在于,当中国的写作题材开始从传统大量的“北方”叙事中转向坚定“南行”之时,这种“方向转换”的选择与历代中国文学的“南北”变化特别是近代以后对南北问题的讨论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而黄锦树回望鲁迅的《伤逝》,又有怎样的心理距离?林森的《海里岸上》写卸甲归田的一代船长老苏,“他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到海上去了”,“一九五○年之后,老苏刚刚上船不久,那时基本不去南沙,而随着船在西沙和中沙捕捞作业。二十多年以后,响应国家战略的需要,他踏上了前往南沙的征途”,所过之地,木牌上写下大红油漆文字:“中国领土不可侵犯。”字里行间,更传达了激昂的民族情怀:“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在这里,个人的情感深深地渗透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家国意识,一路向南的行旅中清晰回荡着来自“北方”的责任和嘱托,它和其他的“南方情怀”是否已经消弭了界线?我想,“新南方写作”的边界划定,还可以有更多的追问。
文学的“南北”之论从来都超出了文学批评本身,指向一种更大的思想文化目标。一百年前,中国知识界也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他们各具风采的论述开启了现代中国从南北地理视野入手解释中国文学、语言及文化的理论时代。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章太炎《新方言》及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都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名篇。《中国地理大势论》从政治、文学、风俗与兵事四个方面入手,论述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与互动关系,其目标在于探究历史上“调和南北之功”,从文化融合的方向上推动社会的发展。梁启超对现代文明的赞赏即导源于此:“今日轮船铁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 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而南北之“合”则与民族之“合”相契合,所谓“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一句话,南北文化之合与民族文化之合是中国的历史大趋势,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王国维将情感、想象等西方文学概念引入对中国南北文学的评述中,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以情感表达为中心的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章太炎与刘师培划分南北的标准并不相同,对南北的推崇也刚好相反,但却都将他们所崇尚的南北文化当作复兴民族生气的根基。“对于章太炎和刘师培,‘南北论’都不是纯粹知识性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旧学新知中不断调试以回应时代变局的积极尝试。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内重新凝聚起中华文化的根脉,是章、刘最关键的问题意识。”总之,一百年前的文学“南北论”,具有宏大的问题意识和文化理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是非优劣的辨析,最后升华为一种社会文化重建的目标。
世易时移,今天的文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是清末民初的重复。然而,在一个传播手段和交流策略逐渐凌驾于内容之上的时期,在许多貌似显赫的声浪都可能流于暂时的“话术”的氛围中,我们也有必要坚持一定的理性,否则就可能如人们的担忧:“‘新南方写作’作为一种建构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力的文学现象,它未来的命运是被短暂地讨论后就如秋风扫落叶般被人遗忘,还是承担起丰富当下文学实践现场这一使命?”而“新东北文学”的前景也可能在戏谑的玩笑中被后人所调侃:“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文学的地方性追求归根到底并不真正指向地方,而是人自己。近现代以来的“南北论”中,可能还是鲁迅的思考最为独特: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与其他的南北论不同,鲁迅没有将南北问题仅仅当作“地方”本身,而是充分重视了其中的“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主动的努力所造成的自我的改变,最后也就是“地方”本身的改变。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这看似来自“相书”,实则为鲁迅“在地方立人”的重要选择,这样的地方文学才是人主动选择的文学,是“人的文学”。
这应该就是一切地方性话题的富有建设性的开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