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刑侦小说是最具当代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类型之一,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本土性特征。而在中国21世纪刑侦小说创作中,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和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代表性。雷米的“心理罪”系列运用侦探小说的类型框架来捕捉当代生活,借助现实化的空间建构与犯罪心理学的专业视角,实现传奇与现实的辩证书写。“法医秦明”系列则更多继承了公安文学、公安言情小说的发展脉络,在展现专业法医学知识的同时表征了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对于个人与日常生活的肯定。这两个系列尽管各有特色,但都呈现出当代中国刑侦小说的现实性指向,在继承传统侦探小说的传奇性特征的同时发扬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科学知识、法律教育的普及与职业体验、日常生活的书写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当代刑侦小说发展的本土化路径。
关键词:刑侦小说;侦探小说;“心理罪”;“法医秦明”;本土化路径
作者战玉冰,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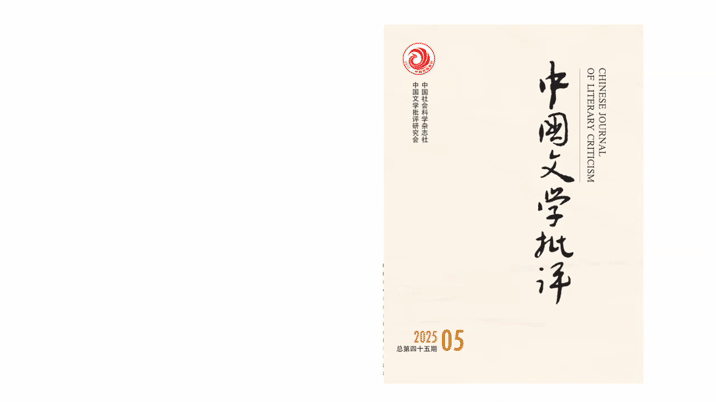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晚清民国时期,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西方侦探小说构成了当时国人了解和想象外来器物发明、司法制度与科学理性的文学中介物,也是本土侦探小说作者模仿的主要对象;20世纪50—70年代,在时代话语和国外惊险小说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侦探小说更多具有现实性意涵;新时期以来,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则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略显繁杂的类型命名——比如有学习日本小说模式的“本格推理小说”,有延续革命年代风云想象的“谍战传奇”,也有着重表现当代公安干警侦查破案工作与生活的“刑侦小说”。其中刑侦小说一方面依托现实办案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甚至有不少作品依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成,因而具有更强的现实性、本土性与当下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刑侦小说可以说是最具当代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类型之一,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式侦探小说”。
一、刑侦小说的类型命名与现实书写传统
严格来说,如果将小说的故事题材限定在表现犯罪与侦破过程,将文学审美机制集中于悬疑和查案所带来的美学体验与阅读快感,“法制文学”与“公安文学”这两个概念无疑都显得过于宽泛和含混,二者都存在着将表现普法宣传、公安职业,乃至纪实报告类等更为泛化的文学作品与传统侦探小说混为一谈的倾向。但需要指明的是,这些文学命名在20世纪80年代的提出,更多带有某种时代现实性和功利性意涵。
所谓“刑侦小说”,主要指的是故事背景发生在当代中国,以公安干警为核心人物,以刑事罪案为主要内容,以调查推理,直至最终侦破案件为基本情节模式的小说类型。这类小说创作中经常会参考或借鉴真实案件中的情节元素;而即使是虚构的故事,也需要符合现实的基本操作规范,具有一定的中国本土特色和现实感。大体上可以认为刑侦小说是“法制文学”“公安文学”与传统侦探小说的“交集”,或者也可以说它是“法制文学”与“公安文学”经历了市场化选择之后的文学类型。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谱系中,新时期以来的“法制文学”和“公安文学”逐渐演进为具有鲜明类型化特征的“刑侦小说”,这一演进过程生动体现了主旋律价值传播与商业化类型叙事之间的有机融合,从而构成了中国当代刑侦小说独特的本土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刑侦小说从诞生之初就天然地携带着深刻的现实书写基因。一方面,中国刑侦小说的叙事核心并非西方侦探小说中常见的私家侦探的调查推理过程,而是公安机关等公共权力机构的刑侦执法过程。这使得刑侦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纪实色彩,注重对现实刑侦程序与司法流程的精准再现。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这类作品的专业特质与可信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家群体的特殊构成——很多刑侦小说作者兼具警察、法医等职业身份与文学创作者的双重角色,这种复合型知识结构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真实质感。
二、“心理罪”系列的现实表达与知识建构
刑侦小说的现实书写传统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之初,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图书市场的发展,以及影视改编(尤其是网剧改编)热潮的兴起,刑侦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天涯论坛上的“莲蓬鬼话”副版,以悬疑、惊悚、恐怖类小说居多,比如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紫金陈的《浙大夜惊魂》,以及莲蓬、老家阁楼、庄秦、大袖遮天、七根胡等人的作品。同时,“莲蓬鬼话”上也有不少刑侦、推理类小说——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周浩晖的“刑警罗飞”系列和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等,都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最为知名的刑侦小说作品系列。其中雷米的“心理罪”系列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雷米原名刘鹏,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教师,对于现实中的警察生活与侦查工作有着深入的了解。作为一名“业余”作者,雷米从2006年开始连载自己的小说《第七个读者》(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心理罪:第七个读者》),并引发强烈的反响。
一方面,小说中的主角方木,不论是其早期作为学生,还是后期作为警察,在人物塑造上其实都更多继承了从福尔摩斯到菲利普·马洛的传统侦探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比如小说中多次强调方木性格上的冷漠、孤僻、深沉,目光锐利与令人难以捉摸。
男孩捧着篮球,转过身。他的脸色潮红,鼻尖上有细密的汗珠,脸颊凹陷,下巴显得尖尖的,浓密的眉毛此刻紧锁在一起,而他的眼神——
冷漠,疲倦,却又锐利无比,仿佛能够刺破午后强烈的光线直钻进对方的身体里。
走出篮球场的时候,邰伟忍不住回过头来,却发现方木已经不在长椅边了。向旁边一看,方木正背对着他孤独地投篮。此时已暮色深沉,篮球场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方木的身影在越来越黑的天色中愈发模糊,只能辨别他不断扬起的手和篮球在空中断续的轨迹。
方木的脸在显示器的照射下显得有些发蓝,眼神也重新变得冷漠、疲倦、锐利无比。
在侦探小说的经典叙事传统中,作者往往通过将侦探形象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塑造手法,刻意强化其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这种人物塑造策略通常表现为:赋予侦探超凡的观察力与逻辑推理能力,同时刻意凸显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疏离感与格格不入的特质,以此构建起“天才侦探”的人物形象,比如作为一架推理机器的福尔摩斯,或者性格坚毅的“硬汉”侦探马洛。而作为一名身体孱弱、出身普通的学生,方木却拥有着惊人的查案天赋,其对手也多半是狡诈的连环杀人犯,比如吴涵、孙普、陈哲,以及“城市之光”江亚。二者间的犯罪与侦破过程,就演变成了一场场正邪之间的智力较量与神魔斗法。《第七个读者》中的吴涵、《画像》中的孙普、《城市之光》中的江亚等人,甚至专门针对方木发起犯罪挑战,整个故事也因此带有明显的传奇化意味。
另一方面,雷米笔下的传奇故事又被巧妙地放置于颇具日常性的空间场域之中,如学生宿舍、大学校园、警队以及普通的北方城市。在描摹这些场景时,作者也采用了高度写实的创作手法,以近乎还原现实的笔触呈现出生活的点滴细节:比如傍晚时分男生宿舍里此起彼伏的洗漱声、嬉笑打闹的日常,以及微妙的室友关系(《第七个读者》);或是北方城市夏日街头扑面而来的热浪、飞扬的沙尘与街边小吃摊升腾的烟火气(《教化场》)。这些极具生活质感的场景描写与情节设置和现实生活中的空间体验形成了高度的互文性关系,为读者营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受。同时,这些充满真实质感的场景也在虚实交融的叙事中消解了“神探”形象所造成的距离感——方木超凡的侦探能力因为扎根于现实土壤而显得可信可感,从而实现了小说“化传奇为日常”的独特审美效果。
而对于对真实罪案和社会新闻有着密切关注和丰富积累的雷米而言,小说中很多看似“传奇”的人物或情节,其实也都以真实发生的故事为基础。比如《暗河》中郑霖等三名警察为了营救被拐卖的儿童而牺牲,这个令读者感到“惊心动魄”的小说情节其实脱胎于当年辽宁省一起真实的生产安全事故。雷米在小说里化用了这起安全事故作为素材,将其改写进自己虚构的刑侦小说中,最终塑造出了一组勇于斗争、不畏牺牲、可歌可泣的警察群像。
无论是《教化场》中的“天使堂”孤儿院的遭遇,还是《城市之光》中“城市之光”对于恶人的处置,无疑都符合某种民间朴素的是非观念和正义想象。而在“心理罪”系列中方木在法律范围内帮助福利院渡过难关,并且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最终将“城市之光”绳之以法等关键情节,实际上是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传递: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实现的正义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正义。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深化了作品的法治理念,更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重新认识了警察的崇高使命。这正是刑侦小说作为公安文学与法制文学的一种“子类型”所内在具有的教育属性与普法功能。雷米对此也有着相当自觉的反思和警醒:“我觉得推理小说也是一种文学,应该具有这方面的价值,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看完我的小说后,只是单纯觉得爽,而是希望能够引导他们对社会现象与人性有所反思。”
概括来说,雷米通过对地景空间的精准刻画、环境氛围的细腻营造,以及基于真实案件原型与专业刑侦经验的创作实践,将神秘的侦探形象、离奇的案件谜团与曲折的查案过程成功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完成了刑侦小说中传奇与现实、虚构与真实、神秘与日常之间深度结合与相互转换的辩证书写。
此外,小说“心理罪”系列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融入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比如模仿犯罪、催眠、心理暗示、PTSD、斯金纳箱、测谎等。小说在纸质出版时也最终被定名为“心理罪”,正是对这些相关情节内容的凸显。我们甚至可以说,“心理罪”系列大概是第一次向广大中国读者普及了“犯罪心理画像”这一侦查技术和手段。比如在《画像》中方木刚刚登场时,就为连环杀手黄永孝作出了准确的犯罪心理画像。
方木对犯罪嫌疑人的外貌、家庭背景、工作环境、生活习惯的描述与黄永孝惊人的一致,唯一的出入就是黄永孝父母离异多年,黄没有男性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并随着母亲嫁到了外地,已经断绝了来往。但这已足以让干警们对这个貌不惊人的男孩刮目相看。他们甚至怀疑黄永孝作案的时候,方木就在现场看着,否则不可能做出如此准确的描述。
这里看似对心理学知识及其实际应用效果有些“赋魅”倾向的书写细节,同时也是对传统侦探小说中侦探破案天赋、直觉与神秘性等设定“祛魅”的过程。即小说中的罪犯与“神探”,其看似不可解释的狡诈犯罪手法与高超侦查过程,最终都被转化为某种可以被认知和理解的心理学知识。比如《教化场》中凶手作案后做出的一系列颇具形式意味的怪异行为在小说里最终都获得了心理学层面的解释。
迷宫里的仪式象征着复仇。
……
凶手,或者说主犯有异常心理的倾向。
……
就好像所有的仪式一样,形式的意义要大于内容本身。
进一步来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那样,侦探文类的兴起本身就反映着西方司法观念的范式转移:从依赖视觉暴力的公开处决景观,转向依托专业知识体系的现代侦查程序。这一转型在《城市之光》中得到了极具张力的艺术呈现:江亚以私刑审判者的姿态在现代科技包装下进行的暴力展演,既制造了新型的犯罪奇观,又对公共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木运用犯罪心理画像等专业侦查技术,通过理性分析逐步锁定江亚的真实身份,最终以法律程序实现正义的伸张。这一叙事对比生动诠释了现代司法从暴力示众到专业侦查的范式转换。
三、“法医秦明”系列的日常经验与职业书写
不同于雷米“心理罪”系列借助带有真实质感的故事发生环境与作为认知媒介的犯罪心理学知识,完成了从传统侦探小说到中国式刑侦小说之间围绕传奇与现实的辩证书写转换;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则更多从警察——特别是法医——的真实工作经历与日常生活出发,在继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公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中国当代刑侦小说本土化与现实化的另一条可能路径。
“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的作者秦明,本职工作是安徽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他以自己多年来从事一线法医工作的经历作为素材,2012年开始在天涯论坛连载小说《鬼手佛心——我的那些案子》,同年这些网上连载的小说正式出版,并改名为《尸语者》。由此开始,秦明陆续创作了十余部法医题材的刑侦小说,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万象卷”(包括《尸语者》《无声的证词》《第十一根手指》《清道夫》《幸存者》《偷窥者》六部作品)和“众生卷”(目前包括《天谴者》《遗忘者》《玩偶》《白卷》四部作品)两个系列。
对于这两个系列,秦明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设计用意和写法区分的;前者“写的是人间万象,所以更接近短篇小说集的写法”,后者“在写法上会有很大不同,就是每一本书虽然还是有好几个案件故事,但整体上是围绕一个社会问题来写。比如《天谴者》主要聚焦的是社会责任感,《遗忘者》主要聚焦腐朽的女德思想,《玩偶》聚焦的是家暴,而这本《白卷》主要聚焦的是亲子关系里的沟通问题”。概言之,相比起“万象卷”更接近于现实中的“案件实录”,“众生卷”有着更为明确的社会问题意识和情感价值判断。
“法医秦明”系列最为读者所称道的,莫过于小说中透露出的令人信服的真实质感。而这种真实感的营造,直接源自作者秦明作为资深法医的专业积淀。以书中围绕创口皮瓣特征所展开的推理为例:
“为什么其他创口没有皮瓣,就这一处有皮瓣呢?创壁是刀的侧面形成的,刀面基本都是平滑的,不应该形成皮瓣。那么形成皮瓣的不会是刀面,不会是刀刃,只有可能是刀刃上的凸起,比如说卷刃。”
这种基于伤口观察基础上所作出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展现出法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又如小说中对皮下出血演变规律的说明:
“皮下出血是有固定模式的转轨过程的。”……“皮下出血的初期,可能不会在皮肤的表面上表现出来,但是会逐渐在皮肤上显现,最初是紫色,然后出血逐渐被吸收,含铁血黄素形成,皮下出血的颜色会变为青紫色、青色、黄绿色,甚至变成黄褐色。”
其中对于不同时段颜色演变的精确描述,既彰显了法医学科的专业性和严谨性,也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可信度。总体而言,正是这些浸润着职业经验的细节描写,为“法医秦明”系列小说构建起了前文所指出的那种强烈的真实感,使读者得以窥见法医工作的科学内核。此外,小说中还有法医用手术刀为死者剃头发的相关细节描写:
法医都是好的剃头匠,对于法医来说,必须用最精湛的刀功把死者的头发剔除得非常干净,既不能伤到头皮,也不能留下剩余发桩。只有干干净净地剔除死者的头发,才能完全暴露死者的头皮,从而更清楚地观察死者头部有无损伤。这种损伤可能是致命性的,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轻微的皮下出血,即使是轻微的损伤,也能提示出死者死之前的活动状况。
诸如“为死者剃头发”这类细节,若不是有着切实的法医职业经历和实践经验,确实很难单纯依靠文学想象而获得,但这恰恰最能体现出法医职业中专业规范与日常工作的完美融合。而对于这些细节的准确捕捉和生动描摹,也奠定了“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在真实性方面的坚实基础,并收获了读者的认可与口碑。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公安文学”到21世纪“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的发展轨迹中,还潜藏着关于“个人”认知与想象方式上的演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公安文学”作品,经常和同时代其他文学思潮彼此重叠,将案件情节、个人遭际、历史反思与人道主义话语相互结合。而这一思潮与文学写作趋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则进一步发展为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肯定。文学开始重新恢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书写,在“纯文学”领域体现为“新写实小说”、女性“私小说”等文学潮流的兴起;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体现为对于晚清文学与民国“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研究的热潮;而在公安文学领域,则最集中地表现为海岩的公安言情小说的出现与流行。
从20世纪80年代公安文学中对特定时代的书写,到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海岩公安言情小说中对于情感乃至情欲表达的偏重,再到2012年以后“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及相关综艺节目中将法医刑侦与职业成长两种题材类型相互融合,我们在当代公安文学—公安言情小说—法医小说的文学发展脉络中能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内嵌在社会史与思想史深处的隐藏线:从“个体的人”到“情感的人”,再到“职业的人”,其中对于个人的想象方式,从抽象逐渐走向具体。与此同时,这一变化背后还对应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以及主体建构方式的巨大变化:从集体主义话语下的个体,到市场经济初期的个人主体,再到社会专业分工背景下高度职业化的技术主体。
除了公安文学与言情小说的类型融合之外,海岩小说还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故事发生空间往往被设置在现代化都市之中,呈现出一种时尚感;二是小说中警察的工作场景从以往的基层派出所转向刑侦、缉毒等现代化警务领域。而后者被“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充分继承和强化。有趣的是,秦明本人最喜欢的侦探小说作家,正是海岩。正如秦明自己所说:“我最喜欢的作家这么多年没变过,就是海岩。”文学思潮的历史伏线在作家具体的创作题材与阅读喜好中获得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印证和延续。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还在于,“法医秦明”系列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小说反映现实,或者小说中包含法医的职业经验和专业技能等层面——比如前文所分析的小说关于创口皮瓣、皮下出血等专业医学知识的介绍,此类知识在“法医秦明”小说中可以说是大量存在——而是二者间有着更为深层的有趣互动。比如在很多“法医秦明”小说及改编剧集的网站评论中,都能看到有读者/观众在看了小说或剧集之后去选择报考法医专业,最终成为一名现实中的法医,文学之于现实的影响就以这样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带有职业成长小说与刑侦小说双重属性的“法医秦明”系列作品,最终影响并重塑了部分读者的人生理想与职业选择。
结语
如果说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在承袭经典侦探小说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现实化的空间建构与犯罪心理学的专业视角,实现了双重突破——既消解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神秘主义倾向,又成功注入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那么“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则开创性地将刑侦悬疑与法医职业成长相融合,凭借严谨的专业细节和真实的职业经验,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刑侦叙事模式。这两种创作取向不仅展现了刑侦题材文学的多元发展态势,更满足了当代读者对犯罪心理侧写与法庭鉴证科学这两种知识的主体性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者在叙事策略上各具特色,却都深刻延续并发展了中国刑侦文学的现实书写传统。这些创作实践生动展现了作家们如何立足本土语境,持续推进刑侦小说中国化的艺术探索。
在中国21世纪刑侦小说的发展谱系中,雷米的“心理罪”系列与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分别开创了两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叙事模式。二者既各自彰显出刑侦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不断创新与突破的可能路径,又共同延续了中国刑侦小说具有的现实书写传统。而这里的“现实”则包含多个维度——在创作立场上扎根中国土壤,在叙事逻辑上恪守专业真实,在价值取向上呼应时代精神。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通过塑造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司法工作者形象,既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艺术化传达,又获得了读者和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从而使刑侦小说得以成为“新大众文艺”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学类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