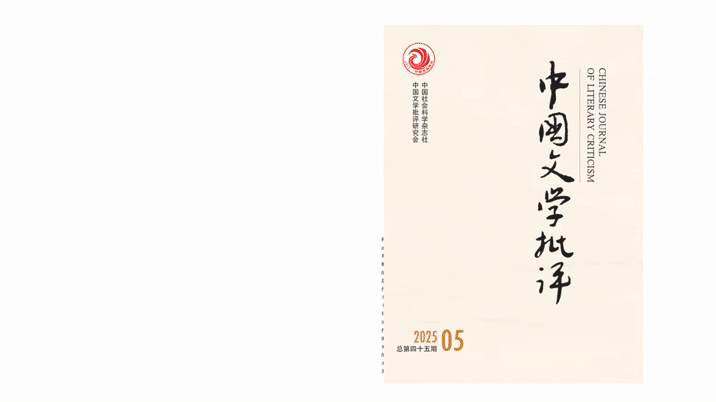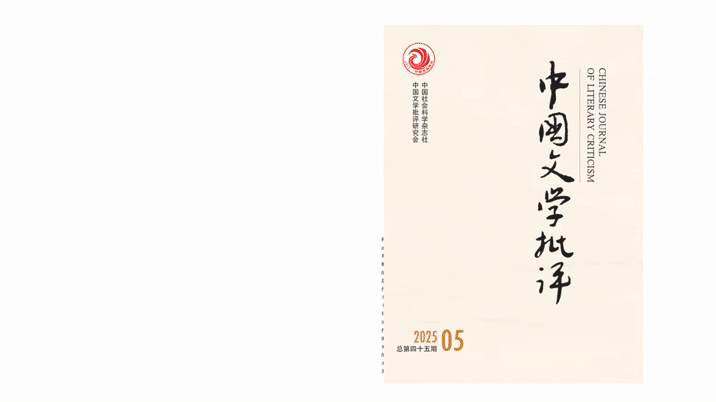
“事件”(event)一词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及日常生活中,一般用来描述历史上或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包括大事、要事和社会活动等。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事件”概念,从文学本质、文本生成、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和文学接受等不同角度探讨文学事件思想,强调文学的动态性,描述文学作为事件的发生过程。“文学事件”是文学创作、文本、阅读过程所包含或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书面文学作品从创作到接受确实与事件有密切关联。事件属于外在动因的一种,历史上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触动作者的情感,驱使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事件在文学作品内容层面表现为作家对情节的安排、现实生活事件对内容的影响等,作家是内容层面事件安排的主导者。文学作品经过阅读后可能也会带来与此相关的一些实践活动,成为生活中的某一事件,例如由文学作品引发的读书会、研讨会、影片拍摄,或者作品中出现的相关地域成为旅游景点。书面文学从创作到接受的整个过程是间断的、分离的、个体性的行为活动。书面文学的生产过程由作家主导,接受过程由读者主导,文学作品成为连接两端的桥梁。而口头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在同一时空中完成,从创编到接受是连续的、整一的、公共性的实践过程,口头文学演述过程就是事件发生过程。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发生在公共场域中,与当下其他生活事件发生关联、产生影响,生活中的事件可能随时会影响演述过程或演述内容。演述人和受众类似书面文学中作家与读者的角色,他们共处同一演述场域中,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口头文学研究范式转换与事件研究有关,口头文学从文本研究、不同门类的事项(item)研究转向事件研究,学术界经历了语境范式转换。从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提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到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演述理论,学者们对口头文学的关注和理解从语言文本层面转向动态生成过程。随着口头理论系列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提出感受生活的民俗学、身体民俗学、实践民俗学和事件民俗学等,将民俗实践活动当作日常生活事件进行过程性研究。朱刚在交流民族志和“以演述为中心”的理论影响下提出“交流诗学”,他将口头艺术视为交流事件,探索作为交流事件的口头文学与人类、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事件对口头文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研究将事件作为口头文学发生的重要部分。巴莫曲布嫫以史诗演述传统为个案,总结出“五个在场”的田野研究操作框架,其中就包含演述事件“在场”。她认为史诗基于传统事件而进行演述,事件对确立演述场域具有重要作用。乌·纳钦将促使史诗演述发生的事件称为“前事件”,扩展了演述事件的研究领域,认为前事件是演述事件的起点和演述发生的动因,规定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但并未将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纳入考虑范围。
口头文学相关领域将事件作为方法,提倡以动态性、互动性和交流性的眼光研究口头文学。研究人员关注到不同事件对口头文学演述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由口头文学所引发的诸多事件关系研究不足。本文从事件视角出发,观察口头文学在具体演述情境中的发生过程和生成机制,从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与作为口头文学内容的事件两个层面探究口头文学与事件、传统、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多重事件关系,以及彼此间在发生、内容和结构等方面的互构共生关系。
一、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
书面文学对语境的关注多集中于文本语境、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书写活动则将必要的语境接纳到文本内部,力求借此保持意义的确定性”。确定的文字符号构成书面文本,孤立的文学作品本身难以与现实语境产生关联,只能通过材料梳理判断创作时的“文化背景”。而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是融于生活之中的,也即处于语境中,是一种语言交流行为,“语言本质植根于文化现实、民族生活和日常习俗,离开情境语境就无法解释语言的意义”。口头文学文本是动态生成的,是日常生活本身,其中包含多模态具身性参与。为方便研究,本文以演述场域为中心,以线性时间为序,将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演述划分为前事件、演述事件和后续事件。这一划分虽然将事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部分,但在实际生活中事件发展随时间流动,并没有截然清晰的界限,而是彼此互融。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各类事件并不是截然区分的不同类别,而是彼此关联的整体。作为事件,口头文学演述与生活中各项事件呈现时序关系、因果关系和包含关系等多种形态,展现出口头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性和功能性。
本文将乌·纳钦提出的前事件概念进一步具体化,前事件指口头文学演述的“诱发性事件”,是促使演述发生的事件。前事件决定口头文学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还会对演述过程中的内容、程序及互动方式产生影响。按照事件属性,前事件可分为特殊事件和日常事件。特殊事件是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不寻常事件、可能会给人生带来转折和变化的事件,常与习俗、信仰、历史和社会发展相关,如人生仪礼、周期性节庆和宗教仪式等传统性活动。特殊事件引发的口头演述实践常受传统规约,传统规制演述发生的时间、地点、演述内容及演述场域中人的行为。例如,在男孩出生时人们演述史诗“英雄诞生”的片段,表达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麻山苗族地区在丧葬仪式中唱诵史诗“亚鲁王”;壮族在三月三歌圩节举行对歌、唱戏等活动。这些都是生活中发生的特殊事件,受传统习俗等影响而进行某项口头演述活动。乌·纳钦提出的“非常态事件”属于前事件中的特殊事件序列,如灾害、战乱、瘟疫、疾病等意外事件发生时进行的演述活动同样受传统影响。又如,遇到牛羊流行疾病、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等情况,内蒙古东部的牧民会请民间艺人演唱“镇压蟒古思的故事”。“蟒古思故事是在世俗领域里举行的禳灾驱邪的仪式,是诸如羌姆的佛教护法神信仰在东蒙古民间信仰中的一种辐射和具体化。”日常生活中常发生不同类型的特殊事件,不同的口头文学演述实践对应不同类型的事件,如果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就会违背演述传统,引起当事人不悦甚至触犯禁忌。
日常事件指日常生活中因某一事件引起的口头文学演述,如因某人的提议或因特定情境需要而发生的事件。日常生活情境中口头文学演述的时间和空间灵活多变,演述事件由行为主体人发起,因而演述场域也在偶然间建构。与特殊事件建构的演述场域相比,日常事件所建构的演述场域更加灵活、随性。此时前事件所发挥的作用更接近于为“这一场”演述的开始赋予合理意义。例如,有人在农闲时提议开展讲故事、唱民歌等娱乐活动;与人交谈一时兴起或根据交谈内容而讲故事、传说、笑话等;家庭聚会、朋友聚餐时在愉快的氛围下放声歌唱或讲与彼此相关的轶事;不同生活情境中讲睡前故事、校园故事等。日常事件所引发的口头文学演述更具随机性,由此建构的演述场域相较而言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前事件为口头文学演述建构语境,促发演述行为。
演述事件是口头文学作为事件的发生过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具有过程性、交流性和开放性,是实现口头文学功能和意义的过程。罗伯特·乔治斯(Robert A. Georges)将讲故事视作交流事件,认为“必须‘整体而非原子地’看待复杂的交流事件”,将口头文学演述视为整体事件或系列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文本。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不同,其“创编—传播—接受”环节都在同一时空中完成,是一个整体。演述人和受众共处同一时空,彼此处于面对面的状态,演述和接受过程呈现出具身性特点,演述人与受众通过口语、动作和表情等进行互动。“演述人和受众维持一种‘交互性’(interactivity) 关系,他们互为存在条件。”演述人与受众的交互性在演述场域中对演述文本产生影响,演述事件发生的过程也是口头文学“创编—传播—接受”的过程。书面文学从创作到阅读可能会间隔数十年甚至数千年,而口头文学演述过程限于当下,每一次建构的演述场域都是唯一的。相较于作家更具封闭性和私密性的创作过程,口头文学演述是开放的动态演述过程,演述过程中允许各种情况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可能会随时影响演述甚至中断演述,如演述过程中人员间发生肢体冲突、在户外空间演述时突遇暴雨天气等都可能会使演述中途停止。口头文学演述是群体性公共实践活动,演述过程中演述人与受众共处同一时空,共享某种语言、文化、生活空间、思维方式、情感体验等,共同参与演述过程。书面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大多是个体行为,在书面文学作品印刷出版前,作者与读者难以实现真正的互动和沟通,而在演述人与受众共同建构的口头文学演述场域中,二者产生强关联和情感共振,在互动中共同完成演述。
后续事件是口头文学演述活动完成后,由演述场域转向生活场域后发生的相关事件,可以及时反馈口头文学演述的功能与效果。后续事件与当下相关,也与未来相关,具有超时空性。口头文学演述过程既承接前事件,又接续口头文学演述完成后的事件,实现前事件引发口头文学演述的动机和演述事件指向的功能。口头文学具有现实功能,诸如社会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以及交际功能等,口头文学的演述效果要看是否实现其功能。例如,风物传说常用来解释某一物品的来源和功能,贵州省荔波县瑶麓村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石碑,瑶族同胞把这些石碑看成圣物,引以为傲。瑶族将创世始祖果阿常抬石立坪规诫儿子的传说代代相传,石碑寓意瑶族祖先所立的规矩就像石头一样,不会轻易改变。这一传说用以解释风物由来,规约族人遵守族群规矩,因而世代流传。相比之下,日常生活场景的口头文学演述更易感受到功能性,如在节日期间举行各类口头文学演述活动,达到庆祝节日的目的;家庭聚会讲述家族故事,促进成员间交流;驱邪禳灾仪式吟诵口头传统,实现心灵慰藉;等等。“这一次”的口头文学演述成为当时演述人和受众记忆中的一部分,对其生活产生影响,有时会在当下立刻体现,有时会在未来某一阶段发挥功效,或是进入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成为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影响未来事件。反过来,后续事件也会影响当时口头文学的演述。如后文将提到的,因着急回去工作和为保存体力而将当时的演述简化,就是后续事件对当时演述场域产生的影响。
质言之,将口头文学演述放归生活场域中,从线性时序来看,口头文学演述形成“前事件—演述事件—后续事件”的发展序列,三者间彼此交互,共同建构演述场域、影响演述过程。
二、作为口头文学内容的事件
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多数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有历史事件、社会事件、个人事件等。被选择为内容的事件,经过演述人再创编,就完成了“口头文学化”过程。已发生过的事件进入文学作品是常见现象,书面文学也常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纳入作品创作中。但由于书面文学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被写入作品中的事件无法随意更改。相比之下,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密,呈现出即时性、变异性和开放性等特点。
事件经过筛选,被传统、演述人和受众等共同选择,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这也涉及口头文学与文化传承、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众多无文字民族而言,口头传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忆保存和反复言说,所以,口头传统往往承载着族群的历史。”口头文学承担记录和保存事件的功能,通过口头传统的反复言说,重要的历史事件被人们保存在记忆中。例如,岳飞抗金事件和岳飞本人的传说、故事在今天依然广泛流传,其中英雄人物以及传奇故事等要素成为岳飞抗金这一历史事件被选择和创编的重要缘由。历史事件是较为稳定的素材来源,而当代发生的各类事件更具灵活性,一些事件会在特定人群中流传,如地方性传说、家族传说和职业故事等。某地发生的偶然性事件等经过口耳相传、不断加工与渲染,衍变为地区传说。例如,在某大学广泛流传的恐怖传说,最初可能是某位同学因某事而一时兴起创编的传说,然后发布到网上,随之在校园中传播,甚至附会成其他学校的传说。传说常被包装为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演述人则会依据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创编。
事件被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度,“我们讲述的传说,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希望、恐惧和焦虑心理的反映”。看似在讲述已经发生的事件,实际上都是述说与当前相关的事件。在不同地区流传的“聚宝盆”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会依据地理位置、地方特色进行适应性改编,如福建的《聚宝盆》故事是从龙王的水晶宫得到宝物,甘肃的《神火盆》故事是在去敦煌的路上得到聚宝盆,而内蒙古地区的《神奇的瓦罐》故事则是在打猎、砍柴时得到聚宝盆。基于当下生活的故事演述更具真实性,也更能吸引受众。口头文学对事件的选择,无论是历史事件、当前事件还是想象中的未来事件,都是基于当下的记忆和体验。除了亲身体验、口耳相传,当下人们还有许多获取事件素材的途径,如报纸、电视及互联网平台等。
口头文学“创编—传播—接受”环节在演述场域中进行,也同样处于生活场域中,事件会随时进入口头文本。身边刚发生的事件可能下一秒就会进入口头演述中,甚至正在发生的事件被演述人看到也会即刻创编进口头文学中。事件经过演述人重组、艺术化处理和适应性创编等,转变为口头文学的内容。在口头文学演述场域中,演述人根据演述需要对事件进行重组,打破事件发生的时空序列,将事件作为内容提取、挪用到不同的情境中,只要符合口头叙事的逻辑和目的,事件顺序与真实样貌并不重要。口头叙事也需要将事件置于某一时间关系中,但叙事的过程不一定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而是从演述人的经验世界出发。与人物相关的事件是口头文学经常进行附会和改编的地方,如“箭垛式人物”就是将与不同人物相关的事件附会到同一个人身上。艺术化处理方式是演述人将事件转变为口语艺术,用口头表达技能吸引受众的过程,也是可以展示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差异的部分。如夜深人静时,在茂密丛林中、废弃的楼宇间讲述曾发生在这些地点的各种传说,再配合有经验的演述人的声音、表情、手势,以及演述人和受众之间的互动等,演述效果要比文字叙述和平淡讲述好得多。
真实发生的事件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会经过不同阶段的变异,事件被不断演绎,口头文学的形式和文类也会发生变化,有时内容会让位于形式,逐渐趋向特定群体所熟悉的形式和传统程式化表达。1891年,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处发生莫斯奎达火车大劫案(Mosqueda’s Great Train Robbery),在边境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这一事件成为当地民谣“科里多”(corrido)的演述内容,并出现多个版本。多个版本填充了这起事件的细节,包括抢劫过程、抓捕过程以及审讯过程等。最后,口头叙事中劫持事件发生的时间、缘由、结果等都发生变异。抢劫火车变成了由于煽动而发起的攻击,劫匪形象也被塑造为边境冲突的英雄。19世纪90年代的早期版本基本上是从墨西哥人的角度描述事件,演述内容有对生活不安定的恐惧、对损失钱财的乘客感到同情以及对劫匪的谴责,反映了边境人民对真实事件的直接体验。到了1939 年,边境冲突的“科里多”模式已经取代了民谣的原意,讲述边境人民心目中的故事。演述人通过删去一些细节,将剩下的内容编排成典型的边境冲突歌谣的模式,而这正是传统“科里多”常见的演述内容。一方面,作为内容的事件为口头文学的内容提供素材,事件会发生多种变异;另一方面,内容可能会让位于形式,最终成为事件与传统的结合。口头文学因其口头特性,更容易让位于便于记忆、可以重复和易于随机替换的话语。作为口头文学内容的事件,被传统、演述人和受众等共同选择,基于现实生活体验,根据记忆和生活经验提取、重组和再创编,事件本身早已面目全非。
处于内容层面的事件有时会凝结成具有特定含义的指涉性内容,在某一群体中广泛流传。中国有流传千年的成语故事,几乎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用以解释成语的来源和含义。如卧薪尝胆、滥竽充数、三顾茅庐等成语,都曾是历史上或传说中存在的“事件”,经过代代相传凝缩为固定表达,最终成为特定传统中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特定事件成为特殊记忆,随着不断复述、提及相关内容使之具有特定含义。某一事件最后浓缩为特定语词,成为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形成口头传统中指涉性内容的一部分。“重要事件被反复演述,地方性知识被系统化承载,思想情感被生动刻画”。不同类型的事件被筛选成为口头文学文本组成部分,对某一事件的反复讲述最终成为口耳相传的素材,成为集体记忆和地方性知识,影响演述人的“大脑文本”和受众的“期待视野”。口头文学成为记录事件、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三、多重事件关系的互构共生
口头文学蕴含的多重事件关系,可以从事件、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和作为口头文学内容的事件三方面进行思考。理查德·鲍曼的著作《故事、演述和事件:口头叙事的语境研究》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概述了事件与演述文本之间的关系,通过恶作剧、荒诞故事等说明事件与被叙述事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事件先于叙事,事件的发生也是人为建构的部分。鲍曼在书中提到的案例更适用于阐释当前发生的事件与口头叙事之间的关系,如果放眼整个文化语境,事件与口头文学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联。生活场域中的事件与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形成“前事件—演述事件—后续事件”的时序关系,其中又含有因果关系、交叉关系和包含关系等,其他事件与口头文学演述事件的关系还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从线性关系进入内容层面的嵌套关系。事件转变为口头文学演述的内容,而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演述又与进入内容层面的事件、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彼此关联、互构共生。
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演述与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并不是完全分隔的状态,彼此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也会反作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过程性事件,甚至改变或引发新的事件。伊丽莎白·伯德(S. Elizabeth Bird)曾研究美国艾奥瓦州(Iowa)的黑天使传说之旅。黑天使是一座坟墓旁的纪念碑,是当地一位女士为早夭儿子雕塑的天使铜像,由于氧化而呈黑色。黑色和天使在美国文化中有着截然相反的象征含义,这座黑色天使雕塑便引起种种猜想,围绕“黑色天使”出现众多传说,还衍生出一个预言:如果访客与天使进行身体接触或打扰天使,将在24小时、7年或未指定的时间内死亡。尽管传言涉及危险因素,但去拜访黑色天使是艾奥瓦州青少年亚文化的一部分。典型的“传说之旅”会在深夜开始,到达黑天使墓地后,青年们会讲故事、喝酒、进行预言测试等狂欢行为,对他们而言这更像是一种游戏,有的还会将黑天使传说之旅作为成人仪式。伯德认为,与传说相关的事件行为与死亡、性、道德密切相关,文本为事件本身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一位母亲为早夭儿子雕塑天使雕像这一事件引发了有关传说,传说又引起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传说之旅”这样的事件又为传说增添了许多同类型传奇叙事。传说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寻常事件作出解释,民间传说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产生双向互动互构的关系,既是内容层面的互构也是现实层面行为事件的互构。
事件与事件、事件与内容的不同层面之间互动与关联十分复杂,彼此互构共生,并不能将它们完全区隔而进行分解式研究,应将口头文学演述事件置于整个文化语境中,观察口头文学从内容层面到作为事件整体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口头文学演述事件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社会生活中各类事件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在研究口头文学时只关注文本或演述本身都可能会断章取义。巴莫曲布嫫曾批评口头文学“文本迻录”过程中出现的“格式化”现象。彝族史诗“勒俄”分为“公本”和“母本”,分别对应婚礼和葬礼等不同场景。而当时的整理翻译者没有关注到演述发生的前事件,对演述事件未能全面观察,认为两种演述文本并无实质差别,于是将两种演述文本整合到一起,阉割了演述与传统、事件、生活之间的关联,只留存了内容。
口头文学演述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与口头文学演述具有整体性。如因交易而进行的故事,故事讲述同时具有社交和交易的功能。鲍曼在书中谈到猎犬交易事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小镇坎顿(Canton)每个月都会举行交易会,交易会上从事猎犬交易的人围绕自己的猎犬讲故事。讲故事的过程既是演述事件,也是吸引顾客进行交易的销售行为,讲故事的过程同时也是交易过程。回到生活场域中,生活事件与演述事件并无清晰界限,口头文学演述事件是现实生活各项事件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彼此交融。
事件是口头文学演述场域建构的要素之一,演述过程中不同事件会影响演述的内容和进程。一位哈萨克族年轻学者在当地两位干部的陪同下采录演述人演唱史诗,结果两位干部在演唱过程中昏昏欲睡,录音机还出了故障,演述人草草结尾并就此唱道:“听我演唱的人不多,其中还有一个听众是录音机。不巧它的肠子出了毛病,变得越来越长,还紧紧地绞在了一起。”演述人因受众的状态和录音机故障压缩演述内容,并将现场发生的事件创编进演述内容中。演述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事件影响演述文本甚至影响演述进程,成为演述过程中的“插曲”。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在一次田野录制过程中,因为歌手的工地领导叫他回去,歌手急于返回工作,于是匆忙结尾,整个诗行相较他之前的演述要少很多。笔者在河南参加马街书会时遇到一位河南坠子演述人,一段即兴演述后,台下受众十分热情地邀请她继续演述,她因稍后有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为保存体力而婉拒了受众的请求。有时演述过程中发生突发性事件,也会导致演述中断。可见,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演述与生活中各类事件互相联系,充满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他事件随时会影响演述场域。人与事件、事件与事件、事件与内容相互建构与塑造,在主体、时空、内容以及形式等不同方面的互构共生,也映射出口头文学演述场域中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结语
口头文学演述是生活的一部分,应将口头文学置于演述场域、生活场域和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之中,对口头文学演述行为、外在关联和内在形态进行系统性、多层次和多维度思考,以“全观”的视角看待口头文学演述实践。“‘全观’并不是在该词‘完整、全体’等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基于‘整全观’(holism)立场——在广泛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系统性地观照研究对象。”
将口头文学演述视为事件的一种,也就将口头文学置入动态、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可以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生活以及人与世界的交流过程。而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由外部关联转向内在互动,包含群体和个人在思维层面与历史和当下的互动。作为事件的口头文学和进入口头文学内容层面的事件,延伸出口头文学事件关系的多种形态,彼此互构共生,共同构成口头文学与生活的多种联系。口头文学演述过程中,事件并非被简单地排列和复述,而是通过演述人创造出事件与传统、演述和生活之间的内在性,展现出不同的交流策略。一方面,口头文学作为交流事件,如同语言一样,是一种交流工具;另一方面,口头文学带有文化传承的烙印,显示出人类与世界多种关联的痕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