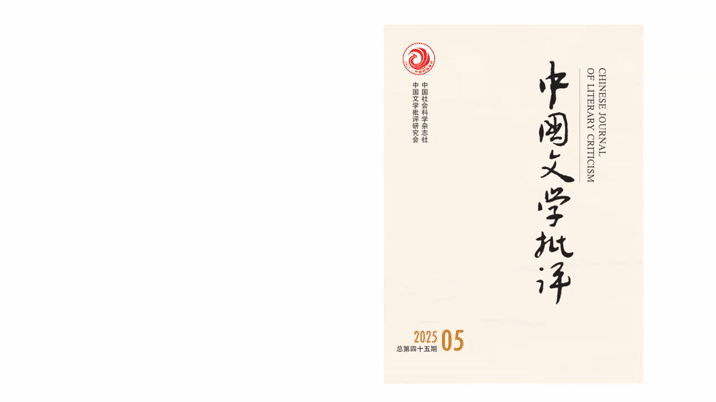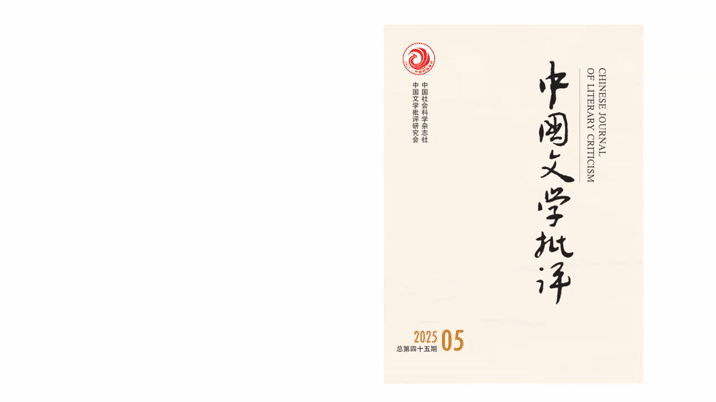
2024年,民间文学重回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序列,由此产生了关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诸多讨论。民间文学学科的主要对象是指民众以口头方式创作、流播、传承的文学,分支学科包括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歌谣学、史诗学等,并强调学科兼重文献和田野实践及调研。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二级学科不同的是,田野作业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也是确立其学科独立性的标志之一。从20世纪初歌谣运动中研究者主张“到民间去”,到采风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采风掘宝”;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现代民俗学倡导“回到语境”,到近年来民俗学研究者倡导“有温度的田野”,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田野”所表征的观念经历了从概念到方法的拓展,田野观在中西文学的交融与变奏中不断发展变化。
从当今的学术研究状况来看,民间文学与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关系密切。人类学研究者将口头艺术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民俗学研究者将民间文学界定为民俗文化,文学研究者将口头文学的研究作为整个文学学科的组成部分。在学术史的书写中,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二者交合重叠,又被称为“口头文学”“口头文艺”,其方法论根植于实证主义,皆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由此,在百余年的田野实践中,中国学者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促成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学科主体性的确立,民间文学的方法想象与本土实践也由此展开。本文以歌谣运动为起点,将中外史诗研究者的田野作业置于多学科交织的整体视野中予以回溯和考察,从方法论建构的视角审视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如何从人类学进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分析在口头诗学本土化过程中,田野观发生的变化。
从“采集”到“采风”:田野观念的发展
我国的采诗传统历史悠久,《诗经》中的大量作品源自歌谣、采自民间。“王官采诗”具有双重意涵:以风化下为教化,以风刺上为讽谏。在中国文学史上,采诗传统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楚辞》以及汉乐府等古代文学经典中均保留着采诗官观风辨俗的印迹。
(一)歌谣运动开启田野调查
20世纪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采集歌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知识分子从歌谣中寻找新文学创作的新材料、新史学建构的新范本。“歌谣”被视为民俗学的重要资料,采集歌谣的步骤是:调查—整理—研究—利用。调查的方式包括采集、征集和辑录,并有“直接采访”和“间接征用”之分。显而易见,“调查”一词具有现代色彩,主张研究者回到民间、采风问俗,这种学术转向必然导向田野实践。施爱东认为,虽然当时强调采集之后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但是科学的方法到底如何界定,则无具体阐发。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是由文学、历史学的本土学者推动的,他们虽然承续了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但忽视了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这种与民间文化剥离的“采集”带有“采风”的遗迹。对当时采集歌谣的知识分子来说,“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方法,虽然不少知识分子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征集歌谣,但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此时的“田野”承载着文学革命的浪漫与想象。这种眼光向下、关注民众的思潮传播开来,开启了民间歌谣的挖掘整理,为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将采自民间的民俗材料与经史材料进行对照研究,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新路径。当时的歌谣运动将现代学术意识注入传统文学研究,突破了静态文本观的认知局限,为后来的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雏形。
(二)采风运动深化田野观念
钟敬文在1935年提出“民间文艺学”时,就重视田野作业,强调关注文本生成的语境,在赓续采风传统与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和方法,重构了“田野—文本”的互动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文学正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倡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盛况空前的民间文学“采风运动”。少数民族史诗开启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采风”,“捕风者”深入民间采集文本,经过翻译、改编形成新的文本。例如,1960年5月至8月,民间文学调查团深入青海等地区,搜集了很多“格萨尔”史诗的手抄本、木刻本等第一手资料,经过翻译、润色形成新的文本。在国家主导的“抢救性采集”工作下,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采风掘宝,将其加工提炼为新的文本。在人民文艺观的引导下,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民间艺人演述本,“文本化”问题成为民间文学的核心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程,据当时统计,全国各地搜集的民间故事、歌谣等,总字数超过40亿字。这种地毯式的、抢救性的搜集、整理工作虽然成绩显著,但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艺工作者主观的删减与改编痕迹,包括翻译水平也参差不齐。
为了提高民间采集工作的质量,中国学者在继承采风传统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收外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强调文艺工作者与民众面对面交流,忠实记录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学素材,促成采风传统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将某种民族民俗作为遥远而疏离的异域风情,或某种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与活力的文化‘活化石’,而是当作依然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文化生产与创造:它不仅是文学知识,更是观念生产;不仅是理论创新,更是生活实践”。随着人民文艺观的深入实践、采风运动的推动,以及国外民俗学、人类学方法和视野的引入,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具有了深厚的民间立场。从“采诗观风”到“采风掘宝”,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田野、从想象田野到深入田野,而民众也从采风客体变为文化主体、从他者表述转向自我表达,其主体性从隐到显。与此同时,田野的观念和方法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发展变化。
参与式观察:作为实验的田野
早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就把口头艺术视为“有趣的文献资料”,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阐述其功能。田野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田野研究、田野考察等,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工作”。田野调查的方法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之后,成功破解了西方的“荷马问题”和中国的“史诗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田野作业不仅是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变革。口头诗学的“田野”是由“问题”引导的,研究者积极寻找反映普遍性的典型个案,观察、记录、感知和阐释活态文本,使田野成为可对话的文学场。
(一)“荷马问题”与西方学者的“现场实验”
“荷马问题”主要与《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创作、作者的身份有关。具体而言包括:荷马是谁,史诗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根据语文学(philology)分析古典文本的方法来解析“荷马问题”,即通过研究各种古典语言间的关系和各种异种语言弄清古典文献的来源,并理清和解读这些古典文献。遗憾的是,语文学所惯用的语法分析、文本对勘分析、修辞分析和历史分析都无法解释荷马史诗的来源、历史和存在方式。
反观口头文学的田野作业,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民族志,如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ii V. Radlov)根据歌手即兴创编史诗过程的观察与描述所提出的“复诵部件”(recitation-parts)的观点,葛哈德·格斯曼(Gerhard Gesemann)使用“现场田野验证”(in situ testing)对南斯拉夫诗歌“创作图式”(composition-scheme)的论析。这些民族志不仅为帕里提供了传统史诗的活态文本,也对他学术思想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提出:荷马史诗是传统的,也一定是口头创作的。帕里对荷马史诗精细的文本分析所概括出的典型特征,在活形态的口头诗歌中得到了映现,但支离破碎的第二手文献难以支撑他的理论设想。
帕里意识到南斯拉夫的史诗演述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原貌相类似,这激发他回到真实的演述场域当中。1933年夏,为了印证荷马史诗的“口头性”,帕里从文本走向田野,前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将荷马史诗与活态史诗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1934年6月至次年9月,帕里再次回到南斯拉夫展开了为期15个月的田野作业,在他的助手洛德(Albert Bates Lord)等人的协助下,汇集了12500个文本,大都是抄本,还有大量的录音资料,大约有3500个12英寸铝制唱片。这次田野作业被称为“现场实验”(in-site testing)。后来这些田野笔记、图片、手抄本的资料以激光唱片的形式与新版《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并面世。
回溯帕里和洛德的现场实验,他们在前往南斯拉夫之前,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田野作业方案,有着明确的研究目的:“要精确地确定口头故事诗的形式,认清它与书面故事诗的区别”。正如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所写:“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弄清歌手们创作、学习、传递其史诗的方式”。显而易见,帕里和洛德的田野作业不仅仅是观察、记录和分析一个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要分析口传史诗表演中的基本法则,从而验证自己的理论预设。因此,在选择田野调查点的时候,他们也是围绕着“问题”而展开的,采用多点式、长时段的田野调查法。洛德在其手稿中写道:“寻找歌手的最好办法,是到土耳其的咖啡馆,在那里交些朋友。这是逢集市时农民的活动中心,也是斋月期间夜生活的娱乐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帕里的“田野”,帕里在这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歌手。
帕里和洛德从书面文本走向活态文本、从文本分析转向田野作业、从历时性研究转为共时性研究,在对南斯拉夫歌手的两次实地考察之后,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正式成形。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即《故事的歌手》,田野作业所搜集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Milman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人类学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口头文学的田野作业是由“问题”引导的“现场实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类学家的“田野”是远方的他者,可能是海外、乡村、草原或者蛮荒之地。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解释人类文化现象为目的,通常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口头诗学的“田野”是传统的文化空间,可以是宫殿、帐篷、咖啡馆或者旷野。田野作业以验证预设的学术问题为目的,研究者将田野视为没有围墙的实验室,通常是在某一时间段内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田野调查的方法移植到古典学研究之后,通过对活态史诗的观察和理解,解决了西方的“荷马问题”,并提出口头诗学理论。
(二)“史诗问题”与中国学者的田野研究
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贯穿20世纪乃至当下。20世纪初叶,西方文学理论观念传入中国。西方文学的源头是神话和史诗,而中国并没有类似西方史诗那样的诗歌体裁,就连神话也是零碎分散于史部典籍和诸子著述。以西方文学惯例来观察中国文学史,自然会产生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中国学人,如“史诗问题”。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有力地回应了所谓的“史诗问题”。中国不仅有《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而且拥有数量丰富、形态多样的多民族史诗。钟敬文认为中国的史诗研究仍然存在“见木不见林”的缺陷,其原因是相关研究停留在资料堆砌和异文本汇编阶段,理论梳理和探究不足。这不仅阻碍着中国史诗学学科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史诗在世界文学之林的地位。“史诗问题”从“中国有无史诗”转换为中国史诗学理论的“失语”问题。
在史诗的田野作业方面,朝戈金的经历和研究具有特殊性。田野作业的前田野,如研究问题和理论预设、研究计划和工作模型、技术手段等是保证田野研究科学性的必要前提。朝戈金研究中的前田野是一个偶然与必然耦合的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看似由生命的“偶然”交织而成,却在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中走向“必然”。第一,朝戈金的父亲巴·布林贝赫先生是蒙古英雄史诗理论的奠基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因此他从小就浸染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另外,在牧区的知青经历让他谙熟史诗演述的过程。第二,1989年,朝戈金陪同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到新疆做田野调查。1997年,朝戈金陪同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到内蒙古考察,参与式观察口传史诗田野作业的过程。朝戈金是弗里进入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向导,而弗里成为朝戈金进入口头诗学的引路人。第三,1995年,朝戈金参加芬兰的国际民俗学会暑期研修班,而后到哈佛大学访学,2001年到密苏里大学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并翻译了《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从实践到理论、从译著到专著,在进入田野之前,朝戈金对江格尔史诗的流布情况已经胸有成竹,并广泛参照国际史诗学界晚近的理论成果,罗列出六大问题:(1)如何正确认识“口头性”与“书面性”的关系;(2)史诗文本的种类和基本属性;(3)史诗文本与演唱语境的关联;(4)给定的文本与整个传统的关系;(5)史诗研究的方法论问题;(6)史诗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使民间文学从抢救性记录变成文本化过程的分析与阐释,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和本土理论自觉。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进入他者的世界,与帕里和洛德不同的是,朝戈金不是以一个文化的“他者”进入田野,而是以一个“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验证田野。现场实验要求田野研究者将自己的理论预设放置到真实的语境中,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在遴选田野作业的对象上,蒙古族歌手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史诗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样本。在方法论上,朝戈金反其道而行之,他两次前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把既定文本放到传统的演述场域中进行对照与还原。口头诗学以精细的文本分析而著称,朝戈金借鉴帕里在南斯拉夫田野作业的模型,参考国际史诗学界共享的分析模型,进行“田野再认证”。他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其词语、片语、步格、韵式和句法进行精密的诗学分析,进而与伟大而悠久的蒙古族史诗传统之间建立学术关联,从而“逆向”地解决口头诗学的问题。
口传史诗的田野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场实验,“现场”意味着回到口传史诗创编、演述、流布和接受的场域之中。当史诗文本还原到传统的文化空间时,之前看似玄奥的理论预设在真实的演述场域中得到解答。2000年,《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史诗研究,给口头传统研究带来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此书也确定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的方法和步骤,后经巴莫曲布嫫等学者在田野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与阐发,确立了口头传统的田野方法,包括:(1)选定一个研究主题;(2)定位一个田野现场;(3)完成田野方案;(4)建立田野关系并发展其亲和度;(5)民族志访谈;(6)参与观察;(7)音影记录;(8)建档;(9)口头档案与文献资料的一体化;(10)处理事件描写和音乐誊写的问题;(11)传统呈现与文本制作;(12)传统阐释。其方法立足于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实践,在系统性梳理、分析和提炼国内外史诗学者田野作业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走向学理性的建构,成为口头传统研究的田野作业指南。正如朝戈金所说:“对口头文本的采集、誊录、转写需要从田野研究、民俗学的文本制作观念及其工作模型上进行更为自觉的反思和经验积累。”这些反思和积累一方面来自中国史诗田野实践,另一方面来自他所承继的语文学传统,以及与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对话、碰撞。这种从文化传统中“提取”样本,把真实的演述场域作为口传史诗的实验室,将“文本对象化”和进行“田野再认证”的模式,为口头传统的田野作业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
取法民间:作为方法的田野
如何定义“田野”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生活本身”,田野的目的是“学术的”还是“文艺的”,研究者是要“冷眼旁观”还是要介入日常生活?围绕着田野的伦理、田野的技术操作的争论向着不同的方向展开。尽管有学者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甚至要“告别田野”,但民俗学家不是要抛弃田野,而是要抛弃平面的、单一的、重复的采集整理,从搜集资料走向理论研究。
中国史诗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季羡林将语文学的精密考证与口头传统动态分析相结合,开创了中印史诗跨文化比较的东方范式,并开拓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例如,“中国史诗研究”丛书显示出创建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目标,标志着学科主体意识的觉醒。又如,杨恩洪回到格萨尔史诗演述场域当中展开田野调查,将说唱艺人分为五种类型。郎樱、降边嘉措、斯钦巴图、刘亚虎对《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和南方史诗的内部结构和文化展开分析,勾勒出中国史诗的整体面貌。面对中国史诗多民族、多语种、多类型、多地域分布的特点,第一代史诗研究者将外来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史诗的田野相结合,突破了结构主义、类型学研究的范式,并把史诗视为活形态的文本置于文化空间中解读,开创了符合本土文化逻辑的方法论体系。从根本上讲,他们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受到故事形态学和类型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熟悉本地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传统,既注重文本的叙事结构,又强调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具有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民俗学“三大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理论、演述理论)的引介和本土化实践引发了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革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其研究重心由民间文学(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民间歌谣、谚语、曲艺、民间小戏等)向民俗事象(节日、人生仪礼、民间游戏、民间信仰、旅游民俗等)偏移。这两个脉络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民间文学研究偏重文本分析和地域传播,研究者在自然语境中观察文学发生、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再现复杂的文本,发掘文学的法则;而民俗事象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强调对文化的阐释,研究者在真实的语境中对民俗事件整体地观察、研究与深描。前者出现了文学转向,后者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展,更深刻地改变了方法论体系与知识生产逻辑。
自《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译介以来,中国学者就意识到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不同于民俗学者书写田野民俗志。以书面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解析民间口传文学,犹如刻舟求剑,难以鞭辟入里。基于这样的探讨路径和研究取向,中国学者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的实践性经验与国外理论相结合,强调在田野中观察、记录歌手演述的情境、歌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史诗演述与传统、文本之间的关系等,开创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论体系。具体而言:第一,结构分析法的深化。斯钦巴图、乌·纳钦等结合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探讨蒙古族史诗的程式意象及其文化隐喻。他们聚焦史诗的文化阐释,从文本和文化双重维度揭示蒙古族史诗的母题类型与多级程式意象。然而,结构分析派的研究其实隐藏着对口头文学的误解,把活态文本转化为静态文本的研究路径,实质上忽视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们也逐渐走向田野。巴莫曲布嫫针对史诗演述场合的传统规定性及其相应的叙事界域,提炼出“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的观点,并将史诗演述场域总结为“五个在场”,即史诗演述传统在场、表演事件在场、受众在场、演述人在场和研究者在场。“五个在场”的提出基于文化语境和演述场域对史诗的形塑作用,体现出高度自觉的方法论意识。第二,比较研究法的拓展。尹虎彬对帕里—洛德理论的核心概念做了深入辨析和本土化阐释,提出史诗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概念的重构拓展了研究视野,推动民间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陈岗龙、姚慧以及笔者尝试以跨族群、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法对比藏族、蒙古族、土族格萨(斯)尔史诗,从文本研究转向语境研究。比较研究借鉴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既注重文本的历时性回溯,又关注多民族文学的共时性传播,对史诗作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整体考察。第三,史诗传承人的研究。如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诺布旺丹等深耕田野,采用长时段、多点式的田野调查法研究说唱艺人。他们把口传史诗放置到活形态表演语境当中,在歌手与民众的互动中考察文本创编的过程,同时借鉴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以传承人的生命史重构文化史。第四,多模态田野的数字化实践。媒介技术的演进,改变了口头传统的记录方式和传播模式,形塑出新的文学生态与文化样式。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研究方法的革新,如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应用多模态记录,抢救性保存活形态的史诗,推动史诗的数字化典藏与活态传承研究。口头诗学的田野作业立足中国史诗的本土实践,吸收了国外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演述中的创编”,将演述场域、文化语境、演述人和受众等活态要素纳入田野研究体系,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参考和指引。
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以问题为导向,学者们树立了“活形态”文本观,从文字采录转向演述事件的全息记录。在“口头诗学”的观照下,中国学者“将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个人生活史书写、在语境框架中解析文本、定向跟踪史诗演述人及其与所在群体和社区的互动等多种田野作业法并置为多向度、多层面的整体考察”。这些具体的田野个案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思考和田野反思,他们扎根中国多民族史诗传统,经过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作业,以跨学科的整体视野提炼出本土化的核心概念、工作模型和“全观诗学”阐释体系,在方法论层面突破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局限,关注语境中的文本呈现,转向以演述者为中心的民族志诗学研究。
结语
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自发轫之初,其方法就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中,中国学者在赓续采风传统、移植外来方法、重视本土实践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演述为中心的范式转型,确立了具有本土经验并能与国际研究对话的主体性话语。在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把“田野”视为“新文学”创作素材的来源地,倡导采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在这一时期,他们把“到民间去”作为一种方法,对民间的注视多多少少具有居高临下的意味,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抵达田野,对田野的凝视与想象停留在思想层面,田野承载着他们再造民间、重建历史的愿景。当时的知识分子尽管有着较为清晰的民间文学意识,却难以摆脱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惯性,将口头文学纳入书面文学的研究范式。在采风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把“田野”视为蕴藏着“矿藏”和“原料”的资料采集地,他们以向人民学习的姿态深入民间、将自然形态的材料萃取出来,加工提炼为新文艺,为后来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使民间文学从抢救性记录转向文本化过程研究,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深受民族志的影响,学者们树立了“活形态”文本观,从文本走向田野,聚焦演述现场的动态过程,开辟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在技术革新与学科自觉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学者以世界性的研究视野关注本土的田野实践,不仅继承了古代采风传统,同时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并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灌注进田野作业的工作模型中,为世界史诗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百余年的文学实践中,舶来的方法与中国的田野不断互动、调适,在古今对话、中西互鉴的本土化过程中推动着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学术范式的转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