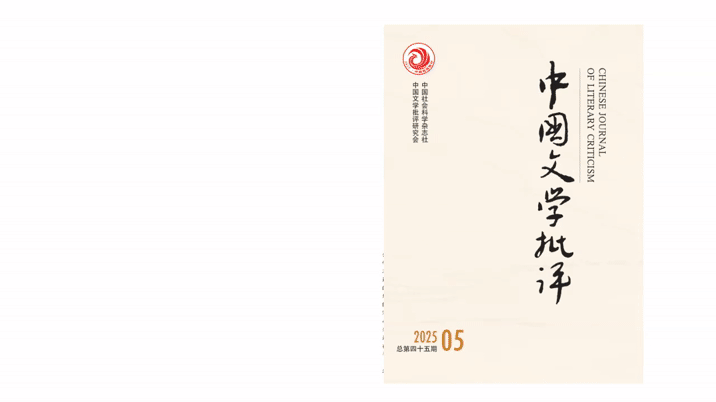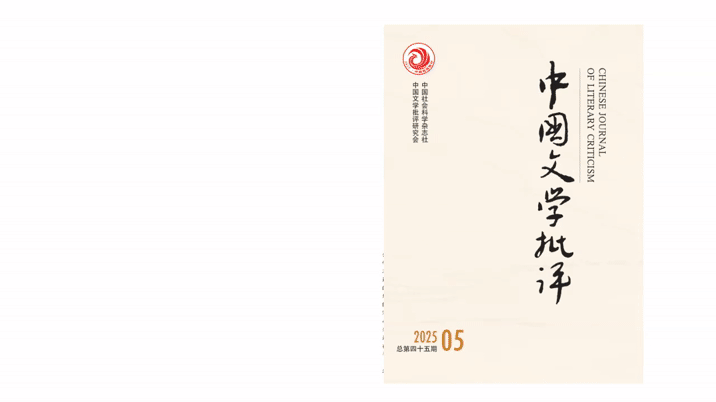
论及文学与艺术的审美创造,中国古人常会标举“游心”说。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有一段经典论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文学作为情感的风向标与心灵(神明)演奏出来的美妙音乐,都有赖于“游心”的审美运作,如此便能“气韵天成”,创造出自在的艺术境域。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则以“游心”论绘画创作:“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绘画艺术也像文学一样,通过“游心”方能作出气韵生动的画。可见,在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游心”成了作家与艺术家进行自由创造的重要前提。
追溯“游心”这一中国美学中的重要观念,自然与庄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论语》中有孔子“游于艺”的说法,但真正将“游”与心灵的创造及运用关联起来的无疑是庄子。方以智《药地炮庄》在释《庄子》内篇时称“《内篇》凡七,而统于游”,当中还引刘辰翁的话总结道:“《庄子》一书,其宗旨专在游之一字。”据杨儒宾统计,《庄子》全书“游”及“遊”字合计出现多达198次,因此他将“游”视为“《庄子》书中的字眼”。颜世安的《庄子评传》直接以“游世思想”概括庄子的核心精神,将这种“游”理解为“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这似乎未能触及庄学追求艺术性生存的终极目标。
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庄子之“游”与西方美学中推崇审美自由的思想相契合。如张世英便很自然地以席勒的“游戏冲动”说阐释庄子:“庄子讲的天人合一境界之自由的特性(‘无待’——无限制)也正如席勒所说,同时是审美——‘游戏’的特性。自然而然,既是自由,也是审美。”其实不只是席勒,康德认为审美(鉴赏)“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黑格尔看重“自由的无限性”,推崇生气灌注的心灵的生命,海德格尔则强调艺术作品是一种澄明,是存在者的自由敞开,即“存在者才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也强调了艺术的自由特性。这些思想均与庄子的“游”或“游心”存在可通约之处。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在分析《庄子》“游”的观念时,将其揭示为一种“活动的机制”:“这一机制没有目的,但会很有用。它有一种哲学的意义,因为其中即有对必然的认识,也有一种由此产生的,由对必然的静观所产生的第二性的自由。”其中“第二性的自由”便强调审美创造的自由。可以说,“游”作为一种自由境界,确实与西方的审美自由观存在相似性。
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徐复观作为率先以西方美学思想中的自由审美创造阐释庄子之“游”,进而阐发中国艺术精神的名家,影响无疑十分巨大。他在多部著作中直接以“精神的自由解放”概括庄子“游”的思想,认为“得到自由解放的精神状态,庄子称之为‘游’,亦即开宗明义的‘逍遥游’”,同时他将以精神自由解放为主要特征的庄学,阐释为奠定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理念。这种阐释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但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局限。我们试图从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谈起,探讨庄子“游心”说内蕴的“自省”精神与“超越”性品格如何渗入中国美学精神之中,深刻塑造古代艺术及审美的至高典范;同时也对徐复观的阐释提出反思,思考“游心”说所代表的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的审美自由观念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些相异之处。
一、自省与超越:奠定中国艺术精神的庄子之“游”
徐复观对庄子之“游”的阐释、对“精神自由解放”之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视,与新儒家对于现代文明之“物化”危机的体认有直接关系。他的老师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说道:“西洋人大抵向外发展之念重,努力于物质与社会等方面生活资具之创新,其神明全外驰。……是则驰外之所获者虽多,而神明毕竟物化。……故曰其失也物”。正是出于这种对过度“物化”的反思,新儒家有意反其道而行,特别张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属性,认为这是与西方文化相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正是缘于此,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的序言中尤其强调中国艺术在人类精神与心性方面的卓越贡献: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而在绘画方面,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画家和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
很显然,在徐复观看来中国艺术所内蕴的“精神自由解放”的价值,主要是由庄学及其“游”的思想所奠定的:“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徐复观之所以特别重视庄学之精神解放维度对于中国艺术的奠基性作用,还与他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观察有直接关系。1961年他赴日考察,深感于“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之下“人性的丧失”,遂大力批判现代文明影响下的艺术创作导向的“非人”特征。此行过后,他多次与台湾现代派画家论战,表达对现代艺术的批判。在他的眼中,诸如达达主义、抽象派绘画、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展现的正是被物欲横流的工业文明所侵蚀的现代心灵,“它是顺承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来的”,观看这类艺术不但不能疗愈精神创伤,反而“更增加观者精神上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感觉”。以下这段话很好地揭示了他以庄子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问题意识之由来:
以庄学、玄学为基底的艺术精神,玄远淡泊,只适合于山林之士,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竞争、变化,都非常剧烈,与庄学、玄学的精神,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则中国画的生命,会不会随中国工业化的进展而归于断绝呢?
很显然,徐复观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了否定。庄学影响下中国的山水画具有一种现代艺术所不具备的自省精神与疗愈功效,“中国的山水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社会,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是反省性的反映”,他坚信这种具有自省精神与超越性品格的艺术对于现代人受伤的心灵更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的山水画,对于由于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正是从这种具有高度现实感的问题意识出发,徐复观开始追溯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并且找到具有精神解放意义的庄子。
从某种角度而言,《庄子》一书确实贯穿着精神自由的气质,书中从最高的宇宙支配法则“道”到具体的身心实践“心斋”“坐忘”,无不蕴含着自由的智慧以及对于艺术性生存的深邃思考。庄子的“道”是从老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其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对现实政治的抵抗和对自然的推崇。韦政通认为:“强烈的反抗情绪,使老子向往一个原始型的单纯社会,使庄子则追求一个超越而又和谐的心灵王国。不论是社会或个人,他们都赋予纯朴、自然的性格,这一点又是完全相同的。”徐复观在分析《大宗师》“造物”观念时说:“庄子和老子一样,以道为形上地造物者。而其所谓‘自然’,乃指道虽造物,但既无意志,又无目的;造物过程中之作用,至微至弱,好像是‘无为’;既造以后,又没有丝毫干涉;因此,各物虽由道所造,却好像自己造的一样。所以‘自然’一词,可以作‘自己如此’解释;这主要是对于传统宗教中的神意所提出的棒喝。”
作为《庄子》全书的开篇,《逍遥游》是庄子追求自由的总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庄子似乎想表达,人生活在暗沉的世界之中,要想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审美自由,唯有努力超越功名利禄的束缚,做到无己、无功、无名。这种精神自由无待的境界就是“逍遥游”。“逍遥游”与作为全书总纲的《天下》篇对“三言”的解释正好形成了呼应:“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然而,具体应该如何超越“天下之沉浊”,在暗沉的俗世中葆有一份清明?在庄子看来首先应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有限性与复杂性。世界上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现象,既有“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也有“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诸如此类,千差万别。因此,必然会出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现象。一个人的德行、认识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人应清楚这些局限,不要因为这些局限拘束自己的精神自由。倘若一个人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抛弃了荣辱,也就实现了精神的自由。而真正的精神自由,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方能实现。由此可见,这种精神自由的实现之途,总是伴随着对有限性的超越。对于这种精神自由,庄子使用了“游”这个精妙的动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显然,这种超越有限性的“游”非身体所能达到,只有精神方能实现。
《庄子》一书中,除《逍遥游》整体讨论“游”之外,其他篇目都提到过“游”。如《齐物论》:“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应帝王》:“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更值得注意的是“游心”一词的提出。《庄子》一书特意将象征自由的“游”与人的心灵活动、精神运作加以关联。内篇中的《人间世》提到“乘物以遊心”,《德充符》提到“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中提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等等。事实上,庄子所说“游”只能是“游心”,“游”只可能是心之游而不可能是身之游,身体的有限与沉浊注定无法乘云气、骑日月、游乎方内与方外,而精神活动却有着无限的潜力与可能。徐复观在阐释庄子之“游”的精神自由内涵时,特别将其与西方美学思想加以互释:
在卡——在其所著的《艺术哲学的经验》(一八八三年)中认为艺术是对自由的表明,对自由的确认。何以故?因为艺术是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的解放。以提倡感情移入说著名的李普斯(Lipps,1865-1930)便认为“美的感情”,是对于“自由的快感”(“A sthetik, S. 156”)。而海德格(Heidegger, 1889-)则以为“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地享受”。柯亨(Cohen, 1842-1918)则以为把科学意识、道德意识作素材,作出新的东西,而产生艺术。艺术是在科学、道德二者之上,心意诸力,作自由地活动。艺术领域的意识方向,是指向自由活动、发挥其自发性。卡西勒亦认为艺术“是给我们以用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内面地自由”。而把这一点说得最透,最与庄子切合的,无过于黑格尔(Hegel, 1770-1831)。他在《美学讲义》一二三—一四八页中,指明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gie des Geistes)中,以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的阶段为“绝对精神王国。艺术乃在此王国中保有其位置”。假定把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王国”改称为庄子所说的“道”,则仅就人的生命在此领域中能得到自由解放的这一点而言,实与庄子有共同的祈向。
通过这种与西方美学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徐复观对于庄子之“游”与“游心”的两层重要理解:一是强调对暗沉之社会现实以及人类之有限性的超越,二是凸显精神及心灵活动的无限潜力,两者共同构成了庄子“游心”说精神自由的重要内涵,且奠定了后世中国艺术精神的超越性品格。后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对于庄子的“游心”说的继承与发展,可从这两个维度上加以体认。
二、“神游”与“逸格”:从自由创造到自在之境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大抵先以庄子为滥觞,继而又以中古玄学作为中介。在他看来,庄学所播种的艺术精神一直潜藏于国人的心灵之中,却要到魏晋时期方才获得普遍的自觉与激发,这种现象“与东汉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的陵替,及老庄思想的抬头,有密切的关系。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实际即是艺术精神;则魏晋玄学对艺术的启发、成就,乃很自然之事”。
魏晋玄学及文学、艺术采用的言说方法是清谈,清谈推动了人伦鉴识与人物品评的盛行,这一过程对艺术的审美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中国艺术对人不可见之“内在”的高度重视,清谈时常论及诸如“精”“神”“德”“性”之类的术语,无不具有指示“内在性”的意蕴。徐复观在关注玄学清谈及人伦鉴识之时,尤其注重其由实用性转向艺术性的过程:
这种人伦鉴识,开始是以儒学为鉴识的根据,以政治上的实用为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分解的方法,构成他们的判断。而其关键之点,则在于通过可见之形,可见之才,以发现内在而不可见之性,即是要发现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要从一个人的根源——本质之地,判断出一生行为的善恶。及正始名士出而学风大变;竹林名士出而政治实用的意味转薄;中朝名士出而生命情调之欣赏特隆;于是人伦鉴识,在无形中由政治的实用性,完成了向艺术的欣赏性的转换。自此以后,玄学,尤其是庄学,成为鉴识的根柢;以超实用的趣味欣赏,为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由美的观照,得出他们对人伦的判断。
这种循名责实,通过外在之形貌直观内在之德、性与神的鉴识,正是一种“艺术性的发见的能力”,而玄学对于人之精神本质的重视,也实为庄学的遗响。因此,玄学提出直达个人内在精神及内在本质的风骨、气韵等概念,很自然地成了后世文艺理论和美学的重要观念。这些无不深刻地打上了道家哲学所赋予的自然的印记。
可以认为,中古时期经常出现的“游心”一词,不但意味着庄学的遗响,更能见出时人对人之精神本质的重视。徐复观指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本质,在老子、庄子称之为德……后期的庄学,又将德称为性。……而人伦鉴识作了艺术性的转换后,便称之为‘神’。此‘神’的观念,亦出于庄子。庄子《逍遥游》‘神人无功’;《天下篇》‘不离于精,谓之神人’,德与性与心,是存在于生命深处的本体,而魏晋时的所谓神,则指的是由本体所发于起居语默之间的作用。”“游心内运”首要运行的是自由驰骋的想象力和思维,即直达个人内在精神深处的“神思”与“神游”。神思是一种融合虚构与想象的思维和心理活动,借助于一种奇妙的思绪将与情感相关联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思维和心理现象,但直到南朝,才明确提出“神思”范畴,形成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的重要发明。从司马相如作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的存在状态,到陆机《文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敞开”,再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的“澄明”,海德格尔式的艺术与审美追问早在六朝时期的文论中已然出现,呈现出了跨时空、跨文明的对话。神思超越时空的思维特征、神秘的心理特征以及其融合万事万物的自然、自由的创造特征被完整而系统地呈现出来。其中,刘勰的“神与物游”概括得最为精准凝练,可以与萧子显“游心内运”说相互发明: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这一段话论及了神思的思维与心理特征以及神思与虚静、神与物游等系列问题,同时还涉及神思的开展与情志、语言及个人修养等关系,其核心则是“神与物游”。“神与物游”是“神”与“物”的自由游戏。“神”是神思,“物”则是指社会现实和自然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甚至还包括虚拟的人、事、物。“游”是自由的作用,意谓“神”对“物”的选择、支配和调动完全自由。在此之前,陆机较早关注到“神与物游”的问题。他在描述神思开展的时候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精”和“心”都是“神”,即神思。神思能够到远达八极,遨游万仞高空,为的是寻找适合的“物”,更好地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情感。陆机清晰地认识到,神思可以使物的形象呈现得更为生动,思想情感的表达更为鲜明。刘勰的神思说正是沿着陆机的思路提出的,不过他对审美创造的自由特质的认识更加深刻,言说也更为具体。“游心内运”“神与物游”之类的观念在后世同样有着巨大的反响。如元代郝经倡导“内游”,他将道家的“游心”改造为儒家化的游心于经史与社会人伦,如以司马迁写作《史记》为例阐述“内游”的重要性:“既游矣,既得矣,而后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视当其可者,时时而出之;可以动则动,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蕴而为德行,行而为事业,固不以文辞而已也。”
如果说“游心”“神游”这类概念意味着古人对于自由创造的重视,那么这种由“游”的自由创造所造就的自在审美境界则可称为“逸”。不论在老庄原典还是魏晋玄学中,“游心”这一概念都意味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而受此影响,强调“心游万仞”“神与物游”“游心内运”的中国艺术精神,在凸显自由想象与创造的同时,贵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个人心性对于暗沉世事的超越,即不被俗物、俗务、俗谛所桎梏,通合于自然之至道的自性。进入这种状态的艺术家应如庄周笔下的鲲鹏或藐姑射仙人一般,是灵明清逸、胸襟超旷的绝世天才。他们的艺术作品不会限于低层次的功利境界或工匠俗手般的技艺,而有一种超离于世间、可望而不可即的“逸气”。具备这一特点的艺术作品不求形似、不拘常法,却能给人带来天然自在的美学感受。文人画兴起之后,文人常以“逸品”为作画的最高境界,关于“逸品”为何人提出一直颇有争议,或谓出于李嗣真(《书后品序》),或谓出于张怀瓘(《画品》),或谓出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而徐复观认为“逸品”这一概念出于张怀瓘,在研究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时,他特就其标举“逸格”作了大量分析。艺术中所谓“逸”者,便是不拘常法、得之自然,这种“逸”更高于黄休复所开列的能、妙、神诸格,表征着艺术的化境和至高典范。徐复观着重从思想层面分析“逸格”与庄学、玄学的联系:
庄子自己说他“以天下为沉浊”;而他的精神是“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这是由沉浊超升上去的超逸,高逸的精神境界。所以他的《逍遥游》,《齐物论》,都可以说是把“逸民”的生活形态,在观念上发展到了顶点。因此,他的哲学,也可以说是“逸的哲学”。以他的哲学为根源的魏晋玄学,大家都是“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的,这可以说都是在追求逸的人生。当时所流行的“清”、“远”、“旷”、“达”等观念,都是由玄而出,都是与逸相通的观念。尤其是在绘画逸格中的“简”或“简贵”的表现方法,是在一部《世说新语》中到处可以遇见的名词。
徐复观在分析“逸格”时很自然地联系到了庄子具有超越性品格的“游”,认为这种高逸绝尘的至高艺术境界源于庄子“上与造物者游”的精神,经魏晋玄学的发展以及中古美学的概念转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清远旷达、遗貌取神的精神基调。清代恽寿平的《南田画跋》论道:“郭恕先远山数峰,胜小李将军寸马豆人千万;吴道子半日之力,胜思训百日之功,皆以逸气胜故也。”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画作工整富丽,纤毫毕现,但在恽格看来较郭忠恕、吴道子便落于下乘,缺少了逸荡自在的仙气。《宣和画谱》卷八称郭忠恕“游规矩、准绳之内,而不为所窘”,《图画见闻志》中称道吴道子的人物画为“吴带当风”,皆意在刻画其艺术上的超逸气质。这种以“逸”为艺术极境的观念尚不止见于画论,张彦远《法书要录》论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时,便以“超然逸品”评骘之。就文论而言,明代的茅坤在品评《史记》时,便特别提出所谓的“逸调”说,认为《史记》的“逸调”堪称古文的至高典范:
予按太史公所为《史记》百三十篇……其所论大道而折衷于六艺之至,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风》、《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剑舞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当疏宕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者乎?
此处茅坤以《史记》之“逸”(疏宕遒逸)凌驾于《汉书》之“密”(严密),强调太史公文字“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的超逸气质,这实际上是庄子“游心”说所确立美学典范在后世文论中的遗响。由此可见,如果说“游心”“神游”意味着古典美学对于审美自由创造的体认,那么“逸品”“逸格”乃至“逸调”等观念在后世画论、书论及文论中的提出,则是这种自由创造的回响,“逸”作为“游”的结果,成了中国美学中至高的自在之境,表征着士人超升于浊世的精神世界。
三、“与物婉转”:“游心”说中的“功用”与“物欲”
借由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我们探讨了“乘物游心”的庄子思想所具有的自省精神与超逸气质,其中那种超升于暗沉俗世、张扬灵明之无限潜力的内涵,深刻影响了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中古文论中的“心游万仞”“神与物游”“游心内运”之类的观念,与时人对于人内在之精神本质的极端重视密切相关,这奠定了古典美学关于审美自由创造的理念。而这种倡导自由创造的“游心”说,又确立了后世以“逸品”“逸格”“逸调”为至高范畴的自在审美境界。不论是在山水画还是诗文品评中,“逸”始终具有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意义,犹如挣扎于俗世中的文人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辟出了一方自在无碍的净土。
但同时也应看到,徐复观对于庄子以及中国艺术精神之自由解放维度的阐释,实际上深受西方美学审美自由理论,尤其是强调审美无功利一派的影响。他在论述庄子之“游”的时候特别以席勒的“游戏”理论加以互释:“(西勒)认为‘只有人在完全的意味上算得是人的时候,才有游戏;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算得是人。’欲将一般的游戏与艺术精神划一境界线,恐怕只有在要求表现自由的自觉上,才有高度与深度之不同;但其摆脱实用与求知的束缚以得到自由,因而得到快感时,则二者可说正是发自同一的精神状态。而西勒的观点,更与庄子对游的观点,非常接近。”他对“虚静”“心斋”“坐忘”等使“游心”之运作得以产生的心理工夫,也往往以类似的角度进行诠释,如强调“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给心以奴役,于是心便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这是达到无用之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精神便当下得到自由”,“与物相接时,不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活动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于是心便从对知识无穷的追逐中,得到解放,而增加精神的自由”,这些说法都与康德以来主张悬置一切功利性心态以欣赏和创造美的观念密不可分。
应该看到,在庄子那里,虚静恬淡可以说是“游心”得以成立的关键,以徐复观为代表的近代美学家借镜西方,以“审美无功利”阐释“虚静”,以“游戏说”阐释“游心”,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庄子所谓“游心于淡”的内涵。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仍显主流的理解是否就足以揭示庄子“游心”说的全部面向,徐复观的看法是否也存在着某种遮蔽?
笔者认为,庄子思想中对于“功用”“物欲”等问题的理解,与强调美对于人心灵净化功能的西方美学存在着隐微的差异。《天道》中说: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通过这段对于天道的阐释可以看出,庄子思想的最终目标并非要排除功用与价值,反而是要为一切的“有用”找寻一个名为“无用”的基底(万物之本),唯有如容器一般的“虚”方能纳“实”,如镜子一般的“静”方能观“动”,所谓“无为”则是为了令“有为”的“任事者”各自守责。老子认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便是道家“无中生万有”“无为而无不为”“无用之为大用”的真正智慧,这种思想不排除“利”与“用”。北宋的苏轼深明此理,他在《送参寥师》一诗中便用“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来概括庄子的哲理。庄子继续说道,只要掌握了这种终极智慧,“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可见“虚静”在庄子这里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看似降低俗欲和追求,实则却通向一种至高的欲望和至大至显的功名。
理清了这一关键问题,如果再仅以“审美无功利”或者“游戏”说来看待庄子的“游心”说,显然也有着一间之隔。这里涉及中西思想对“物”“我”关系,或者主客体关系的不同看法,其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物自体是无法被触及的,主体可以认知的对象是现象界中的“物”,这种现象之“物”在审美活动中以其纯粹形式作为被审美与静观的对象而出现。那种无目的的愉悦感就取决于“物”的纯粹形式所引发的主体想象力与知性能力的“自由游戏”。而席勒的“游戏”说则重在强调“游戏”对于“质料冲动”与“形式冲动”的调和作用。其中“质料冲动”侧重于人受自然欲望支配的、本能的物质需求。这些看法或者概念的提出,与康德、席勒等人对工业化时代“物欲横流”的体验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从中体认到了人的生存危机,担心人沦为“物的奴隶”。因此,试图通过美学或美育的手段暂时在审美活动中缓解主体对于物的占有欲,将物转化为自由的审美对象。在这种思想中,我们能感受到主、客体之间清晰的分际以及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抵抗意识。徐复观也正是从相似的问题意识出发,以西方的“审美无功利”和“游戏”说阐释了庄子之“游”。
而事实上,庄子所谓的“游”是其构想出的一种流动的“气化/物化”状态,这种杨儒宾所说的“游之主体”并不是为了降低物欲,其真实用意在于教人只有放下对“物”的执着与占有欲,方能更好地“乘物”“应物”“游于物”,最终达到一种主客体交融一气、物我浑然的合道境界,《齐物论》称之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借用《天下》中的术语便是“与物宛转”。在康德、席勒发明美学的时代,西方思想界仍处于理性主义认知论的强势传统之下,认知主体和客体之间仍旧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故而无法最终达至庄子这种“物我合一”的境界。此处试对《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作些分析: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在这则著名的寓言中,庄子这头大牛明显就是关于“物”的隐喻。《说文解字》释“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所谓的“解牛”正对应了《天下》篇中所说的“析万物之理”,“解”“析”二字同义,可见“庖丁解牛”讲述的正是一个关于人与物如何相处的故事。作为工具的刀成为人的延伸,刀是人与物相接的关键,刀之伤其实便是人之伤。而应如何才能避免“与物相刃相靡”的为物所伤的状态?庄子告诉我们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直达事物背后的本质,“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依循事物根本的道理与之相处,如此便能“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庄子所谓的“游刃有余”便是设想了一种“与物宛转”的流动状态,即使面对“世界”(“大块”)这个庞然大物,只要能真正做到“神与物游”,总能找到其中的“郤”“窾”,获得真正的自在。这就像《山木》篇所描述的“孔子”,即使与鸟兽同处,也能“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而不再有《论语·微子》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沮丧之态。因此,庄子之“游”与“游心”固然意味着超升于暗沉世事之上,却并非只是以游戏的精神缓解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或对抗躲避现实的物欲横流,事实上他是不惮于与物相接的,因为物之理即是人之理,背后有着共同的自然之道。这种本乎道、依乎理的精神自在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极高明的处世与应物哲学,是一种诗意的、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也正是这样一种诗意的生存美学,方能孕育出后世精彩而深刻的中国艺术精神。
结语
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徐复观率先以西方美学中的自由审美创造阐释庄子之“游”与“游心”,并将庄子确立为中国艺术精神上的“引路人”。通过借镜西方,他以“精神的自由解放”诠释庄子之“游”,认为其奠定了中国艺术的自省精神与超越性品格,这一看法深具洞见,影响巨大。在徐复观的阐释中,庄子“游心”说既体现出对暗沉世事与个人有限性的超越,又彰显了心灵运作的无限潜能,这两点对于后世的文论及艺术理论都有重要影响,中古文论中的“心游万仞”“游心内运”“神与物游”等观念都源于玄学对庄子“游心”说的继承,而后世文论及画论中的“逸格”“逸调”等观念,则正是“游心”之自由创造的审美呈现,表征着中国美学中至高的自在之境。
同时,我们也应反思徐复观关于在庄学、中国艺术精神以及“游心”说的阐释中,可能潜藏着的某种遮蔽。他以西方“审美无功利”和“游戏说”与庄子的“虚静”和“游心”说加以互释,固然深具启发意义,却可能简化了老庄哲学的复杂面向。庄子思想中作为“游心”之基础的“虚静”概念,并非纯粹回避功利和否定欲望,这种以无为用、“空故纳万境”的终极智慧可以容纳一切物,试图转化出一种至高的欲望,通向至大至显的功名。同时,“游”与“游心”固然超越于浊世之上,却并非仅以“游戏人间”的态度对抗或躲避现实的物欲,而是借由“游”的概念,设想了一种充满流动性的、极高明的应物智慧,这体现为一种诗意的处世哲学。故而,要把握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性,不仅要关注其精神自由解放的一面以及对于世俗世界的提撕与超越力量,还要重视其中根植于道家的生存智慧,即一种艺术化的生命实践。这一精神传统与西方美学的审美自由观念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差异,其中的深刻内涵仍有待发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