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庄子将“游”从表示活动范围的游移,升华到精神自由逍遥、天地与我并生之义,成为中国思想史与美学史的核心范畴之一。“游”的自由超越境界,符合审美的本质;“游”的物我合一体验,符合审美的方式;“游”体现了美学的根本精神。“游”的审美精神落实在中国文学、绘画等艺术领域,则体现为:《楚辞》开启的“神游”文学,呼应了庄子的超越世俗与高蹈自由,更突出了“游”所隐含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列子》的“游观”哲学,深化了身游与神游、游目与游心的冥合,即身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这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山水空间表现。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游”与游戏理论的契合尤其受到关注,这有助于认识“游”的审美精神。
关键词:游;庄子;美学;神游;游观
作者张万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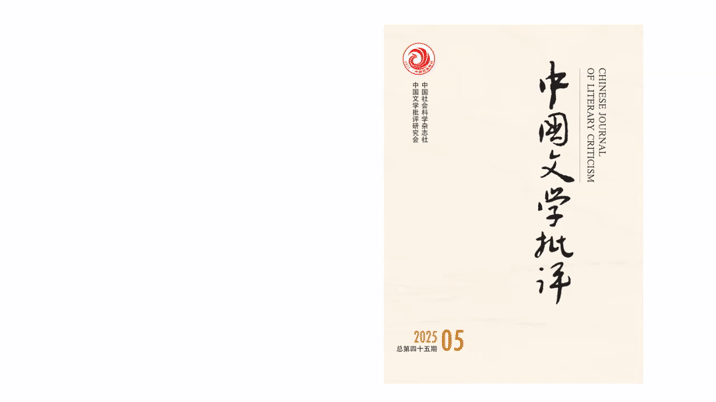
“游”最能体现中国美学的自由、超越精神。“游”的基本意涵,是对原有空间位置的游离与突破。《说文解字》解“游”的本义为“旌旗之流也”,段玉裁指出:“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这是用水的流动比拟旌旗的游移。“游”可进一步引申“为凡垂流之称”,还可引申“为出游、嬉游”。所有的引申义,都源自空间移动的隐喻。
一
庄子:从“游心”到“游于气”
《庄子》一书,“游”字的出现次数和理论深度,远远超过其他先秦典籍。从出现次数来看,《庄子》提到“游”超过一百次。钟泰概括道:“《庄子》一书,一‘游’字足以尽之。故今三十三篇,内篇以《逍遥游》始,外篇以《知北游》终,其余各篇,语不及游者殆鲜。”从理论深度来看,《庄子》的“游”,虽有常见引申义,但更多的是上升到一种理想精神境界的描述,并成为全书的核心概念。王叔岷认为,《庄子》首篇即以“游”为名,“审此游字,义殊鸿洞”,他甚至提出:《庄子》全书“一切议论譬喻,似皆本此字发挥之”,因此“庄子辞虽参差,而此游字,实可以应无穷之义而归于大通之旨也”。
庄子的“游”,可从基本形态、内在本质、实现途径、最终境界四个层面来分析。这四个层面密切关联、层层呼应。
其一,从基本形态而言,庄子论“游”,特指精神的遨游。这是“游”摆脱常见引申义、上升为理论范畴的关键一步。
“游”有游历、交游、游学、游玩等引申义,这些含义虽也涉及精神层面的活动,但主要指形体的游移。庄子论“游”,则特指一种超越有限形体、进入无限想象世界的内心遨游。因此,庄子常用“游心”一词,如《人间世》的“乘物以游心”,《德充符》的“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提到无名人“游心于淡”等。申徒嘉批评子产“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德充符》),所谓“游于形骸之内”也是“游心”之意。正如刘笑敢所言,庄子描述的所游之处,“是思想虚构的幻化之境,是一种神秘的自由的精神体验”,而“所谓游的主体是心而不是身,这是庄子之游与一般所谓游的根本区别。”
其二,从内在本质而言,庄子论“游”不仅指精神的遨游,更指向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这种超越一切现实
虽然《逍遥游》正文出现“游”仅两次,但此篇最集中地体现了“游”的自由精神。《逍遥游》以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开篇,不过,鲲鹏仍然是体现一种相对自由,如“定乎内外之分”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子一样,都有所待,即需要依赖特定的条件,而逍遥游的最高境界,则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才是真正的无所依待的绝对自由。
《逍遥游》的“游无穷”、《在宥》的“游无极之野”,强调对空间限制的超越。《山木》的“浮游乎万物之祖”、《达生》的“游乎万物之所终始” ,强调对时间限制的超越。《齐物论》的“游乎尘垢之外”,则强调对现实世界一切限制的超越。最终,庄子用“无何有”来象征这种绝对自由的境界,如《应帝王》说无名人“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提到明王“游于无有”,还有《山木》的“游于无人之野”。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不仅是“游”的内在本质,也是庄子思想的根本归宿。刘笑敢总结道:庄子“以精神自由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庄子哲学的归宿是逍遥论。”
其三,从实现途径而言,“游”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需要经历否定式的体道工夫才能得以实现。
要进入“游”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就要否定或超越一切现实功利、是非得失的拘限,最后还要超越生死的顾虑。《齐物论》描述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游乎尘垢之外”,描述至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就点出了“利害”“死生”等拘限。在《山木》中,市南子劝鲁侯“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刳形”即忘身、“去皮”即忘国。这种超越,需要循序渐进的否定式体道工夫。《大宗师》描述颜回首先忘仁义,再忘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如刘绍瑾所说:“‘忘’是‘游’的必要条件”,并且“《庄子》‘忘’的秩序在各篇中都显出惊人的一致:从外到内,由有形到无形”。
其四,从最终境界而言,“游”不仅指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更意味着与天地精神相通为一。
庄子之“游”,不仅指“游心”或回归内在精神自由,更指依循和融入天地自然的大道。《天下》曾归纳庄子之学是“上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陈引驰也指出,庄子“逍遥游”的自由,“不是通常理解中的所谓无所拘束的绝对自由”,而是一种以“天地宇宙之大道”为“最终归趣”的自由。
何谓“与造物者游”?《大宗师》曾借孔子之口,区分“游方之内”和“游方之外”,其中“游方之外”就是“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所谓“与造物者为人”,就是与造物者为友,即“与造物者游”。郭庆藩引司马彪注曰:“造物者为道。”“道”就是“自然”,《应帝王》说无名人“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就把“游心”等同于“顺物自然”。那么,“游乎天地之一气”“合气于漠”又指什么呢?《知北游》论证“万物一也”时,曾解释道:“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所谓“气”,就是万物相通的基础,即万物的原初形态、生命根源。这也是《在宥》所说的“万物云云,各复其根”。“游乎天地之一气”,就是游于宇宙万物的本真原初状态,这样才能超越一切外在限定、融入天地自然大道。
因此,“游”的绝对自由,其实是一种与天地宇宙精神相通的境界。“游心”只是基本形态,而“游于气”才是终极境界。《大宗师》“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山木》“浮游乎万物之祖”,《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初”,皆为此意。正如徐复观所说,《逍遥游》的“至人无己”最重要,“无己”就是“让自己的精神,从形骸中突破出来,而上升到自己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
庄子之“游”既是一种与天地合一的最高境界,于是“游”成为体道的代名词。《田子方》借老聃之口说:“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知北游》借颜渊之口问仲尼“回敢问其游”,还有《德充符》说“圣人有所游”,都是用“游”来象征最高的体道境界。《淮南子》等著作,袭用了这种表述方式,如《修务训》“此圣人之所以游心”,《俶真训》“此圣人之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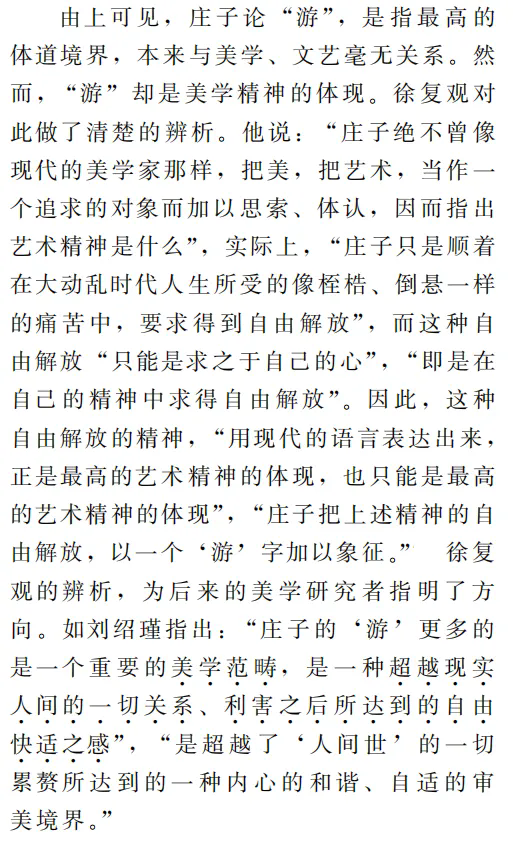
孔子也曾论“游”,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游于艺”主要是广泛涉猎之义。《论语·先进》又载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赞许道:“吾与点也。”这里没有“游”字,却暗合“游”的精神。可以说,儒家的最高道德境界,也与天地精神相通,如《孟子·尽心上》“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虽然工夫实践途径不同,但是,儒家的“风乎舞雩”“天地同流”与庄子的“游”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
二
“神游”美学: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然而,“法天贵真”“虚静”等范畴,也能体现这种审美精神。那么,“游”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它的审美特质是什么?又如何在艺术中具象化?我们可以说,那些超越世俗、追求理想的作品,都体现了“游”的自由精神;陆机《文赋》“心游万仞”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神与物游”,都是“游”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但是,只谈超功利的审美精神、超时空的艺术想象,可能会简化“游”在形式上的特质,及其在艺术领域中“道成肉身”的复杂过程。我们要追问:“游”这种艺术精神和天地境界,如何落实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
庄子之“游”,是无待的绝对自由,本不需寄托于任何具体形式,可以“游无何有之乡”(《应帝王》)。但是,庄子特别善于用具象化的语言,尤其是借用神话传说,表现那些自由遨游的神奇状态,如藐姑射神人“不食五谷”“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至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大宗师》)。
“游”的审美精神,首先寄托于“神游”文学。“神游”在广义上指精神遨游于超时空的神秘境界,在狭义上特指游于天界、交接于神仙。广义的“神游”,就是庄子的“游心”;狭义的“神游”,又与庄子的神人寓言相似。
《楚辞》开启了“神游”书写模式。洪兴祖说:“《骚经》《九章》皆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屈原“托游”描写自己超越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离骚》最精彩之处,就是上下求索的天界远游,包括苍梧问舜、周流求女、昆仑凭吊。萧兵指出,“神游”是“《离骚》形象结构的中心层”,甚至是“屈赋里相当强大的‘动机’或‘母题’(motif)。”《离骚》中三次远游,都采用了朝发夕至的结构形式,这成为汉代神游赋的基本模式。不过,屈原与庄子不同,他无法摆脱追求自由解脱与心系故国美政的矛盾,因此《离骚》最终从天界回到人间。相比之下,庄子之“游”是要忘身、忘国,通过否定式的体道工夫,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刘熙载曾比较,屈原是“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而庄子是“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
不过,“神游”文学虽与庄子思想有相异之处,但二者有相同的旨趣:都是通过在天地之间飞升远游来寄托自由超越的理想。“神游”不仅呼应了庄子的超越世俗与高蹈自由,更突出了庄子之“游”隐约可辨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朱良志曾辨析说:屈赋的远游与《庄子》一样,都追求“性灵的解放”,但是屈赋的逍遥“不像《庄子》那样超迈,带有‘孤沉而独往’的意味”。如果说儒家是不脱人伦日用的超越,道家是逍遥无待的超越,就像方东美所说的“太空人”式的超越,那么“楚辞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超越道路”,是一种“悬在半空”式的超越,即“挣脱现实,又不离现实”,就像“九天求女,上而不可,下也不能,在飞旋和现实之间流连”。因此,这是一种“带血的超越”。
其实,庄子之“游”,虽不是“带血的超越”,而是逍遥无待的绝对自由,但其逍遥的身影之下,却有隐隐的在现实中挣扎的血痕。《人间世》孔子与颜回讨论“心斋”之后,指出:“绝迹易,无行地难。”下一节又借孔子之口指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此外,《山木》“虚己以游世”,《外物》“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都将“游”的背景从缥缈无何有之地重新拉回人间。
因此,庄子乘气御龙游乎四海之外,屈原上天入地追求理想世界,都是源自现实的迫厄局促。杂糅了游仙之愿与老庄思想的《远游》,开篇道:“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很多人都将《远游》的游仙情节,视为突破时俗迫厄的假设之词。明人汪瑗认为:“此章‘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其诸访求神仙、经营四方之说,亦不过推衍轻举远游之意耳”,只是“特假设之词聊舒其愤懑耳”。
这种突破现实迫厄、寻找自由理想的决绝,贯通了庄子之“游”与屈赋的“神游”,并在阮籍、嵇康的作品中进一步融合。身处乱世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的大人先生,与世俗对抗,“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大人先生自述道:“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这就是庄子之“游”的回响,也是屈赋“神游”的延续。钱锺书指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欲兼屈之《远游》与庄之《逍遥》”。
阮籍、嵇康用游仙的假设之词,寄托了更深的感慨。他们采用了一些源自庄子但更加成熟的象征手法,如飞鸟意象。兴膳宏指出嵇诗与庄子的关系:“嵇康诗中的飞鸟都不是实景的写生,而完全是幻想的产物”,“都暗示了遨游仙界的超然者的姿态”,并且“这些飞鸟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赋予庄子大鹏的飞翔的性格,象征着嵇康精神世界中的至上境地”。阮、嵇作品中的飞鸟,确实有《庄子·逍遥游》大鹏鸟的性格。但是,阮、嵇在神游理想的描写中,凸显了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比如阮籍《咏怀诗》其四十三“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之后,突然写道:“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这正是庄子之“游”中未完全说透、却隐约可辨的意蕴。
三
“游观”美学:身体与精神的统一
“游”的基本形态是游心或神游,即突破有限的形体束缚、进入自由的精神状态。那么,有限空间或者山水中的游历,是否也能成为“游”美学的寄托形式?换言之,现实世界的游目或身游,如何与理想世界的游心或神游统一?
庄子反复渲染超越时空的精神自由,要摆脱身体的限制,如庄周梦蝶式的梦游,但他同时又特别善于用各种与身体相关的寓言来表述这种理想,比如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吕梁丈夫的悬水之游。庄子论“自然”,并非指自然界,他甚至认为山水游乐并不能带来超越的体悟,反而会陷入有待的凝滞,《知北游》借孔子之口讽刺世人:“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但是,与天地精神合一却预设了与自然山水亲近的态度。庄子在濠上知游鱼之乐(《秋水》),正暗示了精神自由的体验可来自有形之物的近距离观赏。
与魏晋思想有深刻关联的《列子》,用“游观”解决了“游”的形式问题。于是,身游和神游、游目与游心可以相冥,身体与精神达到了统一。因此,“游”的审美精神,又寄托于这种“游观”哲学,并由此得到深化。
《列子·仲尼篇》说“列子好游”,即好游历游览,壶丘子问他:“游何所好?”列子回答:“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壶丘子指出,列子其实与常人并无不同:“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他接着区分道:“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听了壶丘子的批评后,“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壶丘子又指出:“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视。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是我之所谓观也。”
游观相冥,不仅意味着“外游”与“内观”的辩证统一,也意味着现实世界的身体游历与理想世界的精神游历的辩证统一。魏晋六朝作品中好用“俯仰”表示游目之极境,从另一角度推进了身体之游与精神之游的辩证统一。嵇康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前二句写实际所观,后二句通过“俯仰”进入精神之游。兰亭之游本为现实的游乐,王羲之《兰亭集序》用“俯仰”将其升华至与天地为一的境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于是,重精神自由的庄子之“游”,不必限于“无何有之乡”,而可托付于眼前的山水园林。“游观”美学,即是“不必在远”的美学。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濠上可体验鱼之乐,园林亦可体验天地之乐。田晓菲认为,东晋时期“山水写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向而不是外向的运动”,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对山水的兴趣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外在的自然景观,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人们对内心世界发生新的重视”。因此,“以心眼观看到的山水,反而比肉眼观看到的山水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其实,这正是“游”的审美精神的深化,打破了内外界限,身游与神游冥合为一。
想象之神游可以托付于实地之游览,同样,实地之游览也可以用想象之神游代替。孙绰《游天台山赋》就描写了在想象中游览天台山的过程。结尾一句,体现了庄子之“游”与天地为一的最高境界。“泯色空”“忽即有”则是“游观”美学的体现。于是,“游”成为一种身心合一、游观相冥、远近无碍、天地大同的境界。游心即是游目,游目也是游心,“目所观境,亦即是心所处境”,“既观天地之大,同时也就体察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人与天地的关系”,最终“俯仰宇宙之大观,使人的个体有限性和宇宙自然的整体无限性相互拥有、相互渗透”。
“游”的审美精神,由此落实于艺术各领域。描绘有形山水的绘画,可以是与天地为一的精神遨游。王微《叙画》形容作画的原则:“灵亡所见,故所讬不动,目有所极,固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个作画原则,突破有形的山水、掌握无形的天地精神,正如宗白华所揭示:“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所谓“太虚”或“太和”,都是指天地元气、万物根源。
布置微观山水的园林,也可以寄托与天地为一的精神遨游。明代计成《园冶》提出,兴造园林要巧于“因”和“借”,其中“因”是园林内部的“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借”则是借园林之外的远景、借天地之大景:“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畽,尽为烟景。”所谓“极目所至……尽为烟景”,正是在有形的空间布局,融入无限的天地精神。
描写特定行旅的游记,也可寄托与天地为一的精神遨游。明万历年间的王士性,一生寄情山水、遍游五岳,其记游作品结撰为《五岳游草》。在此书自序中,王士性区分了三种“游”:“夫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无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举形留,下焉者神为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采真。”接下来,王士性用《庄子·逍遥游》提出的凝神,以及承蜩丈人等寓言,描述自己的“游”,最后总结道:“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当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尽丧,吾亦不知何者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为采真。”如此,“游”既区分不同形式,而各种形式又能相冥无间,真是“物物皆游,物物皆观”了。
四
“游”与“游戏”:比较的视野
如前所述,“游”与西方美学提出的审美自由、主客合一等根本精神契合,那么,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看,可以用哪个西方美学概念揭示“游”的特质或形式呢?
根据以上看法,徐复观认为,《庄子》外篇《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一节,揭示了游戏的特性。徐复观从“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的描述中,读出了游戏的无目的性,并指出这也是艺术的精神。徐复观用西方的“游戏”说,解释庄子的“游”,影响深远。比如,有学者扩大比较的范围,用康德的“自由游戏”所揭示的无功利性的自由快感,席勒的“游戏冲动”所揭示的人的自由本质与完整人格,伽达默尔的“本真游戏”所揭示的全神贯注于游戏本身时主客合一的存在论意义,来说明庄子之“游”的美学意义。
我们承认,庄子描述“游”,确有优游甚至游戏之义,但是,庄子之“游”的基本意义,可能不是游戏,而是空间的游移和突破,这是“游”从本义不断衍生出新义的关键,庄子在这意义衍生之链上做了决定性的提升,将“游”从有形的游移升华为无形的游移。
这些译者似乎受到徐复观的启示,在“云将东游”一节中区分云将之游与鸿蒙之游,极力将后者译为游戏,证实“游”的“游戏”意蕴。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将鸿蒙说的“浮游”译为遨游。其实,从鸿蒙回答的“浮游,不知所求”可知,鸿蒙所说的“游”,侧重于遨游,而不是游戏。鸿蒙第一次回答“游”,成玄英疏曰:“乘自然变化遨游也。”鸿蒙第二次所说“游者鞅掌”, 成玄英疏曰:“鸿蒙游心之处宽大。”如果要区分云将之游与鸿蒙之游,只能说云将是有目的、有待之“游”,鸿蒙是无目的、无待之“游”。
在这些译者中,梅维恒最重视“游”,他指出,这个概念“可能是《庄子》中最重要、最精髓的概念,但由于它是以文学术语而不是以哲学术语呈现,故而常被忽视”。在梅维恒主编的庄子研究论文集中,就有一篇文章专门从“游戏”的角度研究“游”。这篇文章全面地运用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分为游戏的形式、游戏的体验、游戏的象征,即作为客体的游戏、作为主体的游戏、作为包罗一切的游戏等三方面,甚至认为“游戏”就是贯穿《庄子》内篇的主线。此文提出,庄子的“化”,意味着作为客体的游戏(play as object),即人生就是一场万物之“化”的游戏(a game of hua),那么应该以何种态度参与这场游戏呢?庄子的“游”,就是作为主体的游戏(play as subject),即“‘游’(wandering)帮我们培养游戏的体验和游戏态度(lusory attitude)的性情”。
康德的自由游戏说寻求感性与知性的平衡,席勒强调“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综合,即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伽达默尔则旨在克服主客二分。无论是游戏理论还是心流理论,都只能揭示庄子之“游”的部分意蕴。庄子之“游”,要求超越一切理性知识或感性经验,并以特殊形式落实在中国文学、绘画等艺术领域,这是游戏理论无法涵盖的。
结语
“游”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主要指追求自由、体悟大道的精神遨游,最终与天地宇宙为一。因此,“游心”是“游”的基本形态,“游于气”是“游”的最高境界。论者多引用“心游万仞”“神与物游”等论艺文字,或追求自由超越理想的作品,来说明“游”的影响,其实未能揭示“游”如何落实于文艺表现的具体形式。本文指出,“神游”与“游观”,是“游”融入具体艺术表现的主要途径,最终形成了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协调身体之游与精神之游的美学。
宗白华曾结合屈原与庄子来说明意境:“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事实上,“游”正是意境或境界等中国美学范畴滋生的深层土壤。“神游”融屈原之深情与庄子之自由为一,“游观”融有形与无形为一,这既是“游”的寄托形式,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寄托形式。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